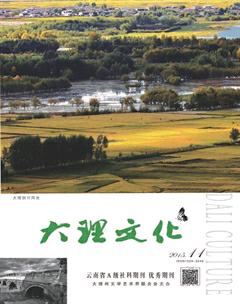記憶中的《洱海》
一
我在拙作《抹不掉的記憶》中,寫了大理市下關職工業余文學創作小組的活動,寫了幾位從那兒走出去的作家、詩人。習作發表之后,我仔細讀了一遍。讀完,內心感到有點不安。因為篇幅所限,很多人沒有寫到。
究竟先寫誰呢?那么多人,真是憨狗咬石獅子——不知從何下口?猛然間,我想起了下關文化站最初成立文學創作小組的初衷。
當時,下關文化站,成立職工業余文學創作小組,是為創辦一張文藝小報,招徠作者。一張報紙,有了作者,才不致成為無米之炊。否則,報紙稿源從何而來?缺乏稿件,報紙就難以為繼。
就是在這個創意之下,下關職工業余文學創作小組應運而生。我也有幸成了業余創作小組的一員。
記得,我們單位收到的邀請函是這樣寫的:
邀請函下關總站工會:
為繁榮下關地區職工業余文學創作,下關文化站決定創辦一張文藝小報,暫定名《風展紅旗》,為我市業余作者提供作品發表園地。要辦好《風展紅旗》,就必須有一支業余創作隊伍。有鑒于此,經研究,我們將組織下關地區職工業余文學創作小組,每周星期六下午,在下關文化站開展業余文學創作學習活動,特邀請你站業余作者韓如龍、彭懷仁兩同志參加。敬請支持為謝!
如蒙同意,請通知他們下周周六,按時參加學習為盼!
此致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下關市文化站
1973年x月x日
我和工農弟兄們,就是被這張邀請函,邀約到文學小組的。文學小組活動,在那家倫和施沛老師的主持、領導下,每周六,雷打不動,風雨無阻,一直開展活動。其間,那家倫老師四處奔走,求爺爺告奶奶,到處化緣,都沒有籌到辦小報的經費。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展紅旗》小報,卻始終未能風展紅旗。那家倫老師,只好發動大家,將文學小組集體討論修改過的稿子,投寄給報刊。幸好沒過多久,就有人在省內報刊發表習作。
但是,小組成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人的作品上公開刊物,就還差那么一點點。如果有一個自己的內部刊物,讓大伙演練演練,便可以從小池塘的淺水,游向大江河的深水。為此,文化站的老師們一直憂心忡忡。“哪一天能有自己的刊物就好了?”那家倫如是說。
二
說到《風展紅旗》,我想起了廣東作家何百源,他讀過我發表在2015年第二期《大理文化》上的《抹不掉的記憶》之后,給我寫來一封信。披露了他誤入其門的事。
何百源來信說,當時,下關市文化站組織職工業余文學小組,根本沒有通知他。他們單位通知了詩人舒宗范。市文化站第一次開展活動,恰好,舒宗范外出進行森林資源勘察去了。單位領導老王找到他,讓他拿了寫著舒宗范名字的邀請函,去文化站聽聽精神。于是,他便去了。去到文化站,一聽各人自報家門,他才發覺,參會者大多數人都發表過作品,少數是愛好文學多年,并且寫過不少文章。而他,一個西南林學院畢業的林業勘察工作者,涉獵文學不多,根本沒有他說話的份。那天,他一言不發,只讓耳朵做客。臨走時,那家倫問他:你想不想參加學習,我看你簽名時,字寫得很好,將來文化站辦《風展紅旗》,你可以幫忙抄抄、寫寫。他回答說,我當然愿意參加。之后,他便成了業余文學小組的成員。
看了他的信,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為,早年那個業余文學小組,是我們走上文學創作小路的跳板,沒有那幾年的彈跳,我們都是散兵游勇,修不成正果。我根本想不到,何百源去學習業余創作,完全是一種偶然。假設,第一次學習時,舒宗范沒出差,就不會輪到他;或者,單位領導另叫一人頂替,那么,他興許也不會愛上文學。一次偶然的機會,成就了一位出版了10本書的中國作協會員,讓人難以想象!要不是42年后,他說出了那一次偶然,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委。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一個林業學院畢業生,在森林勘察單位工作,結合專業,學以致用。那是沒得說的了。他報考林學院,就是想當一個林業工程師。有趣的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改變了他的命運!上世紀的1985年,他在大理的林業單位工作20年后,調回老家廣東南海,先是在政府機關工作,后來,因他在當地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被調到《佛山文藝》當編輯,不久,升任副主編;之后,又調到市文聯工作。他為當地培養了300多個業余作者,其中不乏小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可謂桃李成蔭。退休之后,他筆耕不輟,經常為當地報刊寫專欄稿;不時還到文學創作培訓班講課,扶持新人。他年過七旬,精神健旺,妙語連珠,一點也不顯老!我想,這大抵是文學滋養了他吧?
想到這兒,我給他回了一封電子郵件,我對他說:我一直以為,你早就喜歡文學,想不到,你跨進文學之門,純屬偶然。我們第一次活動,參加的都是文學愛好者,沒想到你是被人拉壯丁,更沒想到,這一拉,改變了你的人生之路。真不知你是該感謝出差的詩人舒宗范,還是感謝臨時拉你當壯丁的那位領導。
他回復說,我是被錯拉的壯丁,搞文學純屬偶然!
三
2013年冬天,白族作家李友文打電話告訴我,下關回族作家楊水清的妻兒,自己掏錢,為老水出了一本書。我們那一輩的人,都親切地稱楊水清老師為“老水”。老李還說,過幾天,我把書拿來給你看看。
三天過后,老李給我送來楊水清的書。水清是下關文學小組最平易近人的一位資深作家。他的家人,在他過世10年之后,為他整理出版專著,精神司嘉。
據說,這本由楊水清家人結集出版的《水韻清香》,是作者在世時,就剪貼好,準備編輯成冊的。因水清是一個厚道人,一直未能為自己出書。本來,他作為大理市文聯主席,多少有點權,找主管領導要點錢,完全可以為自己出本書。但他不以權謀私。心里想著的是業余作者,不替自己打算。所以,他在世時,出書的愿望未能實現,成了平生憾事。好在他的妻兒,最后幫他圓了出書夢。
我在翻閱水清的《水韻清香》時發現,書中所選的69篇文章,有好幾篇,選自《洱海》小報,瀏覽著文章,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下關文化站創辦文藝小報《洱海》的前前后后。
《洱海》就是由最先創意的《風展紅旗》演變來的。經過下關文化站的多方努力,辦文藝小報的經費終于有了著落。這一回可以風展紅旗了,可是,風展紅旗的名字,太革命化了。下關就在清粼粼的洱海邊,洱海是白族兒女的母親湖,白族作家那家倫說,我們都是喝洱海水長大的,就定名“洱海”吧7
1979年1月30日,第一期《洱海》小報呱呱墜地。當然,之前,那家倫、施沛老師,以及下關職工業余文學小組的哥們,也為它費了不少心力。
1978年秋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綠了大理的蒼山、洱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給白族地區帶來了文藝的春天。白族作家那家倫在《洱海》第一期上寫的《春風賦》說:“春風,美好的春風,使祖國變得年輕,使大地充滿陽光,使人間充溢希望,使時代滿是生機。”“我們被壓抑的智慧、力量和創造精神,已經不可遏止地迸發出來,進發在新長征路上”,正是這一陣春風,吹亮了《洱海》。
第一期《洱海》,都是下關文學小組成員,給下關文化站交的作業,有那家倫的《春風賦》,楊水清的《蜜》、張焰鐸的《花》、舒宗范的《懷念烏蒙金沙間》、謝本良的《翠柏·雨花石》、還有著名畫家謝長幸的篆刻、著名畫家董浩川的國畫,著名攝影家釧培基的攝影。可謂圖文并茂,熠熠生輝。
《洱海》的誕生,是下關市業余作者的福音,下關市的業余作者,從此有了自己的家園,有了一展技藝的平臺,拿著第一期《洱海》,我們奔走相告!
四
《洱海》第一期問世之后,猶如一塊巨石投入洱海湖面,激起層層漣漪。不少文學愛好者紛紛給編輯室寫來熱情洋溢的來信。
讀者劉波說,生活中,值得歌頌的事情很多。于是,我下決心學習文藝創作,想用自己笨拙的筆,描繪新時期欣欣向榮的喜人局面。《洱海》這樣的刊物,為我們初學寫作者,提供了學習創作、交流經驗的園地,很受大家歡迎。
劉波,就是當年下關文學小組劉傅森老師的兒子,他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喜愛文學,爾后,寫過不少文學作品,他的處女作,就發表在《洱海》上。
之后,下關地區的文學愛好者,紛紛給《洱海》投寄自己的習作,到《洱海》里游泳,一試身手。有的,很快就在《洱海》上發表處女作,而后,一發而不可收,成了終身與文學相伴的癡情人。后來成為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的作家趙守值,楊中興、楊騰霄、曹高德、趙闊,當年便是《洱海》的忠實作者和讀者,也是從《洱海》這個小游泳池,游向省內外的大江大河的健兒。
《洱海》初創時期,下關地區,可謂文學愛好者云集,不少后來成名的作家,都在《洱海》試過筆,都在《洱海》上空呼吸過《洱海》的氧氣。更有一些后來從政的官員,他們也曾經給《洱海》留下他們的生活手記。我在《洱海》第5期上,讀過一篇題為《彝山素描》的散文,作者是陳天祥,這是他下鄉歸來寫的短文。幾年之后,他成了大理市市委宣傳部部長,后來,又擔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在大理市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記得前年秋天,大理學院原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張錫祿教授,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填一張表格,表里有一欄,何時發表處女作。他思來想去,處女作應該是發表在《洱海》上,《洱海》上的作品,是他的開山之作。讓我幫他查查,發在哪一期?
我當即應允。當時我想,盡管,張錫祿后來有《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明代大理總管史》等民族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但是,他的處女作,發表在《洱海》上,是不爭的事實,《洱海》是他初練游泳之海。經查,他的處女作發表在《洱海》第12期上,題目是《白族民歌有自己特有的藝術形式》。如今,張錫祿已是發表多部研究白族歷史文化專著的知名學者了,但他的第一步,是從《洱海》邁出去的。這是決定他人生命運的第一步,也是他著書立說的起點。
五
1979年4月24日出版的第5期《洱海》,洱海二字,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仔細一看,報頭題字變了。再一看,報頭是中國文壇泰斗茅盾先生的墨寶。
《洱海》編輯室,寫了一篇題為《“把《洱海》愈辦愈好!——賀茅盾同志為本刊題寫刊名”》的文章,介紹了他們懷著對沈老十分崇敬的心情,懷著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責任心,懷著進一步辦好《洱海》的愿望,呈函,向沈老匯報了創辦《洱海》的目的及意義,寄上已出的《洱海》,敬請沈老審閱,懇請沈老為《洱海》大筆書題刊名。沈老在政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于1979年4月5日揮毫寫了兩份刊名,并勉勵編輯人員:“把《洱海》愈辦愈好!”
茅盾先生為一個邊疆小市的小報書寫刊名,不知當時是否空前絕后,但足見文壇泰斗對邊疆白族兒女的眷眷愛心。
之后,《洱海》編輯部召集業余作者座談,大伙,感慨萬千!茅盾先生的題字,極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創作熱情,不少人紛紛表示,一定要刻苦讀書,勤奮寫作,以此報答茅盾先生的關愛之情。有人還即席朗誦詩歌,抒發激情。
那天,那家倫老師,非常激動,因為,請茅盾先生題寫刊名,都經由他一手運作。能夠如愿以償,他當然比誰都激動。有人說,那老師,這刊名,是靠你這個著名白族作家的名氣,要來的。他說,不是靠我的名氣,而是靠蒼山、洱海,靠白族人民的名聲要來的。我們要珍惜茅盾先生的題字,要加倍努力,創作出無愧于茅盾先生“把《洱海》愈辦愈好!”的作品來!
與會者群情激動,紛紛表示,一定要進一步深人生活,寫出無愧于時代的作品來,以此回報茅盾先生對《洱海》的厚愛!
六
1979年5月,我國自衛還擊戰取得重大勝利,中國軍人將凱旋而歸。為了歌頌中國軍隊在前線取得的勝利。《洱海》第6期推出《熱烈歡呼自衛還擊戰重大勝利特刊》。
特刊刊登了解放軍前線歌舞團、上世紀70年代當紅詩人任紅舉的詩歌《東線西線祝捷歌》、《英雄們歸來了》,刊登了白族作家那家倫的散文《戰火燃燒的詩花》,刊登了白族作家彭懷仁的小說《無畏的戰士》,刊登了白族作家楊恒燦的散文《意外的收獲》,刊登了著名畫家楊曉東的版畫《歡迎您,最可愛的人》。小報圖文并茂,套紅印刷。
這期特刊,是《洱海》編輯室為了配合宣傳自衛還擊戰的重大勝利,而約請作者寫的專稿。從組稿到編稿,前后三天時間,真是逼著牯子下兒。《洱海》編輯室的編輯給作者下死命令,一定要按時交稿。無論如何都得寫出歌頌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來。應邀寫稿的作者們,接到任務后,重任在肩。大都認為:歌頌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中國軍人,是文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寫不寫,是態度問題;寫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于是,咬咬牙,挑燈夜戰,硬著頭皮,咬斷筆桿,終于寫出了各自的文學作品,交到編輯室,完成了這個硬任務。
報紙很快就編好,然后,交印刷廠排字、印刷。印刷廠工人,加班加點印出小報。離大理駐軍參加自衛還擊戰凱旋歸來的日子還有幾天。
歡迎參加自衛還擊戰部隊凱旋歸來那天,下關市民在市委、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下,排列在下關的主要街道上,夾道歡迎從前線歸來、勞苦功高的解放軍英雄,軍車、炮車,雄赳赳駛來,小學生紛紛上前,給解放軍叔叔獻花,工人老大哥緊緊握著子弟兵的手,“向解放軍英雄們學習、致敬!”“親人啊!你們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口號聲、歡呼聲,此起彼伏,到處是感人至深的軍民魚水情場面。
第6期《洱海》,成了下關地區業余文學創作者送給凱旋歸來的解放指戰員的一份小禮。
七
《洱海》雖然是一張縣級文藝小報,它是下關市文學創作者的園地,是初學寫作者的練兵場。但它也博采眾長、廣納百家。
下關的作者們,為有了一塊自己的寫作陣地而高興萬分。他們紛紛把自己的習作投寄給《洱海》,想到那兒尋一小塊棲身之所。有基礎的人,如作家張焰鐸、舒宗范、謝本良、楊水清,很快就在《洱海》亮相。稍后一點亮相的有何百源、吳崇仁、鄧英鸚、曹高德。還有一些剛學步的新作者,他們一次、一次地給洱海投稿,《洱海》編輯室的老師們,看了他們的稿子后,把他們請到文化站,讓他們參加文學小組活動,一起學習,幫助他們提高寫作技能。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反復修改作品,不少新作者的文章,也陸續在《洱海》露面。既擴大了《洱海》的作者隊伍,又使新作者看見了黎明的曙光,也成為他們跨上文學舢板的跳板。而今,不少作者,依然在文學的崎嶇小路上行走,矢志不移。
不少省內知名作家都在《洱海》上發表過作品,我州著名軍旅作家樊斌,在《洱海》連載過中篇小說《鮮花湮沒的罪人》,我州安徽籍作家楊美清發表過散文《懷念張明德和尚景波》、《洱海,燦爛的明珠》,著名詩人周良沛發表過詩歌《金橋玉路》,白族作家楊伊達發表過短篇小說《歸來》,納西族作家戈阿干發表過短篇小說《天神巖》,回族作家馬瑞麟發表過散文《歌聲的懷念》,著名白族作家、云南人民出版社《山茶》主編趙櫓的散文《玉白菜》,也發表在《洱海》上,更為可喜的是:發表于《洱海》的《玉白菜》,被收入2014年由中國作家協會編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白族卷)》,讓《洱海》小報傳揚四海,名傳千古!
此外,我省作家劉允裎、王雨谷、駱虢、凝溪也都先后在《洱海》發表過作品。《洱海》還發表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趙衍蓀的《淺談白族語言及其他》,湖南作家魯之洛游大理時寫下的散文《洱海戀》,也在《洱海》問世。
值得一提的是:《洱海》還連載過原中央民族學院吳重陽、陶立瑜撰寫的《云南少數民族現代作家傳略》,系統地介紹了白族作家曉雪、楊蘇、張長、楊明、那家倫等。
八
在《洱海》發表處女作,又從《洱海》揚帆,駛向內地江河的作者,不計其數。翻開《洱海》,我看見一張張熟悉的笑臉。
1979年春天,白族作家楊騰霄,看到新創刊的《洱海》后,立即產生了創作沖動。于是,他創作了一篇寓言,投寄給《洱海》。寓言在《洱海》見報后,他便踏上了文學創作的崎嶇小路。在白族作家那家倫的指導下,他慢慢從《洱海》游向省內外報刊,發表了不少小說、散文,出版了小說集《云在洱海上空》,成為我州活躍的白族作家之一。至今,他說起《洱海》小報來,口若懸河,感慨涕零。他說,沒有《洱海》,就沒有他的今天!
那個曾經在大理學院中文系任教的大理女作家鄧英鸚,從下關職工業余文學創作小組,到《洱海》創刊,以致《洱海》成長的年月,她都與《洱海》相伴相守。她在《洱海》上發過小說、散文,是一位年紀輕、也有才氣的女作者。她十分善于學習,虛心向別人求教。作品寫了改,改了再寫,不厭其煩。寫字一絲不茍,像是寫書法作品那樣認真。
在學習寫作的同時,她不忘復習功課,準備應考升學,功夫不負有心人,恢復高考后,鄧英鸚成了第一批考進下關師專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那時,原在大理師范任教的謝本良老師,已調到下關師專擔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寫作課教師。在下關文學小組時,謝老師就與鄧英鸚熟識。于是,鄧英鸚成了謝老師的高足。理所當然地成為謝老師倡導、扶持的學生文學小組“洱海文學社”的頭兒,也是學生中發表過文學作品的佼佼者。她熱心組織文學社的同學創作,并仿效下關文學小組討論作品的做法,組織學生討論自己的作品,活躍了文學社的創作活動。經過四年苦讀,鄧英鸚學習成績優良,文學創作小有成就,畢業時,留校任教,擔任寫作課教師。她一邊為大理地區培養師資,嘔心瀝血:一邊堅持業余創作。同時,她還繼承謝老師扶持學生開展文學創作的好傳統,幫助學生修改文章,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使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讀書階段就能在報刊發表作品。這些學生畢業后,成為大理地區文學創作隊伍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盡管后來,鄧英鸚調離大理,到昆明鋼鐵公司黨委宣傳部,從事宣傳工作,但她一直堅持業余文學創作,并以豐厚的創作業績,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協會。向下關文學小組和《洱海》小報,遞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九
2014年7月,《洱海》小報的忠實作者、工人詩人曹高德,帶著一疊詩稿,來我家找我。讓我幫他挑選一些詩歌,投寄給《大理文化》。因為,他一直用紙、筆寫作,沒有用電腦,不知道怎樣發電子郵件,特來找我咨詢。
老曹與我都是在工廠干過苦力的主兒,后來,我在《大理市報》當副刊編輯,他是我們報紙的鐵桿作者,我倆相交甚好,經常在一起切磋文字。他的詩,樸實無華,而又韻味十足。語言粗獷、豪邁,擲地有聲。說實話,我一向喜歡他的詩歌。在我當小報編輯時,他的詩,我編得較多。
我接過他的詩稿,說,你拿著紙稿,到電腦室,請人打好后,買個U盤,然后,拷在U盤上,再帶著U盤,去雜志社,請詩歌編輯拷在他的電腦上,就行了。
老曹看著我,笑了笑,說:“阿彭耶,真不好意思,跟不上趟了。又不甘心,還想寫,更想發表出來。”
望著他滿頭卷曲、雪白的頭發,我頓生愛意。寫到這份上,真不容易!70歲的人了,還能寫出激情滿懷的詩篇,不簡單!于是,我翻閱了他的詩稿,選了兩組詩稿,又吹捧了他幾句,可謂互相吹捧,共同提高。
他笑瞇瞇地與我告別,然后,去電腦室請人打稿子。
第二天,他打電話告訴我,他昨天打好稿子,拷在U盤上,當即就拿著U盤,去《大理文化》編輯部,把U盤交給詩歌編輯、彝族作家李智紅,李智紅立馬把他的詩拷到電腦上。不知能不能用出來。電腦確實方便,看來,換筆的人真省事!
放下電話,我翻出了當年的《洱海》小報,老曹在《洱海》上發表的詩歌較多,他是眾多作者中,在《洱海》游來游去的一個,后來,他游出《洱海》,游進詩歌的海洋,發表了數百首詩歌,先后出版了詩集:《白山茶》、《二重奏》、《崇山凈水厚人情》,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我和白族詩人楊黎明介紹他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協會。
2014年12月初,我在第12期《大理文化》上,看到老曹題為《風光》的組詩發表了,一共有12首,高興之余,我立即撥通他的電話,把這喜訊告訴他。我還沒有說完,就聽到他會心的笑聲。這是70歲詩人曹高德心花的綻放!
十
說到《洱海》的前前后后,我的眼前,便浮現出87歲高齡的壯族作家劉傅森老師的燦爛笑臉。劉傅森老師從參加下關文學小組活動至今,42年,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文學翅膀的煽動。
劉傅森老師是云南解放之后不久,被派到大理工作的。他長期在文化部門從事文化工作,為繁榮大理地區的白族文化,做出了應有貢獻。同時,他還創作、發表了大量反映白族人們建設祖國邊疆的文學作品。
1973年夏天,他來參加文學小組學習時,已在省級報刊上發表過不少作品。但是,他非常謙虛,不以能人姿態出現,不以長者自居。依然一副學生模樣,認認真真學習。那時,他正值中年,精力旺盛,一直堅持讀書、寫作,他博覽群書,他讀過的書,說出書名來,我連聽都沒有聽過。他雖發表過不少文章,但他從不張揚。有人讀了他的文章后,對他說,劉老師,你的文章很老辣。他淡淡一笑,說,一般一般,我也是才學寫不久。有人發表了文章后,常常在小組里夸夸其談,他仍舊耐心地聽別人講完。其實,在小組里,他屬于文學前輩,寫作經歷長,發表作品也多,他完全可以大講特講,但他,除了在討論作品時給別人出個點子外,從不標榜自己。
劉老師對于一些初學寫作的人,滿腔熱情地幫扶,只要你有一小點進步,他都及時給以鼓勵,巴望初學者早日上路。我就是在他的指導下,逐漸學步,最終走上文學之路的。經過練筆3年之后,我在《云南文藝》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這篇小說的發表,增強了我繼續在文學小路上前行的信心。
42年來,劉傅森老師一直辛勤筆耕,常常有文章見諸報刊。26年前,他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之后,也沒有放下手中的筆。當年的學友,花甲之后,是他第一個吃螃蟹、率先換筆,用電腦寫作。
這些年來,劉傅森老師寫了不少大理舊貌換新顏的文章,從他的文章里,聽得見白族人民合著時代節拍前進的槖槖足音。他是1956年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眾多見證人之一,他參加了自治州的籌建,對成立白族自治州的往事,如數家珍。他從事多年的文化工作,多次接待過文化名人、專家,我曾經讀過他發表在1999年第9期《民族文學》上的《詩人的足跡一——懷念田間》的美文,他在文章中,詳盡地講述了詩人田間到大理的始末。我還在2011年第12期《大理文化》上讀到他發表的《歲月如歌——記憶中的徐嘉瑞老人》,得知省文化部門老領導徐嘉瑞,對全省文化工作嘔心瀝血的往事。他還是一位潛心研究白族歷史文化的學者。他在2007年第一期《大理文化》發表的《關于白族扎染的文化思考》,在全國引起普遍關注,不少網站爭相轉載。他還在2014年第7期《大理文化》上,以《大理天歌之憶》為題,追溯了1955年春夏之交,他第一次采訪白族民間老藝人楊漢的往事,彰顯了楊漢先生畢生為傳承白族民歌,耗盡心血的奉獻精神,唱出了一曲清新的天歌。
更讓人欣喜的是:2009年9月17日,筆耕60年、81歲高齡的劉傅森老師,被省作協批準加入云南省作家協會。2013年,我又聞聽到劉傅森老師兩本散文集《彩云之南》、《洱海月色》相繼出版的消息。
近幾年來,劉老師年年有作品發表在《大理文化》上,《夢斷雞足山》、《滇緬公路的記憶》、《再走滇緬公路》、《步行到大理》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篇章。
“打虎還靠親兄弟,上陣全憑父子兵”,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劉老師還影響、培養了兒子、影視劇作家劉蘋,劉蘋寫過電影《血魂》、寫過電視劇《阿惠》,《艾倫在大理》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在全國播出后,引起極大反響,為大理地區揚了名,爭了光。
劉家父子二人,不愧是閃爍在大理文學天空里的兩顆星星。
十一
在創辦《洱海》小報的過程中,編輯室的老師們十分熱愛自己的事業,十分珍惜這張來之不易的《洱海》小報。為小報傾注了不少心血。他們認認真真閱讀來稿,仔仔細細挑選好稿,字斟句酌地編輯文稿。他們還開門辦刊,請作者到文化站,不厭其煩地與作者交流,給作者出主意,幫助作者改好稿子。凡是能用的稿件,他們都爭取編上。畢竟是自己的小報,應該讓自己人一展身手。稿子排好版后,他們帶著稿件和劃版紙,走路到位于下關劉家營的下關市印刷廠,交到排字車間。那時,還是鉛印。排字工人,要一個字、一個字地揀。一行、一行地排字,排完版后,他們又到印刷廠排字車間校對。校對完了,經他們簽字后,才送印刷車間印刷。校對之后,他們又走路回單位。
之后,接到印刷廠印完報紙的電話,他們又走路去取回報紙,然后,分發到市屬各單位。盡管,工作十分瑣碎,但他們總是默默無聞地做著重復、枯燥的工作,為他人做嫁衣裳。上一期出版后,又忙著下一期的編輯工作。
讓他們感到欣慰的是,《洱海》的作者們,經過《洱海》的演練之后,一天天熟悉水性,愈來愈游得遠。大多在省內外辦刊發表了一定數量的散文、小說、詩歌。除那家倫外,小有成就的張焰鐸、袁冬葦、趙守值、楊騰霄、彭懷仁,都有作品入選多年后出版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白族卷)》。《洱海》編輯室的老師們當年的心血,沒有白花!
《洱海》初創時期的熱心作者們,大都沒有辜負《洱海》編輯老師的期望,也沒有辜負中國文壇泰斗茅盾先生:“把《洱海》愈辦愈好!”的囑托。他們,一天天長大,一步步登高,至今還在不斷呼吸文學的氧氣,至今還在與文學苦苦相伴,恩愛有加。
細細想來,《洱海》是下關業余作者的家,是作者游泳的海,《洱海》編輯室狹窄的辦公室里,常常人來人往,談笑自如;不像當今一些編輯部那樣,壁壘森嚴,讓人望而卻步,《洱海》,確實為大理地區培養了不少作者,而最初的那些忠實作者,走上合適的崗位后,又帶出了一批批新作者,使《洱海》精神四處開花。
正是:《洱海》真如海,活水滾滾來。編輯手記:
《洱海》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下關文化站創辦的一張小報,但它是下關文學創作者的大園地,是初學寫作者的“練兵場”。通過彭懷仁先生娓娓道來的敘述,讓我們看到了當年一座小城里諸多文學愛好者難能可貴的精神追求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