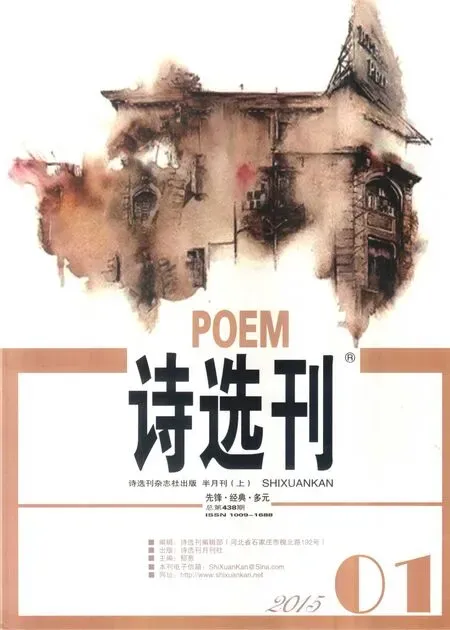我看見轉世的桃花
霍俊明
先生您走了!
我已經在火焰中看見了轉世的桃花。 您曾經在多年前的詩歌里完成了它,“我目光焚燒,震動,像榴霰彈那么矜持——— /在最后的時刻爆炸!裸體的桃花第二次升起,/掛在樹梢。和我年輕的血液融為一體。/但這一切真正的快樂,是我去天國途中的事。”2014年萬圣節,您通過一次真正的飛翔完成了它。我相信,您最終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升階書。 這就是詩人的命運! 先生,一語成讖。
2014年10月30日。 這一天的黃昏我終于編完了年度詩歌評論選的書稿。 在將年選目錄抄寫下來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精力將它們輸入電腦。這個晚上,在北三環附近的一個酒館我和友人吃飯。他們到得很遲。 甫一進來,剛剛倒得滿滿一大玻璃杯子的白酒猝然摔落地上。 實際上,我們都覺得這也不奇怪,但是滿地的酒味讓我們多少有些不安。 夜深了,大家散去。 我卻不知何故久久徘徊在北京的大街上。 實際上很多年來我醉酒后都是在深夜的大街上獨自游蕩。越是到了秋天,我越是被一種悲涼而又明亮的氛圍所籠罩,而懷念則成了我夜晚遙想的最好方式。 幾乎每次夜深靜寂的時候我都會撥通您的電話。 無知的我不會想到我是如此莽撞和無禮,而且一次又一次。 每次您都勸慰我,“俊明,少喝點酒啊! ”每次深夜打電話的時候我都知道您正在燈下寫作。每一次我都感受到靈魂和詩歌的大雪正在降落下來,“我在寫詩。一切喧囂止息了,我得以坐下來面對自己。我發現自己心靈中殘酷陰沉的一面。有時,寫作就是坐下來審判自己。 ”詩人如是說。 詩凌空而降,給人以猝然一擊,狂暴地或溫柔地攫住了卑微或高潔的靈魂。 應該說是雪給了在塵世倦染中的靈魂以理想主義的些許安慰。而遵循內心的寫作肯定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它所承擔的重量是不能估量的。
秋風吹來,我走累了。頭有些暈疼,我靠在青年溝路道旁的一棵銀杏樹下。耳邊偶爾掠過車聲。我該回去了,掏出手機,此時已經是2014年10月31日了。凌晨兩點十六分。躺在床上仍然翻來覆去難以入睡。早上六點多鐘有李建周的未接電話。當時一閃而過的念頭是多年來李建周從來不會在這個時間給我打電話啊! 早上起來上班,公交車遲遲不來,我背著包步行去單位。 快到單位門口的時候又一個電話過來。 沒說話前我已經知道這個電話意味著什么了。 那一刻開始我只有眼淚、寒冷和痛徹。 一座雪山在瞬間崩塌,萬噸寒冷撲面席卷過來。 我想起先生的詩句:“誰疼痛地把你仰望,誰的淚水/像云陣中依稀的星光?”風車閃光的葉片將誰的靈魂刨得雪亮?辦公室坐下來,我發了一個微信,又很快刪掉。內容是:一生的眼淚都要在今天完成嗎?
在去石家莊的路上,那么多的陌生人。他們不知道一個人為什么無故地垂淚。他們不知道,這個人今天為什么急急趕路。告訴你們吧!我從此每天都會走在這條通往石家莊的路上。那里如今因為一個人的離去,已經矗立起一座詩歌精神的燈塔。 它的亮光能夠穿越21世紀霧霾滾滾的城市,能夠穿透我俗世中昏昏不已的內心。
從此以后,塵世再無先生! 可是,您的詩歌和評論必將存留下來。
從此以后,您仍將一次次出現在師大的校園里。
當清晨的陽光鍍亮師大校園女生的背影和闊大的梧桐樹葉, 陳超老師騎著單車斜挎著書包來到面前。那磁性的聲音,那溫暖的微笑!那頭“溫順的獅子”!您的這架單車已經在師大成為佳話,很多年您居住在城北,師大卻在石家莊的西南角。 尤其是在冬天冰雪滿地的時候,當學生瑟縮著袖著手蹩進教室的時候,您卻身著單衣滿頭大汗端著一個飄著咖啡香氣的巨大玻璃杯闊步走進教室。
先生,那架自行車還在嗎? 還是它已經落滿了沉重的灰塵? 它能夠承受這時間的重壓嗎? 當時我窮得只剩一身傲氣, 每次去看您我都跑到超市去給您帶上一盒咖啡, 甚至我到了北京也是如此。 因為在1999年冬天第一次相遇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您喜歡喝咖啡。
師大新校區的圖書館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從此以后,同學們,當你們走進圖書館的時候會想起先生的那首詩嗎?“河北師大圖書館/線條簡潔又流暢/新油漆的桌椅比讀者漂亮/散發著清漆的香味兒/和開朗的光芒//我喜歡的姑娘/正站在鋁合金升降梯上/將新購進的詩集整齊擺放/剛才她還在林子里跳繩兒/起伏的發辮使我悵惘/一些書已經上架/另一些從她手中滑落/我看到地下一本《生命詩學》/擦亮了她野薄荷一樣的目光……”
多年前那個夏日,是您無私而熱情地領我走進詩歌的門檻。您是我的授業恩師,也是我的兄長。甚至在很多公開和私下場合您稱我為哥們兒。 這也是在2000級碩士研究生中我年齡最小、閱世最淺卻傻傻地稱“師母”為“嫂子”的原因。 我的師姐都很不解,當然也很羨慕。 當您今年要出版《詩野游牧》時竟然打來電話并發郵件希望我為書作序。 我當時頗為躊躇,我說,“老師,哪有學生給老師寫序的? ”您懇切的言辭讓我無比汗顏和忐忑。 我最終寫完了“從‘游蕩’到‘游牧’”這篇序文。 當我打開2014年4月10日下午兩點14分您的這封郵件,我除了眼淚還能做什么呢?
俊明,你好。
給你添麻煩了,真有點不忍。如果你忙,一定直接告我,我再找別人寫。真的沒關系,咱們之間什么不能說呢。
我是想,為序,你其實是我最屬意之人。 與其找個同齡詩評家,不如就讓我的學生兼哥們兒———霍俊明來寫,更到位,更有趣些。
書稿你不用全看,主要看一下第一輯“詩藝清話”,第二輯“片面之詞”即可。
其他兩輯,你都熟悉(有些是文章摘段),若有時間,只需瀏覽。
“后記”,交代了多年來我寫大量“詩話”的想法。
你不要有壓力,放開你的性情,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可談談你對我某些詩話的感受,談談我們師生教學相長、交往的趣事。 總之,你寫得自由、明朗、高興就可。
出版社要求二、三千字,不用長。
謝謝。
陳超

《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生成》 陳超著
在時下紛沓錯亂的詩壇上,您冷靜、客觀和敏識的姿態是一般評論家終生都難以修到的境界。 當每次見面您拍著我的肩膀說,“俊明,你干得真好!”我既高興,又羞愧,如今卻是滿眼的浮淚。當多年前我向您談起唐山詩人周建歧上吊自殺的時候,我們一起唏噓感嘆人生的無常。而當我重新打開您的詩集,我看到了您對塵世的熱愛,也聽到你內心深處黑暗炸響的聲音。
先生更像是一個工業時代大汗淋漓的騎單車的人。 你在陣雪、霧霾和逆風中前進,詩思和存在的隱痛在冬夜中靜頓、沉潛。 時間的指針悄然掠過驚懼的目光,您則擦拭和點亮了那個又溫潤縈懷的舊式燈盞,“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曠野/望著你給我展示的家園,/今夜啊,讓我放下火杖,拿起詩歌”。
這幾天在石家莊的時候我一直在心里完成了這樣一首詩。回北京后我在流淚中寫完《悼恩師陳超先生》:“石家莊原來有這么多樓/這么多高樓/這么多需要抬起頭/仰望的高樓/從2014年的萬圣節起/每一個高樓/都會有一個人/跳下來/然后微笑著/走過來/拍著我的肩膀說/‘俊明,我沒事! ’”
而今夜,我已經看到了轉世的桃花。 那些紅,由您的赤誠和熱血染成! 還好,您已經在天國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