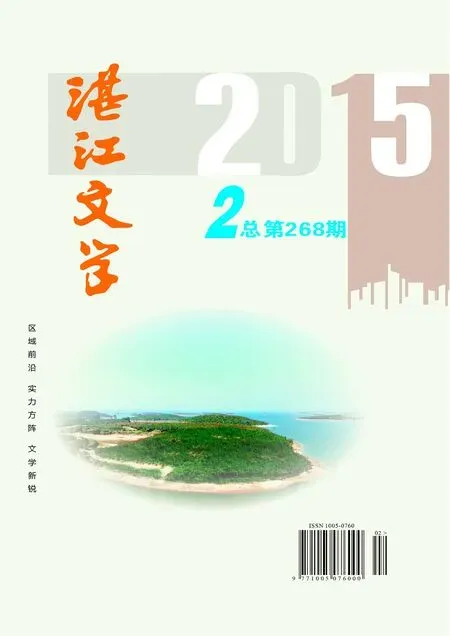心靈解剖(外一篇)
※ 廖增偉
心靈解剖(外一篇)
※ 廖增偉
有一度,我非常迷戀于到處找美食。跟其他有類似癖好的人一樣,我關心著各種休閑娛樂類的報紙,這些報紙里面必有一大版美食專欄。上面有色彩艷麗的照片,配上能把稻草說成金條的解說詞。這些解說詞就像在我腦子里下蠱一樣,讓我按圖索驥,如法炮制。每次奔去時都心情喜悅,甘甜如蜜;返回時則往往帶著失望,感到受騙上當。要是某家餐館在我品嘗之后感到名副其實、物有所值的話,我就會非常愉快,接著找時間再來。
但是不管怎么美味的佳肴,總是在去過兩三次之后,就感到索然無味了。于是又要開始留心報紙的介紹,平時也跟同事朋友交流各方面的情報。
新的期待在尋找和交流中再度出現,某某菜肴就成了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詞句。我們終于坐到這家飯店里,正兒八經地用一種經過修飾的詞語點菜,吃飯時動不動就拿起紙巾擦嘴,談吐聲輕輕柔柔,說話干凈文明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終于也有變成文明人乃至上等人的一天,心里甜蜜得不行。好像六十年前舊上海的風花雪月,通過這種食品和情調,悄悄地占領了我們的心靈。
說老實話,我們就愿意被這種“風花雪月”的感覺占領,這讓我們有受到尊敬的美好感受。至于當年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些“階級”“壓迫”之類的話,全都忘到爪哇國了。
在我們這個城市里,有很多跟我們相似的食客,有些比我們理智,有些更加瘋狂。雖然大家的薪水各不相同,但是要品嘗時新的、自己原來沒有吃過的美食的愿望,在本質上毫無二致。也就是說,我們都在為擴大自己的人生體驗而努力。
大家都在追逐那些新穎的感觀享受,去陌生的地方旅游,期盼著一次驚新動魄的艷遇,傾聽沒有聽到過的音樂,品嘗未曾見到過的美食,去神秘的地方探險,甚至亡命飆車或攀登雪峰,最終的目標,都是要滿足自己的獨特欲望的需求。像我這樣的收入,不能去做其他更多的“冒險”,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通過追逐美食這樣一個行動,來滿足自己的欲望。
這樣一種安全的行為,通過某種自我的幻想和虛構,在本質上,達到了原本做不到的那些事情所給人帶來的快感。
這樣,不管我們是凡夫小民還是達官顯貴,大家的理想都是一樣的。很多學者說,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一個烏托邦消失了之后,我們的人生價值產生了虛空和紊亂,實際上這種觀點卻忽視了我們自古以來尋求世俗享樂的那種內在動力。精致的生活和奢華的享受,永遠是黎民百姓的夢想。
記得以前物質比較匱乏的時代,我們都非常喜歡聽有關毛主席吃紅燒肉的故事。這是一個經典的民間傳奇,后來我在很多各地的朋友那里都驗證了這樣一個故事的廣泛性。
2012年諾貝爾得獎作家莫言就用各種方法表達過對吃的渴望和對饑餓的恐懼,而所有我們這些經歷過物質極端匱乏時期的人,都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往死里吃一頓香噴噴的紅燒肉。
當然,后來紅燒肉是吃過了,但之后就對紅燒肉保持克制態度了。就跟有錢人一樣,等什么魚翅、鮑魚也有幸吃過之后,現在我們都開始裝模作樣地說喜歡喝粥啃地瓜吃咸菜了。
很多鄉村風味的飯店在各種海鮮野味店之后冒泡,滿足了這種愿望。
當然這些鄉村風味已經不再是以前我們吃的那些沒有一點油的粗糧了,而是經過精心炮制的精美食品。
就這樣,食品在不斷地輪回著,飲食的愿望和態度也在不斷的輪回著,我們的愿望卻永遠都沒有得到滿足。就好像《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里那個貪得無厭的老太婆一樣,想了又想,要了又要,總是覺得不夠。
知足常樂
我一度非常迷戀找吃的。
多年前我在內蒙古草原上吃過烤全羊,味道奇美,不似人間之物,外加朋友出錢,我表現得極其英勇,吃得流了一個星期的鼻血,至今津津樂道,沒齒不忘。
一天晚上,我在夢里光顧了這家餐廳。我大模大樣,文明禮貌地坐在椅子上,吩咐酒保上菜,上烤全羊。過了一會兒,侍者端著一只油汪汪的烤鴨上來了。
我說:“我要的是烤全羊啊,靚仔!”
侍者說:“廖老板,這就是烤全羊啊……”
醒來之后,我從收音機那里聽到著名導演李曉(電視劇《向東是大海》、《那樣芬芳》、《北上廣不相信眼淚》的執行導演)因抑郁癥自盡離世的消息。

我那段時間老是想到這個問題,不厭其煩地反問我自己:“李曉為什么會自殺呢?”一個人要自殺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新聞里說是因為抑郁癥。可是,李曉那么有錢,那么有名有地位,他為什么會得抑郁癥呢?有人說,他不滿足,他不快樂,所以得抑郁癥。他為什么不快樂呢?要是他愿意,多少美女嬌娃會排著隊供他喜歡啊,我做夢都想著有這一天。我暗地里估算了一下,發現我按照現在這個樣子,就是像牛一樣干上四十輩子,也混不到李曉那樣的地步。可是他卻自殺了。我感到非常悲哀,覺得自己在路上走著走著,忽然發現前面出現了一個萬丈深淵。想了很久,我明白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問題。很顯然,一個人的快樂和幸福跟他所擁有的金錢和地位不總是成正比的。但是現代的傳媒總是喜歡把有錢有權人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快活事情添油加醋地寫出來迷惑我們,讓我們不由自主地都以他們為目標,使出吃奶的力氣去奮斗。當年的李曉也是一個窮苦的孩子,甚至比我還不如,后來他發達了,做了人上人。最后,他感到了不快樂,得了抑郁癥,自殺了。
如果一個人的價值用他發出的笑聲來衡量,估計十個李曉也比不上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樂觀精神,同時又善于用“阿Q精神”做佐料加以調配。價值這種觀念是很奇怪的,我們的錯誤在于,主流社會通常只用一種角度來衡量所有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