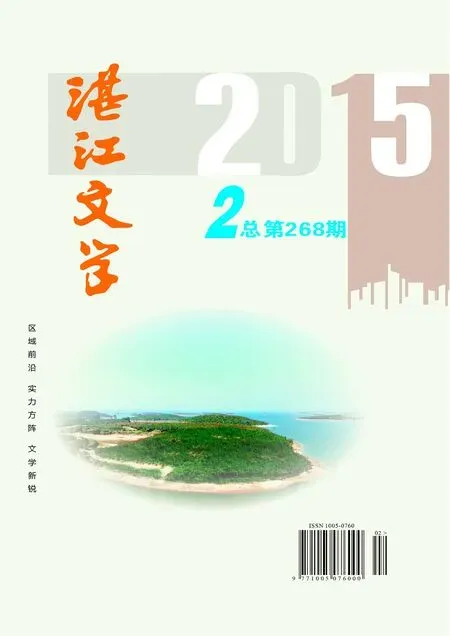存在與超越:梁永利海洋詩(shī)歌的生命意蘊(yùn)
※ 張德明
存在與超越:梁永利海洋詩(shī)歌的生命意蘊(yùn)
※ 張德明

梁永利是雷州半島上出生并長(zhǎng)大的,對(duì)于緊鄰半島的那片廣漠的海域,他是再熟悉不過(guò)了,那里的沙灘、礁石、海風(fēng)、海浪,那里的紅樹(shù)林、海椰樹(shù)、相思林,那里的對(duì)蝦、生蠔、巨蟹,都在他的視野中刻印著深刻的痕跡,留存下獨(dú)特的身形和姿態(tài)。當(dāng)其他海洋詩(shī)人都對(duì)這些海洋事物樂(lè)此不疲地加以細(xì)致描摹、熱情禮贊的時(shí)候,梁永利卻并不熱衷于此,我很少在他的詩(shī)歌中發(fā)現(xiàn)直接描寫(xiě)這些海洋事物的作品。更多的時(shí)候,他會(huì)越過(guò)事物表面的視覺(jué)形象,而將思維的觸須伸向更為深遠(yuǎn)的地方,以海洋為文學(xué)母題,呈現(xiàn)海洋背后所藏蘊(yùn)的更有價(jià)值的深意。在《古渡遺址》中,詩(shī)人這樣寫(xiě)道:
欲上岸的鯨 掠開(kāi)一面堅(jiān)硬
刺穿古船
在歷史的夢(mèng)境中漂流
看見(jiàn)蓑衣垂釣 孤舟橫擺
眾多的顯貴也踏歌蠻荒
古渡風(fēng)凄草瘦
嘆逝川者是誰(shuí)
兩千年的世面太難見(jiàn)
唯有雷鳴電閃震蕩古渡的神經(jīng)
它的遺骸
為今人的歡顏復(fù)活
漲潮之時(shí)
鯨的眼睜得太大
遠(yuǎn)古的中國(guó)一直是以內(nèi)陸文明為基本的文明形態(tài)的,海洋文明其實(shí)只是古老中華文明中一個(gè)極不重要的部分,甚至很可能是極為隱秘的部分。因?yàn)榇耍糯?shī)歌中的海洋書(shū)寫(xiě)是相對(duì)稀疏的,海洋遠(yuǎn)不是古詩(shī)中的重要意象和母題。當(dāng)古代詩(shī)人寫(xiě)“渡口”之時(shí),一般都是指河渡、江渡,而很少海渡。“春潮帶雨晚來(lái)急,野渡無(wú)人舟自橫”(韋應(yīng)物《滁州西澗》),“渡口水流急,回船不自由”(崔國(guó)輔《中流曲》),這些都是寫(xiě)河渡與江渡的好詩(shī)。相比而言,對(duì)海洋世界中的渡口寫(xiě)照,古典詩(shī)歌中很難得一見(jiàn)。梁永利的這首《古渡遺址》,從題材選擇上說(shuō),就是富有新意的。更難能可貴的是,詩(shī)人并沒(méi)有停留于對(duì)古渡現(xiàn)狀的直接描寫(xiě)之中,而是將現(xiàn)實(shí)與歷史交織在一起,在對(duì)歷史的緬懷與追憶之中,表露出有關(guān)光陰如梭、滄海桑田的感慨和嘆惋。
梁永利的海洋詩(shī)歌,往往不是外在事物的簡(jiǎn)單陳列,而是將大海與人類(lèi)聯(lián)系在一起,描寫(xiě)海的時(shí)候,一般都會(huì)有人的在場(chǎng),人是海洋景觀的觀察者和注視者,是海洋變化的記錄者和沉思者;描寫(xiě)人的時(shí)候,常常將他們放置在海洋場(chǎng)景之中,讓海洋成為人類(lèi)生活的重要場(chǎng)域,海洋的驚濤駭浪、迷人風(fēng)物,將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氣度充分照亮。在這眾多的人物之中,“我”是較為常見(jiàn)的在場(chǎng)者,以“我”為抒情主體和海洋觀察者的詩(shī)歌作品是相對(duì)豐富的。《臺(tái)風(fēng)》即是其中一例:
東經(jīng)117 ° 北緯17 °
這是一個(gè)海妖的世界
在陸地 我的耳朵
成了喇叭 海上的旋風(fēng)
以每秒120公里的風(fēng)速
前進(jìn)在我們跳動(dòng)的心臟
我從黑夜開(kāi)始
從一棵棵大樹(shù)開(kāi)始
掩蓋著許多不斷動(dòng)搖的植物
摸黑時(shí)刻
海妖毫無(wú)情面
把即將下卵的魚(yú)摔死
所有的船舨都鋪成她登陸的路
直至東經(jīng)120 ° 北緯19 °
海妖便潛入到我的風(fēng)信網(wǎng)
她帶著怒氣 尋找往年的萍蹤
不過(guò)是與漁夫的誓言
不過(guò)是一次兒戲的情事
多少次葬身魚(yú)腹了 風(fēng)說(shuō)
這漁夫 也經(jīng)常對(duì)著海
作驚天動(dòng)地的胃痛
天漸亮 我看到
海妖被一棵大樹(shù)刮了胸膛
一條血路通往漁夫的小屋
毫無(wú)疑問(wèn),“臺(tái)風(fēng)”是大海帶給海邊人家的最為尋常的海上禮物。臺(tái)風(fēng)到來(lái)時(shí),那巨大的風(fēng)浪、如灌的雨水和此起彼伏的險(xiǎn)情,是海邊人早已慣見(jiàn)的充滿殘忍和暴力的重大海事。不過(guò),由于臺(tái)風(fēng)巨大的殺傷力和摧毀性,所以每當(dāng)其到來(lái)時(shí),很多人都悄然躲藏在最安全的地方,用聽(tīng)覺(jué)在感受臺(tái)風(fēng),而不是用視覺(jué)去直視臺(tái)風(fēng),甚至用身體去親歷臺(tái)風(fēng)。因此,很多詩(shī)人的臺(tái)風(fēng)體驗(yàn),往往停留在想象和虛擬的層面上,很少是視覺(jué)層面乃至身體層面上的。梁永利由于生于斯長(zhǎng)于斯,對(duì)臺(tái)風(fēng)季候司空見(jiàn)慣,他熟視臺(tái)風(fēng),也可能親歷過(guò)臺(tái)風(fēng),他的臺(tái)風(fēng)書(shū)寫(xiě)中,便有了赫然的“我”之在場(chǎng),“我”是臺(tái)風(fēng)中的親歷者,“我”在詩(shī)歌中的現(xiàn)身,將臺(tái)風(fēng)現(xiàn)象的可信度大大提升。“我”與海妖之間的機(jī)緣巧合,道出了臺(tái)風(fēng)嫵媚而神秘的一面,“我”看到“海妖”被大樹(shù)刮破胸膛的情景,將臺(tái)風(fēng)可怖的一面形象地刻繪出來(lái)。不難發(fā)現(xiàn),詩(shī)歌中所著力表現(xiàn)的“海妖”意象,不過(guò)是對(duì)臺(tái)風(fēng)超越常人的肆虐狀態(tài)和不可測(cè)度的存在景觀所作的擬人化表述。詩(shī)人以“海妖”來(lái)喻指“臺(tái)風(fēng)”,為我們理解與認(rèn)識(shí)臺(tái)風(fēng)提供了極大的想象空間,并賦予這一場(chǎng)自然災(zāi)害以某種神秘感和傳奇性。
《臺(tái)風(fēng)》以“我”為抒情主體,生動(dòng)呈現(xiàn)了海邊人家的真實(shí)生存情態(tài),《海邊情事》、《海邊漁女》、《老蟹肖力》則更多是站在客觀述說(shuō)的層面,對(duì)一些平實(shí)的海洋人生命境況的藝術(shù)寫(xiě)真。自然,梁永利不只是簡(jiǎn)單寫(xiě)出了海上人家、臨海生命的存在樣態(tài),還常常能在描寫(xiě)之中滲透著有關(guān)人生和命運(yùn)的更深層次思考,從而凸顯出某種給人啟迪的超越意識(shí)。這是我更看重詩(shī)人作品藝術(shù)價(jià)值的方面。在《波光一閃而過(guò)》里,我讀到了這種超越現(xiàn)實(shí)的思想信息:
一排水杉 碎銀落在空巢
我的小船開(kāi)得飛快
真以為 魚(yú)腥暖和的胃口
保留了秋蓮的滋味
我追尋波光里的影子
我心中的蘋(píng)果
留下蜻蜓飛過(guò)的聲音
走過(guò)漁村 鐵軌交叉前進(jìn)
沿途的魚(yú)骨貼近窗口
村莊的后面 海鹽浸化了古船
我的臉孔蒼白
一張海盜的地圖
畫(huà)著出海口 沒(méi)有風(fēng)標(biāo)
沒(méi)有地名 我發(fā)現(xiàn)一面銅鏡
與波光一樣閃亮
波光是一把刀
很快剝開(kāi)我的雙眼
一切的誤會(huì) 交給海鳥(niǎo)
海鳥(niǎo)說(shuō) 我心中的蘋(píng)果
是天堂的糧食
海洋上的波光以其強(qiáng)烈的照明度和一閃而逝的飛越速度,常帶給人莫名的驚悚和極大的不安,詩(shī)人也如實(shí)交代了面對(duì)“波光”時(shí)內(nèi)心的恐懼與惶惑。不過(guò),正所謂“不經(jīng)歷風(fēng)雨,如何見(jiàn)彩虹”,波光閃過(guò)之后,會(huì)有希望和光芒的力量在人們內(nèi)心珍藏。當(dāng)詩(shī)人借海鳥(niǎo)的口說(shuō),“我心中的蘋(píng)果/是天堂的糧食”,我們可以欣慰地發(fā)現(xiàn)他在經(jīng)歷波光之后的淡定,戰(zhàn)勝驚恐后的升華。
在世界正朝著全球一體化大步邁進(jìn)的當(dāng)下,海洋已成為了各國(guó)異常看重的新的開(kāi)發(fā)地帶和爭(zhēng)奪地盤(pán),其地位將越來(lái)越重要,海洋書(shū)寫(xiě)必將成為未來(lái)幾十年非常重要的文學(xué)形式。面對(duì)海洋題材,我覺(jué)得還有很多值得開(kāi)墾的地方,比如其生態(tài)學(xué)內(nèi)涵、交通和居住意義、礦藏與軍事領(lǐng)屬、國(guó)家社會(huì)力量的博弈等等,相信有這樣開(kāi)闊的書(shū)寫(xiě)空間作保障,梁永利的海洋詩(shī)歌會(huì)越寫(xiě)越出彩,會(huì)向我們呈現(xiàn)更多新穎而奇幻的海洋景觀,會(huì)更為深入地展現(xiàn)其內(nèi)心深處的存在體驗(yàn)與超越意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