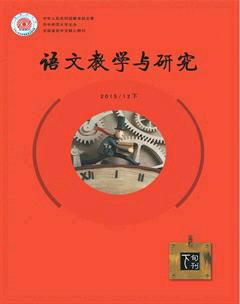自己的道場
胡達瑛
尼采曾自詡為太陽,有人笑他狂妄自大而不知狷介,亦有人把他視為一個時代的拯救者。宣揚“我們不要毀壞藝術(shù)”的泰戈爾成了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再有高呼“藝術(shù)不要毀滅我們”的圣雄甘地開辟了印度民主化新時代。可知,并非所有人都活在同一個道場里。
不同的道場,不啻乎灌木叢與喬木,縱使兩者有各自的生存方式,但是前者可以綿延數(shù)里,后者足以遮天蔽日,沒有孰優(yōu)孰劣,更無誰對誰錯。正如國畫大師徐悲鴻說:“別人看我是荒謬,我看自己是絕倫。”荒謬與絕倫只有一線之隔。
道場之途,本就是一番尋尋覓覓后的花明一村。世人皆知有個“凡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的柳河東,又有多少人知他亦曾在宦海沉浮,十年輾轉(zhuǎn)才覺悟最適合自己的還是那芙蓉桃面、歡歌煙火。前行的人生路,哪能缺了幾番輾轉(zhuǎn)?
尋得道場后,我們更需長駐道場。活在自己的道場上,需要有對理想的追求和對自我的堅守。自我追求,可以是一場無窮無盡、至死方休的奔逐。夸父逐日,如今許只是人們口中的笑話甚至嗤料,卻真切地壯哉了崦嵫的神話。自我堅守,可以是淪落歡場仍以“眾類亦云茂,虛心寧自持”的姿態(tài)綻放。薛濤,家道中落卻不甘墮落,終成就“蜀中四大才女”之名。
人得為自己活著,卻不能獨獨為自己活著。“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晏小山的一曲《鷓鴣天》,點亮了宋代的詞壇,恍惚了世人的眼,卻也使得這位相國公子在老父西去后沉迷于李煜式的舊夢。他花卻金銀無數(shù),卻落了個家人饑寒交迫的局面。終究,既不如李太白“千金散盡還復(fù)來”的快意瀟灑,又失卻唐寅“不使人間造孽錢”的清高傲然。何以至此?想必是他一味追求自我的道場、而忘記了眾人共生于同一磁場這一道理吧。
長途役役,天地宛若一只巨大的磁盤,我們正是那一個個受到牽引的小磁針,小心翼翼地歸屬于自己的道場。縱使行進路上壓力重重,也不忘那始終如一的堅守,而這,便是道場的力量。
(導(dǎo)師:賈玉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