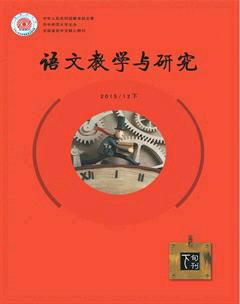質數的孤獨
鄭小驢
那年的年末,送朋友去昆明火車站,揮手告別后往回走,一掏牛仔褲兜,手機沒了。穿著厚厚的羽絨服,我甚至不知道手機是何時沒了的,一點感覺都沒有。失去手機的一剎那,腦子一下空白了,意味著你和這個世界不再有任何的聯系。被剝奪地球籍,估計就是這種體會。
一面發自肺腑地譴責小偷,一面失魂落魄地找到附近的一位巡警,訴說了自己的遭遇。他大概每天都會遇到幾個像我這樣的不幸者,所以當他略帶奚落、嘲諷間夾著些許同情和玩味的眼神端詳著我時,我覺得這家伙簡直就是個混蛋,和長沙、上海、南昌所有警察一樣,要在火車站給你從小偷手中把手機拿回來,簡直就是個冷笑話。他果然沒能滿足我的小期待,說了一大堆廢話后,就讓我回去等消息了。
那天接下來唯一可做的而且必須要做的事,就是買手機了。失去手機,整個世界觀都遭到了顛覆。失去聯系后的恐慌感孤獨感如影相隨,時刻提醒著你,牛仔褲右褲兜里空了,你與這個世界不再有聯系,你無法聯系上別人,別人也無法再聯系上你。就像《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漢娜·阿倫特說到的,人類對孤獨的恐懼,是造成極權主義起源的重要原因。孤獨意味著失去存在感、安全感,只有成為集體的一分子,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才重見天日。
那天的刻骨銘心的體驗,作為關鍵詞——“孤獨”完美地詮釋了我的內心與思想。我像個失去了家的流浪者,走在熙熙攘攘的小西門,面對滿大街的云南方言,作為異鄉人的孤獨與恐慌,徹底暴露了出來。我努力而別扭地學著云南人,每句話的后面加個“嘎”,裝模作樣地和柜臺上的手機銷售小姐砍價。我盡量讓自己鎮定,想象自己就是一個云南人,我有高貴的“云南血統”,我不是一個異鄉人,我是你們中的一分子。
柜臺小姐的眼神一步步地將我的自信心逼退。
“先生,你是云南人?”
“哦,不是啊?聽口音我還以為你是云南人呢!”
她的微笑暗含著無數種玩味的意思,彬彬有禮的背后,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信心立刻分崩離析。這種沮喪感,就像當了假洋鬼子被當眾拆穿一樣,我灰溜溜地走掉了。
那天失魂落魄地走在冬天的昆明街頭,天氣陰霾,老昆明人說,這是最冷的一年了。“還從沒遇過這么冷的冬天呢!”我的褲兜空空如也,或許也只有等失去手機的時候,才能認真地想一想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存在之意義這樣形而上的問題。有沒人給我電話?有沒人還惦記著自己?遇到緊急情況,沒手機怎么辦?得出的結果是那么的悲觀,沒有手機,我和這個世界一毛錢的關系都沒有。悲觀之后,內心反倒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輕松感,像個落魄戶一樣,我自由自在地大街上溜達著,直到一群穿著薄T恤,腳踏人字拖的小伙朝我走來。那么冷的天,他們竟然都光著腳丫子,趿拉著人字拖啪啦啪啦瀟灑地走了。那時候,我想自己應該已經將孤獨感和云南血統拋之腦后了。我甚至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再買手機。
(選自《你知道的太多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