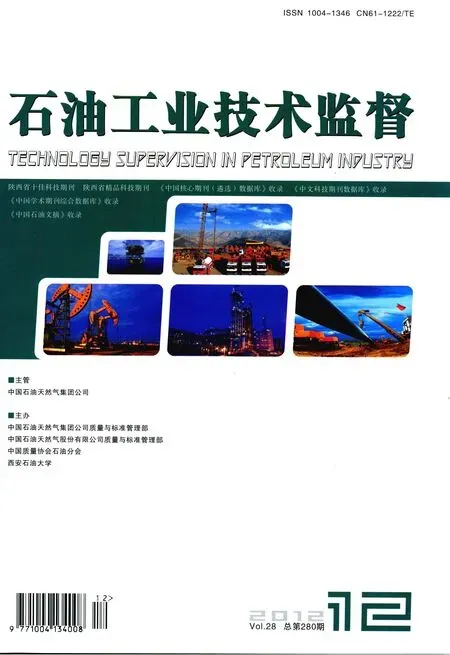落實質量綱要 踐行質量至上促進集團公司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升——在2012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質量工作座談會上的報告*
于洪金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質量與標準管理部 (北京 100007)
1 近3年質量工作回顧
2009年質量工作座談會以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集團公司)認真貫徹國家關于質量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結合總結“十一五”質量成效、制定“十二五”質量規劃,特別是以全面實施基礎管理建設工程為契機,以夯實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發展基礎為努力方向,進一步加大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工作力度,在生產經營業績持續較快增長的同時,取得了質量提升的新進展和新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質量發展目標進一步明確
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化“環保優先、安全第一、質量至上、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集團公司于2010年9月發布了“誠實守信、精益求精”的質量方針和“零事故、零缺陷,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質量目標,從戰略層面確定了質量工作的宗旨和方向。2010年以來,按照集團公司黨組的決策,全面實施基礎管理建設工程,通過制定基礎管理建設工程實施方案,對標分析國際先進企業的領先實踐,集團公司決定在“十二五”時期,將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的管理水平,由規范級整體提高到優化級,逐步縮小與國際大石油公司的差距。同時根據基礎管理建設工程的頂層設計,確定了單項業務能力提升和基礎管理協同作用的工作任務,通過構建管理規范平臺、完善基礎管理體系,實現管理的定量化、標準化、信息化,進而保證工作、產品和服務質量。為此,按照集團公司建設一流的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的發展定位,質量工作的長遠戰略目標和近期階段目標更加明確,質量提升路徑和抓手更加具體。
1.2 質量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
各地區公司根據集團公司 《質量管理體系建設推進方案》的要求,加快開展了質量管理體系建立和認證工作。目前生產經營型企業質量管理體系建立率達到100%、認證率達到98.8%,比3年前提高了1倍左右,其中銷售、工程技術、工程建設、裝備制造企業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率達到100%,勘探與生產、煉油與化工、天然氣與管道企業質量管理體系建立率達到100%。在地區公司建立和認證質量管理體系的基礎上,集團公司還推行了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制度,勘探與生產分公司等7個專業公司組織實施了推進評審工作,推動地區公司理清體系管理思路,運用過程方法加強管理,建立健全質量持續改進機制,并培養了一批體系推進評審專家。目前已有70家地區公司經過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占已建立體系單位總數的56%。部分地區公司通過體系內審和推進評審,進一步完善了各級質量管理體系文件,同時注重在操作層面與其它管理體系文件相融合,既減少了基層體系建設負擔,又持續提高了體系運行的有效性。
1.3 質量監督力度進一步加大
近年來,集團公司和部分企業加大質量監督力度,較好地減少了質量隱患,促進了質量保證能力提高。在采購產品質量控制方面,集團公司對5大類73種石油石化用化學劑實施產品質量認可,嚴格禁止不符合認可條件、質量保證能力差的廠家和產品列入采購范圍;同時組織抽查各類采購產品質量2 374批次。西南油氣田、管道公司等部分單位對監造目錄內的產品和其它重點產品實施駐廠監造;吉林油田等33家地區公司復核審查供應商企業產品標準,都從采購源頭把好了產品質量關。在自產產品質量控制方面,集團公司逐年增加對自產產品質量的抽查,抽查合格率穩步上升。在工程質量控制方面,集團公司組織對11 938個工程實施質量監督,增強了工程建設各方責任主體的質量意識,促使了工程質量總體受控。
1.4 計量保障作用進一步發揮
逐步完善了計量器具配備,在計量器具配備情況普查、典型地區公司計量器具配備調研的基礎上,明確了計量器具完善升級要求和投入渠道。2010年集團公司安排5億元資金用于能源計量器具更新完善,目前能源計量器具配備率達到96.1%,比3年前提高了6%以上;2011年各地區公司計量器具更新改造投入資金7.3億元,完善計量器具14.8萬臺套,為信息化建設增強了基礎保障。逐步規范了油氣交接計量管理,通過實施油氣交接計量管理規定及配套標準,規范了油氣交接計量行為,提高了公司內部油氣流轉效率;通過協調推進跨國油氣管道計量檢驗工作,及時完成了計量檢驗設施檢查驗收、交接計量參數檢測比對,確保了中亞、中俄和中緬油氣管道建設和投運的順利進行。逐步加強了測量過程管理,按照國家有關要求,重點企業加快了測量管理體系建設,目前重點企業測量管理體系建立率達到60%,認證率達到42%,增強了計量檢測對質量提升的基礎性作用。
1.5 標準化的成效進一步顯現
繼續完善了各級標準體系建設,牽頭制修訂國家和行業標準361項,完成220項;制修訂集團公司企業標準523項,已發布348項;制修訂地區公司企業標準2 000余項。一批科研成果和管理經驗轉化為各級標準,一批國家、行業和集團公司企業標準細化為生產操作規程,既發揮了集團公司在國家和行業層面的標準化引領作用,又見到了生產經營的標準化管理實效。強化了各級標準實施工作,各專業公司和地區公司結合集團公司重點標準實施安排,制定本專業本地區的標準實施方案,對照標準內容進行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確保了產品質量達標升級,增加了國內外市場占有率,規范了作業現場管理,降低了生產經營成本。
取得了國際標準化突破性進展,首次代表國家承擔國際標準化組織煤層氣技術委員會(ISO/TC263)、輸送管系統分技術委員會(ISO/TC67/SC2)秘書處,不僅提高了國家在國際標準化領域的地位,更彰顯了集團公司作為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的形象;促成了中土標準合作協議的簽署,為此集團公司在土庫曼斯坦的投資將節省15%~20%,并且施工進度、結算進度都會加快;西南油氣田制訂的天然氣國際標準基本完成,管道公司正在制訂管道防腐國外先進標準,標志著集團公司技術標準能力開始得到國際認可。
1.6 檢測校準能力進一步增強
各級實驗室依據 《實驗室資質認定評審準則》、《檢測和校準實驗室能力的通用要求》、《法定計量檢定機構考核規范》,積極建立和完善實驗室管理體系,增強“專業化,高資質、高水平”的檢驗測試能力,部分重點實驗室具備了國際技術比對的基本能力和資質。在檢測實驗室建設上,制定了集團公司質檢機構布局規劃,增設了哈爾濱和烏魯木齊2個油品質檢中心;共投資近3億元更新改造質檢設備,完善提升了質量檢驗能力。在校準實驗室建設上,國家批準籌建的5個天然氣計量檢定站點全面建設;國家最高等級天然氣高壓大流量標準裝置建成,技術能力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國家最高等級中低壓天然氣大流量標準裝置正在改建,建成后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集團公司天然氣質量控制和能量計量中心正在建設,建成后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集團公司國內最高等級測井儀校準裝置通過了國家建標考核。
1.7 質量工作業績再上新臺階
一是質量管理業績突出。通過推進質量管理體系建設,大慶油田榮獲 “全國質量工作先進單位標兵”稱號,成為全國工業戰線質量管理先進典型;通過參與全國性的質量改進活動,集團公司共獲得全國優秀質量管理小組132個、全國質量信得過班組20個、全國用戶滿意獎18項、全國卓越績效模式先進企業2個。二是按期實現油品質量升級。根據國家汽柴油質量升級要求,研發設計、投資采購、生產銷售等相關單位協同運作,確保了錦州石化、大連石化、大港石化等16家石化公司21套汽柴油裝置升級投產,按期向社會供應高質量油品,2011年國家監督抽查中油品質量全部合格。三是品牌知名度明顯提高。吉林石化、大慶油田、寶石機械、渤海裝備、撫順石化、青海油田、寶雞鋼管等企業的13種產品獲行業知名品牌稱號;克拉瑪依石化、遼河石化、獨山子石化、大慶煉化、蘭州石化、寶雞鋼管生產的部分產品質量處于國際先進或國內領先水平,品牌建設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四是工程質量穩中有升,一批重點工程快速優質建成。哈薩克斯坦第三油氣處理廠等6項工程獲得國家魯班獎;蘇里格產能建設地面工程、阿拉山口—獨山子原油管道工程等16個項目獲得國家優質工程銀獎。五是服務質量不斷提高。工程技術業務實行“一井一策”,提速、提質、提效的三提工程收效明顯,得到了甲方的贊譽;銷售、礦區業務完善服務流程和標準,規范服務內容和方式,開通統一服務熱線,以優質服務贏得了用戶滿意,鞏固了終端銷售市場。
2 近3年質量工作的主要體會和做法
回顧過去3年來質量提升的新進展和新成效,我們有以下幾點主要體會和做法:
第一,圍繞集團公司轉變發展方式主線,以質取勝增強發展軟實力。近年來,集團公司按照黨的十七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將其作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的要求,提出要抓好“發展”、“轉變”、“和諧”3件大事,近期的工作重心是解決轉變發展方式這個主要矛盾。從企業發展階段的歷史經驗來看,當行業市場趨于飽和,企業規模趨于穩定時,也是企業從外延式發展轉向內涵式發展的時期,這時期的企業通過增加對包括品牌形象、運作管理在內的“隱性生產要素”投入,進而帶來豐厚、持續的經營績效。所以,這幾年不論是我們研究發布質量方針和質量目標,還是著力完善質量管理體系、計量檢測體系、企業標準化體系,目的都是以增強集團公司軟實力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也完全符合國家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根本要求。
第二,推進基礎管理建設工程全面實施,提高質量管理能力和水平。集團公司在2010年工作會議上部署全面實施基礎管理建設工程,在2011年領導干部會議上提出全面推進三基工作新的重大工程,2012年初又下發了《關于全面加強三基工作若干意見》,都要求深入推進以基礎管理建設工程為抓手的基礎性工作。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工作是基礎管理的重要組成內容,質量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礎,集中體現了企業為社會所能夠創造的價值;計量和標準化既承載著企業生產經營的所有管理事項,更全面反映了管理水平和持續發展能力。近3年集團公司上下緊緊圍繞基礎管理建設工程的實施,積極開展質量提升工作,不僅取得了階段性的實施成效,更重要的是對照集團公司發展目標,摸清現狀、梳理家底、分析差距、培育典型,制定并正在實施管理能力與發展目標相匹配的質量提升計劃。特別是將以管理規范平臺和基礎管理體系,來提高管理效率、增強管控能力,進而為全面開展管理提升打下堅實基礎。
第三,加強質量計量標準化的組織領導,建立質量可持續發展機制。基礎管理建設工程全面實施以來,集團公司上下在加強領導、健全組織、完善制度等多個方面促進質量提升工作。2011年,集團公司2次召開總經理辦公會,安排部署基礎管理建設工程實施工作,確立了對基礎工作進行總結、完善、提升、提高的總體思路,為質量改進和提升明確了方向和目標;調整設立質量與標準管理部,統一了質量歸口管理工作,強化了工程質量監督職責。地區公司基本上成立了由主要領導負責的基礎管理建設工程領導小組,明確質量管理職責和任務,為質量改進和提升提供了組織保障。同時,結合集團公司規章制度體系完善,集團公司和專業公司制修訂了18項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管理辦法、規定和細則,部分地區公司也對相關的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和完善,質量管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得以不斷建立健全。
第四,緊密結合生產經營業務發展實際,落實各級質量目標和責任。質量是生產出來的,質量的保證來源于生產經營全過程的責任落實,這對于一個產業鏈長、產品線寬的企業集團尤為重要。近年來,煉油化工業務在提升產品質量的同時,下大力氣增強質量檢驗能力,有效地控制了生產過程和出廠產品質量。裝備制造業務制定20種主導產品質量提升計劃,實施“三輪八年”質量提升工程,部分產品質量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工程建設業務以“建管分開”為原則,以“業主+PMC+EPC”為主導,推進工程建設體制機制創新,各方責任主體的質量責任進一步明確,特別在管道、煉化項目建設中見到實效。工程技術業務持續優化技術工藝,將質量責任落實到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操作人員的崗位上,服務質量明顯提高。油品銷售業務不僅有針對性地控制采購、儲運、銷售各環節質量,還開展油品質量安全性研究,以快速識別復雜油源的質量異常,努力守好質量、計量紅線。礦區業務推行服務承諾等制度,以高質量服務來保障油氣主業發展。
第五,樹立標準先行的標準化發展理念,綜合提高發展效率和效益。正像國家《質量發展綱要》所提出的“質量強,標準必須強,建設質量強國,標準必須先行”一樣,我們逐步樹立標準先行的標準化發展理念,先確立標準,后開展業務,以科學配套的標準解決了業務發展的實際問題。勘探與生產業務推行長慶油田“標準化設計、模塊化建設、數字化管理”的做法,以“標準化設計”為核心,延伸到標準化采購、標準化預制,推廣一體化集成裝置,3年節約建設投資29.8億元,多產油104萬t、多產天然氣21億m3,長慶油田更是實現了油氣產量跨越式增長。天然氣與管道業務全面推進“標準化、模塊化、信息化”三化設計,114個重點項目應用三化設計成果,對提高設計質量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部分地區公司建設標準化站隊、打造標準化站場、統一標準化流程、規范標準化操作,提高了生產運行效率,確保了生產現場安全長周期運行。
3 質量工作面臨的新形勢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的曲折性艱巨性進一步凸顯,國際油價劇烈震蕩,地緣政治造成海外資源的不確定性增加,國內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下行壓力加大,石油石化市場需求減緩,宏觀形勢依然嚴峻,外部環境趨緊態勢短時期難以改變。不論是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企業轉變生產經營發展方式,走質量效益型的內涵式發展道路都是必然的選擇。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對提高生活質量訴求越來越強烈,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也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基。這都對我們質量工作提出了新任務和新挑戰。
3.1 國家對質量的約束性要求不斷增加
近幾年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質量工作,加強了對質量工作的引領,進一步明確了質量工作的發展目標和要求。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部署加強質量工作,強調要以優良的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為國家贏得尊嚴。2012年2月,國務院發布 《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以建設質量強國為主線,規劃了未來10年質量發展的宏偉藍圖,提出以質取勝,建設質量強國,并要求把標準、計量、合格評定作為現代質量基礎設施的三大支柱。在質量法制管理層面,國家已經發布《產品質量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成品油市場管理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強化了對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質量約束。在質量推進落實層面,國家質檢總局2012年正式設立了中國質量獎,并啟動了企業首席質量官制度試點;國務院國資委、工信部等部委部署了加強產品質量信譽、推進產品質量達標、推廣先進質量管理方法、加快品牌建設、開展管理提升活動等工作,要求工業企業提升質量、做優做強。在標準實施作用層面,2012年全國標準化工作會議提出,要以標準提振消費信心、提振企業信心、提振政府信心,把提升質量效益作為標準化發展的核心目標,從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3.2 社會對質量的關注程度進一步提高
在產品質量方面,三鹿奶粉、雙匯瘦肉精、染色饅頭、地溝油、塑化劑等問題頻發以來,近幾年全國兩會建議和提案中,加強食品質量監管、保障食品安全,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在工程質量方面,設計缺陷引發的溫州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以及樓脆脆、路塌塌等質量問題,其造成的后果觸目驚心,眾多媒體呼吁誰為百姓住行安危買單;在服務質量方面,2012年3·15晚會中國中央電視臺曝光了麥當勞、家樂福、中國電信等一批國際國內大品牌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虛假欺詐行為,再次倡導了樹立誠實守信的道德風尚。隨著一系列重大質量安全事故的發生,標準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部分領域標準缺失、標準過低、標準陳舊、標準內外不一常常引起人們的質疑,通過標準提升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訴求;同時,隨著消費保護意識的增強,消費者從自由市場的“公平秤”,到對信息不對稱的賣方計量,提出和采取了多種監督措施。這些現象告訴我們,短缺經濟下質次價高、缺斤短兩的行為,已經為社會所摒棄,誠實守信是買方市場對企業的基本要求。一個企業如果做不到誠實守信,就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也就無法履行社會責任,更談不上生存與發展。
3.3 企業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快質量提升
集團公司已經確立了建設一流的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的戰略目標,并且圍繞這個戰略目標要突出天然氣、海外和戰略性發展,打造綠色、國際、可持續的中石油;要實現經濟、政治和社會責任的有機統一,努力建設忠誠、放心、受尊重的中石油。隨著四個大慶、四大能源通道、五大海外油氣合作區建設,以及煉化布局與結構調整,集團公司整體產業布局、發展規模基本確定。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產出效益,就必須著力提升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以先進的標準促進減損耗、增收益,以先進的計量檢測促進信息化建設,進而夯實發展基礎、增強發展軟實力,實現集團公司科學發展上水平,更好地履行國有骨干企業的政治和經濟責任。2010年9月,集團公司簽署了《中國工業企業全球質量信譽承諾倡議書》,向全球消費者做出誠信經營、承擔產品全壽命周期的質量責任、提高質量水平的鄭重承諾;2012年8月29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又一次公開承諾,堅守質量誠信,擔當主體責任,保障消費安全,確保車用汽柴油產品質量。這也是集團公司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贏得社會尊重的質量宣言。另外,我們現在的質量管理水平與發展定位不相匹配,比國際大石油公司尚落后一個等級,只有將質量管理水平提升到與國際先進能源企業相媲美,我們的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才能得到國際認同。
4 “十二五”后3年質量工作安排
2012年7月份召開的集團公司領導干部會議提出,要加強科學管理,提高管控水平,促進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提升發展質量效益,進一步推動“十二五”規劃全面實施。按照集團公司的發展部署,今后幾年質量工作的總體思路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全面開展管理提升和深入實施基礎管理建設工程的進程中,落實國家《質量發展綱要》,踐行質量至上發展理念,堅持誠實守信、精益求精的質量方針,追求零事故、零缺陷,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質量目標,著力提升質量、計量和標準化業務能力,加快提升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為建設一流的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奠定發展基礎。
4.1 質量提升的主要目標
(1)總體發展目標:到“十二五”末,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管理水平整體達到優化級,質量管理體系建設完整有效,基本符合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的發展定位。到2020年,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管理水平全面達到優化級,部分企業達到卓越級,基本與國際大石油公司管理水平相當。
(2)產品質量目標:到 2015年,原油、天然氣、成品油質量優于國家標準;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化肥等化工產品40%以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并形成一批具有競爭力的化工專用料;裝備制造類產品質量國內領先,陸地鉆采裝備、油氣輸送管等主導產品質量達到國際一流;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抽查合格率穩定在99%以上,培育了20項知名品牌產品。
(3)工程質量目標:到2015年,工程建設項目質量全面達到國內領先,重點工程建設項目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工程質量監督覆蓋率達到100%,一、二類工程建設項目一次驗收合格率達到100%,其他工程一次驗收合格率達到99%以上,杜絕重大及以上工程質量事故。
(4)服務質量目標:到2015年,工程技術、銷售、檢維修及礦區服務質量達到國內領先,國外工程技術服務達到國際一流;培育5~10個服務示范區,用戶滿意度達到80%以上。
(5)計量檢測目標:到2015年,計控一體化覆蓋主要生產經營過程,企業測量管理體系有效運行,計量檢測保障能力顯著提高,油氣計量和檢定技術水平達到國內領先、國際一流。
(6)標準化目標:到2015年,基本形成統一、完整、先進、受國際同行認可的標準體系,擁有技術優勢領域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制定的主導權,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明顯提升,執行標準成為員工的自覺行為。
4.2 實現質量提升目標采取的措施
推進上述質量提升目標實現,需要做好以下重點工作:
(1)完善質量管理體系建設。按照集團公司質量管理體系建設方案,推進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運行,推進質量目標責任落實,不斷提高質量管理的規范性。一方面,建立和完善質量管理體系。應通過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的單位,盡快按照GB/T 19001質量管理體系標準進行第三方認證,確保2012年年底前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率達到100%;在體系建立和完善過程中,注重結合生產經營實際,推進體系文件與其他管理文件、管理要素的有機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要加強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結合近2年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工作,細化集團公司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實施細則,增強推進評審工作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探索建立質量管理體系推進評審的良性循環機制,打牢用體系思想抓質量管理的工作基礎。另一方面,逐級分解質量目標、落實質量責任。根據集團公司的質量方針和質量目標,進一步細化質量責任,嚴格過程質量管理,加強質量監督,加大責任追究力度,確保各級質量責任落實到位,開展質量隱患排查治理活動,切實杜絕質量事故的發生。建立質量指標體系,集團公司已經啟動了質量指標體系研究,擬于2013年年底前完成研究工作,之后,以這個質量指標體系為核心,開展質量工作量化考核,按年度對各地區公司質量管理情況進行量化打分,在同一業務板塊內按得分高低進行排序,促進地區公司之間查找差距,加強管理、提高水平。同時,開展質量評價體系的研究,力爭“十二五”末完成。
(2)強化對質量的監督檢查。受業務技能、工作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質量保證還要依靠監督檢查這個重要手段。在產品質量監督方面,首先是各地區公司要積極配合國家或省市組織的產品質量監督抽查,及時將有關抽查信息報送相關專業公司和集團公司,及時改進存在的問題和隱患,維護集團公司品牌形象。其次是集團公司采取定期和不定期2種方式,逐漸增加產品質量監督抽查頻次和覆蓋面,以便反映產品質量真實狀況,調整和采取相應質量提升措施。第三是專業公司要對國家和集團公司監督抽查中發現的不合格產品,認真調查分析、查找原因,督促地區公司制訂整改措施,防止同類問題再次發生,并舉一反三地組織做好質量改進工作。第四是集團公司將建立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結果共享數據庫,全面記錄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結果及不合格產品處理結果,定期公布采購物資質量監督抽查不合格黑名單。在工程質量監督方面,進一步理順監管體系,抓好工程質量監督隊伍建設,探索新思路,調整監督模式,提高監督效率和效能。監督工作要從以工程實體質量監督為主,向行為、實體監督并重轉變;從注重施工階段監督,向設計源頭到竣工驗收全過程監督轉變;從地區公司自我監督檢查,向交叉監督、跨地區互檢轉變。要做到綜合檢查與專項檢查相結合、總部檢查與日常監督相結合、告知性檢查與突擊檢查相結合。要充分發揮工程質量監督信息系統的作用,工程質量監督發現的問題及時在信息平臺上通報,工程質量監督情況定期發布統計分析報告,促進工程建設各相關單位持續提高質量水平。
(3)提升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在產品質量提升方面,煉油化工業務要按照國家油品質量升級要求,加快油品升級改造進程,同時加大高端化工產品技術攻關,加強質量管理與控制,確保產品質量長期穩定,提高名牌產品比例,不斷滿足社會對高品質石化產品的需求;裝備制造業務要以鉆井、采油、動力裝備和鋼管為重點,加快推動傳統優勢產品升級改造,提高裝備產品質量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增強油氣生產用技術裝備的保障能力。在工程質量提升方面,工程建設各方都要認真貫徹 《集團公司工程建設項目質量管理規定》,嚴格遵守基本建設程序,規范質量管理工作行為;建設單位作為工程項目質量管理的責任主體,要切實加強對各承包單位工作質量、資源投入、質量體系建立和運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堅決杜絕“以包代管”;各級工程質量管理部門要定期組織工程質量巡查,查處不良質量行為,減少工程質量隱患,督促各參建單位不斷提高質量意識,落實質量責任,持續提升工程質量。在服務質量提升方面,油品銷售企業要嚴守“三條紅線”,加強購運儲銷各環節數質量管理,嚴格控制采購油品的質量,強化客戶研究,豐富服務內容,提高用戶滿意度和忠誠度;工程技術業務要嚴格施工設計審批和施工過程的全過程監控,建立分層次的客戶回訪制度,根據專業特點做優做精技術服務,將服務質量作為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礦區業務要全面推行優質特色服務,健全完善一站式服務和各種便民服務措施,提高綜合服務保障水平。
(4)提高計量基礎保障能力。一是強化計量器具完善升級。制訂集團公司計量器具配備規范,明確各類業務計量器具配備原則和要求;地區公司要多渠道投入,重點解決計量器具缺配和生產急需問題,加快老舊計量設施升級改造,逐步提高計量器具技術性能,能源計量器具配備應全面達到國家強制標準要求。二是健全完善量值溯源體系。加快推進天然氣計量檢定站點、天然氣質量控制和能量計量中心建設,完善天然氣量值溯源體系,形成國際技術比對能力;統一管理原油、成品油計量標準量器,建設液態烴流量實驗室,完善液態烴量值溯源體系;開展高等級物探、測井計量校準裝置研制,合理設置石油專用螺紋量規區域標準規,規范管理石油專用計量規程,完善石油專用計量校準體系。三是深化油氣交接計量管理。認真實施集團公司 《油氣交接計量管理規定》,制訂實施油氣交接計量過程管理標準,進一步規范交接計量行為,減少爭議、提高效率。四是推進計量技術進步,跟蹤國際油氣計量技術發展,開展油氣計量關鍵技術研究,解決計量技術關鍵問題,提升計量技術水平;積極推廣在線檢測技術,提高生產自動化水平,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五是加強測量管理體系建設,重點企業要全部通過測量管理體系認證,按照測量管理體系開展計量活動。
(5)加快標準化管理的步伐。推行“標準先行、共性為主、源頭入手、執行有力、面向國際、注重實效”的標準化原則,增強全員標準化意識,努力實現以標準化減損耗、增收益。一是優化完善各級標準體系。緊密結合生產經營需求,學習借鑒國內外先進標準,明確各級標準的功能定位,加大標準整合力度,配合基礎管理規范平臺構建,完善統一、完整、先進、受尊重的集團公司標準體系,健全覆蓋生產經營全過程的地區公司標準體系;注重將科技成果轉化為技術標準,把標準化作為科研成果有形化的重要載體,優勢和新興業務領域要形成領先的技術標準。通過優化完善標準體系,解決標準交叉、矛盾等問題,發揮綜合標準化的整體優勢。二是強化標準的實施和轉化。堅持依據標準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總結推廣設計、建設和管理的標準化方法,提煉固化現場標準化管理經驗,對高風險領域作業標準實施加強監督檢查,對供應商的產品標準加強技術審查,促進全員懂標準化、會標準化、受益于標準化;完善標準信息化平臺,建立標準實施反饋機制,研究標準實施效果評價方法,逐步使執行標準的隱性成效更加顯性化,提升標準實施的有效性。三是健全標準化工作管理體系。完善標準化制度建設,進一步明確標準化工作職責,規范標準化工作程序,以標準化委員會來統籌協調標準化工作;加強國家、行業和企業標準化技術組織的協同運作,鞏固集團公司在技術優勢領域的標準化主導地位。四是推進國際標準化進程。加強國際標準研究與應用,切實制訂和提出具有國際水平的標準,做好符合國情和生產實際的雙語版標準制訂、“采標”轉化工作,引導具備扎實專業背景、掌握行業前沿動態并且熟悉標準化知識的高層次人才參與標準制修訂;積極推進標準國際互認,加強海外項目標準使用情況研究分析,輸出集團公司主導的先進標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滿足國際化經營需要;加大國際標準化工作的參與力度,承擔國際標準化組織秘書處、對口工作機構的單位,要履行好工作職責,配備好工作資源,做好國際標準化活動的組織參與工作。
(6)加強技術機構功能建設。質量、計量和標準化技術機構是確保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合格,工作過程質量受控,貿易交接計量公正,以及量值溯源一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和技術保障。集團公司對技術機構的總體要求是“專業化,高資質、高水平”,按照這個總要求,要突出抓好技術機構的優化整合和業務建設。在技術機構優化整合方面,各地區公司要借鑒蘭州石化等單位的做法,結合生產經營發展實際,將本單位的檢測和校準資源實行集中管理、統一使用,簡化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強化檢測校準對生產經營質量的保障作用。在技術機構業務建設方面,國家、行業和集團公司授權的各技術機構,必須認真履行授權職責,出具科學準確的數據,提高檢測校準的公信力,杜絕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違規行為,切實為企業和社會把好質量關;同時,按照《檢測和校準實驗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積極進行實驗室認可取證,開展國內外能力驗證和比對,提升檢測校準技術能力和水平。其他檢測校準機構也要依據相關實驗室管理標準,建立和運行實驗室管理體系,確保檢測校準結果準確可靠。各級標準化研究機構要緊密結合生產經營實際,積極開展標準化方法的研究推廣、國內外先進標準的跟蹤研究、重大技術標準研制等工作,促進企業提高標準實施效益。
(7)夯實基礎性管理工作。一是加強質量、計量和標準化業務培訓,根據各生產經營業務特點,對各級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從業人員開展形式多樣的業務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能力和水平;普及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專業知識,提高全員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工作技能;國家和集團公司有持證上崗要求的監督、監理、檢驗、計量等人員必須培訓合格后持證上崗,確保相關人員的基本業務素質符合崗位要求。二是加強質量、計量和標準化的宣傳交流,大力宣傳國家有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近期以宣貫國家《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為重點,不斷提高全員對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工作重要性認識;積極傳播交流質量、計量和標準化新經驗、好作法,使企業之間、單位之間的質量、計量和標準化工作相互促進、相互提高。三是深入開展群眾性質量活動,積極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知識考核,學習卓越績效管理模式,開展“用戶七滿意”活動,有針對性地開展質量管理小組活動,推進質量管理工具應用,提高質量分析和改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