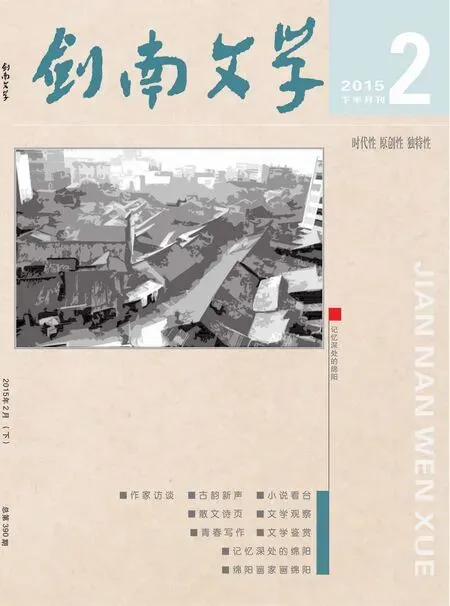讓·艾什諾茲:破碎時空的漫游者
■呂艷霞
法國小說家讓·艾什諾茲筆下出現了大量的漫游者,他們不受地理空間和時間的約束,在世界范圍漫游,用冷漠而犀利的眼睛觀察世界。他們是這個世界的剩余之物。在破碎的時空中,攫取著一個個同他們一樣孤獨的世界的碎片,試圖用碎片拼出一個他們歸屬的世界,來體驗確定的世界的“當下”的生活。
法國小說家讓·艾什諾茲 (Jean Echenoz,1947-)是當今法國最受評論家、讀者和學者欣賞和贊譽的作家之一。他作品頗豐,從1979年至今,已經在午夜出版社出版十六部作品,并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自1979年開始寫作以來,讓·艾什諾茲便以其獨特的小說風格在法國文壇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記。他對運動、對地點的關注,使任何一個第一次閱讀他的小說的讀者都印象深刻。他筆下出現了大量的漫游者,跟隨他們的腳步和目光,小說讀者在現代社會的碎片化空間與時間中游蕩歷險。
漫游的靈魂
漫游者,是法語“flneur”的翻譯,也有的翻譯成 “游蕩者”、“游手好閑者”、“浪蕩子”、“散步者”、“閑逛者”。這個意象最早來波德萊爾。波德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里描寫了這樣一類藝術家,他們是“富有想象力的孤獨者”,喜歡漫游、觀察,喜歡“生活在蕓蕓眾生之中,生活在反復無常、變動不居、短暫和永恒當中”。他們“離家外出,卻總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卻又為世界所不知”。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詳細論述了波德萊爾的觀點,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里專門辟出了一個章節,提出了“漫步者(游蕩者)”和“漫步(游蕩)意識”的概念,將漫步者的種種特征與巴黎、與拱廊街、更與波德萊爾的“都市抒情詩”聯系起來進行了論述。
讓·艾什諾茲筆下的許多人物都具有漫游者的特點:首先,他們都是孤獨的人。在艾什諾茲的筆下,我們找不到幸福的家庭、美滿的婚姻和甜蜜的親情,每個人都生活在孤獨當中。正如《格林威治子午線》中的主人公西奧·塞爾默那樣:“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街上度過的,只在晚上睡覺時才回到旅館,而且一大早就離開了那里。像在紐約的時候一樣,他參觀博物館,去看電影,總是獨來獨往。他是一個完全孤獨的人。人們偶爾會碰到這種人的。”
除了孤獨,他們的共同點是彷徨若失,沒有生活方向,沒有目的。現實中單調貧乏的生活無法讓他們滿足,他們天性厭倦平靜的生活,只要有一絲絲出發、移動的借口,便會馬上付諸行動。西奧本是聯合國的譯員,在紐約生活平靜,可是他卻對這種生活感到茫然和厭倦,但他突然停頓下來,停止了翻譯和工作,辭了職,開始去游蕩。他“被一種難以解脫的情緒所左右,簡直不能夠在同一個城市待半個月以上”。當他最終被卡里耶抓住把柄,雇用他作殺手時,他也并沒有特別的反應,只是領會到他因此而要去旅行,就可以了。而另一個人物薇拉,夏天去清真寺,冬天去東正教堂,只為了在走出教堂的數小時之后真切地感受到空虛。她不知往何處去,就是不想回家,而一旦收到了一個未經任何證實的出發信息,她就立刻啟程上路了。
然而,他們為什么要漫游?在書中,找不出答案,沒有人能確切解釋清楚,有時就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游歷目的,更在于游歷本身。就像《格林威治子午線》中拉謝爾說要去北極,西奧問“為什么呢”,拉謝爾只回答“為了游歷”。游歷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漫游者活著的動力。他們的生活,就是漫游。
盧卡奇在《小說理論》里指出,希臘的史詩世界是一個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在那沒有生活的艱辛、心靈的孤獨、精神的裂變,人在那“既不知道自己會迷失自我,也從未想過要去尋找自我”;而人一旦走出幸福的、令人愉快的史詩世界,進入現代的小說時代,就進入了“先驗的無家狀態”。正是這種“無家”的狀態讓人不停地漂泊,不停地流亡。彼得·伯格則在其名著《漂泊的心靈——現代化過程中的意識變遷》中指出:“受現代化影響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開始對他們的生活意義及社會規范產生懷疑及不確定的感覺,感到自己無根,沒有歸宿。簡單地說,現代化帶來的是一群漂泊的心靈、失落的個人。”
正是“無家”、“無根”,導致了讓·艾什諾茲筆下人物的“漫游”。不過,這種漫游與傳統意義上的流亡、流浪不同。流亡是古典文學的視角,流亡的人走出家門,在世界上孤獨地漂泊,充滿失落、傷感與無奈,他們仍然想念著以前的家園,懷念自己曾經歸屬的美好世界。他們不喜歡呆在人群中,只要一有機會就會離群索居,回到自己的心靈故鄉。所以他們對當下的世界是排斥的,是沒有好感、甚至不感興趣的,他們始終拒絕融入當下的世界。
而漫游不同,漫游者雖然也沒有歸宿,沒有目標,雖然他們也孤獨,可是他們仍然喜歡觀察人群,就像波德萊爾說的:“任何一個在群眾中感到厭煩的人,都是一個傻瓜!一個傻瓜!我蔑視他!”“波德萊爾喜歡孤獨,但他喜歡的是稠人廣座中的孤獨。”讓·艾什諾茲筆下的人物都很孤獨,可是他們仍然喜歡觀察世界,觀察人群:《我走了》中的費雷獨自一人坐在街頭咖啡館的露天座里,看著大街上來來往往的女人;另一個人物,本加特內爾即便在化裝改名之后仍然饒有興致地觀察著世界。漫游者對當下的生活并不排斥,甚至帶有極大的興趣和好奇心,即便是碰上了拉雪茲神父公墓,他們也會好奇地進去看看:“我們進去吧:……完全沒有別的東西可看;我們出去吧。”這些漫游者總是試圖在當下的世界之中尋找美的碎片,而并不是試圖去尋找過往時代的“根”。他們與世界的關系,正如研究者所總結的那樣:“他們既在大眾中間,又獨立于大眾之外”。就像本加特內爾 “只是在遠遠地瞧著世界。如果說他在觀察著人們,他卻離群索居,跟誰都不打招呼”。他們藏身人群,在人世漫步,用冷漠而犀利的眼睛觀看,用耳朵聆聽,只是很少交談。他們與世界的關系既遠又近:既屬于這個世界,又不屬于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的剩余之物。他們從沒想過要從當下的世界退出,回到原初的世界,這也許是漫游者與流亡者最大的不同。
讓·艾什諾茲式漫游者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都不受地理空間和時間的約束,他們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跑動,不停地在世界上游蕩。《格林威治子午線》每一章的情節都發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出征馬來亞》中,人物從法國飛到了馬來亞;《我走了》里的主人公費雷甚至跑到北極去探險;在《格林威治子午線》的最后一章的寥寥幾頁里,我們就跟著小說中的人物西奧從太平洋中央 “與寧波和尤里卡的距離相等”的地方到達廣州,穿越中國海和日本海,經過北海道島、庫頁島,看見阿留申群島的陸地,向著北極進發。小說人物就這樣被讓·艾什諾茲驅趕著,從地球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不停地游蕩著,履行著他們自己或清楚或不清楚的使命。
破碎的時空
在讓·艾什諾茲式漫游者看來,時間和地理空間的限制都是要被突破的,他們看到的都不再是完整的世界,而是時空的碎片。
英國的吉登斯在研究現代性的后果時提到,在現代社會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時空重新分割重組了。他認為,在農業社會中,歷書、沙漏、觀象學為人提供了粗略的時序,那時候時空是彼此互相關聯的。就是說,傳統時間總與地理標志相關。比如太陽下山、牛羊回家,就是要做晚飯的時候了。而鐘表則意味著現代時空的出現,它分割時空,把時間從空間中剝離出來,變成有序的格柵。只有遵守嚴密的時間表,人們才能工作生活。時空這樣重組的后果是:距離感淡化,空間成了幻想,人們無論何時都感受到時間的驅迫。而美國的大衛·哈維則提出了“時空壓縮”的概念,試圖表明:“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障礙,以致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我們崩潰了。”
無論是吉登斯的時空重組,還是大衛·哈維的時空壓縮,都試圖表達人們在現代社會中在時間和空間的感受和表達方面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和焦慮。而讓·艾什諾茲則通過小說創作在這一方面有著更深刻的體會。
從第一部小說《格林威治子午線》,他就試圖表達對已經嬗變的時空的焦慮。他選取了格林威治子午線經過的一小塊陸地、一個小島來切入。這條線是日期變更線,它是人們企圖“將時間留在一個球面上”而隨意設立的一條分割線,將大地和時間分開,分割日期,分割了今天和明天,也分割了世界。他借書中人物之口,認為“人們從來沒有將時間與空間協調好,從來沒有將它們組合為一個整體”(第213頁)。而在那條線經過的小島上,人們“生活在一個一天與次日相距幾厘米的國度里”,“同時迷失于時空之中,實在難以忍受。”(第5頁)通過格林威治子午線這個奇異構思,讓·艾什諾茲一下子就提出了他在時空上的焦慮。因為時空不再像以前一樣相互關聯,人們再也無法根據空間來判斷時間:隔著一條日期分界線的界碑,僅僅前進幾厘米,人們就跨進了“明天”,后退一步,就回到了“昨天”;時空被壓縮,人們曾經需要花費時間去跨越的空間障礙一下子消散了,人們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在固定的空間過著確定的“現在”的生活。那怎樣才能抓住現在的生活?就是盡可能地占有更多的空間,馴服更多的空間,用對空間的占有來體驗“當下”的時間。這也許是讓·艾什諾茲筆下的人物不停地跨越地理障礙,在空間探索的一個原因。
然而,無論怎樣努力,想要得到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巴爾扎克 “人間喜劇”式的宏觀圖照,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再可能,因為以前遙遠的東西不再遙遠,曾經堅固的東西也已經煙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一個個時空的碎片,作家、藝術家所能做的,就是攫取這一個個碎片,在碎片中反照出當代的生活了。在讓·艾什諾茲的作品中,就充滿了這一個個時空的碎片,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城市中的時空碎片。
讓·艾什諾茲在作品中喜歡描寫城市,尤其喜歡巴黎。正如他在《熱羅姆·蘭東》里提到的那樣:他“對巴黎相當了解”,會和午夜出版社的社長蘭東談論“巴黎的街角”,會在一個人很少去的地方 “發現一幢非常奇怪的房子”。盡管他的小說中地理疆域跨越世界各地,可是他念茲在茲的仍然是巴黎。不過他筆下的巴黎城,不是第二帝國奧斯曼男爵規劃下的嚴密、協調、井井有條的城市,因為無論多么規整有條理的地方,他注意到的也是其中的不規則的游離于整體外的細節碎片:少女貞德的雕像 “在灰色的空氣中卻呈現出灰暗的黃色”,協和廣場上“散布著一些風格不相協調的建筑”,蘇伊士街上“那些垂頭喪氣的舊樓房的大多數門窗都被碎石封死”,愛克塞爾曼林蔭大道上“1910年的式樣與1970年的風尚比肩而立”,十六區夏爾東-拉伽什街的某些角落 “顯現出一副核戰爭之后的頹敗景象”,炎熱夏季的巴黎城中“到處都在挖路維修”……這樣的巴黎,怎么也和拿破侖三世時期奧斯曼男爵苦心打造的宏偉壯觀的世界博覽之都對不上號。
讓·艾什諾茲中意的也不是本雅明在《波德萊爾: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提到的漫步者喜歡的商業街區建筑——巴黎的拱廊街。在拱廊街時代,那些漫步者在有著玻璃房頂和大理石地面的拱廊中悠閑漫步,既有遮風擋雨的頂棚又有琳瑯滿目的店鋪,他們有著足夠的空間和時間慢慢地觀賞與沉思。可是到了當代社會,波德萊爾式的漫步者喜歡的嚴密網狀結構的拱廊街已經被一個個大商場、購物中心所穿破,擁擠而喧囂,完全是商品的迷宮。漫步者已經在這找不到可以讓他悠閑漫步的時間和空間。這也就是為什么讓·艾什諾茲筆下的漫游者更喜歡的是巴黎的郊區、高速公路、環形大道這些城市中的邊邊角角:高速公路邊的工廠、空無一人的村莊、孤立的別墅、要被拆除的樓房,郊區商業中心和倉庫、貨棧、工廠……這些地方并不乏美感,有的甚至非常動人,比如陽光照亮了高速公路側邊“一座鮮艷藍屋頂的工廠,而且這種顏色還在陰暗之中閃耀了片刻;那些在陽光中向高處升騰的煙囪的白煙,在同一時刻變得像白雪和泡沫一般生動而耐看”(第118頁)。這樣的地方也不僅僅只是巴黎的特產,郊區、高速公路在世界哪個地方都存在,它們幾乎具有同質性,處在這樣的地方,沒有文字說明,人們根本分不清具體的時空。可是它們都是一些空間的碎片,處在城市的邊緣,蛀蝕了城市的組織規劃,各種風格雜糅在一起,是看似嚴密規整的城市中的不協調、不規范的時空碎片,夾雜在一片空洞和虛無當中,紛紜在世界中。它們就像漫步在其中的人物一樣,孤立著,零散地存在著。
這些時空的碎片沒有完整性和有機性,可是漫游者卻仍然希望從這些碎片中得出世界的完整圖景,讓·艾什諾茲通過人物對拼板游戲的喜愛來闡釋這一點:“拼板游戲的每個片段部分,它是不定形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每個拼板的形象本身,而是最終的形象,重組的拼板形象。”而漫游者正是在這樣破碎的時空中,攫取著一個個同他們一樣孤獨的世界的碎片,試圖用碎片拼出一個他們歸屬的世界,來體驗確定的世界的“當下”的生活。這正是讓·艾什諾茲小說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