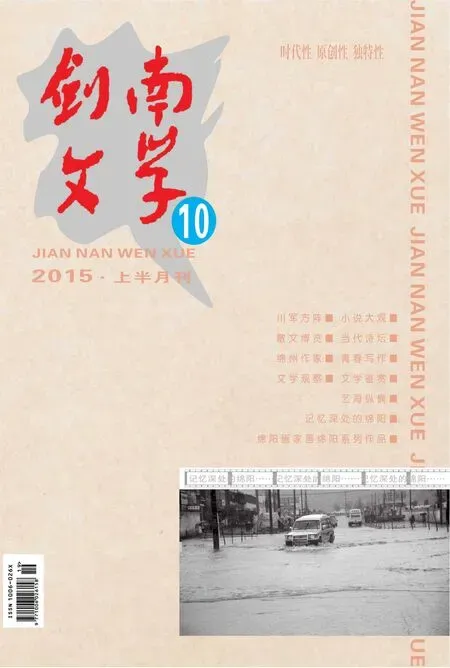20 世紀英國動物書寫詩歌生態倫理觀發展脈絡
■姜慧玲
本文以20 世紀英國動物書寫詩歌中生態倫理觀的研究為主題,選取20 世紀英國代表動物書寫詩人托馬斯·哈代、D.H.勞倫斯、菲利普·拉金和泰德·休斯的代表動物書寫詩作進行系統研究,分析其動物書寫詩歌中生態倫理觀發展脈絡的共同特征:從對動物的同情,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再到對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的向往,包容了生態文學思想的全部內涵。
1.引言
縱觀20 世紀的英國詩歌,從世紀初的托馬斯·哈代、到二三十年代的D.H.勞倫斯、到五十年代的菲利普·拉金,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泰德·休斯等代表詩人,或通過對動物的憐愛與同情,或通過對人類殘害動物等破壞自然活動的譴責,或通過對人與動物平等關系的謳歌,或通過對動物原始力與美的頌揚,以樸實的筆調描寫了人類與動物的共生關系,生動地表現了對動物的熱愛和強烈的生態倫理思想,賦予人與動物的關系以真正的道德意義和價值,使20 世紀英國動物詩歌在思想和藝術上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元。研究20世紀英國動物書寫詩歌,目的在于揭露資本主義工業化和科技文明的高度發達給自然環境和動物造成的負面影響,并分析出這些詩歌中所蘊藏的生態意識和道德關懷,從而對廣大讀者有深刻的警示和借鑒作用。
2.托馬斯·哈代動物詩歌中的生態倫理觀萌芽
作為詩人的托馬斯·哈代開拓了20 世紀的英國文學。長期的鄉村生活使他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感覺細膩敏銳,他善于從自然萬物中攫取人們熟悉的事物作為詩歌意象,并運用令人瞠目結舌的生動性將其描述出來。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哈代有巨大的影響,他這樣論述達爾文進化論的意義:“確立物種共同起源的學說的最深遠的影響是在道德領域……把所謂‘金規律’從只適用于人類調整到整個動物王國”(Florence,1962:349)。哈代的生態整體觀在其動物詩歌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如《關在鳥籠的金絲雀》、《捕鳥人之子》、《被刺瞎雙眼的鳥》和《一包包的肉》等從罹難的動物身上看到人類的無情,從而表達了保護動物的生態意識。
3.D.H.勞倫斯動物詩歌中的“眾生平等”
工業化的步伐擾亂了哈代筆下 “牧歌式的田園”, 煤炭的使用使得倫敦上空霧氣籠罩,森林被砍伐,田野被鏟除,隆隆的火車和機器的馬達聲破壞了鄉村的寧靜,英國變成了彌爾頓筆下的“失樂園”,不再是動物理想的棲息之所,動物的命運危在旦夕。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勞倫斯開始了他的動物詩歌創作,倡導“眾生平等”,歌頌野生動物的自由生活狀態,否認人類的中心主義地位,這正是勞倫斯為尋求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和諧生態關系所做出的努力。
在1920-1923 年之間,勞倫斯創作了大量的動物詩,堪稱動物詩歌的巔峰之作。如在《人與蝙蝠》一詩中,詩人認識到人與蝙蝠一樣有著無法逾越的障礙,對蝙蝠的態度由最初的惡心和厭憎轉向理解和同情;在《蚊子》一詩中,詩人并沒有因為蚊子被打殺而產生某種快意,而是對蚊子“消逝進一坨暗黑色的污跡”表示遺憾和同情;在《蛇》詩中,詩人給我們描繪了一副人獸相遇相知的圖景,詩中洋溢著對蛇的敬畏、尊重甚至崇拜。勞倫斯對“低等”“有害”以及“邪惡”動物的肯定和認同是對物種歧視十分有利的反駁,這無疑對當代生態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4.菲利普·拉金詩歌中“罹難的動物”
到了菲利普·拉金所生活的20 世紀中葉的英國,城市化和大工廠的建立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十分敏感。和勞倫斯擅長寫野生動物不同的是,拉金筆下的動物多是被人馴化的馬、牛和羊。如《在草地》一詩講述了馬的不公平境遇,當馬老得不能再在賽場上馳騁的時候,還是要被套上籠頭在農場干重活,借以批評人類自私地虐待動物、剝奪馬的天性;又如《初見》、《買一只回家給孩子們》都批評了人類對動物的虐待,表達了詩人“生態平等”的生態倫理觀。
拉金更深層次的生態觀表現在對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畫面的描繪。拉金喜愛動物,他的房東太太曾描述24 歲的拉金與貓的親切互動,拉金鉛筆手稿的頁邊空白都是手繪的老鼠、兔子、羊和貓頭鷹。拉金的動物書寫詩歌展現出自勞倫斯之后無人能及的技藝、感覺與移情,如在《鴿子》一詩中,詩人將一群沐浴著和風細雨的鴿子描繪得情趣盎然:“一群鴿子在薄薄的石板上挪動著/迎著西風細雨/風掠過它們縮著的腦袋和收緊的羽毛/蜷縮成溫暖愜意的一團”;在《春天》一詩中,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畫面成了一道最美的風景,詩人對鳥兒、狗兒的動態特寫更能顯示出公園春光中一片寧靜祥和的氣氛,詩中表達了人與動物以及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令人心向往之。
5.泰德·休斯動物書寫詩歌中的 “力”與“美”
在20 世紀60 年代后,泰德·休斯憑借詩集《雨中鷹》一鳴驚人,開始了他在生態危機時代為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在詩學上的不懈追求與探索,每一首詩無不融入他對動物和自然的生態關懷。與拉金筆下被馴化的動物不同的是,休斯的動物書寫詩歌中展現出的是一個“充滿野性和力的世界”。休斯的動物詩以遒勁粗獷著稱,其中少不了對動物細致入微的觀察與生動準確的刻畫,如在《鬼怪螃蟹》中,詩人描寫了一個狂暴躁動的世界:“它們互相追逐,互相糾纏,/互相騎壓,要把對方撕成碎片”。休斯在他的動物書寫詩歌中似乎與動物融為一體,因此他詩中的每一個動物都是以自我而存在的生命,是一個獨立的宇宙。又如在《棲息的鷹》中,詩人用鷹的口吻這樣寫道:“我高踞大樹之巔,緊閉雙眼。/……/是整個宇宙/創造了我的腳,我的每一根羽毛/現在我卻把整個宇宙用腳抓牢/或飛上天去,在空中徐徐地旋轉/我隨心所遇地捕殺,因為萬物屬我”,可見動物的本能與沖動被書寫得淋漓盡致。
而在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后的詩歌創作中,休斯吸取了大量道家思想的精髓,如在詩集《摩爾鎮》中,通過主人公杰克對牛羊的悉心照顧,詩人表達了人類不再對動物專橫跋扈,彌漫著的是人類對動物的關愛尊重;在詩集《河流》中,休斯為我們展示了一副“天人合一”的理想畫卷:老漁夫心系鮭魚的命運而放下漁網,并追逐其蹤跡,在最后一首詩《鮭魚產卵》中,老漁夫沉醉于自然美景,一片溫暖祥和的景象躍然紙上。
6.結語
綜上,將生態倫理批評和文本細讀的文學批評理論相結合,分析20 世紀英國代表動物詩人托馬斯·哈代、D.H.勞倫斯、菲利普·拉金和泰德·休斯的動物詩歌,可見20 世紀英國動物詩歌的發展脈絡:從對罹難的動物的同情,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到人與動物平等理念的尋求,再到對野生動物“力”與“美”的向往,從而不難歸納總結出20 世紀英國動物詩歌“生態倫理觀”的共同特征。同時,通過對處于相近時代的哈代與勞倫斯、拉金與休斯動物詩歌的橫向平行比較研究,以及對創作風格相近的哈代與拉金、勞倫斯與休斯的縱向影響研究,比較其生態倫理觀的差異并挖掘其背后的根源:動物詩歌的創作既與生態危機的時代社會背景有關,又來源于詩人的成長和生活經歷,因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經驗主義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