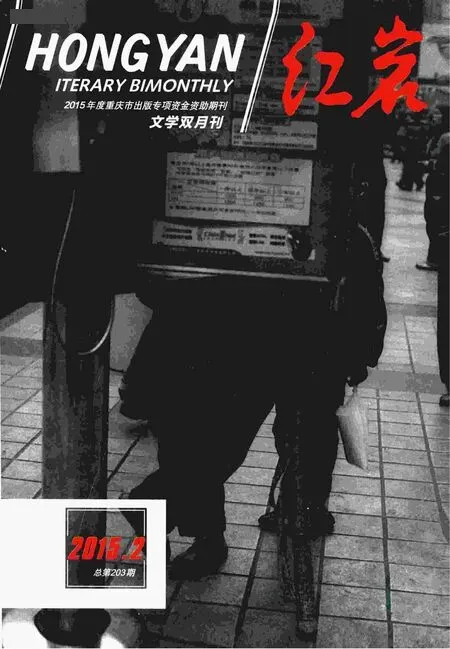讀菲可,回憶第三代
2015-11-17 21:32:27唐云
紅巖
2015年2期
唐云
這么數(shù)著日子過來,猛嚇一跳!30多年歲月流水般逝去,是不是該回憶一下了?
很難說個人回憶與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一致的,正如歷史如果沒有了個人回憶就是殘缺的一樣。
時至今日,“第三代”這個專用名詞已經(jīng)不大被非詩人們知曉了。這個時候突然讀到菲可的詩,真是別有一番滋味!
一
10年前,我在精典書店發(fā)現(xiàn)了李亞偉《豪豬的詩篇》,記憶中這是這批詩人中很少見的一本正規(guī)出版的詩集,粉紅色封面在那立著,不像打鐵匠和大腳農(nóng)婦的范兒,也就是說這個設(shè)計走的是與莽漢相反的路子,和我一起到書店的是朱智勇,就是當年大學時期在李亞偉隔壁編《彩虹》雜志的那個半詩人半思想家。那時在南充師院,很有一堆莽漢……1985年,詩人阿野給我看了兩集《非非》,之前,周倫佑或者周倫佐到學校演講了一番。也是在那一年,我在四川青年詩人協(xié)會成立的大會上,聽見一個叫劉東的女詩人在臺子上朗誦,而后臺,從北京趕來祝賀的北島正在被一群年輕人圍觀,那時候,還沒有粉絲一說。1988年,一本叫做《第三代詩人探索詩選》的書正式出版,主編是溪萍。若干年后讀到了楊黎寫的《燦爛》,看見這個題目,想起劉太亨曾經(jīng)開玩笑說的:老子要寫兩個情人,一個叫燦一個叫爛……
上世紀末,盤峰論劍很是熱鬧了一番,這大約算是第三代們在多年以后弄出的一點聲音,整整一個90年代,幾乎集體沉默的第三代,終于總體爆發(fā),“民間立場”或者“知識分子寫作”這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