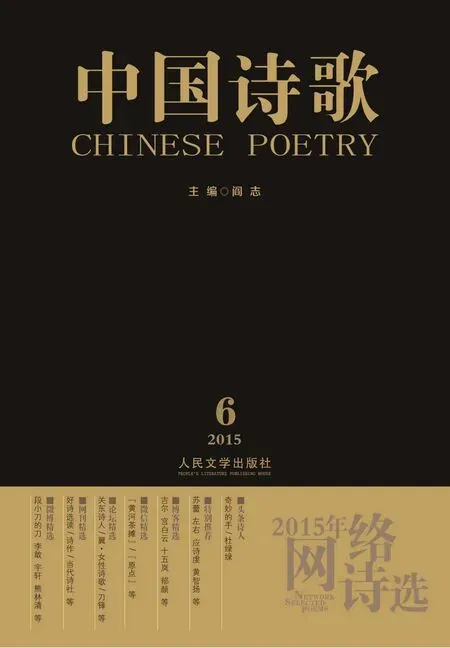黃智揚的詩
黃智揚的詩
HUANG ZHI YANG
寫作的囚徒
用湖水能否在玻璃上寫下詞語
寫下失去,失去的正存在著
寫下醒來,醒來就需要不停地寫
寫下佛家的空,空本不需要出現
寫下道家的逍遙,逍遙勢必掉頭而走
寫下儒家的仁,仁是透明的,“虛偽”作證
寫下法,湖水過于放松
寫下理,玻璃不夠堅硬
寫下自己、他人、樹、月亮、霧霾
玻璃出現裂痕,手指越磨越短
還能寫些什么,才能不讓自己消失
梵文、希伯來文、德語
語言在翻譯中死掉
選擇不寫?
但玻璃背后有人
二分之一的人在與你對抗
背靠不同的湖水
朝同一塊玻璃開槍
傷口重合的概率約等于
雪白的麻雀飛過頭頂
寫下的越多,玻璃越小
拖拉機捕魚
——贈新浪潮三班詩友
洱海邊,拖拉機參與到捕魚行動中來
中午,我曾見過一條北京來的魚
環湖公路上奔跑著一輛小巴車
豐收的“漁船”載滿了全國各地的魚
睡覺時,他們一動不動
對自己的作息充滿自信
(每一張網的縫隙都略大于他們的身軀)
成群結隊并不能帶來一種安全感
但他們愿意這樣
團結得像水中的蒲扇
對接下來游去哪并不確定
繁星
此刻我站在繁星下想你
一架飛機剛剛飛過
水龍頭滴水的聲音隱約可聞
這是村莊里的絕對寂靜
我對著寂靜說話
滅掉了最后一點光
仿佛你在對面
黑暗中我伸出手臂
辨認應該把哪一顆星送給你
我們常常看到的獵戶座今天沒有出現
腰帶被解開,獵人在沉睡
天空中到處都是勺子
我舉起手機
固執地拍下了一片空無
這空無中藏著一顆星
低下頭,有大片的樹葉
在寒冷中互相擁抱
山的輪廓在遠方清晰可見
它的存在并沒有星星作證
絕句
群山蒼翠,南京的雨下到了北京
站在兩旁的樹悄悄坐下
身著襯衫的人都開始喝起酒來
在某個瞬間,椅子們改變了固有的位置
點煙時,幾只飛鳥來來去去
曾經討厭的流行音樂
因四周過于空曠
而不小心成為葉子綠起來的理由
他
他獨自坐在空空的書桌前,剖開夜晚
他不能看到你,更不能借別人的眼
來穿越你
八月,他無助地站在一座山丘上
只不過剛剛爬上來,就已經想下去
此時,他正在讀著一卷舊詩
“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
然而他腦子里想的,卻是另外一句
在朝北的房間,他還看到了一場雪
不合時宜。正如他這兩年耐心挑選的
一根針。應該把它扎在哪?
你注意到了,他的嘴里
有著無數的縫隙。
黑鳥
城市里沒有黑色的鳥
當它飛躍橋梁
墨水散開
今天下午,我和母親坐車回鄉下
這只黑鳥出現了兩次
我們討論,它是否昭示著什么?
解讀完全不同
“不是祥兆,你回北京后要事事小心
不能再這樣熬夜了”
這令我哭笑不得
母親具備一種奇怪的能力
任何事情在她口中
都能在高速沖刺中突然轉彎
直接扎進我的身體
慢
她的車讓我變慢
天上的光落得慢了
高架橋的倒塌也慢了
喉嚨里的水以及身體里的水分子慢了
冬天,慢了就會變成冰
冰永遠不會變成風的形狀
冰的沉默,不會再慢了
它停留成無聲的空間任人敲打
地鐵速寫
他可能是個作曲家
晚上,戴著墨鏡坐在地鐵十號線上
我的旁邊,這個白頭發的老頭
像一只蜜蜂
重復的音調從他嘴里哼出
這令我厭煩
令我想到
鉛筆劃過干燥的紙張
我確信
他是在作曲
可我被蜇了一口
手中的書掉了
他的嘴里沒有刺
到底是什么扎疼我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跟著旋律,我滑到地面
水的分子不斷靠近
我差點變成冰塊
直到他起身下車
消失在北土城站
魚的聲音
你可曾聽到過魚的聲音
在玻璃后面,剔除了水管的聲音
呼吸的聲音
秒針的聲音
只剩魚在交談,氣泡浮出水面并沒有消失
它們代替那些被我們囚養一生的魚
出去看看
你可能聽到過魚的聲音
那聲音柔軟,發涼,每次都不一樣
它們指向我
好像我是囚徒的同時
也是罪犯
你真的聽到了?
不是油鍋里噼里啪啦的那種
而是——
呼和 唉
鳥鳴
驚訝于窗外的鳥鳴
鳥,來自煙囪
為了抖落身上的灰
撞擊墻壁
一些石頭比另一些石頭脆弱
鳥來自這種石頭
字典里的親密愛人
被不同的手相隔萬里
物理運動
有時會觸及神經
從耳朵進入大腦皮層
的石灰巖,落地時
如冰凍的雪花被肢解
天空的手掌突然閉合
有粉末掉下來
滿地都是玻璃
摩斯密碼在光的羽毛中
撒謊
臺階
臺階之上是什么
睡意昏沉的你,破爛的廚房
鴿子,棲息在窗邊
玻璃,被風敲碎
這些統稱為家的事物
充滿了愛意
我剛剛踏過的這些臺階
和樓上的有什么區別
每跨一步,身體解散地愉快
當我進入那狹窄的
最狹窄的空間
所有的臺階都被抹平
房間里跑步的人
提到房間,你以為它是狹窄的:
白色的墻壁,暖色的地板,一群匆匆忙忙的螞蟻
耳機自動播放著流行音樂
每個人都是來自“美國”的天使。
鏡子產自中國。
湖面一樣的光閃爍,
同事們隱隱約約的眼神像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