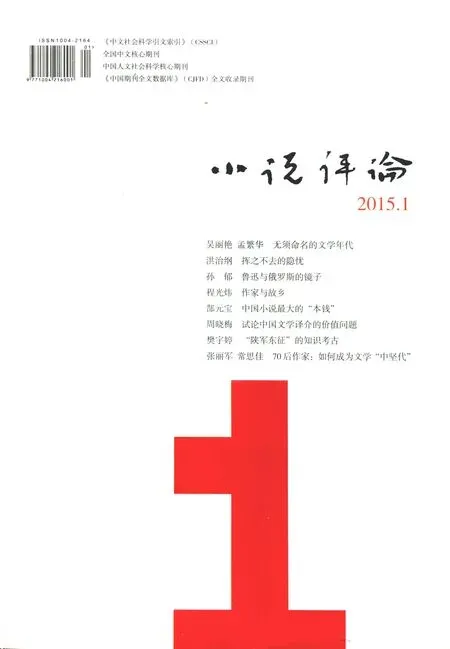當代廣西小說的一個話題:文學的傳統
鄭立峰
當代廣西小說的一個話題:文學的傳統
鄭立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西小說(也稱“桂軍”)在中國當代文壇“突然”“崛起”,特別是以“三劍客”為代表的作品迅速進入文學主流的視野。90年代廣西小說現象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無法繞開的焦點。曹文軒說:“在商品經濟大潮不斷侵蝕、威脅文學的上世紀90年代,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異軍突起,舉起了廣西文學新軍的大旗,帶著他們的巫氣水氣為中國九十年代的文學風景增添了令人難以忘懷的旖旎”;陳曉明說:“不管怎么說,這三個作家同出于廣西,他們風格其實大相徑庭。但他們的存在給當代文壇輸入了活力,他們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在當代中國文學最薄弱的那些環節起到支撐的作用。”“廣西人天生具有激進的革命素質”,“他們的寫作萎靡困頓的文壇造成有力的沖擊”,“他們的寫作顯示了當代小說久違的那種直面現實的勇氣,一種毫不留情揭示生活痛楚的筆力,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其評論界的話語背后所指的是廣西獨特的地域文化、世俗的現實主義、革命性先鋒意識,等等。那么,以廣西三劍客為代表的小說,其創作傳統源生何處?這是我們亟待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
在中國文學史的視野中,當代廣西文學是以少數民族文學進入文學史的。40年代的延安文學傳統影響下的中國當代文學,以“民族”的眼光來接納和規訓全國的文藝創作,特別是毛澤東在1942年“推陳出新”戲劇改革政策和1956年“雙百方針”的推行,具有“民族性”寬泛藝術性的文藝進入“主流”文學史敘述的范圍,這為文學敘述打開一個“全民” 述史的場域。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建構者身份被正式納入敘述中,當代廣西文學“乘勢”被接入了當代中國文學史視野。廣西文學是以少數民族文學的身份進入文學史的,在長期以來很多學者和述史家將此看法當作是合理闡述的常態,而且簡單化的認為廣西文學就是少數民族文學。這一個問題,值得商榷。
在“建國初期”廣西文學的確是將“民族”作為文學的敘述對象。韋其麟的《百鳥衣》,陸地的《美麗的南方》,包玉堂的《歌唱我的民族》、《為社會主義歌唱》,秦似的雜文《在崗位上》、《為幼小者而戰斗》,周民震的《花中之花》等等都是在“延安文學”傳統的影響下產生的“階級斗爭”模式的文學樣式。韋其麟的《百鳥衣》中將“壯族”小伙子古卡作為英雄形象來刻畫,把壯族的民間傳說:“集一百只鳥的羽毛,制成的一件羽衣”可以飛越高山峻嶺,飛越土司建造的牢房,
“美麗的公雞”是善良美麗的仙女依娌為感恩而變的,那是為感恩古卡的救命之恩,依娌甘做民間的貧窮人家的妻子,還有“好人終升入天堂”美麗的傳說等等,這個長詩敘事,有故事性。把土司、狗腿子置于敵對的階級,古卡、依娌、古卡娘視為善良勤勞英勇的貧農階級。古卡為了營救依娌,歷經千辛萬苦的磨難,怒殺土司。這是典型的“階級斗爭”的文學。從魯藝歸來的陸地,他于1960出版單行本《美麗的南方》,被學術界贊譽,他們認為這“是一部以廣西壯族人民土改斗爭為題材比較好的作品”,“美麗的南方,美麗的人”、“真實的人物形象”:很多文學評論者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包玉堂的《歌唱我的民族》將么佬族的社會變遷,么佬族人民對新生活的渴望與勇于追求的心愿用民歌的形式來表達;還有他的《我握著毛主席的手》獲得少數民族文學的獎譽,“這標志著仫佬族農民之子的詩,贏得了全國詩界的認可,仫佬族文學史當代作家文學的可紀念一頁,由此揭開。”此外,還有苗亞延秀的《紅色的布色》,《共產黨又要來了》,莎紅的瑤族民間長詩《密洛陀》,黃青的《紅河之歌》,《歡樂頌》,劉玉峰的《山村復仇記》,秦兆陽的《在田野上,前進》,李英敏的《南島風云》,黃飛卿的《五伯娘和兒媳》等到老舍的贊揚連續創作出了《愛子之心》、《金花與金水》、《牧場新手》等等小說,都是解放區文學影子文學。從創作上看這些作品是屬于“革命歷史戰爭”題材的小說,或者稱為“鄉土革命歷史小說”,這些圍繞革命與戰爭、階級與進步為核心的敘事,總體呈現出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形態的樣式,以歌頌新鮮的事物和人物為主調,在宏觀視野中試圖建構一種“史詩”的結構,關注社會重大的問題或者關注現實農村是他們共同的追求。“革命與鄉土”的話語是一種文學敘事的傳統,他們往往將革命的政治的話語有意無意依附在敘事中,悲壯、英勇、犧牲“紅色”感情的渲染成為習慣,這是一種慣性的傳統,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文學史的傳統。
然而,在廣西文學的演變進程中,我們看到另一個文學創作的脈源,那就是文學自律的“先鋒”傳統。這個現象在改革開放后的文學“新時期”和“商業化”時期,廣西文學似乎有一種“敢為世人先”的勇氣。值得我們重提的一個重要的廣西文學現象是關于“百越境界”文學討論。廣西作家,楊克、梅帥之在1982年3月《廣西文學》就廣西的文化“百越境界”文學開始了探討,他們聲稱:“當我們把目光投向荒莽險峻的大山,云遮霧掩的山寨,當我們沿著歷史的遺跡,追蹤巡山狩獵、刀耕火種的民族的過去,我們發現,生活在廣西的十二個兄弟民族,有著比較共同的、與中原文化有所差異的文化淵源。”、“百越民族的審美理想和豐富多彩的神話以及師公文化、道公文化等,構成了百越民族真實生活整體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今天的廣西文學反映的是社會主義時代廣西各民族的生活,但今天是明天的進步,是人類歷史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揚棄。離開百越文化傳統以及由此產生的審美意識與心理結構(即把虛幻境界與真實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來反映廣西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生活是難以想象的。理解這一前提,對我們探索形成新的自成一種風格的文學現象有著重要意義。”后來,在1985年4月號的《作家》才發表了韓少功的《文學的“根”》,這一宣告“尋根小說”誕生宣言。可見,廣西文學的“先鋒”意識是前瞻性。(當然,因廣西文學屬于少數民族文學這一弱勢的態勢,這一個富有激情和理性的宣言。也是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學活動,沒有被中國文學史提及。)
我們從文學文本上看觀察。藍懷昌的《波努河》“開創瑤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敘述了海外歸國華人鄭萬明后人鄭玉竹、鄭玉梅的愛恨情仇,他們作為“波努族”人誠信于神靈,卻被惡棍、卑鄙小人的陷害,商業利益和人心丑惡,與神靈的真誠“二元對立”,藍懷昌開始了“現代文明”質疑,這是“先鋒”的信號。王云高的《彩云歸》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人民文學》刊發,首次將臺灣少將黃維芝的婚戀故事公開。1987年王云高的《明星恨》敘述了亂倫荒唐的婚姻以及人性情與欲的悖論。黃繼樹的《桂系演義》則開創了廣西文化歷史大演義題材敘述先河,這是一部通俗有故事趣味的小說,是一部暢銷書。爾后的《第一個總統》則是中國民國題材敘事的濫觴;聶震寧《去溫泉之路》展現了很現代自由思想:離婚,再婚是人自由的選擇的問題。詩意般的敘述有沈從文《邊城》的美感,1985年后的聶震寧到了北京,《巖畫與河》(1985)明顯轉向“文化尋根”創作,《長樂》(1986)的文化展現是“長樂縣”的文化風俗習禮;《暗河》(1986)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人生的生存哲學的問題的,人與人之間愛情的光明與黑暗,還不如動物(狗熊)與人之間的關系真誠,現代思想的意味綿長。林白的《從河邊到岸上》(1986)開始了女性詩意般講述女性那幽怨鬼魅的心靈獨白體小說。梅帥元的《紅水河》于1988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是揭示“百越境界”(廣西文化)色彩最濃郁的作品。把紅水河的文化:河葬、招魂、神話、道公宗教文化亦真亦幻的圖景鋪敘。將古駱越文明重現試圖展現“百越境界”。
后來的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則是質疑“現代文明”的。啞巴、瞎子、聾子三個人組成的家庭,實際暗喻的是:本來一個正常的人,在現代社會里,人將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三個人組合成為一個家,三個人組合才能做一個人的事情,行動的艱難程度可以想象。在“無聲”的世界里,其實涌動著巨大“撕裂心肺的悲慘”力量。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則是一個饒有意味的是“情”與“法”的“二元悖論”的故事。曉雷殺人了,這個人罪大惡極,該殺。但曉雷不是有意殺人,而是無意的,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惡人”死了。爾后曉雷又被腐敗黑心的官員“謀殺”了,我們面對“曉雷”如何評價?這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李馮的《孔子》、《牛郎》、《另一種聲音》等歷史的“戲仿”故事,讓我們體驗到了魯迅的《故事新編》的痕跡,對于敘述關注,使他更接近“先鋒小說”群體,《英雄》和《十面埋伏》電影的成功,使得李馮在商業電影編輯與文學創作之間游走。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1993)林多米的同性戀敘述,與賈平凹《廢都》莊之蝶的“淫亂”敘述同樣具有“時代的爭議”,后來的《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致一九七五》在涉及女性個體敘述轉向依然具有“先鋒”的意味;凡一平《跪下》、《尋槍記》、《理發師》等以及辛夷塢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在現代化思想進程中扮演著的“前沿”意味。這些作品基本與“少數民族”沒有了任何的關系,他們已經成功“脫冕”加入現代性的敘事,當代評論者也不再以“民族”的話語來定義他們的小說了,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為什么會這樣呢?么佬族作家鬼子有一個宣言式回答:“有人說,我的創作于我那民族本身的一些淵源有關,但我卻絲毫沒有找到這樣的痕跡,”“說真話,我那民族的自身并沒有給我一創作的影響,原因可能是我們那民族演變到了我們這些人的時候,已經和漢人沒有了太多可以區別的東西了”。
由此看來,當代廣西文學是不能簡單地歸納為“少數民族文學”的。廣西文學的內部與主流文學一直保持先鋒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先前是“少數民族”式的間離,后來是純粹的文學現代意識堅持。
二
當代廣西小說有兩個文學傳統,一是解放區(延安文學)文學史的傳統,二是先鋒現代意識的傳統。解放區文學的傳統可以看做是當代廣西文學的第一代文學傳統,它是在“魯藝”影響下發軔的,例如“魯藝”的“陸地(壯),苗延秀(侗)等作家在40年代文學創作達到了很好的水平”,還有40年代桂林抗戰文化城時期的秦似、林煥平等的作家創作,他們的文藝創作是在“政治性”規訓下寫出了壯族人民抗戰的英雄史詩例如陸地《美麗的南方》韋其麟《百鳥衣》。第二文學傳統是先鋒現代意識的傳統,它是中國當代文學80年代中期出現的“尋根文學”之前的“百越境界”文學以及后來的具有“先鋒”意味的小說傳統。這兩種文學傳統潛伏在廣西文學中,他們如何共融和反哺的?這是廣西文學思潮內部細節的問題。
解放區(延安文學)文學史的傳統最本質的特征是具有“政治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就是文學文本中所蘊含的政治話語。先鋒現代意識的傳統,在文本中往往以“故事”或者創作技巧來呈現。這兩者的共融是互為相依的。
我們來看廣西文學是如何“政治化”哺育先鋒的。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廣西文學就一種“異質性”的文學間離式地參與了共和國文學敘事。韋其麟的《百鳥衣》雖然很明確以“階級斗爭”政治話語來敘述一個少年反抗地主階級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本身是“一個愛情故事”。在“雙百方針”是視野下是屬于“干預作品”,是一個“先鋒”性質意義的長詩。陸地的《美麗的南方》敘述的是南方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土改運動,但是農民韋延忠也具有現代意識:他對于離婚的單身人士的尊重,對于自己妻子比自己大而沒有“封建意識”,沒有覺得掉臉,革命意識來自自我的覺悟,對于知識分子改造不是粗魯“強派”勞動任務,而是很有人道主義“委以重任”等等都是跳出政治的話語,轉向人性轉向人道主義,橫向的與同類作品相比較,《美麗的南方》在現代性的表現高出一籌的;潘大林的《南方的葬禮》,以歷史文化著筆,試圖“文化尋根”。通過一次葬禮來展現“文化”景象。在有關“葬禮”的敘述中他有意進行“意外”的補述,關于族姓以及家族的神話故事。潘家的歷史如何在“斗爭”中獲取生存權利,對于“異姓”交戰,“八死七傷”的故事,時常讓作家寒栗。每每敘事以小段故事,都回回到“葬禮”進行程序。例如,小說在開題:“‘南方沒有小說’。文壇上有人這樣的感嘆”,“這里所說的南方,是狹義上的南方,指的是五嶺以南那么一塊地帶”這是小說的開端,采用的是閑聊式的談話風。“是的,南方沒有小說。該輪到我們自己反省了。”進行推動和控制小說的敘事的速度和張弛。在論述自己的作品不是小說的小說里“旁白”:“我在一篇小說中,就這樣富于創造性描寫過人從五樓摔下地的場面:那個三十二歲有十個月零四天的男性公民,在十七點二四米高的五樓頂上,在百分之二秒的時間里,由直線運動變作拋物線運動,繼而又作圓周運動,頭發放射狀向空中飛揚,全身按每秒980厘米的重力加速度向地面接近,最后頭部以每平厘米五千公斤的壓力接觸硬度為500標號的土敏土,導致頭蓋骨粉碎骨折,鮮血及腦漿成放射狀濺出……此準確精細的描寫,仍然無法得到編輯贊賞。”“葬禮有結局,小說也有結局,但生活卻永遠不可能有結局”潘大林這個作品的先鋒意味在于他敘述跳出故事,把個人感情和議論帶入小說敘事,重在敘述技巧的加入,是“先鋒”小說最常用的模式,故事是“具有樂觀的現實主義”性質的。
“先鋒”形態的“政治化”。這種類型的文學作品一般是90年代,或9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那里擁有。例如獲得郁達夫小說提名獎的小說《陪夜的女人》講述的是一個大齡女青年給一個將要臨終的老人的陪夜故事。故事的吸引力來自她的行為:陪老人臨終,送孝。這與當下的國家意識形態有高度吻合。還有東西的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表面上是沒有政治色彩的,但只要我們主要與90年代的商業化的社會聯系起來,我們似乎有這么一種感覺:東西要表達是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化的意義——商品化的社會需要人堅守“個人”的職責,既要團結協作又要分工明確。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表面敘述的是李四的遭遇,兒女多而無人養的悲哀,作家更多是質疑“城里人”的親情的缺失。但細心的讀者肯定在閱讀中發現一個國家話語的“身份證”的作用。李馮的《英雄》(電影)敘述的是“刺秦”的故事,這“羅生門”式先鋒敘述,為什么無名不殺秦王的原因?那是寓意“天下”“和諧”的國家意識形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1993)這個故事敘述的是一個女“同性戀”的故事。這似乎是女性“個人化”的敘事,但如果我們聯想“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后來中國在90年代對于女性評價和社會分工的政策的頒布,還有婚姻法的重新頒布,都涉及到了“女性”話題。其實,林白的社會意識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先鋒作品以反哺的形式出現,這是傳統文學史在新世紀文學作品里潛伏的因子。誠如鬼子關于文學作品與政治的關系的話題時,說“我們的作品是脫離不了政治的,這就像我們人要大便一定要進廁所去蹲一樣,明知道它是臭的,但我們必須進入蹲,除非不大便。”這雖然講得粗俗一些,但這非常鮮明一語中的。
當代廣西小說是在這兩種文學傳統互為潛伏和反哺培育生成的。“政治化”與“現代性”以間離和依附的方式存在文學之中,使得廣西小說的“異樣”不再陌生化。
本文系2013年廣西哲社資金項目,項目編號13BZW005。
鄭立峰 玉林師范學院
注釋:
①曹文軒:“先鋒”與“藝術”的廣西文學[N].北京日報2006.6.13.
②陳曉明:又見廣西三劍客[J].南方文壇2000(2).
③陳曉明:直接現實主義:廣西三劍客的崛起[J].南方文壇1998(2).
④譚紹鵬:南方土改運動的生動描繪——重讀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J].廣西文藝.1997(1).
⑤李建平等:廣西文學50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44.
⑥龍殿寶、吳盛枝、過偉: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仫佬族文學史[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⑦楊克、梅帥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與我們的創作[J].廣西文學.1985.3.
⑧李建平等:廣西文學50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161.
⑨鬼子:艱難的行走[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2.9:16—17.
⑩潘大林:廣西當代作家叢書潘大林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2.
?鬼子:鬼子話文學[N].桂林日報2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