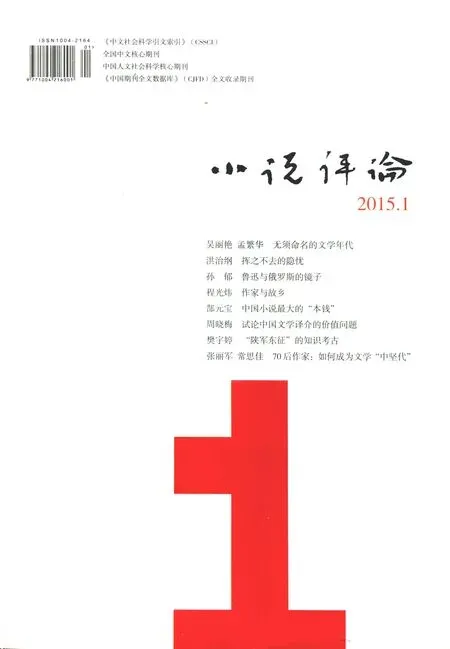沉默與吶喊
——自述
邵 麗
沉默與吶喊——自述
邵 麗
不管別人覺得當一個作家多么光鮮,很多深諳內情的人卻知道他們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其實寫作就是一件非常吊詭的事——一個作家要把別人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情想到想透,還得用一種藝術或者文學的方式告訴人家,這純粹是跟自己過不去。據說作家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個職業——干上帝的活兒,幫人家拿捏命運,能落得個好嗎?
在大多數時候,作家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TA生活在現實和虛構之間的邊緣地帶,而且界限尚不是那么分明。但TA又是一個容易沖動的人,稍微覺得超出常識——物理、人情——TA就會放聲吶喊。TA就是這副德性,因為TA是一個作家。
然而,很多讀者問起我為什么寫作時,我常常無言以對。這是一個輕易就能拿起來、卻很難放得下的問題。事情就是那么發生的,說不清楚為什么——從故事本身到我的寫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謂靈感,也許就是上帝之選,在合適的時間,把某些東西交給合適的人去做。這件“東西”,肯定有它堅實的內核和內在驅動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僅僅是把它呈現出來,所能改變的,無非是表現的方式,盡管帶著強烈的個人印記,但不會改變它的本質和方向。這樣說起來好像有點宿命,甚或有人認為是傲慢。不過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話,我就只能這么說。
難道還有更合適的解釋嗎?我做不到,也不相信。很多人以為,小說家都是憑空編故事的人。這么說也許沒錯,但除非是用唯心主義或者先驗主義的觀點去解釋這一切,否則是站不住腳的。故事從何而來?從形式上看,它可能是一場白日夢,可原故事不是這樣的,它是生長出來的,它先于文字和作家存在。講故事的人會死去,可是故事不會,它會永遠活下去,直到人類的最后一個被毀滅——不過,這也是一個故事。
也許到這時候,可以初步回答讀者的提問了:故事就在那里,我忍不住要寫出來。但這樣又容易誘發另外一個問題,莫非所有的寫作都來自于生活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多玄幻和科幻小說,它們橫空出世,卻又非常輕巧地嫁接在現實生活上,甚至連茬口都不留,好像生活本身就具有千奇百怪的N度空間。但是,我不禁要問,那些點石成金、死生穿越的人,他們面對的不是現實問題、解脫的不是當下的苦惱嗎?它介入我們的生活,不是否定或者改變了世界,而是改變了我們看世界或者處理與這個世界關系的能力,變換了新的角度。因而不管它有多么想當然,它是現實的,是活生生的,是接著地氣的。
因為現實,我常常為筆下的人物憂傷萬分,那是一種近乎絕望的無力感。也許就是這種絕望逼出了我的決絕,因而使我的作品有了態度。《劉萬福案件》里的劉萬福,每每想起他來,我總覺得非常慚愧。雖然我把他領到了讀者面前,引起千萬人的圍觀,可是那于解決他的問題,改變他的命運,并沒有任何裨益。甚至往深處說,即使解決了他的問題,那孫萬福,陳萬福,張萬福們的問題呢?
絕望——如果我們忽略了它的存在,整個社會都將被逼入絕望。
《第四十圈》里的齊光祿,是我筆下另一個殺人者。這部小說交出去很久,已經被《人民文學》刊發,以及多家刊物轉載。但他那帶著風聲的刀光,還一直糾纏著我,有時候會在我獨處的時候上下翻飛,嗖嗖作響。我相信,如果有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齊光祿會成為一個好老板、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可是,就連這一點卑微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點一點地把它掐滅。說實話,當他懷揣著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場的時候,我的心情躊躇萬端,寫到這里,或者每每讀到這里,我既血脈賁張又淚流滿面,久久地回味著這個細節,五味雜陳。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錯,我也不忍心讓他停下來。那是他這一輩子惟一的一次生命綻放,如飛蛾撲火般決絕和神圣。我更不忍心指責他,因為我沒有資格那樣做。
我的兩部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和《我的生存質量》,有人說是官場小說,有人說是自傳體小說。都對,也都不對。我寫的確實是官場,但已經遠遠地“去官場化”。如果官場是一條大河的話,這兩部作品應該是站在河邊的反思。這兩部作品有著內在的邏輯性,對于官場,從進入到退出,是一個輪回,也是一種升華。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長。我們最后能夠面對,既是堅毅,也是無奈,因此這就是生活。
從小秋、秋生到小舅舅,那是我看到的另一幕生活圖景。與快意恩仇相伴,是大部分人對這個世界的依偎、眷戀和忍耐。小舅舅這樣的人,不管生活在哪個時代,都會把不平和不公化于無形,因為他們更多的是為別人活著。這本無對錯,它是這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并以此延續五千年的香火。而小秋則恰恰相反,她希望看到不變之中的改變,希望找到蕓蕓眾生里的自己。她有目標,有性格也有態度。她給我們以希望和安慰。我的其他作品里的人物,我常常能想到他們現在的樣子,我覺得我用詞語創造了另外一個世界,他們讓我牽掛,也讓我踏實。
現在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價值觀多元且思想紛呈的時代,我們被信息所覆蓋,也被它捆綁。我們寫出來的,到底是被縛的感覺、解脫的愉快還是對繩索的“斯德哥爾摩”依戀,很難說清楚。這很有意思,也著實令人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