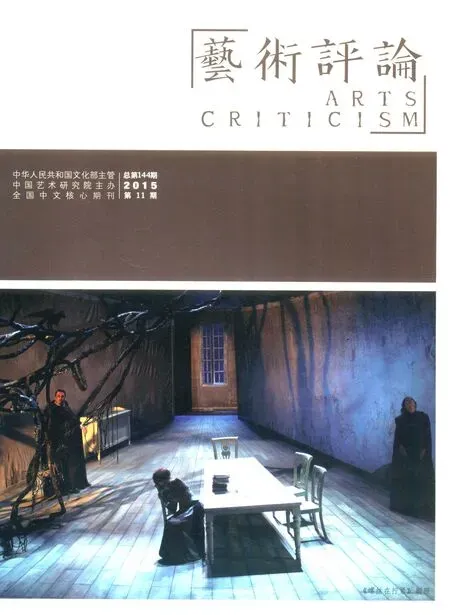從《太陽·地球……》到《詩經·國風》
——萬素大型舞蹈創作感思
于 平
一、總想用充分的“言說”來昭示自己的“坦白”
這是一篇五年前就在醞釀的“感思”,彼時的題目叫《從〈太陽·地球……〉到〈坊巷春秋〉》。2009年,萬素在福州市歌舞劇院完成《坊巷春秋》的創作,她是由筆者推薦去擔任這部“舞蹈詩劇”的編導的;筆者作為編劇,是應福州市政府之邀為“三坊七巷”寫一部可以駐場演出的臺本,選定的是曾居住于此的現代史名人。筆者寫了9人,萬素擇取了7人并分為3篇:《鴉戰遺恨——林則徐》《審判東京——王冷齋》合為《愛國衛士英勇篇》;《早春夢痕——林旭》《血性柔性——林覺民》合為《愛國青年悲情篇》;《重塑風塵——林紓》《蹈海叫天——嚴復》合為《愛國文人筆墨篇》;還有一篇《春水繁星——謝冰心》被萬素用作“詩續”,表示“在冰心的詩句中,我們走過,我們走來,敞亮民族的情懷,聆聽時代的呼喚……”說實話,在結構《坊巷春秋》的文本時,我曾聯想到屈原屈大夫的《九歌》。有所區別的是,《九歌》的諸神為情而情,沉溺于悲情而難以自拔;《坊巷春秋》的仁人志士為義而情,獻身于悲情而警醒世人。在拿到臺本時萬素對我說了兩句話:一句是“你已經用文學編出來了”,另一句是“這些內容我可以編三臺晚會”。我當時只是希望萬素“取精用簡”,因為“簡約性”意味著高度概括性。它不僅表現在形式的簡潔與明了,更體現在內容的豐富與深刻,即“言簡意賅、文約義豐”。現在許多編導都在大談“簡約”甚至“簡約主義”,但對“簡約性”的基本特征卻不甚了了——不明白它需要實現“多樣統一”的具體性,需要不同主體相互溝通的通約性,需要把握對象的復雜聯系并將其加以條理展現的清晰性,還需要把握接受者思維特點、內心體驗和交流水準的現實性。現在回想起萬素創編的舞臺形象,我一方面感慨她對于臺本構思的深邃洞察和深刻理解,一方面也感嘆她舞臺呈現中的繁瑣與拖沓——總想用充分地“言說”來昭示自己的“坦白”,這正是萬素骨子里的“真實”。
二、因持守“真實”而體現出某種“固執”
這種“真實”的流露和對這種“真實”的持守,往往就形成了一種“固執”。想起2005年,也是筆者推薦萬素去云南玉溪擔任一臺晚會的總導演,她將那臺晚會命名為“舞蹈散文詩《滇土悠情》”。其實彼時玉溪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舞者,《滇土悠情》的表演者主要是玉溪市紅塔區花燈團的演員。為了讓其能盡可能地表現出萬素那“坦白的言說”,她竟帶著助手對那幫演員連“訓練”帶“排練”達半年之久。舞蹈散文詩《滇土悠情》由四個篇章構成,分別是《追述原固》《情思悠長》《事事皆通》和《回歸旅途》。彼時的云南,正掀起結伴旅游的歌舞表演熱浪:楊麗萍領銜的《云南映象》坐陣昆明,其他則有楚雄的《太陽女》、大理的《蝴蝶之舞》、麗江的《麗水金沙》……玉溪的《滇土悠情》上追古滇國的青銅文化,下溯花腰傣的民俗風情,用萬素的創作理念來說,叫做“生命誕生生命,旅途只在回歸。時空在這里超越,理想在這里升騰。象征吉祥的青橄欖,帶著古滇國故里的祝福,從這里灑滿天地,灑向人間。”當我應玉溪文化部門前往觀看之時,平心而論,似乎并沒有覺出多么厚重的文化感,也沒有覺出多么厚重的鄉土情。
萬素其實也知道自己奉命而為的是古董的仿照和鄉俗的比擬;她在第三章《事事皆通》中,從古人的生殖崇拜,講到今人的“紅白”喜事——從“干欄房”到“土掌房”則成了時空變遷、人事依然的“旁證”。那時我只是不明白,萬素為何要將溘然長逝者的“壽材”擺放在舞臺中央,為何要用冗長的儀式來沉湎生命所謂的“白喜”之境?現在想來,萬素的情思中有濃重的“回歸”情結,這“情結”之濃重似乎使她忘記了這臺晚會負有“結伴旅游”的使命,這也使我們看到萬素即使在“命題編舞”中也體現出某種“固執”——而這其實是深植于她“本我”的某種“真實”。
三、率先關注萬素的“城市舞蹈”之夢
萬素的大型舞蹈創作,在我的記憶中始于1993年創編的《太陽·地球·月亮》。這臺為北京舞蹈學院社會音樂舞蹈教育系所做的畢業晚會,其實無關于太陽、地球和月亮,萬素創作的7個作品是《同窗》《減肥》《相識》《一樣的情》《女人》《魯冰花》《掌聲響起……》。這體現出當時少見的“都市青春”風采!觀看那臺晚會后,我為萬素寫了一篇短文,題為《萬素的城市舞蹈之夢》(載《中國教育報》1994年3月16日),也算是率先關注了她的“城市舞蹈”之夢。筆者在文中寫道:“萬素認為自己‘天生是跳民間舞的’,她的寬肩、粗腿并不符合芭蕾的人體美準繩。但因為不堪忍受‘總是一張笑臉’的民間舞,所以傾心于芭蕾動態中的延伸。但在芭蕾課的學習中,又總想重新處理其運動節奏,為的是想使其符合中國人的運動方式。她在舞院畢業后,最初分配到北京體育大學任教,其間聽說王玫在舞院舉辦現代舞短訓班,便自費參加學習,后來,便做起了她的城市舞蹈之夢……萬素很喜歡現代舞的‘工作室’制度,因為許多動作是在那里‘試’出來的。有了這一經歷,創作便很輕松,創作的過程也很有意思……在萬素做她的城市舞蹈之夢時,她從北京體育大學調回北京舞院社會音樂舞蹈教育系任教,主要給國標舞專門化班上基訓課。我覺得她的基訓課很有針對性,她則告訴我:就運動方式而言,芭蕾面向單一,先定位再舞動;而國標舞則多方位,在流動中找位置變化……”這樣你就能理解,多年后(2008年)她何以能自如地去創編一部“國標舞劇”《長恨歌》。
四、從“都市青春”的活力沉潛到“京城風韻”的情致
動筆作此文時我對萬素說:“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對《同窗》《減肥》《魯冰花》等的印象依然清晰;只是不明白那種‘清純’的清晰為何要叫《太陽·地球·月亮》?”萬素說:“命題是他們的事,我只編舞。”那之后的1996年,萬素又擔任了“命題晚會”(萬素語)《京都伊人》的執行編導和編舞。《京都伊人》的命題者是呂藝生,他那時剛卸任北京舞蹈學院院長,受聘為“天創女子舞蹈藝術團”團長。呂藝生在《〈京都伊人〉的創意》(載《舞蹈》1997年第1期)一文中說:“前幾年,我在任北京舞蹈學院院長時,曾與民間舞系商量,要為北京整理些味兒足的民間舞教材,也搞點京味兒舞蹈……機會終于來了,剛建立的天創女子舞蹈藝術團聘我做團長,我將原來萌生的為北京搞點東西的想法移到這個團來……”《京都伊人》在公演時的穹形幕沿上寫著“大型京味舞蹈晚會”,但它其實就是風情和煦、韻味濃郁的“舞蹈詩”。這部“舞蹈詩”由三章九闕組成,分別是第一章《市井風韻》(含《茶樓》《鳥市》《胡同口兒》)、第二章《梨園軼事》(含《聞雞起舞》《公子詠嘆》《夜深沉》)、第三章《都市即景》(《叫賣》《打花巴掌》《賣布頭》)。除《公子詠嘆》這闕由唐滿城編舞外,其余都由萬素來創編。相對于《太陽·地球·月亮》而言,《京都伊人》的命題取向明晰、意象精確,萬素也就從那種“都市青春”的活力沉潛到“京城風韻”的情致中來了。看《京都伊人》之時,我最強烈的感覺是萬素“編什么像什么”。你想想,萬素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望”是江南水鄉;要編京都的“伊人”,又沒有什么具有地域特征的舞蹈素材來支撐。除第二章《梨園軼事》還可用戲曲舞蹈來演繹外,其余似乎都要到那些泛黃的老照片中去咀嚼了。《市井風韻》和《都市即景》的六闕,其實都很“市井”,因為創意者根本就無法從“都市”中看到“京味”。現在看來,作為“京味”晚會的《京都伊人》,雖不乏情致但少了些時尚,多了些《茶樓》《鳥市》《胡同口兒》而少了些“空港”“股市”“公交站兒”,多了些《打花巴掌》《賣布頭》而少了些“北漂一族”“大媽舞”……不過對于萬素來說這樣更好,這個“京城風韻”與她此前的“都市青春”晚會形成了一個反差,也由此充分體現了萬素舞蹈創編的可塑性。
五、在別人的“命題”中開掘出自己的人生“題旨”
萬素很敬業——我說的是很盡職的那種“敬業”。她創編的許多作品,其實都是北京舞蹈學院畢業生的畢業晚會,但好像又是這所很職業的藝術院校里某些不很職業的“畢業晚會”:比如說為社會音樂舞蹈系中師班創編的《芭比娃娃在中國的搖滾》(1997年);比如說為繼續教育學院“專升本”班創編的《誰知道時間到哪里去了……》(2003年)和《農民報告:城市滋味》(2004年);當然也有很職業的、為社會音樂舞蹈系國標舞班創編的國標舞劇《長恨歌》(2008年)。萬素創編《芭比娃娃在中國的搖滾》之時,筆者還在北京舞蹈學院擔任主持院務工作的副院長。當時不太明白萬素為什么要“芭比”而且要“搖滾”。這似乎是一部由三場戲構成的“無沖突舞劇”,分別是一場的《呆》、二場的《逛》和三場的《撞》,然后有一個“序”和一個“尾”。用萬素留在場刊上的話來說,一場曰《呆》,在于“呆之困之,便有了胡思亂想”;二場曰《逛》,在于“逛之閑之,便有了似是而非”;三場曰《撞》,在于“撞之碰之,便有了銘心刻骨”……我以為,這個“芭比”倒有點像萬素自己,神態像、性情像、心思也像,只是不明白她為什么要把自己托付給“一不留神、降到中國”的芭比娃娃。或許她想自己給自己“命”一回“題”,或許她也不能不考慮“中師班”作為表演者的特質所在。當萬素的《誰知道時間到哪里去了……》公演時,筆者已調文化部藝術司任職了。前兩年在央視春晚火了一陣的“時間都去哪兒了”,原來是萬素十余年前就有的感觸。其實這之前,萬素由肖蘇華推薦為俄羅斯室內芭蕾舞劇院創作了一部現代舞劇,劇名用的是《我們從哪里來?又去哪兒……》。而對這個人類總在叩問的疑慮,萬素用中國舞蹈常用的水袖、折扇這類極具可塑性、象征性的道具來表現較為抽象的四個理念:1、活的意識;2、需求只為需求;3、死與生是一種概念;4、去哪兒——永遠是人類的追尋。相對于這種恒久的、抽象的概念,《誰知道時間到哪里去了……》似乎更當下、更具體。作品的構成是《已是過去》《不在過去》《只有存在》3段,再加上尾聲《還是未來》……或許可以說,萬素雖然偶爾也會想想“生”“死”“活”“尋”那些恒久的叩問,但她更多地是存在當下,感覺當下,反思當下。正如她總能在別人的“命題”中開掘出自己的人生“題旨”,她也總能用鮮活的、具體的當下去詮釋那些虛無縹緲的、抽象的概念!
六、在元素層面上實現舞蹈語言的轉換
就個人偏好而言,繼大型京味舞蹈晚會《京都伊人》之后,我最喜歡的是國標舞劇《長恨歌》(2008年)。這部《長恨歌》無關于白居易的長詩,它所依據的文本是王安憶的同名小說,而這是一部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但既然王安憶要用白居易的名篇來做文章,就不會沒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題旨。其實在此之前,萬素已創編了兩部舞劇:一部是為天津歌舞劇院芭蕾舞團創作的《精衛》(2004年),另一部是為她所服務的北京舞蹈學院創作的《唐琬》(2007年)。天津歌舞劇院的《精衛》,除萬素外,好像門文元、鄧林也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參與過,因而我并不視其為了解萬素舞蹈創編之必須;北京舞蹈學院的《唐琬》,編劇是該院黨委書記王傳亮,為頂頭上司的劇作編舞,我以為也難以表現萬素的“真才情”。不過萬素一再要我看看該劇的視盤,因為她自認為是“相當不錯的”。還是先回到國標舞劇《長恨歌》。這部舞劇的“這一個”(獨特性),當然首先體現為用那種不僅類型化而且標準化、不僅表演性而且競技性的“準舞蹈”作為舞劇語言;其實,舞劇的“這一個”更體現為由人物關系結構出的舞劇結構。筆者曾認為,大部分舞劇是“以女首席為核心結構人物關系”,且大多又以女首席的戀人(或愛人)構成唯一男首席。國標舞劇《長恨歌》的女首席叫王琦瑤,是個“命運多蹇”的美女(曾當選“上海小姐”),也是“紅顏命薄”的確證。該劇結構的“這一個”,在于作為“結構人物關系”之核心的女首席獨特的結構取向 ——即并非共時態中的“并聯式”結構而是歷時態中的“串聯式”結構。舞劇敘述的時間跨度是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在王琦瑤近四十年的人生中遭遇的四位男性,分別是激情雄霸的李主任、體虛情溢的康明遜、神采煥發的老克臘和懦弱默然的程先生……正是這個程先生,目睹了王琦瑤一而再、再而三的“愛河情劫”,而這個目睹者其實才是深墮愛河、自甘情劫的“遺恨者”,其實才是“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男首席。梅林在《用國標舞述說中國故事》(載《舞蹈》2009年第8期)一文中提問萬素創作該劇的“最大挑戰”,萬素說:“我要在《長恨歌》中深刻把握的是國標舞種自身的魅力,以及將這種魅力轉換成舞蹈語言去述說舞劇內容的‘核’;要拋開特定動作的外在形態,找到它與人物內心情感活動相關聯的某種狀態和特質……打破國標舞種程式化的動作形態和程式化的情緒表達,在元素的層面上實現舞蹈語言的轉換是我在這部戲中下功夫最多的地方。”因此,萬素用華爾茲表現王琦瑤和程先生的柔情,用探戈表現王琦瑤和李主任的激情,用倫巴表現王琦瑤和康少爺的纏綿,用“恰恰”表現王琦瑤和老克臘的狂放……萬素并沒有忘記告訴提問者:“其實劇中我最鐘愛的人物并不是女主人王琦瑤,而是程先生。他性格猶豫,有些懦弱,但永遠關心她、呵護她,需要的時候一定會出現在她身邊。這是一種美好、善良和真愛。”萬素甚至還意猶未盡地說:“如果十年前,我面對這部作品可能不會有這樣的認識,這是生活閱歷給予我的眼光和選擇……文學界把茅盾獎頒給小說《長恨歌》,體現著一種對人性更開闊的理解和眼光。我希望我們舞蹈創作中也能有更多這種表現平凡生活和普通人物的作品。”
七、一部“舞”被“劇”拖著跑的舞劇
我認真地觀看了萬素自認為“相當不錯”的舞劇《唐琬》。這部舞劇的創作在《長恨歌》之前、又在《精衛》之后,應當說是最能體現萬素駕馭舞劇創作能力的作品。《精衛》是芭蕾舞劇,內容是“單純的不能再單純”的神話故事;《長恨歌》是國標舞劇,內容是“將不單純表現得很單純”的平凡人生;而舞劇《唐琬》,表現的是極其繁復、極其困擾、極其糾結并從而極其追悔的文人情懷。因為唐琬,歷史賦予了陸游“但悲不見九州同”之外的意涵;因為唐琬,人們才絡繹不絕地去沈園追思緬懷;還因為唐琬,人們才長久吟誦“錯錯錯”“莫莫莫”和“難難難”“瞞瞞瞞”的《釵頭鳳》……舞劇《唐琬》由六幕構成,每幕的名稱很長,當然是王傳亮書記的手筆:一幕《節日臨安·心悅抒情緣》,二幕《靈致之愛·美景漂隱憂》,三幕《宗教圣言·休書舍愛妻》,四幕《人自各方·沉寂度春秋》,五幕《沈園再遇·悲憤留訣詞》,六幕《香消玉殞·真情凝愛魂》;此外,還有序幕《愛之詞夢源》和尾聲《幽夢太匆匆》。其實,筆者以為名稱完全可以大大地簡練,六幕稱為《情緣》《隱憂》《休書》《沉浮》《再遇》《訣別》即可。說這部劇“繁復”,主要是對事由交待得過細過雜,特別是第四幕分述陸游再娶王氏而唐琬下嫁趙士程,還要分述兩人十年間各自的生活:一個是戎馬倥傯存斗志,一個是閨房惆悵難銷愁……但也正是這個“分述”,在舞劇結構中形成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之妙,使“繁復”成為其結構的特色。說這部劇“困擾”,主要是陸母這個人物的設置及其作為“沖突源”的作用,特別是讓其在第二、第三兩幕中逼子休妻,且此后又息影匿蹤,于舞劇而言頗顯“突兀”,也就憑添許多“困擾”;但這個編劇的“困擾”卻需要萬素以編舞來“引渡”,以“情思的呼應”來化解“沖突的無解”,這又使“困擾”成了敘述的特色。看過舞劇《唐琬》,我總的感覺只是演劇太瑣屑而編舞略拖沓,也許這“編舞的拖沓”根由于“演劇的瑣屑”。你想想,要從陸游、唐琬“兩小無猜”一直講到“兩心長恨”,要說明陸游休妻的無奈,要說明陸游、唐琬各自另一半的“不解琴”和“不識書”,還要說明沈園重逢時的克制和繾綣……怎能不讓“舞”被“劇”拖著跑!三幕陸母上場下場,為促成陸游休妻而使自己成了個啞劇化的“活道具”。在這種境況中,萬素的編舞一是逮著雙人舞(陸游與唐琬)就恨不得絮絮叨叨;二是為雙人舞鋪墊、鑲襯群舞(特別是女群舞)增添色彩;三是盡可能讓語匯風格貼近中國古典舞形態——不過“形態”只是取其“形”而未能展其“韻”,語匯的生成轉換是萬素自己的創編理念。這當然也構成了萬素個人風格的“這一個”。
八、“暈菜”在萬素的“理論”或“論理”中
據我所知,王傳亮編劇的《唐琬》之所以由萬素編導,是因為呂藝生的推薦。呂藝生作為北京舞蹈學院的院長是我的前任,后來擔任著學院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對推薦萬素編《唐琬》,學院被稱為“民族舞劇系”的中國古典舞學科的專家們很有些“不同看法”。想到萬素創編的《京都伊人》便是呂藝生的主張,可以認為呂藝生是高度認同萬素的創編才能的。為寫好此文,我查閱了萬素寫下的一些文字,這些東西大多發表于《北京舞蹈學院學報》,主要有《舞種角度下的舞劇言語》(2009年第4期)、《建立舞者身體的“感受”系——由身體是舞蹈的載體引發的思考》(2010年第2期)、《營造及需還本的舞者身體(上)——對舞者身體的淺層描述》(2013年第2期)、《營造及需還本的舞者身體(下)——對舞者身體的潛層描述》(2013年第4期)等。平心而論,萬素的這些文字作為“理論”太“澀”,完全不像一個在舞蹈編創實踐中久經磨煉的編導者所為。比如她用“內容核”和“形式核”來解說“舞劇的構成”,認為“‘內容核’即主題思想、內涵意境、故事情節、人物命運及關系;‘形式核’是對‘內容核’賦予結構,分布整體的內容量和內容關系,并進入一定的時空量中劃分,同時,舞段布局的方式和不同的分布關系及量的比例由此建立。其中,一部分屬編舞成分的‘組織形態’,包含‘動作形態’和‘畫面構成’兩個類別,另一部分屬編導成分的‘組織符號’,即不再以‘動作形態’制造符號,而是通過綜合其他藝術元素來組織語言符號”(《舞種角度下的舞劇言語》)。引述這一段,只是想說明萬素的主業是編導的教學而非作品的編創,她可能太想讓自己的教學系統化,并且是“言說的”系統化;可她似乎不太熟悉(也許是“熟悉”但并不“習慣”)“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只能把自己“命名”并強行在課堂上“灌輸”的概念組織起來——這種“論文”的組織方式也體現出她“舞蹈作品”的組織(創編)理念。不過,到寫作《建立舞者身體的“感受”系》一文時,這種狀況有所好轉但卻仍然存在。如她所說:“這里提到的‘感受’系,即是以‘意識’為條件,這個‘意識’是指舞者對于自身身體動作的敏感性、能動性、挖掘性和自由度。在這樣的‘意識’概念下,以‘感受’為基礎,構成身體的舞蹈動作性。由此,不管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以‘感受’來構成、觸動及形成意識,并以此作為舞蹈動作的基礎框架、出發點和平臺。”說實在的,讀這樣的“理論”或“論理”我都快“暈菜”了,好在萬素是編導無需苛求。她想要說的,無非是舞蹈編導要能動地、敏銳地、自由地開發動作,而前提是通過“感受”來形成“意識”。
九、“以不變應萬變”與“集小成為大成”
為了解萬素在2009年以后的創作,我給她打了個電話,誰知她幾乎是一年一臺:2009年是民族舞蹈詩劇《熱貢神韻》,2011年是交響詩劇《鄉愁》,2012年是舞蹈詩《在那遙遠的地方——推進走來》,2013年是舞蹈劇場《昨日留言》,2014年是漢族民間舞實驗劇場《悠然情韻》,2015年則是舞蹈詩《國風》。其實,萬素的作品除了《精衛》《唐琬》《長恨歌》是舞劇外,其余基本上是舞蹈詩和舞蹈詩劇。如同前述《滇土悠情》表現的是云南玉溪的土風鄉情外,《熱貢神韻》表現的是青海黃南的鄉情土風——它的四幕是《家園鄉情》《祭拜千年》《石經心歷》和《異彩奇葩》。相對于這些被要求貼近熱土淳風的作品,《在那遙遠的地方——推進走來》似乎讓萬素得到了更大的發揮。我稱為“舞蹈詩”的這部作品是萬素帶著北京舞蹈學院編導系2010級新疆班所作,它的三個部分分別是《彌漫出的驛站》《聞熟了的背后》《久藏著的味道》。實際上,這是繼《京都伊人》《長恨歌》《坊巷春秋》之后,我最喜歡的一部萬素的舞作,它使我猜測萬素最擅長的是一個個相對獨立、整體上又相互關聯的“舞蹈詩”。第一部分《彌漫出的驛站》有四個片斷,即《凈·禮拜》《在“艾特萊絲”中融合》《摘葡萄的時節》和《小唱“哎拜麗”》;第二部分《聞熟了的背后》也有四個片斷,即《傳情在老歌中》《愛在何處》《回情于大自然》和《馬車夫之戀》;第三部分《久藏著的味道》是三個片斷,即《手鼓拍出的風味》《四個民族“聚會”畫》和《生命的呼喚》。可以說,這是我所見到的在極具新疆文化底蘊中最具創新意識(不失本源的創新)的舞作。萬素告訴我,全部作品是由她創編的,但動作主題來自這個編導班的同學。我需要補充的是,舞蹈表現中彌漫的幽然諧趣乃至堅韌樂觀的情調也是同學們與生俱有的。萬素的創新,如同《唐琬》中面對中國古典舞語匯時一樣,她無需刻意去改變,因為她本身就沒進入、也不想進入新疆各族(主要是維吾爾族)舞蹈的運演邏輯;萬素從來是以自己長年編創教學中形成的“生成轉換語匯”來“以不變應萬變”。我以為,這部舞蹈詩中最能體現萬素創編能力并形成其特質的,是第二部分的《傳情在老歌中》和第三部分的《四個民族“聚會”畫》。前一個用了5首歌的核心樂句來組織,分別是“阿拉木罕怎么樣”“美麗的姑娘見過萬萬千”“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掀起了你的蓋頭來”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因為都關涉男女情愛,串聯中的共性基調和差異轉換十分自然也十分有機。后一個涉及的4個民族分別是蒙古族、柯爾克孜族、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萬素用了一個大的形態框架——在凹形大圓弧的環抱中、由領舞者從臺中跪蹲起舞開場,使不同民族動作基調的個性差異有區別但是不“各色”。我認為這體現出萬素編創中“集成創新”的理念和能力,是與其“以不變應萬變”相呼應的“集小成為大成”。
十、“編導文化”就是需要大徹大悟下的自以為“是”
在取萬素2009年以后創作的視頻時,她正與助手在工作。見我到后,她告訴助手我便是于平,是第一個寫她的人。的確,我寫萬素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短文是20年前,那時只覺得她有靈氣、很執著,是一支尚未有上揚勢頭的潛力股。因為考不過外語,直到我擔任北京舞蹈學院主持院務工作的副院長(1996-2001)期間,萬素的職稱仍只是講師。從學院以特批的方式分給她一套兩居室住房來看,足以說明對她才華及業績的認可。取視頻之時,不曾想她遞給我3大本厚厚的專著,還自謙地說:“出了一段時間,不好意思送你過目。”這專著統稱為《留給時間的舞蹈》。一部叫《生命會怎樣起舞》;另一部分上、下兩卷,叫《舞蹈編導的學問》。《生命會怎樣起舞》是關于“舞蹈即興”或曰“即興舞蹈”的,是一部42萬字的大作。“即興舞”是舞者極重要的能力,甚至是一名優秀舞者應當具備的天賦,它也是一名靈慧的編導創作靈感生發的引擎。但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為它是不可言語、無法言說的“黑箱”。好一個萬素,她不僅編出了系統的“即興舞”教材,不僅理性地“敞亮”那神秘的“黑箱”,而且居然全面闡述了舞蹈思維的特性、以及建立舞蹈思維特性的方式。正是基于這方面長期的教學、創編實踐以及對實踐孜孜不倦的反思,萬素又寫作了《舞蹈編導的學問》,這回更是了得,上、下兩卷共計80萬字。你想想,能寫出如此編導大作的人,她的創編是有厚實的技法支撐和系統的學理統轄的,不過這一切,在萬素的作品中全然不顯山露水,甚至無履跡擦痕。萬素在該書“前言”中說:“編導文化是非常具有個人言說性的藝術特質和藝術能量。所以,沒有任何人可以要求編導‘萬眾一心’;沒有任何人和某一理論能為編導制造出‘萬能鑰匙’;一句話,編導文化就是需要大徹大悟下的自以為‘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十一、“得吧得吧”表象下的“涵虛”與“淳樸”
還是要回到活生生的作品。萬素最近的創作是《國風》,這是一臺從古老《詩經》演繹而來的晚會,我認為它還是可被稱為“大型舞蹈詩”。這臺晚會再次讓我認定萬素的強項是“大型舞蹈詩”的創編。《國風》由五個部分組成,其中第五部分可看作一個“尾聲”,場刊上就此只有一句話:“心系古人——挽在舞中致。”但演出時滾動的字幕告訴我們:“它們本是各自獨立于《詩經·國風》里的詩篇,但經舞蹈結構,可營造出整體一個‘劇’的演繹。讓我們在熟悉和新鮮、求異與感受并存中,覺悟那揮之不去的中國文化的恒定與溫感。”也就是說,晚會之所以命題《國風》,是因為前四個部分都是對《詩經·國風》詩篇中充溢著生活情趣和生命情調之愛情詩篇的演繹。除第三部分《周南·桃夭》是“一舞”對‘一詩’的演繹外,其余幾部分都體現為“集成”演繹:第一部分合并《周南·關雎》與《秦風·蒹葭》;第四部分合并《鄭風·女曰雞鳴》與《邶風·綠之》;第二部分則是“三合一”,即《鄭風·子衿》《王風·采葛》與《王風·大車》等整合。聯想到萬素《在那遙遠的地方——推進走來》中的《傳情在老歌中》,我感覺萬素已十分青睞、且十分自如于“集成創新”了。《國風》的音響構成,除純粹音樂外,主要是對詩篇的吟唱與誦讀,誦讀又分為普通話(女聲)和古音韻(男聲),這“古音韻”誦讀乍一聽很像閩南方言。對詩篇的舞蹈呈現,給人總的印象是偏“靜”偏“雅”,特別是女性形象,在許多群舞中是“多舞姿變幻”而“少舞臺流動”——《周南·關雎》中的“大斜排”舞隊和《周南·桃夭》中團聚在臺中的舞隊均是如此。我對萬素說,就我對《詩經·國風》大部分愛情詩的理解,舞蹈似乎少了些直率乃至任性……可萬素的想法是:“我沒有能力再現《詩經》那個年代的場景,也沒有能力塑造離我們很遠的古人。但《詩經》對我的文化沖擊和我對《詩經》的向往,就是那純樸和淳樸、情蘊和情韻,就是那含蓄和涵虛的意境和藝境。”(場刊《編導的話》)你看你看,整天惦記著“編舞”的萬素這會兒在“拽”詞呢!忽然想到,萬素在寫那些大部頭論著時總在講“舞蹈思維”,莫非她是用“舞蹈思維”來馭使文字?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她馭使文字的風格去審視她編舞(舞蹈敘述)的特色——這便是有點兒“得吧得吧”和更本能的“涵虛”與“淳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