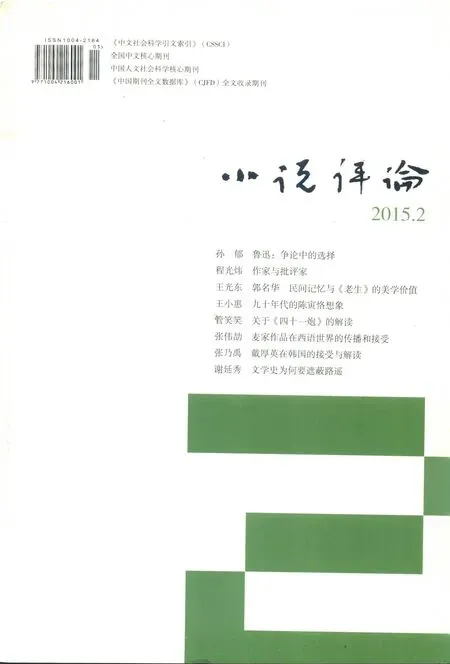論《陸犯焉識》中的悖論現象
魏李梅 房福賢
論《陸犯焉識》中的悖論現象
魏李梅 房福賢
悖論是一個邏輯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人生問題,與我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悖論(Paradox)最令人不解困惑與著迷的地方,用西方哲學家丹尼爾的話說,就是結局總“與期待沖突”。悖論一詞與文學批評相連,發端于20世紀20年代的新批評,新批評把研究的重心引向作品本身,悖論研究成為新批評的一個重要分支。在文學批評中,悖論原是一個修辭學術語,是指表面上看似荒謬、不切實際的陳述,實際上卻是成立的,是一種客觀存在。“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方法,悖論揭示了現實世界中互相并置的矛盾因素和對立關系。”悖論理論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魯克斯把悖論提高到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認為悖論是創作者不可或缺的一種思維方式:“科學家的研究必須消除任何形式的悖論,但是對于文學創作者來說,悖論是他們表達思想的必須途徑。”《陸犯焉識》就是一部充滿悖論或是在悖論啟示下創作出來的小說,在結局總與期待沖突的故事背后,內置的卻是對人生客觀存在卻又難以理清的種種現象的思考與揭示。可以說,悖論構成了小說《陸犯焉識》顯著的美學特征。
一
任何故事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與環境下發生的,但基于不同的藝術需要,不同的作品對歷史的處理也自有不同。有的小說中,歷史僅僅是一個背景,有的小說中,歷史則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陸范焉識》中,主人公1954年被捕后20余年的那段歷史在文本中占據了相當重的分量。從主題的意義上看,這一時期的歷史描寫的目的是什么?是作者對具體時代政治的再度反思,還是對復雜生命現象的深度探尋?人們切入問題的角度不同,自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在法國電影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電影刊物《電影手冊》編輯部集體撰寫的長篇論文《約翰·福特的〈少年林肯〉》談到文本和它所反映的歷史之間的關系時說,每個文本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因此我們必須將其放入一個更大的關系范疇——一個“歷史”文本之中予以考察。從更大的歷史文本去考察,《陸犯焉識》對這段歷史的重視,并非特意強調歷史性的傷痛記憶,而是在歷史記憶中尋找一種超歷史意味的生命體驗,亦即一種解說不清的人生悖論,這雖然會使那些更多地關注小說中政治意義的人產生消解歷史的疑問,但這樣的認識卻更符合小說的深層邏輯與生命本色。
從時間跨度來說,《陸犯焉識》的生活史不可謂不長,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小說以敘述過程中時空的自由閃回和幾個不多的獨立小標題“恩娘”、“上海1936”、“重慶女子” 穿插著講述了陸焉識必不可少的前史,但它的著墨重心無疑放在了1954年陸焉識被捕之后。莫名其妙的荒唐的被捕,不經審判隨意更改的刑期,大西北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嚴苛的勞教生活,監獄里的各色人等,各種死亡和人性中的惡,不僅構成了小說的重要內容,而且都給予了細致的描寫,極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說開篇引子就以極具陌生化效果的描寫令讀者在痛苦、震撼的閱讀體驗中被深深地吸引。犯人們在獸群橫行的大草漠里是新來的“著衣冠的直立獸”,他們的到來徹底打破了生物界的天然的平衡,“活物們被吃得所剩無幾,都是‘談人變色’。”寒冷、饑餓、高原反應、勞累等等原因也使犯人們成批倒下,陸焉識卻是頑強生存下來的不多的犯人之一,簡短的幾句話讀者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特別的犯人:“他會四國語言,會打馬球、板球、彈子,會做花花公子,還會盲寫(即在腦子里書寫)。”這樣一個知識精英何以會成為反革命?小說開篇就使故事充滿了懸念,同時,小說更有大量的篇幅直接對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有現象進行了特寫,如“加工隊”、“梁葫蘆”、“監獄門診部”、“夜審”、“萬人大會”這些特定的詞匯也使歷史這一要素得以突出。從一般性的閱讀經驗出發,人們很容易將這樣的描寫視作是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批判性反思,這樣的理解并不錯,但這樣的理解卻是簡單的。事實上,對這段歷史的政治性反思并不是這部小說的新發現,因為早在上世紀80年代的“歸來的作家”如王蒙、張賢亮、從維熙等作家的筆下,這些令人驚悚的故事早已出現了。而且嚴歌苓對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遭遇并無真實的體驗,無論是對環境的描寫,還是對時人心靈的把握,都很難超越張賢亮、從維熙等親歷過那段歷史生活的作家,以已之短較他人之長,一個聰明的作家是不會去做的。嚴歌苓在《陸犯焉識》中這樣寫并不僅僅是為了引起人們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痛苦記憶,而是尋找人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中發生的令人驚嘆的變化,在這里,作者非常巧妙地將丹尼西所謂的“與期待相沖突”的悖論引進了文本的敘述中,不僅改變了人們凝固化的意識形態想象,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陸焉識在人與獸、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博弈中經歷了許多死亡的威脅和考驗,但是這種惡劣至極的生存境況并沒有使這個精英知識分子產生一種政治上的反抗或有意識形態上的自覺,他既沒有像張賢亮筆下的章永璘那樣去讀《資本論》,從歷史的規律與當下的現實中認識當代中國產生問題的原因,也沒有像王蒙筆下的“少共”那樣愈是在艱難的環境下其理想信念愈加堅定,可以說,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段里,陸焉識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幾乎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他既沒有面對殘酷的現實而成為一個思想家,也沒有因為陷入絕境而向環境投降,而是更多地退回到內心,在自我人生的回憶中咀嚼生命過程,特別是他與妻子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在不斷的內省中他逐漸清晰地明了了自己的感情,發現自己是愛自己妻子的,妻子也逐漸成了陸焉識心中的摯愛,成了他活下去的最大動力。懺悔的心使他開始了瘋狂的逃離勞改農場的行動,老年人的身體迸發出了少年人的熾熱愛情,只為見妻子一面并向她告白自己的愛情就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危險執意回去,但是女兒電話中的回應像是隔空對敵喊話,使陸焉識如影子般地跟隨了妻子幾天卻始終沒有相見便自首回去了。二十幾年的牢獄生涯結束之后,陸焉識終于回到上海,卻發現妻子已經失憶,他以陌生人的身份,以無限的愛心和耐心每天陪伴妻子,讓馮婉喻終于等到了她堅信的愛情,雖然這愛情是有缺憾的,是錯位的,但卻擁有一種別樣的美,那是一種含淚的微笑的美。
《陸犯焉識》沒有用美好愛情的毀滅來批判歷史的錯誤,而是在歷史與生存環境的極端冷酷中表現令人嘆為觀止的愛情。小說似乎是在告訴人們:陸焉識無辜被捕是不幸的,他所經歷的那段歷史是荒誕的、丑陋的、亂象叢生的,是值得人們去認真反思的,然而事情的悖論是,沒有這一段的歷史,沒有陸焉識的無辜被捕,沒有大西北勞改農場不堪的生活,馮婉喻一生的愛意也許就永遠得不到熱烈的回應,歷史的不幸卻催生了凄美愛情之“花”,正是這種歷史與生命的悖論使作品充滿了強大的思想張力,讓人們對人生的復雜性產生了極為豐富的聯想。當然,凄美愛情在歷史的不幸中誕生并不是為了解脫歷史的責任,它也不影響人們對于歷史的深刻反思,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它還強化了歷史反思意識,因為這種愛情無論怎樣令人贊嘆,但以這樣的付出作為代價畢竟是太大了,這不是正常歷史應有的意義。如果說,從審美的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歷史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但是從人生來說,這決不一種理性的選擇。從不幸歷史偶然結出的凄美結果中思索人生的悖論,既帶給讀者理性思考的力量,又令讀者領略到感性審美的愉悅,是《陸犯焉識》最令人不解也最讓人感嘆的地方。
二
悖論不僅是一種歷史現象,也是一種人性現象。幾乎每一個人生下來就有著自由的意志,向往著無拘無束的美好生活,但不幸的是卻經常陷入社會的或自造的束縛中,然而當你為這人生的不幸而痛苦時,卻發現其實你獲得了另外的自由,正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陸犯焉識》中的人物似乎都有著這樣的宿命,無論是那個“必須比壞人更壞,才能盡他的天職”的小弒母犯梁葫蘆,還是那個只有放棄愛才能得到愛的農場干部“鄧指”,以及他那個終于離開了農場卻因為不能適應外面的生活又回來到農場的兒子小三子。當然,最能表現這種人生悲劇的代表無疑是兩位主人公陸焉識與馮婉喻。
陸焉識是一個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知識精英,他從思想到行為都表現出了行使自由意志的無限渴求,然而生活卻使他每每放棄了自由,而選擇了束縛或囚禁,無論出自何種原因。這種內心欲求和外在行為之間的悖論或許讓人不解,但這卻是實實在在的。小說關于陸焉識人生選擇的悖論的敘述,主要是從三個層面展開的。第一個層面是陸焉識人生早期的愛情選擇,他熱愛自由卻身不由已或者說有意識地讓自己陷入了包辦婚姻。作為一個在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留洋博士,陸焉識是一個極度熱愛自由的理性之人,在學術圈存在著復雜派系斗爭的情況下,他可以堅決地選擇做一個只愿自由表達自己觀點,不與任何派系親近的獨立學者。但陸焉識又是一個情感細膩、對女性懷有悲憫情懷、內心柔軟善良的男人,因此陸焉識的愛自由在女人的眼淚面前只能是不徹底的愛自由,是打了折扣的,表現在家庭生活中就是他既追求自由,但面上他又不愿與親人發生沖突,最終總會依順親人。當陸焉識意識到眼前的馮婉喻正是恩娘馮儀芳想要掌控他而推薦給他當他妻子時,他不動聲色地進行反擊,他說出他打算考官費留學,但是面對恩娘無助的反應,陸焉識心即刻軟了下來,答應了恩娘的建議先結婚后留學。在這里,陸焉識的愛自由出現了悖論結局,他自愿屈服于束縛,而他俯就的是女人的眼淚和柔弱。包辦的婚姻使陸焉識既是恩娘表面順從的兒子,同時又是內心充滿了叛逆渴望的不羈的浪子。他以不冷不熱的態度對待妻子,以此來對抗強加于他的不自由的命運,甚至是一種自我欣賞式的反抗。在國外留學時與意大利姑娘望達的戀愛和在成都教書時與念痕的同居均因是他的自由選擇而令他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偶爾對妻子的親熱同樣是對抗恩娘鉗制的結果。第二個層面是陸焉識人到中年時的遭遇,身體遭到囚禁精神卻獲得了極大自由。1954年陸焉識被當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在大西北失去自由的監禁生活中,外在行為上的不自由卻使陸焉識的思維更加自由奔放,馮婉喻以家書的形式讓陸焉識知曉孩子們成長的點點滴滴,以此令陸焉識參與到家庭生活中來,在馮婉喻對過去點點滴滴的回憶絮叨中,作為記憶力的高手陸焉識開始回憶起馮婉喻的一舉一動,馮婉喻堅定的愛情表達使陸焉識有關她的記憶一天比一天生動起來,陸焉識意識到自己對妻子有著深厚的愛,為了告訴妻子自己的愛,他冒著生命危險謀劃并成功實施了一次逃跑。“他要告訴她,老浪子是冒著殺頭的危險回來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來的。他太愚鈍,那些眼神的騷情他用了這么多年才領略。”陸焉識智勇并用成功逃回上海,他冒著生命危險爭取了“自由”,但卻只是遠遠地看著妻子,在如影子般跟隨著家人,以此方式和他們一起生活了幾天之后,為了家人不受自己牽連,陸焉識自首,又被押送回了西北農場。第三個層面是人生的晚年,他終于獲得了自由卻重歸囚禁地。文革結束陸焉識被平反釋放,陸焉識結束二十幾年的直立獸的生活終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妻子身邊,然而妻子已經失憶。雖然陸焉識每天陪伴妻子,但他卻再也無法讓回到他們曾經的過去。作為一個會四國語言、記憶力超強、會盲寫的天才型知識分子,陸焉識一生渴求自由,然而在他身上卻不時出現阿爾都塞所謂的“主體”性,即“自由”地服從的特性,這種悖論現象的出現有外力作用下的被動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卻是體現了陸焉識天性中的善良、寬厚和他對親人無私的愛和付出。陸焉識執著自由卻總是選擇束縛,但是在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束縛中他卻又獲得了自由,這是他神秘的命運,還是其性格使然?《陸犯焉識》對這種難以言說的生命狀態的敘述是極其細致巧妙的,從某種意義上,沒有這種悖論式的敘事藝術,也就沒有陸焉識這個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
與陸焉識不同的是,馮婉喻則是在束縛的選擇中獲得了自由。馮婉喻之所以在她與陸焉識的愛情長跑中始終將自己拴在陸焉識的戰車上,是因為她把陸焉識愛成了“神”。在馮婉喻眼里陸焉識的天才資質放射出神性的光芒,在還未見到陸焉識之前她就早已為他的才學所折服。陸焉識十幾歲時在等家人看戲回家的時間就背下了小半本字典,十六歲被老師保送上大學,小小年紀就親政救下了馬上要被趕回娘家的繼母,這些不凡的事件使她在未見陸焉識之前陸焉識便成了她的“神”。因此雖然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前陸焉識從不對她親昵,馮婉喻卻欣然受之,“馮婉喻對陸焉識,不求親近的原因也在于她把他當神。對于神再喜歡都不能沒高沒下,有點距離是對的。”正是這種敬神心理使馮婉喻矢志不渝地愛著陸焉識,甚至為愛而做出背叛的事情。當陸焉識以自己流利的口舌為自己辯護而由有期徒刑改判死刑后,馮婉喻賣掉自家的房子,提著禮物一家家地敲門,在得知學生的家長戴同志正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而他又垂涎于自己的美色的情況下她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婦,她清楚地意識到:“她是找到獵人門上的獵物。”只要能救自己被判死刑的丈夫,馮婉喻不惜一切。她心里時刻想著陸焉識的安危,“她做戴同志的情婦是要他出高價的:背叛組織原則,把她死到臨頭的愛人陸焉識救下斷頭臺。”因此她會一點也不難為情地提醒壓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陸焉識的事情你要快點想辦法。’”馮婉喻愛陸焉識愛到能嗅出他的氣味,她有時驚異地想到:“一個人到了連另一個人的體嗅都認得出、都著迷的程度,那就愛的無以復加了,愛的成了畜,成了獸。”馮婉喻心中只有陸焉識,然而正是出于對陸焉識的愛她消弭了自己的尊嚴,做了戴同志加起來幾個小時的情婦,這種身體上對婚姻的不忠彰顯的卻是愛情本身,雖令人糾結痛苦,然而在某些異常情況下愛情就是具有如此的悖論性。最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是馮婉喻愛陸焉識時,陸焉識不愛她,而當陸焉識愛上馮婉喻時,馮婉喻卻已經無法感知他的愛情了。在此,我們不知道對馮婉喻的人生同情還是惋惜?然而無論抱有什么態度,我們都不能不為之深深感動。
三
《陸犯焉識》中的悖論似乎無處不在,它不僅是主人公始終擺脫不了它的夢魘,讓他不得不接受它的擺布,做出各種讓人無法通過正常的思維予以解釋的行為,充分展示了人性之“謎”之“惑”,也是小說文本結構中重要的邏輯線索,對整個敘事過程起著獨特的制約作用。嚴歌苓作為接受過美國大學文學寫作專門訓練并獲得寫作學位中最高的MFA學位的小說家,文學寫作技巧非常純熟,她“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就因為深諳文學之道在于怎樣講故事。看起來這是一個十分老套陳舊的說法,其實卻道盡了小說創作的真諦。綜觀近些年來在歐美成長起來的華裔作家,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他們都非常重視小說中的技術活,簡單的故事在他們的筆下風生水起波瀾叢生,而平淡的生活也有了思想的深度。《陸犯焉識》以時空交錯的方式敘寫了陸焉識的大半生,看起來“風云數十年,縱橫幾萬里”,舉凡男男女女,天堂地獄,精英罪犯,無不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世界上的事總是事與愿違,結局總與期待沖突構成了小說最主要的敘事模式。
陸焉識的形象無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創造,他的與眾不同,就是在期待與結果的悖論中敘述出來的。對陸焉識,讀者首先認識的是一個具有異常稟賦的天才型少年。陸焉識從小就是神童,是天才,他是妻子心中的“神”,是弟弟崇拜的對象,“我一直想,阿哥從小就那么天才,天底下的頂好的房子就應當給他住,頂好的汽車,就要給他開,頂好的吃的穿的,要給他吃給他穿,才公平。”而陸焉識的確才智過人,二十四歲留美博士畢業,精通四國語言,在國外就已寫了十六篇論文;大學西遷重慶后,他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全憑著記憶中的外國教課書去授課。然而作為一個天才少年、知識精英,他給人的期待卻與他實際所到的卻不符合:一方而確實很有才智,另一方面又經常表現出“無用場”。他因恩娘的眼淚果斷做主把即將被婆婆趕走的恩娘留在了陸家,但卻不得不接受恩娘強加給的妻子馮婉喻;他因為太聰明而不按照教育部審定的教材上課還寫諷刺文章,只能去重慶的牢獄蹲上幾年。1945年陸焉識從重慶回到了上海,因為堅持言論自由在重慶時被關押過兩年的經歷成為他找工作的“污點”,他只想憑本事吃飯,不懂得圓滑世故,因而屢屢碰壁,有個機會卻會因自己不愿受辱而放棄,他想到請凌博士幫忙推薦,因為凌博士在學術圈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凌博士亦明了他的學識能力,可是他卻想不到凌博士是個心胸狹窄之人,陸焉識傾盡全家所有精心準備了一桌酒菜,又請馮婉喻用娟秀的小楷寫好菜單,給每一道菜都起上一個別致文雅的名字,恰在那時卻有一群流氓來要接收陸家的房產,這時一直視陸焉識為心頭肉的恩娘忍不住說了一句:“焉識,真沒想到你讀書讀得這么沒有用場。”
經歷了漫長的農場勞動改造生活后,陸焉識終于獲釋回家,然而小說并沒有按照一般的思維邏輯給他安排一個家人終團圓,智力超群的他終于得到了家人、社會的尊重這樣一個幸福美滿的結局,而是由“老幾”變成了兒女口中的“老頭子”,擺脫了稱謂中的諧虐因素,但同樣的不敬依然存在。陸焉識有著優于一般讀書人的才氣,他也有讀書人的清高、尊嚴和在物質利益面前的不爭,這種不爭在許多時候“沒了用場”,陸焉識不但自己不爭,他還試圖勸說兒子也不要與女婿一家計較,結果兒子立刻回敬他:“我才不會跟你一樣沒用場!我一定要跟他們搞搞清楚的!”陸焉識在無力說服兒子、無處棲身的情況想只好留信悄然退出了兒女們的生活,回到了大西北那個他一心想要逃離的囚禁地。天才陸焉識獲釋后連一般人都擁有的平靜生活也沒有得到,而是因為自己的“沒用場”被排擠出局,這一悖論結局令人不禁對社會、歷史、人性進行深思,它是陸焉識的悲哀,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嚴歌苓曾經自言《陸犯焉識》是她的轉型之作,這種轉型表現在哪里,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悖論在這部小說中以如此鮮明的面貌出現,應當是其藝術轉型的重要表現。悖論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一種真實現象,雖然它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但在傳統的認知觀念影響下,人們似乎還沒有習慣于用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這一令有困惑的人生主題。悖論之與傳統觀念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并存等價矛盾含義的陳述”。在這樣的一種價值體系中,現實生活中互相并置的矛盾因素和對立關系并不必然地呈現出某種因果,反而會在不同的維度形成若干新的事件。悖論重在創造一個新世界,讓人們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挑戰傳統的觀念,從而引導人們獲得有關社會、人生及外部世界的全新認識。就此一點來說,《陸犯焉識》就足以得到讀者的尊重了。
魏李梅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房福賢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①②⑥廖昌胤:《西方文論關鍵詞: 悖論》,《外國文學》2012年第5期。
③轉引自王業昭:《解讀〈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的悖論與反諷――一種新批評的視角》,《四川理工學院學報》 ( 社會科學報),2008年第6期。
④⑤轉引自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