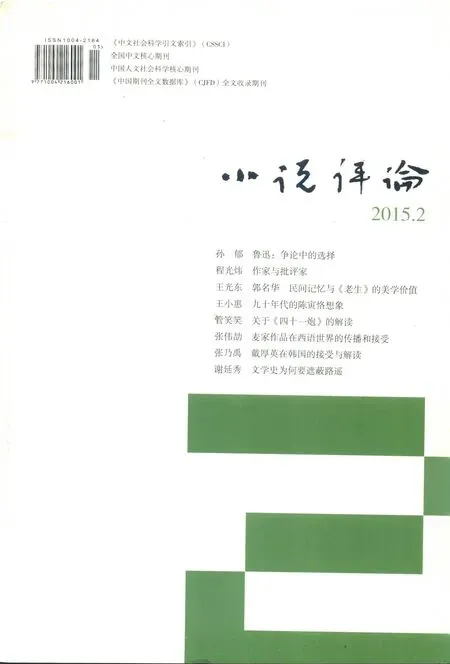從《上海是個灘》到《鹽道》
——李春平文學心路探析
楊明貴
從《上海是個灘》到《鹽道》——李春平文學心路探析
楊明貴
一、上海灘外來者生存敘事:獲得作家身份
李春平是一位有著文學信仰和敘事野心的作家。在這種信仰和野心的驅使下,他下決心要做魯迅筆下那棵直刺天空的棗樹,而非故鄉山洼中最常見的順勢鋪展攀爬的葛藤。自古至今,這樣的人也許注定要忍受孤獨、遭人謗訕。一位心膽赤誠、情志浪漫且帶有氣質上的敏感和憂郁的文學青年,在重視權謀操作和幫派界限的官場上的遭遇,大都是悲劇性的。李春平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說,李春平當年是帶著“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滿腹戾氣和“摧眉折腰事權貴”的自我厭憎逃離故鄉的。根據李春平的自述,從故鄉出走時,他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一腔豪情,相反,心理蓄積著的是“失魂落魄”的悲涼,甚至有“死在外面”的不祥預感。
李春平之所以去上海闖蕩,表面看是因為他為自己爭得了在紫陽縣駐上海辦事處履職的機遇,事實上,這是骨子深處有著強烈浪漫情結和自戀傾向的李春平遭遇感情危機和仕途瓶頸后,為自己精心設計的精神逃逸之旅。另一方面,出生并成長于中國西部陜南這一沉落地帶,在庸俗化、人情化、權勢化官場生態中飽受擠壓的李春平,對改革開放背景下以上海為中心之一,以自由、開放、公平為重要特質的海派文明有著近乎狂熱的向往。就這一點而言,李春平當年的選擇,投射出中國在加速開放進程的時代背景下很多與他境遇相似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惱和自救策略。
闖進十里洋場之初,李春平帶著興奮和貪婪去感知上海這個世界級都會的脈搏,也以一種近乎宗教式的虔誠去接受海派文明的洗禮。但是,他唯一真實的身份是寫作者。寫作者的理性思維和渴望被世界關注的天性,使他很快意識到自己事實上已沉陷于浮世喧囂和精神空洞之中。沖入上海灘的新鮮感和興奮感消褪以后,李春平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如何以文學寫作者的身份在上海站穩腳跟并放出光芒。李春平帶著山野世界中民眾那種樸素的“精明”,開始重新設計自己文學言說的策略和內容。李春平深知,作為一個外來的未入流的寫作者,要在上海文苑發出聲音、爭得位置,就必須設法融入上海庶民文化圈。只有如此,自己的創作才可能進入上海官方文宣部門和主流評論界的視界,也才可能得到他們的關注甚至獎掖。這是李春平為寄居上海的自己量身制定的身份崛起路徑。《上海是個灘》、《上海夜色秀》、《玻璃是透明的》等小說及長篇報告文學《辭海紀事》等作品,就體現出了李春平的這種敘事企圖。
上海期間的幾部小說作品,基本上都設置了“外來者”的敘述視角,寫的主要是外來者“在上海的愛與恨、夢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在人物塑造和情節架構方面,李春平有意地斂束批判的鋒芒,盡力使文本世界中那些發生在上海灘的尋常故事能釋放出上海人的善意和溫情。毫無疑問,就接受效果而言,這幾部作品都成功了。通過以文學敘事的方式表達一個外來的寫作者對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認同甚至熱愛,這一有利于上海城市形象包裝與宣介的寫作立場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上海主流媒體關注和支持。在上海文學界還沒來得及認真打量這位闖入者的時候,上海的官方媒體和文學評論界就已經非常慷慨地賜予李春平“著名作家”的頭銜了。可以說,李春平成名于上海,緣于他的創作素材和敘述內容與上海庶民文化實現了強有力的對接。
受江南傳統文化和近現代西洋文明的共同塑造,上海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審美指向——古典與現代相映,雅致與時尚兼容。同時,由于在中國近代以來經濟和政治發展進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上海文化及上海人骨子深處可謂傲氣逼人。上海人迷戀的是經濟文化和城市身份上優人一等的自我感覺,他們不習慣甚至是不屑于關注自我在他者眼中的形成的鏡像。李春平上海灘題材小說中的“外來者”形象雖然承載有向上海文化及上海人示好獻媚的敘事功能,但文化上自我優越感強烈的上海人對這種有意為之甚至是帶有某種功利主義動機的敘事策略是不以為然的。同時,“外來者”的敘述視角一旦程式化,勢必導致接受疲勞,進而使一度形成媒體關注熱潮的“李春平現象”在上海文藝界歸于冷寂,或者使李春平本人歷經艱辛后獲得的“著名作家”的身份被其他外來者制造的新的上海灘題材文學寫作潮流吞沒。
二、官場政治文化生態敘事:提升市場人氣
21世紀前十年,是市場化背景下中國式官僚和市儈文化恩愛相攜、風光快活的十年。一方面經濟數據高歌猛進,另一方面官商關系魚水相依。亦官亦商、官商結合而形成的權貴集團迅速崛起并固化。加之意識形態領域多元化、自由化局面的進一步顯現,民眾開始普遍關注中國官場政治文化生態現狀尤其是領導權力運作的流程,對涉及權力尋租、權色交易、香艷緋聞、黑白人生之類的官場故事,更是表現出近乎狂熱的接受興趣。官場,是這一時期最具市場人氣、最受大眾期待的小說題材。在作了這樣一番市場評估和判斷以后,李春平便積極地加入到已初具流派效應的官場小說家的陣營。
從2003年至2008年,李春平創作完成了《奈何天》、《步步高》、《領導生活》、《玫瑰花園》共四部官場題材的長篇小說。此外還完成同類題材的中篇小說《讀古長書》、《良辰美景奈何天》、《把人做成一朵花》、《我男人是縣長》、《市長的父親》、《一路飆升》等。其中很多作品都獲得了良好的市場收益和接受口碑。尤其是《步步高》,被譽為“中國第一部關注執政智慧和領導藝術的長篇小說”。在這一時期,李春平憑借自己創作產量和市場聲譽,迅速成為官場小說潮流中的一員悍將。李春平官場題材的作品大都圍繞這樣一個問題展開敘事:當公權力遭遇個人私情的時候,領導者該如何把握一個理性的尺度。李春平官場敘事中的領導者在這一問題上的掙扎和抉擇,被部分評論者認為是對官場文化心理的全息透視。通過揭秘執政智慧和領導藝術,李春平的官場小說強烈地投射出政治和領導的魅力。李春平在官場小說領域橫空殺出并大放異彩,不僅提升并鞏固了他在中國文壇的地位,而且也使他真正成為在中國當下文壇和官場都釋放出了話語影響力的文化人物。
就才情氣質而言,李春平是一個純粹的文人。當年的文學青年變成政府秘書,并由此開始長達十年的官場生活。現在看來,這簡直就是人生中的一場意外。文人眼中的深邃和敏銳,使他看清了權力帷幕內部的爭斗和算計;文人胸中的悲憫和孤直,又使他厭憎官場上的貪虐慵惰、蠅營狗茍者。李春平由農村青年躋身官場,實屬幸運,身邊艷羨者有之,謗議者有之。但其襟抱卻始終在官場之外,其內心也始終近乎天然地抗拒官場法則。這樣的人在官場上不獲于上、不容于群、不信于友的悲劇性境遇,可謂命中注定。對這樣的人來說,官場生涯,其實就是誤落塵網,自囚樊籠。李春平與官場之間的這段悲情姻緣,既為他的官場敘事提供了豐厚扎實的素材儲備,也使他能持客觀冷峻的立場打量官場眾生相。
在聚焦官場生存圖譜的過程中,李春平使用的是一種存在心理距離的敘述話語。這樣的敘事立場,使李春平官場小說所揭示出的官場政治文化生態顯示出了一定的深廣度和真實性。和其他一些官場小說家相比,李春平在塑造領導形象時已成功突破了臉譜化、模式化的窠臼,使領導者真正成為“有血有肉,有精神和肉體欲望的個體”。就品行做派而言,其筆下的領導者大約可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以《步步高》中古長書和《領導生活》中鄭嘯風為代表的楷模型領導,他們恪守官德,踐行善政,正氣逼人,心系民生福祉,勇于改革創新,他們是黨和國家的脊梁;第二種是以《奈何天》中楊子晨為代表的才子型領導,他們睿智儒雅,熟諳官場之道,但因浪漫多情,往往“失身”于紅粉,進而導致聲名受污、仕途終結;第三種是以《玫瑰花苑》中羅達順為代表的貪腐型領導,他們貪求官祿,一心鉆營,挾權肥私,受賄獵艷,最終畫皮剝落,難逃黨紀國法的制裁;第四種可被稱之為政客型領導,他們熱衷追逐權勢,精于厚黑之道,擅長制造派系之爭,視公權為私器,爭名位不擇手段。《領導生活》中的鄭永剛、《玫瑰花苑》中的女干部葉沙就屬于這一類型。領導干部政客化,是馬克主義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頭號敵人。同時,李春平的官場敘事還傳導出官場文化方面的基礎知識,厘清了大眾容易混淆的一對概念,即領導藝術和政客權術。政客權術的本質是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未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而“把人做成花一樣……讓反對你的人理解你,讓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讓支持你的人忠誠你,讓忠誠你的人捍衛你。允許有人不喜歡你,但絕對不能讓他恨你,如果有人恨你的話,那就讓他怕你”,則是對領導藝術的經典概括。
總之,李春平的官場敘事,沒有沉淪為攀貴諂勢媚權的一劑春藥,也沒有變為執政黨反腐倡廉的傳聲筒。李春平從普通人性的視角審視官場領導者心理深處的困惑和掙扎,拂去了籠罩在官場上空的神秘詭譎的色彩,以工筆細摹的方式繪制出一幅交織著理想信念和紅塵私欲的中國當代官場風俗畫。這幅風俗畫既投射出官場生活的魅力,又觸發了大眾對當下官場政治文化生態的沉思。從這一層面看,李春平絕沒有忘卻文學的現實使命。可以說,投射出現實主義光芒的李春平官場敘事,是本世紀官場小說的重要收獲。
三、秦巴鄉土歷史文化敘事:尋找文學之根
2011年以來,李春平的文學事業在外界看來似乎進入了蟄伏狀態。作為秦巴作家群中一位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作家,李春平這一歷時近三年的寫作空窗期,一度引發了關注他、愛護他、崇拜他的各方朋友的焦慮甚至不安。很多人都試圖打探出李春平寫作停滯的原因。接受者的這種集體反應,生動地反映出李春平在陜西文學界的地位。地域歷史題材的長篇力作《鹽道》的問世,證明了這次蟄伏是宏大的寫作欲望在重重阻塞中的艱難升華,是寫作身份完成華麗蝶變前的痛苦蛻蛹。李春平攜《鹽道》與讀者見面,重新成為文學界的焦點人物。可以說,“這不是所謂的回歸,而是李春平蓄謀已久并最終實現了的自我突圍。”
經過三年多的沉淀過濾和醞釀培植,《鹽道》在體現出李春平一貫的真誠細膩、清新靈動的敘事風格的同時,更強烈地濡染出李春平回望秦巴歷史播遷時洶涌于心底的激動、感傷與悲涼。敘事風格的變化,強烈地釋放出一種信號——從懸浮于十里洋場到扎根在秦巴故土后,李春平拂去了都市寫作、官場寫作曾經帶給自己的光鮮和榮耀,暫時終止了對都市精神洪荒、官場權力生態的講述;真正開始拒絕煽動食色化化、權力化生存欲望的膨脹,徹底清除了以往敘事中存在的玩賞和艷羨欲望饗宴的精神雜質。
從展開《鹽道》創作構思開始,李春平便用生發于靈魂中的深沉和悲憫打量秦巴、觸摸故鄉。他帶著返鄉赤子的自覺和焦灼,長時間地沉潛于秦巴地域的歷史長河,尋覓著文學言說的靈感與激情。在斑斕而混沌的秦巴歷史畫卷中苦苦探求,他渴望發現秦巴歷史進程中最為真實和動人的文化符號,并以此作為打開秦巴生民精神記憶的鑰匙。李春平最終找到了這個符號,那就是攸關秦巴民生的鎮坪鹽道及曾經行進、掙扎于鹽道上的鹽背子們的愛恨苦樂、命運變奏。以鹽背子們這個一百多年前秦巴庶民社會最底層的生存群體為描摹對象,以背鹽世家崔無疾家族中父子、夫妻、兄弟關系的發展演變為敘事主線,同時,通過穿插巫術場景、匪事活動和生產勞作、飲食起居、鹽業生產、集鎮販售方面的民俗剪影,李春平最終不僅藝術地還原出能展示出秦巴地域文化精髓和秦巴生民精神筋骨的鹽道歲月,也成功地繪制出一幅十九世紀后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的秦巴歷史風俗畫卷。從這個層面上看,李春平又一次成功了!誠如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所總結的:“這部小說還原了鎮坪古鹽道上跋涉者的風采,寫出了傳統美德的光亮,達到了一定的審美高度,是一部具有純正精神指向和歷史文化內蘊的佳作。”一部厚實的《鹽道》,浸潤著李春平筆耕的心血、感恩的淚水、虔誠的期望。《鹽道》的問世,使秦巴這一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和文化的沉落地帶,在中國現代以來鄉土文學敘事的場域中又多了一幅屬于自己的文學鏡像。《鹽道》的傳播,使秦巴尤其是陜南的鎮坪,在本地域以外的民眾的文化視界中,不再只是四省交匯處的一片深山野洼,不再只有文化的貧瘠和浮薄。在鹽道的盛衰變遷和鹽背子們的悲歡吟唱中,在山野苦難群像和地域精神筋骨的塑造中,李春平完成了對秦巴山水、人情、風習的忠實記錄和審美巡視,秦巴山野中的人性美、自然美、文化美得到了強有力的提煉與展示。在推進秦巴文化建設事業、豐富秦巴文化底蘊、解析秦巴文化特質、美化秦巴地域文化形象方面,李春平和他的《鹽道》做出了積極貢獻。
縱觀李春平的創作歷程,《鹽道》體現出了兩個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題材重大,在秦巴歷史文化變遷中有著特殊地位和價值的鹽道生活、鹽道文化首次在中國當代文學敘事中得到了全面而具象的呈現,這對秦巴地區的歷史文化及社會轉型研究將產生推動效應;二是轉型成功,通過搜掘扒梳、融匯整合秦巴地區重大的歷史文化素材,精心建構秦巴特別是陜南在文學敘事中的地域形象,李春平在陜西乃至中國當代以來的鄉土歷史敘事中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位,“這充分體現了李春平作為多面作家的能量和潛質。”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鹽道》是李春平寫作題材轉型過程中的拓荒之作,加之李春平在審視秦巴歷史畫卷時還存在視角上的盲區,所以《鹽道》在文本架構方面還存在歷史文化視野不夠開闊、人物生存場域單一、空間視域比較模糊、人物形象的差異性不夠突出等問題。相信這些問題在以后同類題材的創作中能得到有效解決。
結 語
從寄居上海到返歸故鄉,在二十年的文學征程中,從書寫上海灘外來者生存故事到聚焦官場政治文化生態,再到追攝秦巴地域歷史文化播遷,李春平文學言說的對象不斷地發生著轉換,他在文學題材方面反復上演著驚險的跳躍。與之對應,李春平的文學身份也不斷地被評論界重新界定。繼上海灘新生代作家、官場作家這些頭銜之后,《郎對門唱山歌》尤其是《鹽道》的問世又將迫使評論界為李春平設計新的身份標簽。李春平似乎樂于制造關于自我文學身份真相的謎題,這充分說明了李春平的敘事自信和文學野心。鄉土文學是現代中國文學賴以成長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根基,民間視域下的鄉土歷史敘事是探尋中國文化根脈的重要途徑,鄉土作家是中國現當代文壇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群體。我們有理由相信,《鹽道》的創作,是李春平創作生涯中的一次尋根之旅;《鹽道》是一部有根的小說,《鹽道》的問世標志著李春平決心把自己的文學之根扎在故土之上、秦巴之間。從《上海是個灘》到《鹽道》,李春平的文學人生找到了根也扎下了根。有了文化的、精神的根系,文學之樹必會枝繁葉茂并繼續結出靈果。真誠地希望扎根于故土的李春平將來能以中國當代著名鄉土作家的身份繼續放射文學的靈光,繼續為讀者制造閱讀的驚喜。
楊明貴 安康學院
注釋:
① 李春平.《李春平自述〈激動得很累〉》[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1:18.
②吳紅艷.《官場文學,一個特有的文學現象》[N].中國圖書商報,2009-11-3.
③在當前學術界,“官場小說”至少是一個有歧義的概念。孫郁認為:“什么叫‘官場小說’不好回答,大概描寫了官場沉浮、政治風云的小說可屬于此類范疇。”轉引自王軍:《官場文學:火爆中的冷思考》,《記者觀察》2003年8期,第23頁。也就是說,只要是描寫官場的小說都可以稱作官場小說。事實上,多數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
④宋先紅.《真實而理想的“領導生活”》[J].小說評論,2008(3):152.
⑤ 李春平.《步步高》 [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
⑥⑧戴承元. 《轉型與蛻變》[N].安康日報,2014-11-6.
⑦ 雷達. 《大道至簡——長篇小說〈鹽道〉的文化情懷》[N].光明日報,201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