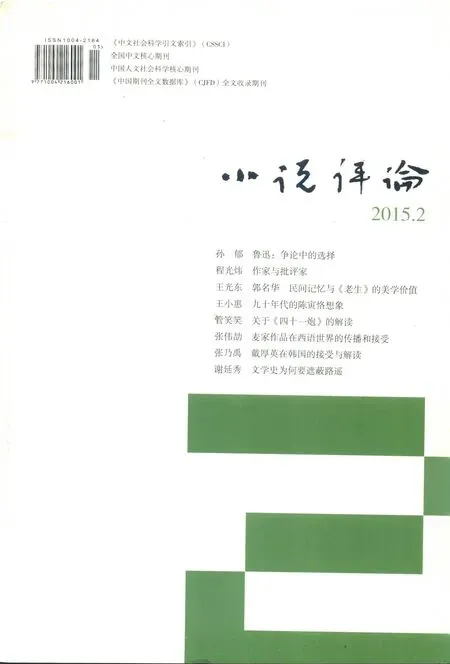論蘇童“少年敘述”及其文學史意義
宋 雯
論蘇童“少年敘述”及其文學史意義
宋 雯
一、蘇童創作中的“塞林格”影子
“少年敘述”在世界文學中由來已久。英國文論家戴維·洛奇在研究《麥田守望者》時,將塞林格獨特的敘述文體一路追溯到馬克·吐溫,稱其為“少年侃”,并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做了如下解釋:“少年侃”用來指代某種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口語體小說形式。”里面的少年主人公用一種新鮮的眼光來透視周圍的世界,展現自己的心理以及諷刺成人世界的虛偽,文本中充滿著口語,俚語甚至黑話。事實上,塞林格的小說塑造了許多少年人物形象,選取少年視角書寫了少年在青春期的困惑、彷徨、孤獨等復雜的心理,而這種風格對蘇童的創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蘇童曾坦言:“對于美國作家塞林格的一度迷戀使我寫下了近十個短篇,這組小說以一個少年視角觀望和參與生活,背景是我從小長大的蘇州城北的一條老街。”他的這些少年敘述小說,大都以青春期少年為主人公,講述他眼里發生的一切,關注的重點即是少年自身的青春成長——這點和塞林格的相關創作是一致的。同時,塞林格的語言風格同樣影響著蘇童。他談到:“對我在語言上自覺幫助很大的是塞林格,我在語言上很著迷的一個作家就是他,他的《麥田守望者》和《九故事》中的那種語言方式對我有一種觸動,我接觸以后,在小說中的語言上就非常自然地向他靠攏,當然盡量避免模仿的痕跡”。
塞林格對蘇童的影響是全面且深遠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少年視角和敘述語言,還有時代背景模糊、故事情節的淡化零散化、靈活的時空轉換、自由穿越的時間修辭、關注個體成長、重視對細節的還原等。但是蘇童并不只是對塞林格的簡單重復,和塞林格相比蘇童小說中的少年敘述有著其更多自身特點:
其一,成人立場更突出。
雖然在塞林格和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中,都存在著兩個“我”,即一個是追憶往事的敘述主體“我”,另一個是往事中的作為被敘述者的經驗主體“我”。這兩個“我”,構成了兩個人在不同時空的相互對話。但塞林格《麥田守望者》的文本整體建構于霍爾頓17歲時對16歲一小段人生經歷的自敘性回憶,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的年齡差距小,這就使得兩者敘述眼光的重合處大于兩者的相異處,遮蔽了隱含作者的成年立場。而在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里,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的年齡跨度比較大,他常在小說中點明敘述人的成年人身份,比如:“那時候我還沒長大,要是長大了這些事情也沒有了。”(《金魚之亂》) “現在我能編一些像模像樣的小說,就得益于那時想象力的培養。”(《桑園留念》)所以在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里,他經常以成年人的口吻發表評論,這就使得成人立場顯得更加的明顯。這樣的好處是拉開讀者、人物和敘述者的距離,以客觀冷靜的姿態調控著人物主體的感傷姿態和矯情姿態,就好像一個人不動聲色地對待另一個人的悲泣哀號,洞見其內心的暗疾隱患,這種情感態度的反差,往往會產生更大的張力。其二,敘述語言的陌生化。
在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中,除了師法塞林格在文本中運用口語和黑話外,他還擅于運用感覺化的語言和新奇的比喻,如:“太陽猶如破碎的蛋黃懸浮于銅尺山的峰巒后面。”(《我的帝王生涯》)“其聲哀怨凄愴,似一陣清冷之水漫過宮墻。”(《我的帝王生涯》)。此外,蘇童對于詞匯超常規的操作組合也是其敘述語言陌生化的一個很大原因,“或者把抽象概念事物化或者運用多重感覺復合,或者用動賓不調式,或者用矛盾形容法,或用詞與表現對象的不等式,作者在語言的實驗上可以說是十八般武藝全使上了。”在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中,像“華麗流暢的驚雷”、“墮落的骯臟的火焰”這樣的詞匯組合隨處可見,令人回味無窮。其三,敘述策略的多樣化。
較之塞林格,在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中,敘述策略顯得更為多樣。首先在視角上,也許是因為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年齡跨度較大的緣故,蘇童的視角轉換更加靈活,除了在敘述中成年敘述人經常跳出來發表議論之外,在他的長篇小說如《河岸下篇》中“名人”“人民理發店”這兩節,敘述者完全擺脫了主人公庫東亮視角的限制,變成了一個全知敘述人。其次在修辭手段上,除了比喻隱喻象征等手段的大量應用,蘇童還擅于運用移情,比如在《傷心的舞蹈》里,“我”哭了,“我”看到的油菜花也是傷心的,在《我的帝王生涯》里,因為菊花總讓“我”聯想起死人,所以在我眼里,菊花“都是一片討厭的散發著死亡氣息的黃顏色。”再次,蘇童作品中的人物對話多取消了標點符號,這就使得小說人物與敘述融為一體,在閱讀和感官體味上更加的流暢。二、蘇童“少年敘述”的文學史價值
中國文學中的“少年敘述”可追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早運用少年(少兒)視角的小說當屬魯迅的《懷舊》、胡也頻《小人兒》等,在1930年代,則有張天翼的《蜜蜂》、魯彥《童年的悲哀》以及一些京派作家小說,以及凌叔華的《小英》、《八月節》,蕭乾的《鄧山東》、《籬下》等。到了1940年代,在東北作家群的“童年回憶體”小說中,少年視角更是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如蕭紅的《呼蘭河傳》、駱賓基的《幼年》、《少年》,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等,它們多以少年兒童的視角去追憶故土和已經逝去的歲月,形成了文學史上少年視角小說的高潮。
這些少年視角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第三人稱居多,且作為敘述者的少年多為旁觀者。如蕭紅的《呼蘭河傳》,端木蕻良的《初吻》等作品就以“童年時期的作者”為主人公,擷取作者一段童年往事,利用他的眼光與感受去發掘出別樣的成人世界。這批少年敘述作品有著共同的敘事特征——遠離宏大敘事、冷靜客觀的敘事口吻、情節的淡化和零散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和印象化、平淡淺白的流水賬式語言、擬人手法的大量運用等。這些特征在蘇童的少年敘述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不過除此之外,作為當代作家的蘇童還有著和現代少年敘述小說不一樣的特點:
其一,成人立場的表現方式不同。
在現代作家的少年敘述中,雖然也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回憶“我”的童年和少年時的往事為主,但那個成年的“我”往往被隱藏了起來,不直接露面。但作為成人的作者在面對以少兒視角建構的文本時,不可能完全不做任何的介入,尤其是當這些作者“返回到自己的童年”時,成年人的姿態總會禁不住流露出來。雖然沒直接露面,讀者也能感受到彌散在小說的敘述中的成人情緒。但蘇童的少年敘述小說則大都采用了“往事追溯”的模式,用了明顯的雙重視角,成年敘述者的聲音經常直接出現在作品中,“那時候”、“當時”、“多年以后”這樣的詞時刻提醒著讀者兩個“我”的存在,相對于很多現代的少年敘述作品,成人立場表現得更為直接。其二,更加多元的敘述策略。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視角轉換更加的靈活。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都是以“限知”少年視角貫穿全文,但在蘇童的少年敘述作品中,視角轉換更加的靈活,雖然總體保持了第一人稱“限知”的少兒視角,但有時也不完全嚴格受第一人稱視角的局限,常為了服從敘述的需要走進別人的內心世界,而這種轉換非常靈活;另一方面則具有更為突出的時間意識。因為蘇童“少年敘述”小說中的成人立場比現代文學中的少年敘述作品更加直接,因此敘述時間在保持整體敘述線性發展的基礎上運用了多種時序,順敘、倒敘和預敘交替進行。這種語式使“敘述作為獨立的一種聲音與故事分離,故事不再是自然主義的延續,敘述借助這種語式促使故事轉換、中斷、隨意結合和突然短路。”這樣的敘述無形中起到了制造懸念的作用。其三,“少年侃”式的敘述語言。
現代少年敘述小說中的敘述人形象,往往年紀較小,都是單純稚嫩天真活潑的,都是以簡單美好的少兒世界映襯復雜丑惡的成人世界,因此敘述語言是比較平淡淺白的,句式較簡單,多語詞和句子間的重復,如“桃花也是白的了櫻桃花也是白的了,杏花也是白的了,李子花也是白的了”(《初吻》第152頁)。而在蘇童小說中的少年敘述中,敘述人以處于叛逆時期的青少年居多,少兒世界總是給描寫得充斥著反叛和暴力,同時因為受塞林格的影響,蘇童的敘述語言充滿著口語、俚語和黑話,和現代文學少年敘述的平淡淺白大為不同。三、蘇童“少年敘述”的獨特性
新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運用少年視角進行創作,少年形象也由現代文學中單純天真的孩童變得更加多元,除了天真爛漫的兒童,更多的是處于不同時代和各種成長環境中的叛逆的青少年。總體來說,在中國的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寫作者采用少年視角進行文本敘述的方式并不屬于主流創作方法,嚴格意義上的少年敘述更為少見,但是使用少年敘述的作品在敘述語言、敘述策略等方面都展現出別樣的特點,豐富了當代創作的形態。除了蘇童的《傷心的舞蹈》、《金魚之亂》等部分“香椿樹街少年系列”,以及《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稱得上少年敘述外,莫言的《四十一炮》、王朔的《動物兇猛》、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在細雨中呼喊》、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等作品也都屬于當代“少年敘述”小說的代表。
這些小說都發表于80年代中期之后,它們并不以對社會歷史的史詩性表現見長,而是更關注自身的成長經驗,關注人性和欲望。不同的是,王朔、莫言、遲子建等作家僅有的幾部“少年敘述”作品都帶有自傳的性質,有著個人親身經歷的影子,而蘇童的“香椿樹街”系列作品,雖然也與他親身經歷分不開,但時代背景更為模糊,外部歷史時間的交代只是為小說制造某種氛圍而添加的標簽而已。如果說,從“香椿樹街”系列的少年敘述作品我們還能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那么,《我的帝王生涯》無論從主人公還是歷史背景都純屬蘇童的虛構了。張學昕直接指出:“蘇童小說的審美、敘事方式的獨特性,就在于想象創造了他文學世界的無窮魅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蘇童小說中的少年敘述表現更為多樣,這種手法,用蘇童自己的話說就是一種“歷史勾兌法”。他說:“我隨意搭建的宮廷,是我按自己的方式勾兌的歷史故事,年代總是處于不詳狀態,人物似真似幻……”蘇童對于歷史的絕對真實性持懷疑態度,“他把歷史的客在現象提煉為文化、人性和生存的歷史“要素”,然后再將它們勾兌還原為歷史的敘事,這樣在具體講述中他既獲得了想象和虛構的自由,同時又在實際上更接近了歷史的本原。”
這些“少年敘述”作品都遠離了宏大敘事,除了都運用了“往事追溯”的模式、雙重視角(少年視角和成年視角)之外,還都具有線性時間的打亂,情節碎片化,重視細節描寫等特點。這就使得王朔的小說呈現出一種幽默、詼諧、玩世不恭的敘述風格;出生年代和蘇童離得最近,同為“先鋒派”主要干將的余華,雖然嚴格意義上的“少年敘述”作品不多,但在敘述語言、敘述策略方面,表現出了和蘇童更多一致的特征,如都喜歡運用比喻、移情、象征等修辭手段,視角轉換都很靈活,但余華的“少年敘述”小說也有著自己的特點——比如余華擅于設置與日常現實有著相當明顯距離的敘事語境,給人荒誕的“陌生化”的感覺,這和蘇童擅于用語言來營造敘述的陌生化效果是不一樣的。通過比較我們看出不同的作家的少年敘述有共通的地方,但各自又呈現出不同的美學風格。
四、蘇童與80后作家中的“少年敘述”
由于人生經歷的局限,在“80后”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關注社會歷史的宏大題材,他們的寫作題材,多為自己身邊的事情,或者是通過想象創造的世界。“少年敘述”作品在這些80后作家里隨處可見,如韓寒的《像少年啦飛馳》、郭敬明的《幻城》、李傻傻的《紅X》、張悅然的《桃花救贖》和《葵花走失在1890》等。在這批作家的少年敘述中,韓寒的敘述風格以幽默諷刺為主;而更多的則如張悅然、郭敬明在敘述則專注于個人情感的孤獨、憂傷、焦慮,敘述風格是憂傷哀婉唯美的,他們更接近于蘇童的美學風格。張悅然曾在《幻城·序言》表示:憂傷的敘述是“80后”對于純真被永久埋葬的一種紀念形式。
總的來說,“80后”作家的少年敘述,在追求敘述話語的陌生化和敘述策略的多樣化方面,和蘇童等前輩作家是比較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的創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他們的小說題材相對狹窄,敘述多專注于個人情感的孤獨、憂傷、焦慮;(二)他們在敘述中過分沉湎于自我,抒情是“敞開式”的,顯得缺乏節制,給人矯情的感覺;(三)故作老成,不管是用華美的詞藻裝飾干癟的情節,用滿不在乎的語氣嘲笑傳統的價值觀念,還是用著意樸素乃至寒愴的零度敘述復現場面,都不能完全褪去少年學說大人話的夸張口氣;(四)在敘述中缺乏“成人—外視角”的參與,使得小說缺少深度和張力,缺乏一種復調的美學效果,暴露出作者生活經驗的空洞以及自我反思意識和歷史意識的缺失;(五)原創性的缺失,而這種不足在文本的敘事模式中表現的尤為明顯,那就是框架與情節的復制。
楊俊蕾認為:“中國當前文學寫作中的少年敘述可分為兩類,一是成年作家自覺地選取少年敘述的方法,另一種是年輕寫手在寫作發軔期自然地采用少年敘述。”蘇童無疑是前一類作家的代表,他的少年敘述都是回溯性的,作品的外在形式是成年敘述者的回憶,內在肌理卻是少年講述者的當下經歷,這就造成了多個時間敘事層面的重疊,浮現在文本表層的是未經世事的少年視角,而歷經滄桑的的成人視角始終隱含其中,與之并行不悖、輪流切換。應該說,蘇童自覺意識主導產生的少年敘述在比那些缺乏經驗和閱歷的80后作家具有更為深邃的話語指向。成熟的自覺意識導向深入歷史的反思,揭示了復雜的人性,賦予了作品的思想性和哲學性。
余 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蘇童“少年敘述”小說的獨特風格主要體現在其驚人的想象力、意象化的語言、舒緩柔婉略帶感傷的敘述語調以及敘事策略的多樣化等方面,塞林格對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但更多的是他有著自己的創新,他極大的豐富了中國少年敘述的樣態。而和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蘇童小說中的少年敘述是最多的,種類也是最豐富的,在小說的形式方面也可謂獨樹一幟。他對80后作家的影響是深遠的,從新生代作家代表郭敬明、張悅然等人的少年敘述作品中,無論是敘事語調、敘事話語、敘事風格還是敘事策略,我們也都不難看到蘇童的影子。
宋 雯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注釋:
①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王峻巖等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②蘇童:《尋找燈繩》,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版,第116頁。
③林舟、蘇童:《永遠的尋找—蘇童訪談錄》,《花城》1996年第1期,第105-111頁。
④季進、吳義勤:《文體:實驗與操作—蘇童小說論之一》,《當代作家評論》1990年第1期,第100-108頁。
⑤陳曉明:《無邊的挑戰》,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頁。
⑥張學昕:《蘇童小說的敘事美學》,《呼蘭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第53-57頁。
⑦蘇童:《蘇童文集·后宮》,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⑧張清華:《天堂的哀歌—蘇童論》,《鐘山》2001年第1期,第197-205頁。
⑨⑩楊俊蕾:《當代寫作中的少年敘述》,《文藝研究》2006年第11期,第19-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