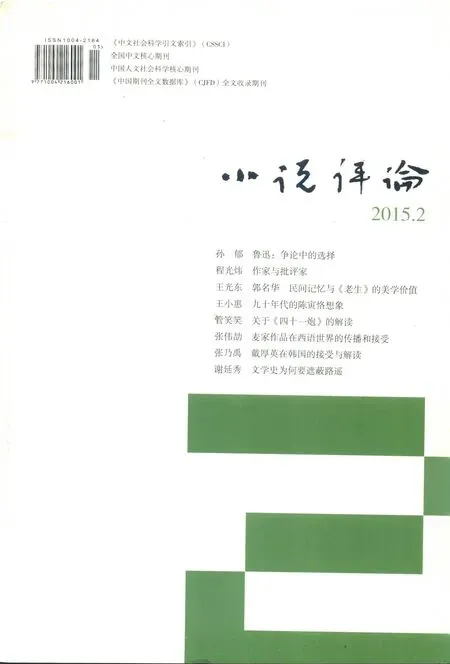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母親的風月》與女人的戰爭
黃立華
《母親的風月》與女人的戰爭
黃立華
一
讀完畢非一的小說《母親的風月》(《鐘山》2015年第2期),首先想到的是它很像當年的“傷痕文學”。細看之下,才發現它與傷痕文學的不同:這不是政治賤民的簡單的受難史,而是一個女人的性別戰爭——小說中說母親是“一個堅強的戰士”就是一個確鑿的證據——是用身體作為武器、性交易作為手段的女性戰爭。
母親高圓圓與趙立的關系,不是簡單的愛情,更不是簡單的性欲沖動,而是一場性別戰爭的啟動。高圓圓與趙立見面的場景,是高圓圓面對著趙立的槍,這是一個真實的場景,更是一個象征: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那個時代最經典的表述;槍桿子不僅是政治權力的象征,更是男性的象征。那一時刻,高圓圓面對的是權力象征與男性象征的雙重壓力。高圓圓與趙立見面的那一晚,村子里在放映電影《紅色娘子軍》,那是女性戰爭——階級斗爭——經典故事;而高圓圓和趙立上演的是女性戰爭的另一個版本。可以說,高圓圓與趙立的遭遇,固然是意外的遭遇,卻也包含了精心的策劃和布局,高圓圓對趙立的愛情,其中包含了性別政治的目的:是高圓圓這個政治賤民尋求自我保護的一種本能選擇:趙立不僅是同胞、同鄉、同學、男性,更重要的身份是軍烈屬的子弟,是政治良民。高圓圓發起這場旨在自我保護的戰爭的目的,是想加入政治良民的隊伍,最低限度是要尋求軍烈屬的保護。只可惜,無論高圓圓如何聰慧,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她所設計的劇本很快就被時代的大戲所扭曲。她和趙立的關系,變成了父親“反革命”的罪證,而她的身體也迅速被雄心勃勃的政治暴民——趙德生所占有。于是高圓圓發動了第二場戰爭:對趙德生的復仇之戰,仍然是以身體為武器,誘惑了高柏年,結果卻是:高圓圓受到了殘暴的輪奸。
高圓圓的戰爭非但沒有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反而讓父親因此而死,更可怕的是,它還導致了一個更為可怕的后果:女兒小青與趙德生之子趙兵的相識、交往所萌生的陰影,那一刻,高圓圓的恐懼和絕望到達極點——她不僅擔心女兒的早戀,也不僅擔心女兒“破處”,更擔心的是,女兒與趙兵存在亂倫的風險!
從小說的開頭我們就知道,高圓圓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值得探究,那時候已經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地主子弟的政治賤民身份符咒被解除,大地回春,高家莊也恢復了人間氣象。但,當她恢復人的身份,同時也恢復了人的良知,無法忍受自己的過往,更無法忍受女兒與趙兵亂倫的未來,這無情地宣告:高圓圓的戰爭以徹底慘敗而收場。
二
高圓圓的戰爭失敗,與“浩劫”后高家莊的人文生態密切關聯。簡單說,當年的高家莊處于文化荒漠化的極端時刻。“文革”的邏輯,是要把高松年作為階級敵人批斗——不是因為高松年有罪惡而要批斗,而是因為高松年被命名為“地主”而要羅織他的罪名、完成對他的批斗。這樣的政治邏輯,為趙德生這樣的政治暴民的登場創造了機遇:此人別出心裁地創造了“高松年反革命案”,一舉完成了對鄉村政權和美女高圓圓的雙重占有。這時的高家莊已經步入文明退化的軌道。作為退化的標志,高家莊的村民們再也不敢阻擾對高松年的批判,再也不敢對高松年表達正常的人間情感。此時,高圓圓的自然身份是美女,政治身份是賤民,在高家莊,高圓圓既是“圖騰”、也是“禁忌”,所到之處,常被熾烈的欲望灼傷,同時又被恐懼厭憎的冷漠所困,如此反差巨大的目光塑造了高圓圓,挑起了高圓圓的戰爭,也注定了高圓圓的戰爭必然的失敗結局——高家莊的村民已經進一步退化為野蠻人,并很快出現原始部落的野蠻風景:美女高圓圓被村民輪奸,而施暴者是一群野蠻的“無名氏”。
小說中講述了高圓圓的父親高松年的故事,作為歷史敘事,高松年的故事顯得單薄、甚至一廂情愿;但作為象征,高松年的的知恩圖報和有情有義,無非是作為“他是一個人”的確切能指:當年的高家莊是一個正常的人間世界,高家莊的村民也都有人性、人情和人味。即使是在“文革”開始時,高家莊村民對待高松年的態度,也仍然延續了鄉村人情標準:高松年有恩于鄉土,鄉親們也報以寬宏。也就是說,高松年的故事,是作為高家莊文明退化的象征性參照。
作為退化的另一標志,革命后代趙立并沒有膽量保護自己的情人,很快就“逃跑”了,意味深長的是,趙立的“逃跑”甚至也可說是“變節”行為是在其母親的壓力下完成的,母親成了兒子的男性身份的閹割者。雖然,母親和父親將兒子命名為趙立(趙立、趙起兄弟之名是“立起”即“雄起”之意)。
此時的高家莊,“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唯一的“男兒”,反倒是敢作敢當、至死不悔的強奸犯趙德生。趙德生是政治投機者、無良惡棍、強奸犯,但在這部小說中,此人并非簡單的惡的符碼,因為他也敢做敢當,且致死也不后悔他對高圓圓的“愛情”——這當然是原始人愛情。此時,高家莊已退化為缺乏現代人氣的原始人部落,母親為什么會在聽了趙德生臨死前對她說的話后,先是“愣住,然后嚎啕大哭”,其中也就充滿了一言難盡的意味。
三
在《母親的風月》中,還有另一場女性戰爭,即女兒小青的青春期反叛。這場戰爭的不同尋常之處,是戰爭的緣起:母親高圓圓檢查女兒的處女膜,從此女兒變成對母親、父親、老師及整個學校體制發起反抗——“不斷地想操臟話罵娘,摔東西,我想像一頭母獸一樣,嘶喊,叫,咬,甚至,殺人。”
女兒的反抗,并非尋常的青春期典型癥候,而是母親高圓圓的戰爭的后遺癥。在女兒的記憶中,母親是疏離的,甚至,她對母親只有一個書面化的“母親”概念,而“媽媽”卻說不出口。雖然,女兒不知道母親的經歷,更不懂得母親對她與趙兵亂倫的恐懼,但檢查處女膜的粗暴行為讓女兒感到巨大的羞辱和傷害,從此與文明教育的理想即與人格的尊嚴和完備背道而馳。小說的結局,是小青繼續母親的反抗方式,繼續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反抗的武器,即使明知與趙兵的性關系可能導致亂倫的風險,但仍然不想停止其冒險反抗的旅程。小青的反抗戰爭,不僅是母親高圓圓的女性戰爭的繼續,也有與母親的戰爭有相似的走向:不是走向女性的精神自覺,而是走向濫用身體的權利;不是走向女性的尊嚴,而是走向性的墮落和冒險;不是走向性愛的文明,而是走向性愛的蠻荒。在很大程度上,女兒的反抗戰爭,比母親的反抗戰爭更加殘酷,也讓人更加目不忍睹。因為,女兒所生活的時代已經是人道恢復的世界,不再存在政治扭曲和文化退化的外在社會壓力。女兒的經歷,只能說是母親宿命的繼續。如此,小說的思想主題就進入了另一個深度層面,這也是《母親的風月》與過去的傷痕文學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四
母親高圓圓和女兒小青兩代女性的反抗和戰爭,確鑿是性的戰爭,也是女性的戰爭,它是不是女性主義的戰爭?這還是一個問題。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使用女性主義觀點審讀和評價這部作品的沖動,但仔細掂量之后發現,很難用既有的女性主義思想模式套裁和解讀這部作品:高圓圓和小青的反抗,確然是女性受難的故事,確然受到了男性中心社會及男權的壓力;但這對母女的反抗,卻明顯缺乏真正明確的性別政治和性別文化的精神訴求。換言之,母親和女兒的反抗,沒有“主義”,也缺少“精神”的意涵,也就是說,這里只有生物性別(sex)意義上的戰爭,卻沒有社會性別(gender)意義上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她們的反抗戰爭,是盲目的,甚至是蒙昧的;更可怕的是反抗的后果,會走向進一步的盲目,和進一步的蒙昧。高圓圓和小青的性別戰爭故事,與西方女性主義精神有明顯的區別。這區別,應該與高家莊的人文生態密切相關:這是一個未經啟蒙的村莊,一個文明退化的村莊,也是一個亟待人道精神照耀和人性康復治療的村莊。或許,這也正是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或許我們不應要求小說去擔負女性主義精神闡釋的義務,而應該在故事層面、形象層面和人物心靈層面去勘驗女性的深刻創傷,并以此作為女性主義訴求的證詞。
黃立華 安徽黃山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