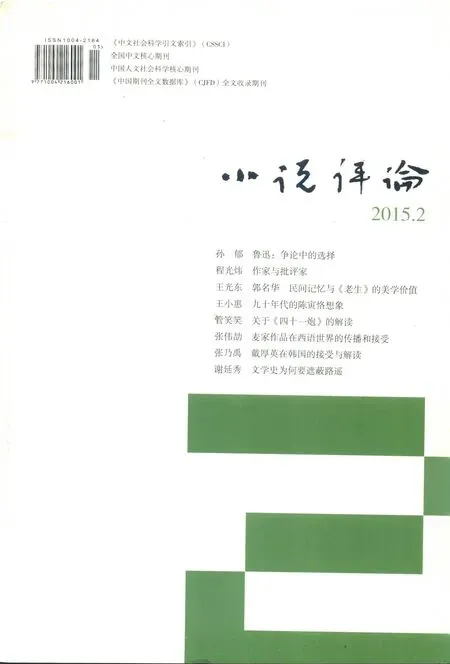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解密》的“解密”之旅
——麥家作品在西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
張偉劼
《解密》的“解密”之旅——麥家作品在西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
張偉劼
在本世紀中國文壇升起的新星中,麥家無疑是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不僅收獲了多個重要文學獎項,也憑借其小說作品的改編引領了近年來中國大陸“諜戰劇”的熱潮。2014年,麥家的名字和形象開始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繼其初版于2002年的成名作《解密》在英美世界廣獲好評之后,2014年6月,麥家開啟了他親身參與的作品海外推廣之旅,首站選擇的是西班牙,隨后到訪墨西哥和阿根廷,在這三個擁有深厚文學傳統的西語國家推動《解密》西文版的發行。該書由西語出版界巨頭行星出版集團(El Grupo Planeta)發行,3萬冊的首印數和12.5%的版稅率,以及規模龐大的廣告投入和造勢活動,是當代中國作家在海外難得享受的待遇。從西語世界各大媒體的報道和文學評論界的反應來看,《解密》得到了高度的認可,有力地提升了中國當代文學在西語國家的認知度。麥家作品在西語世界的初獲成功,是否預示著中國文學海外譯介的一些新趨勢呢?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來說,麥家及其作品的西語世界之行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啟示呢?
一、原本與譯本
事實上,首部翻譯成西班牙文的麥家作品并非他的成名之作《解密》,而是《暗算》。該書從中文到西文的翻譯由一位中國譯者與一位西班牙譯者合作完成,系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與行星出版集團的首度合作,于2008年8月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亮相。不過,行星方面雖已簽約引進,卻“因翻譯的版本不理想便擱置了計劃”,這部小說并未成功走入西語世界。2014年在西語世界引發關注的《解密》西文版,則是從該書的英譯本轉譯的。以下我們將集中討論這本書的中文原版和西文版。
盡管我們無法確定,麥家的海外巡回推廣之旅從西語世界開始,是否是出于作家的個人感情因素,但作家與西語文學的因緣之深卻是無法掩蓋的。麥家曾在國內的訪談中承認,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是他的“精神之源”。《解密》一書的開頭就引用了博爾赫斯《神曲》中的一句話,似是作為對故事的帶有神秘主義意味的預告:“所謂偶然,只不過是我們對復雜的命運機器的無知罷了。”《解密》圍繞情報與密碼的題材探討人生哲理,而博爾赫斯的著名短篇小說《小徑分岔的花園》(又譯《交叉小徑的花園》,以下簡稱《花園》)亦將形而上學的思考融于偵探小說、間諜故事的形式之中,二者之間似有隱密的師承關系。如果我們細讀文本的話,還能在《解密》中發現更多的博爾赫斯的影子。比如在故事中,希伊斯給主人公容金珍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句子:
“現在,我終于明白,所謂國家,就是你身邊的親人、朋友、語言、小橋、流水、森林、道路、西風、蟬鳴、螢火蟲,等等,等等,而不是某片特定的疆土[..]”
試比較《花園》中,主人公的一段心理描寫:
“我想,一個人可能成為別人的敵人,到了另一個時候,又成為另一些人的敵人,然而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即螢火蟲、語言、花園、流水、西風的敵人。”
這兩段話都涉及國族身份認同的問題,前者是一位猶太裔流亡科學家的獨白,后者是一個為德國人賣命的中國間諜的獨白,其相似度是顯而易見的。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對博爾赫斯的作品,麥家已爛熟于心,以至于能在寫作中不經意地引用;或許我們可以認為,麥家是以這樣一種隱秘的方式向博爾赫斯致敬。
另外一方面,如果單看《解密》第一篇的話,我們似能找到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名著《百年孤獨》的影子。這一篇是容金珍家族歷史的敘事,簡直是一個微縮版的《百年孤獨》:一個家族相繼幾代人的人生經歷、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對本土固有文明的沖擊、超自然現象的涌現、夢與現實的奇妙關系等等,無不是《百年孤獨》同樣涉及的題材。而作家本人也曾對西班牙記者坦言,《百年孤獨》是他最鐘愛的書籍之一。
考慮到《解密》與西語文學的這種不解之緣,《解密》西譯本的書名是耐人尋味的。不同于英譯本的直譯(Decoded),西譯本將書名定為El don,意為天才、才能。據作家本人說,西譯本的這一改動給了他“一個驚喜”,他欣然接受。從動詞“解密”到名詞“天才/才能”,《解密》在西語世界中的這個新名凸顯了故事主人公的悲劇命運。作家本人或許沒有想到,“El don”會令人聯想起博爾赫斯最有名的詩篇之一:Poema de los dones(《關于天賜的詩》),同樣是以don這個詞為題。對于西語讀者來說,如果稍作提示,從書名中就可以隱約感知到這兩位作家間的師承關系。
遺憾的是,《解密》的西譯本系孔德(Claudia Conde)從英譯本轉譯的,在這種雙層的過濾中無疑會遺漏一些東西。如前文提到的小說開篇引自博爾赫斯的話,2002年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版和2009年的浙江文藝出版社版均保留有此句,然而在西譯本中卻找不到這句引言。前文提到的與《花園》文本中相似的句子,在西譯本中則變成了:
Ahora por fin he comprendido que cuando la gente habla de “su país”se refiere a su familia, sus amigos, su idioma, el puente que atraviesa cuando va a trabajar, el riachuelo que pasa cerca de su casa, los bosques, los caminos, la suave brisa que sopla del oeste, el rumor de las cigarras, las luciérnagas en la noche y ese tipo cosas, y no una extensión particular de territorio rodeada de fronteras convencionales[...]
試比較《花園》中相應的原文:
Pensé que un hombre puede ser enemigode otros hombres, de otros momentos de otros hombres, pero no de un país: no de luciérnagas, palabras, jardines,cursos de agua, ponientes.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段西文之間并不存在可以被認為有所暗合的地方,像“螢火蟲”“流水”“西風”這樣的詞,在從博爾赫斯的西語原文到中譯本、再從麥家的中文小說“回”到西文語境時,變成了另一種說法,使得《解密》與《花園》間存在的互文性關系受到了破壞。從這點上說,《解密》的西譯本并不完美。
我們如果再仔細對照中文原本的話,可以發現,這個西譯本并不是非常“忠實”的,在很多地方采取了照顧到譯入語讀者口味的歸化譯法。我們試比較幾個案例:
1、原文:在真人不能屈尊親臨的情況之下,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譯文:Si Mahoma no iba a la monta?a, entonces la monta?a tendría que ir a Mahoma.(如果穆罕默德不前往大山,那么大山就自己來找穆罕默德)
2、原文:有點塞翁失馬得福的意思
譯文:Fue como agacharse para recoger una semilla de sésamo y encontrar una perla.(這就好比彎下腰來撿一粒芝麻籽,結果發現了一顆珍珠)
3、原文:福兮,禍所伏。
譯文:La buena suerte depende de la calamidad y viceversa. Lo bueno puede venir de lo malo, y lo malo, de lo bueno.(好運依附于厄運,反之亦然。好事可以從壞事中來,壞事也可以從好事中來)
在例1中,譯者憑空插入了一句西班牙諺語,以方便讀者理解情節。在例2中,本應是一條中國成語的地方,西譯本中又是一條西班牙諺語,讀者自然能無障礙理解,原文籠罩的中國傳統哲學的韻味卻消失了。在例3中,譯者似乎是在不厭其煩地解釋這句來自《道德經》的名言。在小說原文中,這句話是作為“榮金珍筆記本”的獨立一節出現的,而“榮金珍筆記本”一章的安排頗具先鋒文學的實驗意味,從中西經典中借用了不少資源,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學價值,因此,譯者對這一句話的翻譯處理同樣破壞了原文本與經典文本之間存在的互文性關系,或許,在忠實翻譯的基礎上加注說明該句出處的做法更為妥當。
目前,與英語世界和法語世界相比,西語世界的漢學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漢學家人數稀少,很難找到像葛浩文、陳安娜這樣的在中國文學譯介方面富有經驗的譯者,這樣的現實與使用西班牙語的龐大人口并不相稱。直到今天,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仍主要是從英譯本或法譯本曲折進入西語世界的,這無疑為這兩個世界的文化交流多加了一層隔膜,而由中國和西語國家譯者合作翻譯的模式還有待檢驗。雖然《解密》獲認可、《暗算》遭挫折的事實并不足以說明前一種模式優于后一種模式,卻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策略的選擇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參考。
二、傳播策略
單昕在探討中國先鋒小說的海外傳播方式時指出,從先鋒小說開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漸與國際出版操作規律接軌,作為文學生產的產品而不再是政治宣傳品走向市場。西方出版社和代理人的主動出擊、作家的明星化、作品的文集化等都表明著傳播方式的轉型。麥家作品在西語世界的傳播就體現出這種中國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產品進入國際出版市場的新趨勢。經由中西出版方的合力運作,麥家作品得到了全方位的推銷,實現了中國作家與外國新聞界、文學界與讀者群之間的良性互動。“誰是麥家?你不可不讀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這是西班牙出版商印在馬德里公交車上的廣告語。“誰是麥家”隱藏的信息是,在2014年之前,麥家在西語世界幾乎無人知曉,不像莫言、蘇童、王安憶這樣的在西語世界已有作品譯介、具備或大或小的名氣的中國作家。后一句廣告語則極盡夸張地鼓吹麥家的文學地位,制造一種爆炸式的幻覺,仿佛麥家作品是一個剛剛被發現的新大陸。麥家在西語世界知名度的迅速提升,絕不僅僅是作品質量的原因,也絕不僅僅是其作品與西語文學關聯度的原因。用布爾迪厄的文化生產場的觀念來看,“構建名譽”的不是單個的名人或名人群體,也不是哪個機構,而是生產場,即文化生產的代理人或機構之間客觀的關系系統,以及爭奪神圣化壟斷權的場所,這里才是藝術作品的價值及價值中的信仰被創造的地方,也就是說,藝術作品是有著共同信念和不等利益的所有卷入場生產的代理人們(包括作家、批評家、出版商、買家和賣家)共同完成的社會魔力運作的結果。盡管麥家在西語世界的迅速“走紅”有助于提高中國文學界的集體自信,也是增強民族自豪感的好事,在考察這一案例時,我們仍應保持審慎的目光。
前文提到,麥家作品的西譯與推介,系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與行星出版集團的首度合作。事實上,在此之前,五洲傳播出版社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將中國當代作家成系列地譯介到西語世界。如該社已經推出了劉震云的《手機》《溫故一九四二》這兩部暢銷小說的西文版,并運作了劉震云訪問墨西哥之行。與外方出版社的合作無疑能大大增加中國文學作品打入國際市場的勝算,畢竟在發行渠道、對本地讀者口味的把握、與當地媒體的溝通乃至作家和作品的形象設計等方面,外方出版社具備更豐富的經驗。麥家作品首度進入西語文學市場就是掛靠在西語世界出版巨頭行星集團名下,且與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同列著名的“命運”(Destino)書系,即已在其通往“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的道路上成功了一半。五洲——行星的合作或許標志著一種新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模式的誕生:將中國出版社對本國文學現狀的熟稔與外方出版社對其傳統經營領域的掌握這兩大優勢結合起來;中國出版社推出的外譯中國文學作品在接受國際市場的考驗之前,先接受外方合作出版社的考驗。
作家親身參與作品的海外營銷,也可視為麥家案例的一大亮點。我們可以從各大西語媒體的報道中看出,既然作家本人能與西語世界的記者、讀者、評論家乃至同行面對面交流,麥家的形象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其個人經歷與《解密》主人公的經歷及故事背景被有機地纏繞在一起。密碼的主題、神秘的東方、深不可測的中國軍隊等等,無不成為激起西語讀者窺秘心理的元素。在作者與文本的互動中,作家本人則成了窺秘目光的聚焦所在,這位沉默寡言之人的舉手投足都令記者和讀者充滿好奇。《解密》西文本的五洲傳播版(中國國內發行)和行星-命運版均附有作者簡介,用的是同樣的作者照片,我們試比較二者文字的不同:前者共151個西班牙語單詞,簡單介紹了作者的作品概貌、寫作風格和所獲獎項;后者則長達309個西班牙語單詞,超過前者字數的兩倍,在介紹作者所獲獎項和作品概貌之前,先以足夠吊人胃口的方式介紹作者生平:“他當過軍人,但在十七年的從軍生涯中只放過六槍”、“他有三年時間住在世界的屋脊西藏,在此期間只閱讀一本書”,“他曾長時間鉆研數學,創制了自己的密碼,還研制出一種數學牌戲”……所有這些都與小說主人公容金珍的經歷暗合,在作家的真實人生與文本的虛構人生之間建立起引人一探究竟的內在關系。由此可見,西班牙出版商將麥家形象的建構納入到一個由作家神秘人生、故事文本和作家現身說法共同構成的體系中。西班牙文學界的加入則使麥家世界級作家的地位獲得了進一步的認可:知名作家哈維爾·希耶拉(Javier Sierra)在馬德里參與《解密》的發布會,將容金珍比作西班牙人熟知的堂吉訶德;另一位知名作家阿爾瓦羅·科洛梅(álvaro Colomer)在巴塞羅那的亞洲之家(Casa Asia)與麥家展開對話。就這樣,《解密》作者的西班牙之行亦成了一次解密之旅:解作品的密,也解作家的密;作家闡釋作品,作品也闡釋作家,創作者與創作文本之間形成了富有神秘主義意味的互動。
可以預見的是,繼麥家之后,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走出國門參與自己作品的宣傳,藉此也更為近距離地加入到與外國文學的互動之中,而作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與否,將會是多方合力的結果。
三、西語世界的接受
如果說麥家作品在中國往往被貼上“特情小說”或“諜戰小說”的標簽的話,在進入西語世界時則被納入了另一種認知模式。在西班牙最重要的在線書店之一的“書屋”(Casa del libro)的網頁上,《解密》被歸入“偵探敘事——黑色小說”的類別中。西班牙新媒體“我讀之書”(Librosquevoyleyendo)發布的專訪報道也是這樣評價麥家的:“他向我們證明,黑色小說之王的稱號并非由北歐人獨享。”
“黑色小說”(novela negra)是從偵探小說(novela policíaca)中發展出來的一個門類。根據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的定義,黑色小說是這樣的一種文學:記錄一個處于危機之中的社會,以一種對現實世界保持批判的眼光揭示人性的幽暗一面,多有道德層面的追問但并不作道德說教。也就是說,黑色小說不僅僅是玩弄懸疑和推理的游戲,也致力于作社會批判和探討人的內心沖突,將商業文學的魅力與嚴肅文學的關懷結合起來。在西班牙當代文學中,黑色小說崛起于1975年隨著獨裁者佛朗哥的去世而到來的文化解禁時期。經由巴斯克斯·蒙塔爾萬、加西亞·帕翁和愛德華多·門多薩等作家的努力嘗試,黑色小說成功地將偵探小說帶入高雅文學的領地,成為西班牙當代文學中的一大重要體裁。近幾年,隨著瑞典的亨寧·曼凱爾(Henning Mankell)、冰島的阿納德·因德里薩森(Arnaldur Indrieason)、挪威的喬·奈斯堡(Jo Nesb?)等這些北歐偵探——犯罪系列小說作家被西班牙出版社引進后的風行,黑色小說正在西班牙讀者群中享受前所未有的熱捧。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文化版2014年7月的一篇評論就指出,黑色小說在西班牙獲得了太大的成功,有必要擔心如何避免盛極而衰了。由此可見,一旦把《解密》一書納入黑色小說的類別中,這本中國小說就趕上了黑色小說的熱潮,盡管它并不完全符合黑色小說的定義。麥家的系列作品會不會繼續貼著“黑色小說”的標簽在西班牙上架,是否會達到像北歐作家那樣的歡迎度,將有待時間給出答案。
很可能為《解密》一書在西語世界的受寵起作用的另一個因素,是引發全世界持續關注的“棱鏡門”事件。斯諾登何去何從、美國的監聽網到底覆蓋了多大的范圍、信息時代的公民究竟有多少隱私可以保留,成為全世界熱議的話題。《解密》的故事涉及情報、間諜、信息戰,恰好契合了西方世界公眾的興趣。在被墨西哥記者問起《解密》與斯諾登事件的關系時,麥家稱,“可以理解,斯諾登事件有助于刺激國際讀者對我的書產生興趣”。他接著指出,“斯諾登事件對于所有人是一個警示。也許我們從沒有想到會存在這樣的事實,但事實就是如此,情報活動無處不在,不管在哪個國家,我們的隱私和秘密已經無處可藏。當《解密》與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熱點問題聯系起來時,這部作品也就真正超越了中國本土的邊界。
在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相信一個神話: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推介到國外的中國文學作品首先應當是包含了最本土化、最能代表中國特色的題材的作品。于是,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中國文學的看點和賣點成了諸如文革、一夫多妻、農村問題等“特色”題材,契合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想象。在與我們同為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作家們也曾普遍相信類似的神話,極力在作品中展現被賦予了魔幻色彩的本土民間文化。博爾赫斯就曾批評過這種傾向,他在探討阿根廷文學的傳統時指出,“整個西方文化就是我們的傳統,我們比這一個或那一個西方國家的人民更有權利繼承這一傳統”。博爾赫斯自己的創作就完全不受本國題材的束縛,游走于全世界各種文化之間,而作為博爾赫斯的私淑弟子,麥家在《解密》中也游刃于東西方文化之間,甚至多次引用《圣經》的段落,并沒有表現出對“本土化”“中國性”的刻意追求。在全球化時代,“本土化”已然是一個神話,約翰·斯道雷在審視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概念時指出,環繞全球的人口和商品流動把全球文化帶入到本土文化中,它明顯地挑戰了本土確立的文化邊界觀念;全球文化表現出一種游牧的特性。《解密》的故事背景不僅有中國歷史,也有世界歷史:納粹德國迫害猶太裔知識分子、以色列建國、冷戰等等,都成為麥家的文學虛構游戲的資源,而譯者的進一步加工處理(如給原故事中沒有名字的洋先生安上一個像模像樣的名字,給波蘭猶太人希伊斯換上一個典型的波蘭姓氏:Lisiewicz)則邀請全球讀者一同加入猜測故事人物是否確有其人的游戲中。中國作家大量取用西方文化的資源,同樣可以成就一部獲得全世界讀者認可的小說,而這也代表了全球化時代本土的邊界消弭、文化雜交形態加速形成的趨勢。西班牙《公正報》就為《解密》給出了這樣的評論:“這是一部卡夫卡式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道家的小說。[...]在小說的最后部分,卡夫卡和維特根斯坦應著道家和禪的節奏翩翩起舞。”或許,麥家走出國門、接受外國記者采訪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隱喻:中國文學完全可以跨越固有的傳統邊界,與世界展開對話。
從西語世界對《解密》的接受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對中國文學的聚焦不再僅限于政治。以往中國當代文學在進入西方世界時,往往被當作了解中國政治社會現實的文本,其美學價值被社會批判價值所遮蔽,而后者往往被故意夸大。比如許鈞就曾指出,在法國主流社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學價值受重視的程度要大于其文學價值,中國文學對法國文學或其他西方文學目前很難產生文學意義上的影響。我們可以注意到,盡管西語世界對《解密》的解讀仍不乏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指涉,但更多的關注則集中到文學層面,對敘事技巧、語言風格、主題思想的興趣超過了對中國政治的興趣。吉耶莫·羅恩的評論文章就勸誡讀者: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說,而小說就是小說,不要嘗試在其中尋找對任何一個國家表現出的政治同情傾向。哈維爾·貝爾托西則指出,盡管《解密》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政治批判力度,這并不妨礙讀者從書中獲得一種愉快的、引人深思的、尤其考驗智力的閱讀體驗。莫妮卡·馬利斯坦從文明與野性的角度來考察書中主人公的命運,指出天才的悲劇在于文明對野性自然的壓制;對于一個從小自由生長在與人類社會隔絕的環境中、有著超常能力的人來說,文明世界不啻為一個地獄。麥家在《解密》的敘事中對中國古典小說技法的借用也引起了評論者的興趣,盡管評論者并不一定能意識到這種敘事特色師承于何處。如沙維爾·貝爾特蘭就指出,“整個故事的編排技法精湛[…]所有的章節都帶有一種富有魔力的節奏,激發讀者在看完這章時迫不及待地要進入下一章。[…]也許,評價這部小說的最準確的詞就是‘非典型’。”所謂“非典型”,就是西方讀者鮮有見識過的講故事的方式。由此可見,麥家從章回體小說中借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式的敘事技巧也獲得了西方讀者的認可。
總的來說,作為一名中國作家,麥家在西語世界是迅速成名的,出現誤報、誤讀也在所難免。在西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經常能找出撰稿人的失誤,如按照西語姓名的習慣把“家”當作麥家的姓氏,搞錯麥家這位浙江作家的出生地——或是“富陽省”、或是安徽省……可見西語世界對中國仍缺乏足夠的了解。麥家在接受阿根廷記者采訪時也指出,《解密》之所以在中國首版十多年后才被譯介到西方,主要還是因為東西方交流的不對等,“在中國,我們非常注重引進西方文學,任何一個知名作家都在中國有翻譯出來的作品,而中國作家的作品要被翻譯成外文,則要困難得多。[...]中國作家仍然處在一個邊緣的地位,而我是幸運的。”麥家的“幸運”是否也能成為更多中國作家的“幸運”呢?從麥家作品在西語世界的命運中,我們可以得到不少積極的啟示。
張偉劼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注釋:
①高宇飛:《麥家:西方不夠了解中國作家》,《京華時報》,2014年6月25日,A27版。
②王懷宇:《麥家作品“遠嫁”歐洲》,《青年時報》,2013年8月25日,第10版。
③史斌斌:《麥家——西班牙語文學市場上一個嶄新的“中國符號”》,國際在線,2014年7月25日,http://gb.cri.cn/4 2071/2014/07/25/6891s4629693_1.htm
④徐琳玲:《麥家,一個人的城池》,《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35期。
⑤麥家:《解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另見麥家:《解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
⑥???麥家:《解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33頁至第134頁,第3頁,第147頁,第264頁。
⑦見豪·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王央樂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75頁。
⑧Aurora Intxausti: Mai Jia, el espía chino de los 15 millones de libros, El País, 26.06.2014. http://cultura.elpais.com/ cultura/2014/06/24/actualidad/1403617161_754164.html
⑨Karina Sainz Borgo: Mai Jia:“Hay escritores que opinan, pero la literatura es superior a la política”, Voz Populi, 28.06.2014.http://vozpopuli.com/ocio-y-cultura/45592-mai-jia-hay-escritores-que-opinan-pero-la-literatura-es-superior-a-la-politica
⑩Mai Jia: El don, traducción de Claudia Conde,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2014, p197.
?Jorge Luis Borges: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見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I, RBA Coleccionables, Barcelona,2005, p475.
???Mai Jia: El don, traducción de Claudia Conde,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2014, p11, p217, p264.
?單昕:《先鋒小說與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之轉型》,《小說評論》,2014年第4期。
?高宇飛:《麥家:西方不夠了解中國作家》,《京華時報》,2014年6月25日,A27版。
?皮埃爾·布爾迪厄:《信仰的生產》,見Thomas E.Wartenberg編《什么是藝術》,李奉棲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9頁。
?麥家:《解密(西班牙文)》,孔德譯,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4年。
?Mai Jia: El don, traducción de Claudia Conde,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2014.
?Guillermo Lorn: “El don” de Mai Jia, Las lecturas de Guillermo, 30.07.2014.https://laslecturasdeguillermo.wordpress.com/2014/07/30/el-don-de-mai-jia-seudonimo/
?見“亞洲之家”官網:http://www.casaasia.es/actividad/detalle/213640-presentacion-de-la-novela-el-don-de-mai-jia
?見“書屋”官網:http://www.casadellibro.com/libro-el-don/9788423348060/2293278#
?Entrevista a Mai Jia, Librosquevoyleyendo, 7.7.2014.http://www.librosquevoyleyendo.com/2000/07/entrevista-mai-jia.html
?La novella negra, Instituto Cervantes,http://www.tetuan.cervantes.es/imagenes/catálogo2ecoacoplado.pdf
?Inmaculada Pertusa: Emma García, detective privada lesbiana: la parodia posmoderna de lo detectivesco de Isabel Franc, Revista Canadiense de Estudios Hispánicos, oto?o de 2010.
?Juan Carlos Galindo: El éxito mortal de la novela negra, El País, 09.07.2014.http://cultura.elpais.com/cultura/2014/07/08/actualidad/1404826359_583177.html
?Héctor González: “China se está volviendo irreconocible”: Mai Jia, Aristegui Noticias, 07.07.2014.http://aristeguinoticias.com/0707/lomasdestacado/china-se-esta-volviendo-irreconocible-mai-jia
?博爾赫斯:《阿根廷作家與傳統》,見博爾赫斯:《博爾赫斯談藝錄》,王永年等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約翰·斯道雷:《作為全球文化的大眾文化》,見陶東風編《文化研究讀本》,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7頁。
?José Pazó Espinosa: Mai Jia, El don, El Imparcial, 20.07.2014.http://www.elimparcial.es/noticia/140163/Los-Lunes-de-El-Imparcial/Mai-Jia:-El-don.html
?許鈞:《我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法國的譯介》,《中國外語》,2013年第5期。
?Guillermo Lorn: “El don” de Mai Jia, Las lecturas de Guillermo, 30.07.2014.https://laslecturasdeguillermo.wordpress.com/2014/07/30/el-don-de-mai-jia-seudonimo/
? Javier Bertossi, Tres apuntes sobre El don, Ojo en Tinta, 21.08.2014.http://www.ojoentinta.com/2014/tres-apuntes-sobre-el-don-de-mai-jia/
?Mónica Maristain: Mai Jia y el don de la literatura, Sinembargo, 04.07.2014.http://www.sinembargo.mx/04-07-2014/1046399
?Xavier Beltrán: El don de Mai Jia, Tras la Lluvia Literaria, 08.07.2014.
?Dolores Caviglia: Entrevista a Mai Jia, La Gaceta Literaria, 20.07.2014.http://www.lagaceta.com.ar/nota/600115/la-gacetaliteraria/vivi-estado-abandono-escribir-se-convirtio-necesidad-fisiologic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