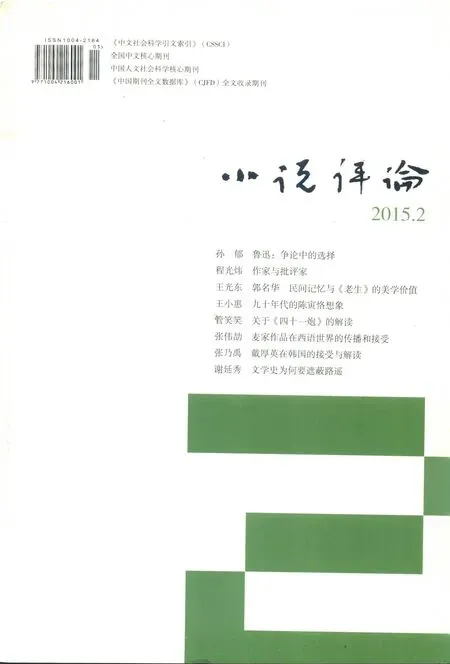當時間化為肉身
——關于《四十一炮》的解讀
管笑笑
當時間化為肉身——關于《四十一炮》的解讀
管笑笑
自2004年《四十一炮》問世,迄今已歷整整十年。雖然在問世之初它也引起過一些反響乃至批評,但與其它作品相比還是顯得過于寥落了些。作為一個比較特殊的讀者,我對這部作品確有些偏愛,有些心得,所以這里想舊事重提,與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對這部小說的解讀,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現代文明棄兒的歸屬
《四十一炮》以上世紀90年代初充滿變革動蕩的鄉村為背景,通過一個“炮孩子”羅小通的敘述,給讀者講述了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的悲歡離合。羅小通的母親務實能干,緊跟時代潮流發家致了富。而羅小通的父親羅通則不能“與時俱進”,最終因難以忍受妻子與人通奸的恥辱,殺死了妻子,鋃鐺入獄。羅小通則成了孤兒。十年蹉跎后,羅小通流落到故鄉附近的一個破落不堪的五通神廟里,試圖用敘述來打動老和尚,讓他收自己為徒。
在《四十一炮》中,莫言再次發揮了他撒豆為兵、化陳腐為神奇的講故事的能力,用濃墨重彩的語言,虛虛實實煞有其事的腔調,將一個尋常的家庭倫理故事,演繹為一場肉味撲鼻熱鬧非凡的敘述狂歡。
有論者言及,“肉體和欲望是構成莫言小說最重要的兩大元素。欲望的來源是肉體,肉體歸屬于物質,莫言小說的核心構成,其實是物質。”這一說法不盡全面,但確乎有其道理,肉體書寫與歷史的關系確屬討論《四十一炮》繞不開的話題。
其實早在《紅高粱家族》中,作家就表現出了“返回現代之前”的文化與美學意圖,人物的感性生命時時流露出的原始與狂野的氣質,余占鰲的一泡尿就釀出了絕妙的好酒,這當然是寓言化的表述方式。按照巴赫金的說法,拉伯雷的主要特點就是運用粗俗化和器官化的語言,來達到其戲謔權力、顛覆制度、解放感官、達到生命狂歡的目的。小說中甚至用了大量的議論,來表達對于現代文明的反思與批判。《豐乳肥臀》中,母親的乳房以一種大地般沉默而堅韌的姿態,在動蕩血腥的歲月里,戰勝了死亡、戰爭、政治,并滋養了一代代的子孫,這仍然是對現代文明對立的原始生命的寓言。《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的肉體書寫,一陽一陰,正如太極的二極,剛猛狂放又沉默堅韌,書寫了肉體是如何在歷史中幸存、如何被歷史銘刻以及如何戰勝殘酷的時間的壯美篇章。
而《四十一炮》中的肉體敘事,相較于《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則顯得瑣碎而卑微。炮孩子羅小通,這個土匪種的后代,早已失去了祖宗們撒潑尿就成就一壇美酒的放蕩不羈的豪邁氣概。在小說中出現的他,雖是余占鰲的年齡,但卻再也沒有先輩們的高大與優秀。小說中少有對羅小通肉體的描述,但從他對神秘女人乳汁的渴望中,我們卻可以讀出他肉體的孱弱和萎靡:“她距離我這樣近,身上那股跟剛煮熟的肉十分相似的氣味,熱烘烘的散發出來,直入我的內心,觸及我的靈魂。我實在是渴望啊……我想吃她的奶,想讓她奶我……”,這又是一個上官金童的難兄難弟。
羅小通的形象確不像紅高粱般生機勃勃的祖輩們,在空間上表現為高大與偉岸,在時間中則表現為強悍有力到可以改寫歷史的進程。他的肉體力量只表現在對“肉”的強大吞食和消化能力上。他愛吃肉,“那時候我是個沒心沒肺、特別想吃肉的少年。無論是誰,只要給我一條烤得香噴噴的肥羊腿……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叫他一聲爹……”。他理解肉,“這個世界上,像您這樣愛肉、懂肉、喜歡肉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啊,羅小通。……您是愛肉的人,也是我們肉的愛人……”
與此同時,羅小通的肉體與欲望的關系也迥異于《紅高粱家族》的余占鰲和《豐乳肥臀》中的母親。羅小通的肉體在欲望面前表現出來的,更多是一種卑微的臣服。他的肉體只是在被動地接受欲望的召喚。他甚至可以忍受吃注水肉和混合了大量化學成分的肉。他甚至會為了一根枯瘦的熟豬尾巴而苦惱。
這不免讓人想起拉伯雷的《巨人傳》中的場景,全篇充斥著食物、餐飲的場面。拉伯雷對食物的極度狂放的鋪陳和描寫,在文學史上可謂登峰造極。巨人每日吃喝,大量豐盛的食物源源不斷地進入他無邊的肚腹。他強壯有力,生氣勃勃,他的身體需要生長和發展,發展滋生欲望,欲望的滿足又進一步滋養了他的身體,進而產生更多的欲望。需求和欲望周而復始,不斷向未來發展。這是巴赫金所贊美的理想時代和理想的人:“人們所期望的未來,以其全部力量深刻地強化了這里的物質現實的形象。首先強化了活生生的血肉之軀的人的形象,因為人靠著未來而成長”,他們“具有前所未見的體魄、勞動能力。人同自然的斗爭被英雄化了,人的冷靜現實的頭腦被英雄化了,甚至他的良好食欲和饑渴都被英雄化了。”毫無疑問,誕生《巨人傳》的文藝復興時期如同歐洲的青春時代,人類擺脫了神的世界的束縛,成為獨立的、具有自我意識的、區別動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人。這時的人類對于世界充滿了孩子般的好奇和信心,他想要去創造,去發展。所以,《巨人傳》中關于“龐大固埃”進食的描寫,便總是洋溢著一種純粹、天真、樂觀的“青春期癥候”。
反觀《四十一炮》中,我們也依稀看到了龐大固埃的影子,但其所蘊含的寓意卻是完全不同的。蘭老大與沈瑤瑤的愛情結晶是一個身體龐大,有著極好的胃口,經常感到饑餓,需要不斷地進食大量食物的孩子。這個孩子經常因為饑餓而難受得哭泣,一旦食欲得到滿足,便會沉沉睡去。食物并沒有給他帶來活力,只是維持他生命,滿足他的生存需要。他不想發展自己,時間對于他而言終止了,只是在吃和睡的兩端枯燥地往返。最終,這個愛吃肉的孩子無疾而終。
如果說《巨人傳》中巨人與食物的關系是一種生機勃勃、歡快豪邁的關系,蘭老大的孩子對食物的強烈需求帶給人們的,則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末日感。
而羅小通作為一個現代的“龐大固埃”,他和肉欲的關系既與《巨人傳》中快樂、豪邁、面向未來的關系不同,也不同于蘭老大兒子那種死寂、令人生出一種駭人的恐懼的關系,羅小通與肉欲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表面上,羅小通對肉食的饑渴是一種物質上的匱乏感,他愛吃肉,急切地渴望滿足欲望,但實質上根源卻在于清教徒般的母親的禁欲主義壓抑,作家夸張地表現了他的病態的欲望,以及一種深刻的孤獨感。
風流倜儻頗有古風的父親因為不適應新的時代,選擇離家出走。等到父親再次歸來時,已成一個怯弱膽小的中年人。羅小通母親在丈夫離家后,發奮圖強,拼命賺錢,想要擺脫丈夫帶給她的恥辱。她的本就稀薄的女性氣質被高強度的艱苦勞作榨得干枯,幾乎成為一臺不知疲憊的賺錢機器,也無法給予羅小通精神上的“乳汁”。于是,羅小通在日復一日的枯燥勞作中(這恰恰是現代生活的典型狀態)長大,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是吃一點點肉,比如說一根瘦小的熟豬尾巴。羅小通不僅在物質上是貧乏的,在情感上,他也缺失了父母親的愛和溫情。生活的重壓剝奪了他和人溝通的機會。諷刺性的是,和他溝通的不是父母親,而是毫無生命的肉食。
《四十一炮》有一段荒誕不經的吃肉的描寫:“我低頭看著這盤洋溢著歡樂氣氛的肉,看著它們興奮的表情……它們說:我們曾經是狗身體的一部分,是牛身體的一部分,是豬身體的一部分,……我們已經成為了獨立的有……的個體。……像我們這樣純潔的肉,已經很難找到了。”
在這里,莫言出人意料地讓肉說了話,將一個日常場景以愛情悲喜劇的方式呈現出來,并具有了一種詩意、悲傷、幽默的微妙趣味。華麗、流暢、戲劇性的語調與平淡的日常行為之間的張力,營造出一種荒誕的喜劇感。
在這一場羅小通和肉的對話中,肉塊充滿感情地證明自己的純潔,并請羅小通這個愛吃肉又懂肉的知己吃掉他們。羅小通更是被肉的最后的愿望和祈求感動得眼淚汪汪。這場小型戲劇以一種荒誕的方式呈現出現代商業的黑暗和骯臟,以及現代人的孤獨。“我將第一塊親愛的肉送入了口腔,從另外的角度看也是親愛的肉你自己進入了我的口腔。這一瞬間我們有點百感交集的意思,仿佛久別的情人又重逢。”羅小通的孤獨感隨著同父異母的妹妹的到來而略為減輕。這個妹妹也嗜好吃肉,羅小通找到了知音。在父親入獄,母親死亡,唯一相依為命的妹妹也因過度食肉而死亡后,羅小通被徹底地拋棄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現代文明世界。
從龐大固埃,到蘭老大的兒子和羅小通,我們可以梳理出“龐大固埃”式的人物在時間中的演變。《巨人傳》的龐大固埃生活在盧卡奇所言的“原初的總體性時代”,這是一個人類與世界和諧共處的黃金時代。人類自身即是世界,即是家園。而當時間進行到羅小通生活的當下時代,土地因為已經不能滿足人類膨脹的欲望而不斷地荒蕪,或者被改造成一塊塊工業用地,世界的神秘性和整體性正在消失,往日熟悉的家園已變成了不能安頓心靈的異國他鄉。羅小通不僅僅是父母雙亡的孤兒,他更是現代文明意義下的孤兒。他不讀書,沒有精神養料,滋養他的只有肉食,只有動物性的肉欲。雖然羅小通在肉食方面具有神奇的“通靈“才能,與肉之間產生了一種相知相惜的關系,這可能部分地填補了他精神上的饑餓和孤獨。但一個心靈殘缺的孤兒,是無法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一樣掌控欲望的,相反欲望征服了他。
“我嘔,我吐,我感到自己的肚子像個骯臟的廁所,我聞到自己的嘴巴里發出腐臭的氣味……”
羅小通在一次嘔吐后,喪失了對肉的欲望,也失去了大量吞食肉類的能力。肉體力量喪失后,一種新的力量和欲望取而代之。那就是他強烈的語言表達能力和傾訴欲望。在《四十一炮》中,我們可以看到莫言的肉體敘事經歷了從下到上的行進路線。從《紅高粱家族》中撒了一泡尿就釀出美酒的下體,到《豐乳肥臀》中分泌溫暖的乳汁來捱過殘酷時代變遷的乳房,再到《四十一炮》中不停吞咽的嘴巴,莫言的肉體書寫路線,呈現出一個越來越遠離大地的傾向。希臘神話中大神泰孫的力量來源于他的大地母親,每當他接觸大地,他就會擁有無窮的力量;而當他遠離大地時,他的力量就會減弱。莫言在《四十一炮》前創作的作品,如《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往往展示了肉體的強大的力量,肉體改變了歷史,它摧朽拉枯的力量戰勝了流逝的時間和殘酷詭譎的人間政治。在《四十一炮》中,羅小通這個紅高粱家族的后人,其肉體力量正在漸漸減弱。羅小通的肉體力量來自于他的嘴巴。嘴巴有兩個功能,一是吞咽進食,二是敘說。在《四十一炮》中,形而上的語言漸漸置換、取代了形而下的肉體,這使得莫言的肉體書寫在這部書中呈現出相對衰弱,卻又是最饒有意味的態勢。
二、打谷場、屠宰場、廟宇的時空體
《四十一炮》中羅小通的敘述是通過小說獨特的“時空體”展開的。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識的兩大范疇。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闡釋則是人類的心靈和思想的延伸。巴赫金在其論文《小說的時間形式與時空體形式》中提出來一個重要概念“時空體”——“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系和空間關系相互間的重要聯系,我們稱之為時空體”,“我們所理解的時空體,是形式兼內容的一個文學范疇。”
為了充分闡釋“時空體”的內涵,巴赫金選取了從古希臘羅馬時期到十九世紀的小說,充分闡釋了時空體所具有的體裁意義、情節意義和形象意義。他認為時空體是與小說的情節展開有著重要的聯系的時間和空間的構成方式,更是作者認識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時空體是溝通主體與世界的橋梁。自然,對作者主體思想的闡釋,離不開對作品中時空體的分析。本節中,筆者試圖借鑒巴赫金的理論,通過分析《四十一炮》中獨特的時空結構,來探究莫言對于歷史和時間復雜的態度。
《四十一炮》延續了《紅高粱家族》以來莫言對“古老時代”緬懷的鄉愁主題。在作品中交錯存在著兩種時間的復調結構:一種是古老的、英雄輩出的原始時間,一種是物欲泛濫卻衰弱無力的現代時間。這兩種時間在小說中,分別通過打谷場和屠宰場這兩個空間得以表現其內涵。打谷場是羅通大展身手的地方。羅通身上頗有灑脫風流的古風,同時他也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手藝人,他可以“庖丁解牛”式地不借助機器的測量,而僅憑經驗和直覺準確地評估牛的出肉率,從而獲得了牛販子的尊重和信任。在打谷場以及與之緊密相戀的空間,如鄉村土路、歷史悠久的運河,我們看到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時間的展開:
我記得在一些明月朗照之夜里,村子里的狗叫聲一片后,母親就裹著被子坐起來,將臉貼在窗戶上……看到牛販子們拉著他們的牛, 悄無聲息地從大街上滑過,剛剛洗刷干凈的牛閃閃發光,好像剛剛出土的巨大彩陶 ……簡直就是一個美好的夢境。
打谷場的時空體中存在著的,是月光、牛群、田野以及千百年來不變的穩定的生活和行為模式。在這個時空中,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類還未從世界中分裂出來,分裂出具有自覺意識的主體。這個時空充滿了神秘、穩定、完整的特質,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一種無法言明的人照不宣的默契。沒有人試圖以他者的眼光,將世界放在客體的位置上,去分析、理解它。當少年時代的羅小通向父母親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詢問,為何牛販子總是夜深人靜才進村子時,“他們總是瞪著眼看著我,好像我問他們的問題深奧得無法回答或者簡單得不需回答。”
同時,打谷場時空也是屠宰村曾經的英雄時代。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人們有著強健有力的身體,“甚至是良好食欲和饑渴都被英雄化了。人的理想身高和力量,人的理想價值,從來都不脫離開空間的寬度和時間的長度,大人物就連體魄上也是高大的,高視闊步,氣宇軒昂,要求有廣闊的空間,并以實在的軀體長期生活在時間之中”。屠宰村的村長老蘭的祖上就曾經出過舉人、翰林、將軍等杰出人物,而如今英雄逝去,祖先的榮光不再,只剩下些孱弱無能的子孫,使得后人不禁唏噓不已。“嗨,一代不如一代!”與打谷場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屠宰場”的時空體。這是一個充斥著機械化勞作、僵硬的動物尸體,被技術理性和金錢物欲所控制的地方。適應現代社會資本運作機制的老蘭如魚得水,獲得了經濟和社會地位,而代表逝去的古老時代的羅通卻被逼上了高聳的“超生臺”,試圖用空間上的距離來逃離這個冷酷無情、物欲橫流的空間。
除去打谷場和屠宰場,廟宇是《四十一炮》中最不容忽視的另一個時空體,它承擔了舞臺的功能,它將真實的日常生活、古老傳奇、通俗電影敘事和荒野鬼魅故事緊密地聚攏在一起,從而強有力地支撐起小說中獨特、復雜的敘事結構。
這是兩個繁華小城之間的一座五通神廟,據說是我們村的村長老蘭的祖上出資興建。雖然緊靠著一條通衢大道,但香火冷清,門可羅雀,廟堂里散發著一股陳舊的灰塵氣息。
這座廟宇建立在羅小通故鄉的邊緣,且年久失修,墻體已經坍塌,越過斷壁殘垣,即可以看到一條繁華大道。這不是一個中國古典小說中常見的封閉的與世隔絕的廟宇。這個廟宇是敞開的,它坐落在屠宰村與外界的交匯點上。而廟宇時刻都會塌陷,成為一堆亂石瓦礫。在這樣一個敞開的、動蕩不安的空間中,五通神廟充當了時間的舞臺。不同的時間,現在,過去,未來也匯集于此,粉墨登場。
在這里讀者隨著羅小通的眼睛,看到了屠宰村正在進行的欲望橫流的肉食節,看到了現代官場各色人等對權力的阿諛奉承,看到了底層人們對時代的迎合,看到了風流神秘的蘭老大的愛情傳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交際歡場……在廟宇這個空間里,充分反映出現代農村在商業浪潮中正在經歷的深刻的蛻變,人性的分裂和扭曲,以及各種欲望奇觀。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過去的傳奇歲月是如何和現代時間交織、凝聚在一起,成為羅小通身后一部正在上映的時空穿梭交錯的電影。
莫言通過羅小通的幻想和敘述,以語言為載體,將時間空間化,讓過去、現在和未來,變成具體可見、感性直觀、有血有肉的東西,變成了清晰的情節,并濃縮、匯集在這個破落的神廟中。
時空體,是創作主體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溝通橋梁。五通神廟的時間意義上的破落和空間上的開放性質,折射出作者對時間和空間的感受。顯然,莫言選擇廟宇作為建構整部小說框架的時空體,是寄予深意的。在中國傳統古典小說中,廟宇是一個常見的所在,出現在《紅樓夢》和《金瓶梅》中的廟宇是一個封閉的結構,它在過去的時光背后,關上了來路,又在未來的時光面前,閉合了去路。它是一個終點,它與過去和未來不發生任何聯系,它是時間長河中的一個孤立的島嶼。它沒有通向過去和未來的道路。在此的時間,不再發生變化,它是空虛和死寂,它意味著欲望的終結和滅絕。時間回到太初,化為了混沌。此外,傳統美學意義上的廟宇也承當了洗凈主人公塵世污穢的空間意義。《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在歷經俗世的色欲情劫后,最終在廟宇中了斷塵緣,滅絕罪業,最終超脫了污濁人世。
而在《四十一炮》中,莫言卻選擇了一個非傳統意義的廟宇——“五通神廟”不似傳統的佛教廟宇或道家道觀,它甚至不是民間信奉跪拜的以真實人物為基礎神化了的偶像,如關公廟等,五通神是民間的荒野邊僻的野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神。拜這個廟的多為女性,為求子嗣,會偷偷地夜里來拜祝。“有些官員到任之后就下令拆掉,說它是淫神廟,蠱惑男女,敗壞風氣。”此外,五通神廟和世俗經濟的關系也比較密切。據說求這個神特別容易得到回報。蘇州的五通神廟實際上有很多買賣人去求發財的。”
在這個廟宇中,我們看到了蘭老大充沛的性欲,我們看到了屠宰村在金錢的魔杖下,蓬勃而野蠻的物欲,而坐在五通神廟敘說的羅小通也是心猿意馬,不時被神秘女人的行動所牽動欲念。“心中一陣陣的激動和雙腿間的東西不時地昂頭告訴我:你已經不是那個孩子了。”
可見,《四十一炮》中的五通神廟是匯合了人類色欲與物欲的一個空間。五通神廟特殊的欲望性質,加之它敞開的性質,莫言使得五通神廟充滿了不死的欲望。
甚至羅小通的肉體本身也是一個潛隱的時空體。小說中羅小通的“嘴巴”是被提及最多的器官。羅小通的肉身被簡化為一個“嘴巴”。嘴巴、食道、肚腸是承納、吞食欲望的通道和容器。面對新的欲望,新的時代,羅小通的身體敞開了,他的肉身成為時間和歷史通過的導體。時間給肉體銘刻痕跡。但肉體并不會全然被動接受時間的暴政。從一個能吞食大量肉食的孩子,到喪失吃肉能力,成為一個不能停止敘述、滔滔不絕的炮孩子,羅小通的肉體最終將時間和歷史消化、反芻、加工成語言,再次通過嘴巴這個器官,傳達了出去。而這個過程,是時間的“借尸還魂”術,時間通過羅小通這個中介,獲得肉身,于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農村變遷通過羅小通的肉身得以展現。
從不停地吃(《巨人傳》的龐大固埃)到不停地說,羅小通的身體(嘴巴)成為跨越過去與現代社會的通道。我們看到人的身體在經歷了與欲望共謀的短暫蜜月期后,是如何被現代過度的欲望所征服,被拋棄,被抽離出物質性,而成為某種空洞的象征,失去了與世界的具體、真實的聯系。失去了吞食大量肉食能力的羅小通的肉體似乎消失了,只剩下嘴巴還在一張一合間生產出大量的語言。無形的虛妄的聲音和語言,它在空間中并不占據任何空間。我們無法從在空間中找尋語言的存在。語言被說出,又很快消失在時間的黑暗長河中,如夢如幻如泡影。
從這個意義上,《四十一炮》是一部語言之書,是一場語言的狂歡。四十一炮不僅僅是羅小通射向老蘭的復仇炮彈,它更暗喻了全書即是四十一個語言的炮彈。但語言炮彈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語言能否反抗現代文明的暴力?語言能否洗滌我們的罪惡?莫言給出了他的答案。羅小通的四十一炮只是一個弱小的孩子用語言編織的幻想,他在敘述中獲得了虛假的精神滿足和心理補償。炮彈濃霧散去,一切都未改變。老蘭依然活著。欲望仍在生長,甚至是想要度入佛門的羅小通的欲望仍在滋生著。
看,那個神秘的女人走過來了。
“一個就像剛從浴池里跳出來、身上散發著女人的純粹氣味、五分像野騾子姑姑、另外五分不知道像誰的女人,分撥開那些人,分撥開那些牛,對著我走過來了。”
敘述又開始了。于是,我們重新又回到語言的陷阱中去了。這個滿口言之鑿鑿、煞有其事的炮孩子又要開始講述下去了。
敘說就是一切,但一切只是敘說而已。
三、關于敘述的敘述
莫言在后記中寫道:“在這本書中,敘說就是目的,敘說就是主題,敘說就是思想。敘說的目的就是敘說。如果非要給這部小說確定一個故事,那么,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少年滔滔不絕地講故事”。羅小通對歷史的回憶和虛構,展示了他想要恢復自己的過去,并與他的現在融合起來的努力。作為一個肉體被現代文明抽取了物質性的棄兒,羅小通試圖在五通神廟中,在宗教中找到歸宿。但五通神廟早已搖搖欲墜,它在羅小通的漫長的敘說中不斷地倒傾。羅小通敏銳地覺知了自己無法在宗教中找到歸宿;而語言才能提供給他虛假卻也是唯一的安慰。于是,羅小通在敘述中為自己虛構了一個“父親”的形象——蘭老大。
蘭老大風流倜儻,擁有強大的性能力,同時又占有了大量的財富。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在這里套用了一個現代大眾神話的欲望模式:一個出色強大的男人被眾多女人所圍繞。但是他對女人們從來都是敷衍了事,直到一個命定的女人出現在他的世界。他和這個女性結合,生育后人,共度此生。蘭老大的愛情模式也延續了這個庸俗的欲望模式。他被仇人女兒的美麗和楚楚可憐所打動,并愛上了她。而這個男人在娶了美人的同時,也沒忘記恩怨,他愛憎分明地殺了仇人,盡管這是自己妻子的父親。因為這樣的情節設計更會突顯和強化蘭老大的男性氣質。莫言用來敘述這段傳奇愛情的語言是一種淺顯、華麗、流暢,富有畫面感的電影化語言。這種語言不同于日常語言,它帶有一種夢幻般的不真實的氣質。隨著蘭老大被洋人打碎生殖器,這個幻想中的父親,轟然倒地。
于是,羅小通只有繼續敘說,敘說是他唯一的救贖之道。他用訴說,來填補被分裂的自己,找尋喪失的自己。他以語言為橋,試圖建立自身與歷史的一種聯系,填平逝去的童年與現在的巨大鴻溝。
然而,羅小通的敘說不僅是在語言編織的夢境中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一個歸宿,也是試圖以語言為武器,講述歷史的另一種真相的嘗試。
在《四十一炮》中,存在著對屠宰村歷史的兩種敘事。一是羅小通的回憶和虛構,另外一種是老蘭的《肉孩成仙記》。在第一種敘事中,羅小通作為一個早慧的少年,敏感地預感到父親羅通所代表所堅持的傳統鄉村文明必將被老蘭這種野蠻卻有效的商品文明所淘汰。于是他很快地和母親投靠到老蘭這邊,成為屠宰場的車間主任。但他也試圖在兩種文明之間找出一條折衷的道路。如當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自己不賣注水肉,注定在殘酷的商業競爭下遭遇慘敗,所以他提出了一個“天才”的倡議,給待宰的牛羊“洗肉”,并強調用純凈的井水可以讓牛羊的肉更加純凈、鮮美,甚至可以治療疾病。羅小通在擁抱新的時代的同時,他對父親又充滿了同情,對父親身上殘留的孤傲和耿直,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欣賞。可以說,羅小通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和鏡子。他在道德上的矛盾、含混、折衷、自欺欺人的態度體現出這個時代的復雜和混沌。
而老蘭的新戲劇《肉孩成仙記》,講述了一個以羅小通為原型的孝道故事。肉孩的母親病重,卻無錢抓藥。肉孩無奈,只得割下自己的肉,來給病重的母親增加營養。肉孩最終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去。神靈贊嘆肉孩的孝心,收留肉孩,使其成仙,專門負責人間吃肉的事情。
老蘭用虛構的戲劇置換了真實的歷史。在《肉孩成仙記》中,我們看不到新舊時代更替時人們的掙扎、創傷和痛苦,人們為適應新的時代所付出的代價,以及人性在新時代面前復雜的反應和態度。這一切都在戲劇中被簡化,被虛化。肉神本來是欲望的象征,而在《肉孩成仙記》中,老蘭通過語言,包裝粉飾了赤裸裸的肉欲,使其成為孝道的化身。這正是現代欲望的化妝術。語言則是裝扮欲望的華麗畫皮。觀看戲劇的人們,也安于這樣的催眠術,他們為戲劇而歡呼而激動。他們暗自竊喜語言的陰謀,為自己的縱情聲色犬馬提供了一個安全、合理甚至是光榮和堂皇的借口。
顯然羅小通的敘事根本無力反抗老蘭的戲劇敘事。我們看到就在羅小通的敘述過程中,在語言的泡影中,巨大的肉神像被工匠們塑造出來。官員們參觀,并預言肉神廟必將取代破落的五通神廟,成為眾人膜拜、香火鼎盛的一座新廟。羅小通的敘事注定是一次語言層面上的無力反抗。
很顯然,《四十一炮》是一部“肉體之書”,更是一部“語言之書”,他將肉體放在時間的洪流中,給讀者展示了肉身如何被時代所銘刻,以及時代是如何通過肉體得以展示的。《四十一炮》也是一部關于敘述的書, 一場關于敘述的敘述。莫言探討了語言的敘事能否把握歷史的真實,能否對抗時間和歷史的暴政,并隱隱流露出他對歷史以及在如何評判歷史這個問題上的審慎而冷靜態度。當然,這也可以視為面對現代欲望的一種逃避。既然無從對抗現代泛濫的欲望,那不如退到語言的城堡中,發射四十一枚語言炮彈,沉醉在語言自我繁殖的夢境中。它的一個不可忽略的作用,是使得莫言所有的小說“在這部小說之后,彼此貫通,成為一個整體。”
管笑笑 北京師范大學
中國藝術研究院
注釋:
①《論莫言小說“肉身成道”的唯物書寫》,《文藝爭鳴》2012年8期第26頁。
②③④⑦⑧⑨???????《四十一炮》,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頁,第7頁,第218頁,第110頁,第218頁,第297頁,第376頁,第32頁,第32頁,第2頁,第1頁,第45頁,第399頁,第401頁。
⑤⑥⑩?《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頁,第344頁,第274頁,第344頁。
?莫言、楊揚:《以低調寫作貼近生活——關于〈四十一炮〉的對話》,《文學報》200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