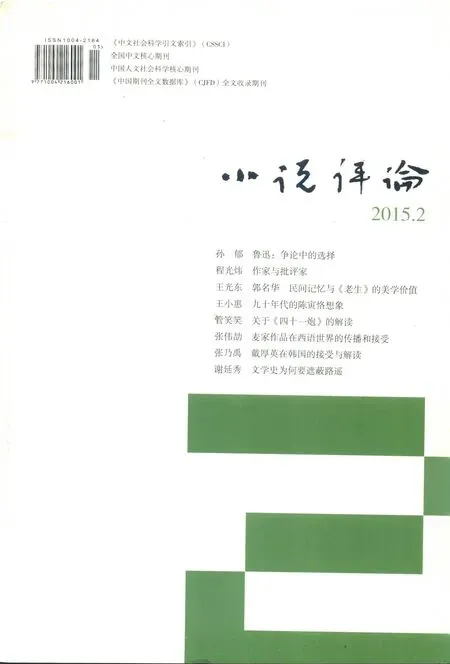論現代性視域下的莫言“鄉土文學”觀
彭在欽 段曉磊
論現代性視域下的莫言“鄉土文學”觀
彭在欽 段曉磊
什么是鄉土文學?魯迅稱當時一批作家“在北京憶敘故鄉的事情”而書寫鄉愁情懷的文學作品為“鄉土文學”。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進一步指出,所謂的鄉土文學,主要是在文學研究會和語絲社等社團的倡導下,為了迎合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任務,在1923年前后陸續出現,它延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充滿了“地方色彩”。隨著文學觀念的進一步發展茅盾在《關于鄉土文學》中提出,若“鄉土文學”單單是刻畫特殊的風土人情,那就“不過像看一幅異域的圖畫”,只是一種對人的好奇心的滿足。他提倡作家應該將筆觸放在“特殊的風土人情”之外,更加強調“鄉土文學”中的“普遍性”,以及人類對于“命運的掙扎”。進入現代社會,鄉土文學概念進一步深化并逐漸演化出了三個層次:首先是鄉村或田園的文學,其對立面為都市文學,例如趙樹理的山藥蛋派和孫犁的荷花淀派的作品;其次是地方或地域的文學,其對立面為主流文學,如,魯迅的小說多以浙東地區作為寫作的范本,沈從文的則是湘西世界,而莫言在他一系列的小說中刻畫的山東“高密”等;最后是本土或民族文學,其對立面是外來文學,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聶魯達的《西班牙在我心中》等。
莫言在自己的小說中創造了“高密”王國,它不僅僅是山東的,也是中國的,瑞典文學院對莫言的認可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國。從《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十三步》中對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的亦步亦趨,到《蛙》、《酒國》書信式的新穎敘事手法的嘗試,再到《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紅樹林》、《檀香刑》、《生死疲勞》和《豐乳肥臀》中張揚生命意識以及對人性異化的揭示,總有一種新奇且涌動的氣息徜徉在他的文字里,貌似丑陋的書寫以及對現實的嘲諷并不僅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清高。火紅的高粱、激情奔放的高密人形象、混雜著丑惡與真善美的較量,還有一種更加高尚和陽光的東西隱藏在他的筆下。莫言的“鄉土文學”不僅僅關涉到民族文化,它更是一種在現代意義上的創新和發展,悲憫情懷造就了莫言特殊的“鄉土文學”觀,這悲憫不僅僅屬于佛教,也屬于基督,更屬于全人類。因此,在現代性的視域下對莫言的“鄉土文學”觀進行討論無疑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民族形式與民族文化
“本土的”與“民族的”問題討論最初是在20世紀40年代,最終演變為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個口號在當時提出來無疑是為了能夠更好地處理“民間文藝形式”和“國際主義的內容”的關系。在毛澤東看來只有將“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相結合,才得以創造出一種“新鮮活潑的”并且能夠被中國普通老百姓接受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胡風根據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將“民族形式”問題予以深化,“‘民族形式’,它本質上是五四現實主義傳統在新的情勢下面主動地爭取發展的道路。一方面使主導的基本點爭取前進,一方面使這主導的基本點受到妨礙的弱處或不足爭取克服:是這一爭取發展的道路。它的提出,原是由于形式的能動作用能夠達到內容的正確的把握而且前進這一方法上的意義,也只有在實踐里面固守住這一意義才能夠取得戰斗的作用。”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左”的意識形態日益嚴重,革命文學的意識形態性更加突出,文學的功用在于其服務于政治的工具性,這無疑造成了革命文學和五四傳統的一種斷裂。
相比于魯迅筆下的文化批判式的鄉村景象,以及沈從文等作家所建構的“鄉村烏托邦”甚至是50到70年代間的作品中對當代鄉村生活的政治圖解,莫言的視角都是傳統而新奇的。莫言繼承了“五四”新文化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是“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相結合的產物。筆者在論文《接受美學視域下莫言對“講話”的繼承和突破》中曾對莫言的“中西相結合”的視野做過系統的論述,“除了從十七年文學作品中汲取營養,馬爾克斯和凱爾納也對莫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可以說,莫言筆下的‘鄉土’,并非閉門造車,他是立足于世界的,他的作品是一個到處洋溢著生命和活力的田野,是一種對人性的詮釋。”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說:“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莫言在自己作品中的大膽實踐是對“本土的”與“民族的”問題的進一步深化,他繼承了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對所謂的“民族文化”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在現代都市文明的不斷侵蝕下,傳統的鄉村社會再也無法維持原本的自給自足狀態。中國鄉村在自鴉片戰爭以來痛苦的現代化過程進程中,處于一種不中不洋的尷尬生存狀態中: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殘存,封建遺老遺少仍懷念著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另一方面,擴張式的機器文明憑借武力迫使鄉村無法回到原初的封閉狀態。中華民族在這樣的一種“被迫”現代化過程中,無法避免遭受列強的蹂躪,也可以說,中國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化是在戰火中淬煉而成的。《紅高粱家族》中的戴鳳蓮與余占鰲、《檀香刑》中的錢丁、《生死疲勞》中的藍臉和《豐乳肥臀》的上官魯氏等,他們堅守著傳統的信念在現代社會中痛苦掙扎,可他們既無法逃脫舊思想的束縛,也不能擺脫現代力量的羈絆,他們只能放棄個體的自我寄希望于“我們”的力量。在戰爭年代,個體的“我”憑借“我們”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迎來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然而革命結束后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逐漸淪為不可靠的“幻影”,個體的“我”依然在痛苦地掙扎著。
二、洞穴“幻影”的破滅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危機四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左翼作家們毅然舉起了“集體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旗幟。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強調所謂的“具體人性”只能是人的“階級性”,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我”必須無條件的屈從于“我們”的意志。在高強度意識形態下凝聚起來的“我們”的力量使得抗日戰爭以及之后的解放戰爭,甚至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勝利。但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的意識越來越成為“我”的自由的束縛。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首次提出洞穴“幻影”的隱喻,“洞穴”中的人固步自封,無法認識自己與他人的身份,根據自身的直接經驗,墻上的影子反倒成為了真實的自己,人就這樣把自己囚禁在了“幻影”中。“我們”是否就是“我”的“幻影”呢?
莫言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了許多節日慶典活動,例如《豐乳肥臀》中的“雪集”,《檀香刑》中的“叫化子節”,《四十一炮》中的“肉食節”,《酒國》中的“猿酒節”等,充滿著荒誕、調侃、笑謔、怪誕、變形,“雪集”中的“雪公子”摸乳,“叫花子節”中的黃袍加身,“肉食節”和“猿酒節”中的胡吃海喝,但是在這個世界里小人物的價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對于他們來說,“狂歡世界”甚至理想于現實世界。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蘊含了狂歡的色彩,反抗著“我們”強大意識形態對“我”的壓迫,但是這種反抗卻充滿著悲劇色彩,因為反抗的行為并非某個個體“我”的有意識的行為,而是通過面具下力量相對弱小和邊緣化的“我們”來反抗掌握主流話語的“我們”。這似乎是在洞穴里面建造了另外一個洞穴,逃避了前面洞穴的“幻影”,卻又自我安慰地創造了另一個“幻影”。魯迅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了一副“個體”淹沒于“群體”的圖景,“個人特殊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區分,且欲致之滅絕。……精神益趨于固陋。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一曰汝其為國民,一曰汝其為世界人。……而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泯于大群……”存在主義之父克爾凱廓爾也有過類似的話,“從屬于公眾的單個的個人沒有一個能做出一個真正的承諾,……當個人什么也不是的時候,由這樣一些個人所組成的公眾就成了某種龐然大物,成了一個既是一切、但又什么都不是的、抽象的、被遺棄的虛空”,“公眾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是最危險的力量,但又是最無意義的東西。”市場將人本身所固有的欲望無限放大,作為群體的“我們”在個體的利益面前顯得越來越不真實。《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官員以權謀私、《四十一炮》中放縱的肉欲和《紅樹林》中被金錢驅逐的淳樸,小人物們的欲望蘇醒了,但他們只能眼看著自己的肉體和靈魂被駕馭和折磨。狂歡對于個體來說是暫時的,而現實中無法逃避的痛苦則是漫長的。
在莫言給出的偌大狂歡場景中,無論是語言、場景亦或者是小丑加冕式的人物狂歡,都好似是一場夢,夢醒后必然是一場空。全民狂歡的場景,不受官方世界束縛的第二個世界,這些都是蒙蔽人眼的假象,舞動的群體在狂歡過后除了返回現實世界重新做回自己的角色別無選擇。當個體由虛幻的群體中蘇醒過來再次面對舞動的群體時,油然而生的失落感是不可避免的。在生命根本價值的問題上,只是聽從群體性的時潮,得到的只能是一種價值假象,只有從個人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穿越公共世界中的價值假象而獨立抉擇出自我生命真正信從的價值原則。
三、“自我”的復歸
文藝復興最大的貢獻就是發現了“人”的存在,到了啟蒙運動時期,個體的“人”也蘇醒了,“天賦人權”、“民主”、“自由”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但是伴隨著“人”的權威的增強,失去上帝庇佑的人并沒有能很好地“認識自己”,人而神的現象大批出現。希特勒在成為日耳曼民族的神后將其他種族判為劣等,大批的猶太人、波蘭人被投入集中營像豬狗一樣被宰殺;同樣癲狂的事情也發生在日本大和民族身上,明治維新之后天皇被奉為具有絕對權威的神。萬能的上帝已經死掉了,莫言毫不猶豫地戳破“幻影”的泡沫,“我們”也只是假象,人剩下的唯一依靠便是“自我”。
在他筆下出現了一系列的生動的農民形象,他們固執地堅守著“自我”的信仰。《生死疲勞》中的藍臉在土地改造運動中寧可選擇離開妻兒也要守護自己的“私田”,《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歷盡千辛養育著自己的兒女們,《紅高粱家族》中的羅漢大爺為了“大義”遭受日軍剝皮的酷刑,《紅樹林》中的無依無靠的珍珠和小海,《檀香刑》中起身參加義和團的孫丙等。當然,與這些堅守者相比,沉淪者也存在著。《檀香刑》中的異化為殺人機器的劊子手趙甲,《豐乳肥臀》中具有“戀乳癖”的上官金童,《四十一炮》中“肉欲”化身的羅小通,《紅樹林》中順從和公公“扒灰”的林嵐,《酒國》中的“食嬰”事件和《蛙》中的“代孕”行為等等。科恩在《自我論》中指出英語“the self”指的是“自我性”,而這樣的詞匯常見于費希特和黑格爾以及海德格爾的著作中。所謂的個體自我,在希臘語境中是一種相對于人類整體性而產生的一種自覺意識。歐洲近代的自我意識的興起離不開文藝復興以來對上帝的解構。當笛卡爾指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后,此世的人的主體性置換了彼岸的上帝的全知全能。“我究竟是什么東西呢?”這樣的問題在笛卡爾看來這首先是一個認識“自我”的問題,“我”在思考的同時意識到了“我”的存在,我可以懷疑一切,卻唯獨不能懷疑這個正在懷疑著的“我”的存在。然而在洛克看來,意識決定著“自我”,人的職業可以隨意改變,甚至自身的一部分肉體可以喪失,清醒時或者是醉酒的狀態下,人依然可以認同自己改變前后是同一個自己。在意識的支配下,痛苦或者快樂才能夠被“自我”感覺到。而幸福或者不幸的感覺只不過是意識對自己的關心的程度不同而已。魯迅將優秀的悲劇比作“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而在莫言在自己作品中直接將“我”撕裂給“我”看。《紅樹林》中的林嵐和《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與其他人物形象是不同的,他們在精神上的蘇醒抵不過肉體欲望的惰性,林嵐順從了公公的“扒灰”,上官金童無法擺脫乳房對他的誘惑。清醒者痛苦著,沉睡者沉淪著。然而生長在高密鄉土的農民們卻固執地堅守著,《紅高粱家族》羅漢大爺和《檀香刑》中的孫丙笑罵著面對酷刑,《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昂著頭承受命運拋給她的一切……他們同樣痛苦,但是他們的生命卻充滿激情和活力,他們是生命意義的堅守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提出“沒有了上帝,那么人的一切行為就都是被允許的”。沒有了上帝的制約,沒有了“我們”的束縛,“我”也就無須對什么東西負責,因而就能盡情地在虛無中遨游嗎?人能夠在虛無中生存,但是他無法在其中生活。“這沒有愛的世界就好像一個沒有生命的世界,但總會有這么一個時刻,人們將對監獄、工作、勇氣之類的東西感到厭倦,去尋找當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加繆的思想是極其可貴的,他始終在拒絕著價值虛無主義,并且自始至終堅持著對人的一種信念以及對生活的熱愛。無論他自身的處境如何艱險,他始終由衷地贊美著這個世界和生命的美好。莫言筆下生命意義的堅守者無疑都是懷有人間信仰的,對親情的留戀、對信念的堅持、對正義的忠誠等都足以讓他們平淡地看待世間的繁華和騷動。
四、結語
人是一種意義和價值性存在的動物,這就意味著個體的人不可能徹底地脫離群體,完全脫離外部世界而獲得有意義的存在。然而,過于沉重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枷鎖,以及上帝之手對人類的思想鉗制,必然導致人的內心的不滿。在莫言的故事中,堅守者與沉淪者碰撞著,堅守者依然堅守著民族文化中精粹的傳承,沉淪者在現代社會的牽引下無情地瓦解著世間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這是一個看似互相矛盾過程,現代性亦是這樣,一方面它崇尚“無所不能”的工具理性,而另一方面卻對工具理性充滿懷疑,甚至是對抗。莫言獲得諾獎并非意外,他本人的文字功力無疑是深厚的,其筆下的故事代表了山東高密,更代表了中華民族。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和由西方拿來的“各種主義”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促成了現代性視域下的莫言“鄉土文學”觀,它在向世界標榜中國文化的同時,又推動著中國民族文化的創新與現代發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現代性與本土化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3YJA751039);湖南科技大學科技創新團隊:“現代性與當代文學新潮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
彭在欽 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段曉磊 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注釋:
①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416.
②茅盾.關于鄉土文學.[J]文學(第6卷第2 號),1936.
③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④胡風.胡風評論集(中卷)[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219.
⑤⑥段曉磊,彭在欽.接受美學視域下莫言對《講話》的繼承和突破[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7):164.
⑦魯迅.魯迅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6.
⑧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68.
⑨彭小燕.存在主義視野下的魯迅——穿越生存虛無、撞擊世界“黑暗”的現代信仰者[D].北京師范大學,2005.
⑩科恩.自我論[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19.
?洛克.人類理解論(上冊)[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309.
?阿爾貝·加繆.鼠疫[M]. 北京:譯林出版社,200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