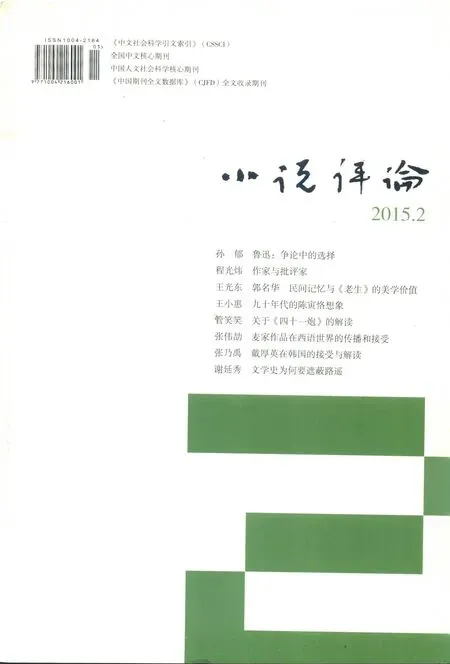記憶書寫后的釋然與痛楚
——論賈平凹的《老生》
張 英
記憶書寫后的釋然與痛楚——論賈平凹的《老生》
張 英
一
《老生》主要以四個故事結(jié)構(gòu)全篇,記錄了發(fā)生在陜西南部一段跨越近百年的革命歷史。這部小說依然延續(xù)了賈平凹作品一貫的地域文化品格和鄉(xiāng)土文化色彩。小說當中唱師所唱的陰歌,是賈平凹所在的商州及整個陜南流行的民歌,是人死之后唱給亡靈聽的,既表達生者對死者的想念,也蘊含對生者的希望與寄托。生離死別、悲歡離合已是人生的痛楚。在蕩氣回腸的陰歌中,人生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旦夕禍福帶給生者無盡的痛楚,帶給讀者強烈的震撼。作者通過小說表達了自己的生死觀:“常言生有時死有地,其實生死是一個地方。人應該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一股氣,從什么地方冒出來活人,死后再從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墳。”在作者看來,故鄉(xiāng)的祖輩人都是從牛頭坡上不斷冒出的氣又不斷地被吸收進去。小說當中的蕓蕓眾生,便是從故鄉(xiāng)的土地里冒出的清的、濁的各種各樣的氣,經(jīng)過人世的飄蕩,最后又回到原點。小說中唱師的一生就是鮮明的寫照。
在《老生》中,浸透著作家對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思考,體現(xiàn)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賈平凹在這部小說中的主要敘述者是一位唱陰歌的唱師,通過這樣一位往來于陰界陽界、和死人活人打交道、幾近永生不死的唱師的視角,書寫百年中國的時代變幻與人事浮沉。如果賈平凹僅僅寫自己故鄉(xiāng)村子的故事,這在他以前的小說中無論是鄉(xiāng)土還是地域都有所呈現(xiàn),正如作者所說的,差不多在寫在以往的書里。“故鄉(xiāng)的棣花鎮(zhèn)在秦嶺的南坡,那里的天是藍的,經(jīng)常在空中靜靜地懸著一團白云,像是氣球,也像是棉花垛,而凡是有溝,溝里就都有水,水是捧起來就可以喝的。”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絕大多數(shù)都在寫他熟悉和熱愛的鄉(xiāng)土。故鄉(xiāng)的山水牽動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神經(jīng),這也是作家最敏感的題材領域。而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地注入了更多的內(nèi)涵,表達了更深的思考。對于歷史的書寫,作者采用了一種民間寫史的方式,文學與歷史的結(jié)合,用文學的方式來講述歷史,賈平凹是用記憶來還原一個真實的時代。一個人有自己的歷史,一個家族有自己的歷史,一個村莊有自己的歷史,一個國家有自己的歷史。賈平凹親身經(jīng)歷的六十年來的命運,聽到的、看到的民族人事的沉浮,目睹了中國社會幾次轉(zhuǎn)型期。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聯(lián)系起來,將小歷史與大歷史聯(lián)系起來,將歷史歸于文學,用一個唱陰歌的唱師的回憶和敘述,讓不同歷史時代,甚至不在一地一山發(fā)生的不同人物命運故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小中見大,巧妙鏈接,意味深長。改變了歷史書寫方式,打破了讀者傳統(tǒng)的歷史閱讀視野,讓讀者眼前一亮。
在《老生》的全篇中滲透著作者執(zhí)著的文化觀。小說雖然由四個故事組成,但“其中加進了《山海經(jīng)》的許多篇章,《山海經(jīng)》是寫了所經(jīng)歷過的山與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見所聞所經(jīng)歷的。《山海經(jīng)》是一個山一條水的寫,《老生》是一個村一個時代的寫。《山海經(jīng)》只寫山水,《老生》只寫人事。”《山海經(jīng)》是我國一部重要而珍貴的古典文獻。也是作者近年來非常喜歡的一本書。作者對傳統(tǒng)文化是有著強烈的驕傲感和使命感的。將《山海經(jīng)》的篇章雜糅在歷史的敘述中,這種貫通古今的時空視野和回歸傳統(tǒng)的文化觀念是沒有人嘗試過的,賈平凹寫出了歷史的大悲憫大關懷,充分顯示了作者的大文化哲學思想,把開天辟地的神話歷史與當代中國變遷歷史水乳結(jié)合,達到一種貫通古今的勾連。
二
在賈平凹獨特的歷史文化意識的統(tǒng)攝下,作者為讀者講述了不同年代、不同村子、不同人的故事。“如果從某個角度上講,文學就是記憶的,那么生活就是關系的。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活得自如,必須得處理好關系,而記憶是有著分辨,有著你我的對立。當文學在敘述記憶時,表達的是生活,表達生活當然就要寫關系。”在《老生》中讀者看到的正是許多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卻不愿說的真實、苦難、不幸、黑暗。作家在小說中描繪了在動蕩、戰(zhàn)亂、災荒、土改、革命、改革的社會轉(zhuǎn)型和風云激蕩的一個世紀里人的命運浮沉,而在記憶的描繪中,“在為了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出人樣,我的爺爺做了什么,我的父親做了什么,故鄉(xiāng)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兒孫又做了什么,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是齷齪罪過?”這其中滲透著作家強烈的歷史憂患意識和悲憫的人文情懷。
小說中人和人的關系錯綜復雜,小說中展示了原始的復仇觀念,王世貞的姨太太為了報仇,不放過已經(jīng)死了的四鳳和肚子里的孩子,“四鳳的眼睛還睜著,剖肚子的保安就把四鳳的襖割下一片,蓋住了臉。孩子被挑出來了,是個男孩,用刀像剁豬草一樣剁成碎塊。”而雷布為老黑復仇的時候,用刀在王世貞的姨太太臉上寫字,“鼻梁以上寫了個老字,鼻梁一下寫了個黑字,臉就皮開肉綻,血水長流。”而老黑被處死的場面更是將暴力書寫到極致:“幾個保安就扛來一頁門扇,把老黑壓在了門扇上,開始拿四顆鐵打的長釘子釘起手和腳。……長釘全砸釘好了,老黑的眼珠子就突出來,那伙保安又把一塊磨扇墊在老黑的屁股下,掄起鐵錘砸卵子。只砸了一下,老黑的眼珠子嘣地跳出眼眶,卻有個肉線兒連著掛在臉上。”這種場景和莫言的《檀香刑》中對刑法的描寫有異曲同工之妙。革命的年代,老鷹嘴村的苗天義被關起來審判拷打,他不停地號叫,聲音凄厲。為了讓他笑,組長想出一個辦法,“再不拷打,而把苗天義綁在一個柱子上,雙腿跪地,又脫了鞋在腳底抹上鹽水,讓養(yǎng)不停地添腳心,果然苗天義就笑,笑得止不住,笑暈了過去。”讓讀者不禁想起余華的《現(xiàn)實一種》里兄弟殘殺的血腥,將人性在驚心動魄的描寫中把冷漠、殘酷的一面暴露無疑。
人和人的關系,除了混亂、凄苦、殘忍,復仇、殺戮和血腥,小說中還全書還流淌著一股觸動人心的暖流。“凡是優(yōu)秀的作品,不管它要表現(xiàn)多么沉重的主題、多么深刻的思想,或者多么復雜的人性,總是能夠找到溫暖的原點,并以此為中心,四散開來,綿延出去,從而傳遞出某種堅定的力量。這也一定是文學的重要使命之一。”當老黑在路上看到瘋了的四鳳,面對心愛的人,老黑把頭埋下去,眼淚長流,不愿再看到她。當看到四鳳被人調(diào)戲蹂躪,老黑撲出來舉槍就打,打死了要強暴四鳳的人,也打死心愛的四鳳。他不愿心愛的人以這樣的面目活在世上。游擊隊員雷布冒死找到場師請求為三海、李得勝和老黑唱陰歌,說他們死得那樣慘,尸體不全,不能入土。周百華戴重孝為李得勝老黑他們致哀。這份義氣讓唱師感動。
時代為人的存在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一路走來,人事盡在時代里淘沙。沒有人不死去的,沒有時代不死去的。生命的偉大與卑賤,人性的丑惡與真善,命運的荒唐與凄涼在小說的各種關系中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正如賈平凹所說:“《老生》中,人和社會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是那樣的緊張而錯綜復雜,它是有著清白和溫暖,有著混亂和凄苦,更有著殘酷,血腥,丑惡,荒唐。”
三
《老生》向讀者展示了豐富的文化觀念和思想內(nèi)涵,也描繪了刻骨銘心的凄苦、殘忍的和溫暖。那么,在創(chuàng)作手法和風格上,這部小說同樣突顯了賈平凹以往作品中沒有的東西,體現(xiàn)了作者獨特的藝術追求。
作者用《山海經(jīng)》的方式講故事,這種敘事模式更有新意更富禪意,這也是用中國的最古老的方式來記錄歷史。他用解讀《山海經(jīng)》的方式來推進歷史,具有很強的空間延伸感。在小說中,《山海經(jīng)》與主體故事是靈魂相依的,《山海經(jīng)》表面是描繪遠古中國的山川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寫,真實意圖在描繪記錄整個中國的經(jīng)歷,主旨卻在寫人。作者的思想也在此,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寫:戰(zhàn)亂、土改、革命、改革……,一個人一個人地寫:老生、老黑、李得勝、四鳳、王世貞、雷布、馬生、白土、王財東、玉鐲、白河、馮蟹、拴勞、劉學仁、苗天義、墓生、戲生、馬立春、劉四喜、張收成……,一個村一個村地寫:正陽鎮(zhèn)、清風驛、皇甫街、黃柏岔村、王屋坪、澗子寨、嶺寧城、老城村、首陽山、過風樓、野豬寨、棋盤村、八王寺村、茍家村、老鷹嘴村、陳家村、當歸村……,無論怎樣滄海桑田、風云變幻,本質(zhì)都是寫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的命運。賈平凹不僅將《山海經(jīng)》融入全篇,而且講故事的手法也很傳統(tǒng)化中國化,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他們的鄉(xiāng)土記憶和歷史記憶日益淡薄。如何讓這種題材得到更多普通讀者甚至年輕讀者的青睞是作者認真思考的問題。可以說,賈平凹是深懂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筆法在《老生》中運用得更為自然圓熟。“至于此書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個人的一生活得太長了,或是僅僅借用了戲曲中的一個角色,或是贊美,或是詛咒。老而不死是為賊,這是說時光討厭著某個人長久地占據(jù)在這個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談,這又說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誑語吧。”書中每個故事里總有一個名字里有老字,如:老黑、老皮。總有一個名字里有生字,如:馬生、墓生、戲生。這些都是作者獨具匠心的體現(xiàn)。在一定意義上說,《老生》的創(chuàng)作手法既是創(chuàng)新,也是作者更深層地向傳統(tǒng)進行回歸的嘗試。
賈平凹說:“現(xiàn)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憶往事,而往事如行車的路邊樹,樹是閃過去了,但樹還在,它需在煙的彌漫中才依稀可見呀。”作家把從小到大的真實經(jīng)歷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實現(xiàn)了作家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百年的命運的熔鑄。《老生》的節(jié)奏舒緩和醇厚的意蘊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創(chuàng)作觀念密不可分。作者認為,寫小說就在于說公道話。因此,《老生》就試圖老老實實地去講述過去的國情、世情、民情。真實是文學作品安身立命的重要品質(zhì)。中國的現(xiàn)當代名家一直都強調(diào)和實踐著這一準則。如魯迅的《野草》、巴金的《隨想錄》都是勇于坦露內(nèi)心的真實的作品。“要寫出真實得需要真誠,如今卻多戲謔調(diào)侃和偽飾,能做到真誠,我們真誠了,我們就在真實之中。”雖然創(chuàng)作各有路數(shù),但藝術真實性標準是從古至今的重要準則。小說的封底上印有賈平凹的一首詩:“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風起云涌百年過,原來如此等老生。”《老生》又一次告訴我們作家的使命感、歷史意識與人文情懷。真正的文學永遠與現(xiàn)實、時代、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結(jié) 語
賈平凹說:“我不知道這本書寫得怎么樣,哪些是該寫的哪些是不該寫的哪些是還沒有寫到,能記憶的東西都是刻骨銘心的,不敢輕易去觸動的,而一旦寫出來,是一番釋然,同時又是一番痛楚。”在賈平凹的這部新作《老生》中,用年齡和經(jīng)歷包漿生命,用傳統(tǒng)文化詮釋民間歷史,用殘忍暴力批評人性的丑,用清白溫暖謳歌人性的善,用記憶觸碰一個作家、一個村莊、一個國家刻骨銘心的東西。當這種記憶被書寫,是一番痛楚,也是一番釋然,更是一番希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村莊敘事與中國鄉(xiāng)村小說的嬗變”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BZW181。
張 英 渤海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賈平凹:《老生·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290、294、292、293、293、294、289、293、295頁。
⑥周景雷:《文學與溫暖的對話》,春風文藝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