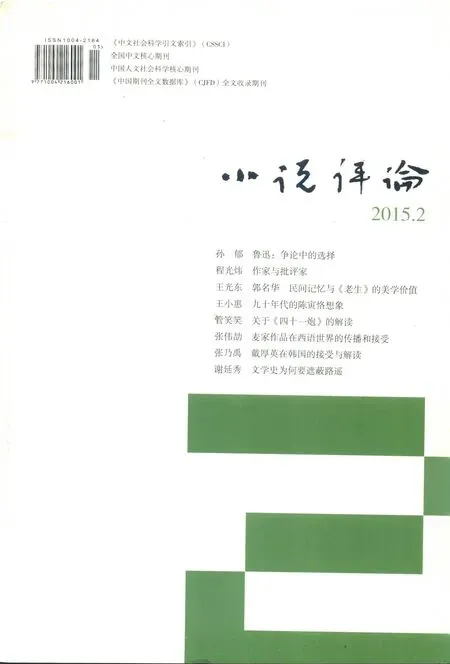百年歷史 境界相通
——賈平凹《老生》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朱靜宇
百年歷史 境界相通——賈平凹《老生》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朱靜宇
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是賈平凹喜愛、并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外國作家。他曾經說過:“讀了馬爾克斯的書,就永遠記住了《百年孤獨》四個字”,那么,這被永遠記住的《百年孤獨》,對賈平凹的長篇新著《老生》創作有著怎樣的啟悟?《老生》與《百年孤獨》之間又有著怎樣的相通呢?本文擬從百年歷史的書寫、藝術技巧的借鑒以及文學境界的追求等方面展開探討。
一、百年歷史的書寫
自十九世紀英國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創始歷史小說以來,許多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當作“社會史”,公開宣稱自己要忠實地書寫歷史。法國的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序言中就表示要寫一部“許多歷史家們所遺忘了的歷史,即人情風俗的歷史”; 左拉在1868年制定他的《盧貢-馬卡爾家族》的計劃,就決意要寫出第二帝國(1851——1870)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用歷史價值代替審美價值,這是西方文學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到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所秉承的傳統,重視文學的歷史性,把文學當作歷史來書寫。這種對歷史價值的追求,直到今天依然是許多作家的夙愿。
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就是一部再現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圖景的鴻篇巨制。小說以虛構的馬孔多小鎮為背景,從容不迫地講述了布恩迪亞家族一家七代由盛而衰綿延百年的歷史。而這一切,再現了哥倫比亞和整個拉丁美洲近百年來的歷史和各個時代的社會面貌。
小說將布恩迪亞家族的生存樣態和小鎮馬孔多的百年嬗變與拉丁美洲的百年歷史交織在一起,荒原上馬孔多的初建、曠日持久的內戰、永無休止的黨派爭端、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香蕉熱)、專制統治的血腥恐怖(大屠殺),都集中反映了哥倫比亞和拉美大陸的現實矛盾,從而折射出了哥倫比亞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
“歷史如何歸于文學”,這無疑是賈平凹在寫作《老生》時縈繞于心的問題。在他反復誦讀《山海經》之時,筆者以為《百年孤獨》這種書寫家族乃至民族歷史的思路,對賈平凹的《老生》創作一定也有著深刻的啟迪。
于是,二十世紀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在《老生》中就通過秦嶺倒流河旁的四個村鎮故事串連了起來。
小說的第一個故事主要講述了老黑、李德勝等人的秦嶺游擊隊的故事。中國共產黨自領導武裝斗爭開始,就十分重視建立和發展游擊隊。秦嶺游擊隊的故事可謂極具典型性。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人,懷著起初各自不同的動機和目的 ,走到了一起。老黑“或許就是玩槍的命”、“誰有槍了誰就是王”,為了槍就和李德勝一起拉桿子干;匡三只知道革命了就可以吃飽飯,當老黑對他說:“要吃飽,跟我走!”匡三就跟著老黑走了。一年半后游擊隊就壯大起來,“所到各地,遇到高門樓子就翻院墻,進去捆了財東,要錢要物,能交出錢和物就饒命不殺,如果反抗便往死里打,還舍不得子彈,拿刀割頭,開倉給村里窮人分糧。許多人就投奔游擊隊,最多時近二百,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卻人人系著條紅腰帶,腰帶上別著斧頭或鐮刀,呼啦啦能站滿打麥場。”然而,革命并不是一帆風順,從皇甫街的激戰到轉入深山的游擊戰、部隊人員的死傷以及缺彈少藥、游擊隊的解散和重組等等,都是革命草創時期的生動寫照。
《老生》中第二個故事是“老城村”土地改革的故事。“老城村”的故事形象地折射出了中國那個歷史階段的情景。
在中國,土地改革過后,伴隨著大饑荒的年代,農村開始了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展開了人民公社化的運動、農業學大寨、反右運動和史無前例的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老生》的第三個故事——“過鳳樓公社”的故事,生動概括了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一系列社會變遷。我們從“過鳳樓”公社西北角的棋盤村的統一著裝統一發型出工修梯田,看到了“人民公社化”“農業學大寨”的情形;從老秦蘿卜絲湯碗里看到半圓形的油珠珠,不免讓人感嘆那大饑荒年代人吃人的慘相;從劉四喜夜間從檢舉箱里夾紙條偷看,感受到了反右斗爭中互相檢舉揭發所造成的人與人關系的“間離”;從苗天義和張收成在磚瓦窯場的改造,不免令人對“文革”浩劫的唏噓。“過風樓”公社幾乎成了那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縮影。
翻過那令人沉重的歷史篇章,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老生》中第四個故事——“當歸村”的故事就發生在此時。當歸村的人一開始因為沒有技術,只能外出撿破爛脫貧。后來,戲生在老余的指點下,開始搞養殖業,將當歸村變成了回龍灣的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群眾收入也明顯改觀。可是,為了增加產量快速致富,原本質樸的農民們開始昧著良心在各種植物動物的養殖過程中摻入激素飼料等,致使食者出現拉肚子、孕婦流產等不堪情形。這不免讓我們想到了黃浦江上的大量“死豬”、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地溝油”等等當今社會的食品亂象。當歸村的農副產品被勒令停止生產,回龍鎮街上的所有銷售點也被取締,戲生的村長也當不成了。正在他情緒低落之時,老余又給他指了一條路,讓他去雞冠山礦區發財。于是,我們又跟著戲生看到了當今礦產的無序開發和骯臟交易的黑幕。從礦區回到當歸村的戲生,緊接著又在老余的策劃下,為了一百萬的政府獎勵,來了一出弄虛作假的“秦嶺尋虎雙簧計”。自然,紙包不住火,最終事情總是要敗露的。這一事件深刻地諷刺了當今社會上的弄虛作假的丑行。背著罵名回到當歸村的戲生這回只有哭的份了,可是老余依然有辦法讓戲生重新站起來。戲生在老余的點撥下,首先種植起了當歸,真的翻身成了回龍灣鎮的首富。正在他風光無限,期待著拜見匡三司令之時,他等來了一場瘟疫。這一下子讓我們記憶起了2003年的那一場“非典”。戲生在回當歸村的村口被村人堵住了:“你是帶來過財富,可你現在要帶來瘟疫!”是啊,改革開放的確給當今的中國人帶來了許多,有利的方面,也有弊的方面。這確實值得我們掩卷而思!“當歸村”的故事在警醒著我們!
賈平凹的《老生》以發生在秦嶺倒流河旁“正陽鎮”、“老城村”、“過風樓公社”和“當歸村”的故事,濃縮地將中國紅色革命從游擊隊起家到建國后的土地改革、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直至改革開放的近百年的歷史和社會時代風貌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它是賈平凹對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內涵厚重的記錄,正如賈平凹先生在后記中所言:“《老生》就得老老實實地呈現過去的國情、世情、民情。”賈平凹的《老生》不僅具有著文學的歷史價值,而且還有著豐富的文獻意義。
因而,我們不難發現,賈平凹的《老生》近百年歷史的書寫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歷史書寫有著相同的歷史價值意義。
二、藝術技巧的借鑒
除了要歷史地再現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近百年社會變遷外,賈平凹在寫作《老生》時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敘述又如何在文字間布滿空隙,讓它有彈性和散發氣味”,這就涉及到小說藝術技巧的問題。在仔細品讀《老生》之后,我們發現,《百年孤獨》的小說藝術對《老生》的文本敘事或多或少有著一定的影響。
首先,在小說開卷句式的時間維度上有著一定的相關性。
法國學者塔迪埃在《普魯斯特和小說》中就有“將小說中的時間作為形式來探討”的話題。時間在小說中是無形的,是讀者看不見的,但卻是小說中潛在的重要形式。塔迪埃認為:“在作品中重新創造時間,這是小說的特權,也是想象力的勝利。”
《百年孤獨》的開卷句式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隱含的時間維度。“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準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馬爾克斯以這一句為起點,回頭追敘奧雷里亞諾上校幼年時代的經歷、馬孔多創建初期的情景,然后講述馬孔多的史前狀況,之后再描寫馬孔多的建設和發展以及布恩迪亞家族的繁衍,一直講到奧雷里亞諾上校站在行刑隊前。《百年孤獨》這一開卷句式一反傳統的依時序進展的敘事程序,而以一個不確定的現在為端點,既能指向未來,又能回溯過去,一下子把時間的三個維度都包容在小說的第一句話中了。這種同時瞻前顧后的敘事方式奇特而新穎。
馬爾克斯這一煞費苦心的經典句式,曾經受到很多中國當代作家的競相模仿。從莫言的《紅高粱》(1986)、韓少功的《女女女》(1986)、蘇童的《平靜如水》(1989),陳忠實的《白鹿原》(1992),再到郭敬明的《幻城》(2003)、余華的《兄弟》(上下,2005-2006)等小說,都出現了“多年以后……”類似句式或者類似句式的變種。其實,這不只是一種模仿,而是意味著對中國當代小說敘事的一種解放。這種解放主要體現在作家的時間觀上,作家可以不再恪守過去傳統刻板的線性時間觀,時間在敘事里面可以自由折疊、交叉乃至重疊,使讀者領略到敘述的無限機智和巧妙,這是對固有的小說敘事的極大沖撞和革新。
賈平凹《老生》的開卷句“秦嶺里有一條倒流著的河”,可謂是這種時間觀解放的又一體現。雖然作者沒有采用馬爾克斯“多年以后……”那樣融過去、現在、將來三維時間于同一言語時空的經典句式,而是采用傳統的線性時間觀,但卻一反傳統大多按“過去-現在-將來”安排事件的發生發展的時序,小說以現在作為端點,順著這“一條倒流著的河”來“回歲”——追溯過去。正如薩特所言:“小說家的技巧,在于他把哪一個時間選定為現在,由此開始敘述過去。”《老生》就是這樣從終局(“石洞”)開始,再回到相應的過去和初始,然后再循序展開,最終構成首尾相連的封閉圓圈。
好的小說是需要一個好的開頭。馬爾克斯對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的重要性曾這樣說過:“長篇小說或短篇故事的第一句話決定著作品的長度、語調、風格和其它的一切。關鍵問題是開頭”,“因為第一句話有可能成為全書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全書的風格和結構,甚至它的長短。”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開卷句式無疑是精彩的,以致中國作家何況說:“在我讀過的所有作品的開局中,我最喜歡這個精巧神奇的開場白,在這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隱藏著一種深沉的悲涼和無可奈何的宿命感,卻又憑借著巧妙的時空交錯形成了巨大的懸疑。”無疑,賈平凹《老生》的開卷句式在某種程度上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開卷句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老生》中也具有著《百年孤獨》中“重復”的文本特征。
重復是《百年孤獨》的一個很重要的文本特征。這種重復最明顯的是體現在人名的重復。小說中布恩迪亞家族人名和性格一再重復。布恩迪亞和烏蘇拉這第一代創始人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就是第二代。大兒子叫阿卡迪奧,次子就是小說第一句提的奧雷里亞諾上校。小說接下來的第三代第四代一直到最后一代,有五個取名阿卡迪奧,有三個重要人物叫奧雷里亞諾,另外還有第二代的奧雷里亞諾和十七個女人生的十七個私生子,都叫奧雷里亞諾。不過其中有條規律可以遵循,就是所有的奧雷里亞諾們都遵循一種行為方式,都是一樣的性格,而阿卡迪奧們都遵循另一種,兩類人絕不會混淆。布恩迪亞家族子孫的名字、秉性、命運都一成不變,男性均為奧雷里亞諾或阿卡迪奧,女性均為阿瑪蘭塔或雷梅苔絲。這種刻意地重復人物的名字和性格以致類型化的傾向,除了拉美地區的起名特色以外,無非是為了淡化人物的個性特征而突出家族、集體的氣質。
我們再來看《老生》。《老生》中的人名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重復。在后記中賈平凹談到:“此書之所以起名《老生》,……書中的每一個故事里,總有一個名字里有老字,總有一個名字里有生字。”也就是說,賈平凹在《老生》的四個故事中也有著“老”字和“生”字為名的重復:第一個故事中的“老黑”,第二個故事中的“馬生”,第三個故事中的“老皮”和“墓生”,第四個故事中的“老余”和“戲生”。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老黑”和“老皮”都是因自身體貌特征而得名:“老黑”得名是因為從娘肚子里被拽出來后,“實在是長得黑,像是從瓦窯里燒出的貨,人見了就忍不住摸下臉,看黑能不能染了手”;老皮是“出生時像個老頭,臉上的皮很松,家里人為了好養他,故意起了難聽的名字。”“墓生”和“戲生”均為侏儒都因其父母而得名:“他爹他娘被槍決時,他娘已經一頭窩在沙坑里了卻生出了他”,故為“墓生”;“戲生”的爹是雙鳳縣在幕后舞皮影戲的簽手。
賈平凹《老生》中這種“老”字和“生”字的名字重復,雖然不同于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有血緣關系的家族成員之間的名字重復,但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帶這“老”字和“生”字的名字的人,多少都和秦嶺游擊隊有一定的瓜葛。譬如,第四個故事中的“戲生”就是李德勝同意加入游擊隊的“半截子”擺擺的孫子,而對第四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老余”,作者在第一個故事中就作了交代:老黑跟著王世貞到龍王廟來緝拿兇犯,“把龍王像推下來,砸成碎塊。廟里再沒了龍王像,卻住了個老頭,是來采藥的還是逃荒的,誰也不知道,但老頭越來越長得像那個跛子老漢,只是個子矮,腿長短一樣。這老頭后來落戶到嶺寧縣,生了個子,兒子當了縣人大主任,孫子就是過風樓鎮政府的老余。”而那個跛子老漢就是先前被李德勝和老黑一起商議拉桿子之事,擔心被他偷聽到后通風報信而被誤打死的。由此,我們也可以說《老生》其實講述的是秦嶺游擊隊三代人的故事。
第三,《老生》中也運用了大量的魔幻因素。
眾所周知,《百年孤獨》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巔峰之作,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是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征。魔幻因素在作品中可以說俯拾皆是:人愛吃泥土、愛啃墻灰;湯鍋、瓦罐、書、籃子、鮮血可以自己走動;人喝完巧克力茶徐徐升騰;幽靈、鬼怪反復顯現;人鬼交往、天人感應等等。小說運用極度夸張、詼諧的筆觸描寫種種奇人奇景,讓讀者在強烈的感官刺激、“陌生化”的效果中獲得了或歡愉或恐懼的審美體驗。
賈平凹在《老生》之前的許多作品就引進了魔幻因素,在寫實的基礎上大量揉進了怪異神奇的故事,如《懷念狼》中金絲猴成精,變成女人來報答恩人;狼成精后,可以隨便變成女人、老頭、小孩和豬來迷惑人;《秦腔》中引生唱秦腔唱得清風街的白果樹流淚;夏天義的兒子因長得瘦小,就認豬為干爹,之后變得身體健壯,像豬那樣能吃能睡;瘋子引生不僅有高于常人的領悟能力,而且還能化身為昆蟲與蚊蠅,因為他喜歡白雪,有時就變成蛾子粘在她衣服上,有時變成螳螂爬在她肩上,有時變成蒼蠅繞著她飛……。在《老生》中,我們依然能夠讀到這些怪誕之事:第一個故事中正陽鎮茶姑村的貓竟然說起了人話,喊起了“婆,婆”;虎山的龍從天上下來和牛交配,“生下一頭豬,但又不像豬,嘴很長,耳朵太短”,預示著英雄要行世;老黑被殺時,“靈桌的豬頭上趴著了一只指頭蛋大的蒼蠅,王世貞的姨太太趕了幾次沒趕走,突然哭起來,說:世貞,世貞,我知道你來了!就破嗓子喊:剜他的心!剜他的心!老黑的心被剜出來了,先還是一疙瘩,一放到王世貞的靈牌前卻散開來,像是一堆豆腐渣。”在第二個故事中有牛皮卷拴牢的蹊蹺之事;有張高桂一哭,家里驢豬狗貓全哭的事;有張高桂一死,魂附在邢轱轆身上的怪事;有徐副縣長看到蓋著豹紋被單的匡三成了一只豹子的事;有馬生一呵斥,場子上的塵土竟然像蛇一樣向辦公室這邊游動等等……這些描寫透露出濃厚的神秘、魔幻色彩,使得《老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既受馬爾克斯影響啟發又帶有本土化色彩的中國式的“魔幻寫作”范例。
第四,《老生》和《百年孤獨》都擁有一個隱身敘事者。
關于小說敘事視角的問題,賈平凹認為略薩的《綠房子》“由作者敘述,但讀者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敘述人是“隱身的”,他明確表示“喜歡略薩的《綠房子》”。
同屬拉美文學的《百年孤獨》就有這樣一個隱身的敘事者。這個敘事者是吉普賽預言家梅爾加德斯。梅爾加德斯是死后復活然后再死去的神奇人物。在第二次真正死去之前,用一種密碼寫下了這個家族的全部歷史,這就是羊皮紙手稿,留給一百年后布恩迪亞家族最后一個人——也叫奧雷里亞諾——來破譯。讀到小說的最后,我們才發現馬孔多的故事原來是一本書,是由梅爾加德斯留下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百年孤獨》這本書,也是由梅爾加德斯敘述出來的。
同樣,《老生》也采用了這種隱身敘事。小說中唱陰歌的唱師,其實是和梅爾加德斯一樣的人物。他是“一輩子在陰間陽間往來,和死人活人打交道”的神奇人物。在老唱師真正死去之前,聽著《山海經》一山一水的注解,聯想到自己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往事。一個山一條水,一個村一個時代。讀到小說的最后,我們發現秦嶺倒流河旁的各村鎮的故事串聯起來就是我們近百多年的歷史,就是一本書,這是老唱師給我們留下的。因此,毋庸置疑,《老生》這本書是老唱師敘述出來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老生》中有許多藝術技巧的處理,或多或少地受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小說藝術的啟發和影響。然而,不可否認,賈平凹不愧為中國當代小說的藝術大師,他在注重吸取馬爾克斯的創作經驗的同時,又極力凸顯和保持著其不同于拉美魔幻的本土化特色和異質化特征,也正因如此,《老生》的寫作無論與《百年孤獨》的藝術親緣關系是深是淺,它始終是“賈平凹式”的。這也充分展示了賈平凹在對馬爾克斯的文學借鑒過程中那種積極探索的民族精神和勇于創新的民族意識。
三、文學境界的追求
一直以來,賈平凹并不滿足于停留在對外來藝術技巧的借鑒上。通過對中外文學作品的大量比照和發現,他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現代派大家的作品,除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思維角度不同外,更重要的那些大家的作品是蘊有大的境界和力度,有著對人生的豐富體驗和很深的哲學美學內涵。這才是青年作家真正需要學習借鑒的,若僅從外在的毛皮上仿描,那只能是鉆胡同。”他說:“我近年寫小說,主要想借鑒西方文學的境界。”賈平凹的《老生》可以說正是這種西方文學境界追求的一部力作。筆者以為這種文學境界的追求主要體現在對歷史性的追求、對民族性的追求以及對人類共通性的追求等方面。
歷史如何進入文學?作品如何典型地反映時代特征?賈平凹從馬爾克斯那兒得到了很好的解答。他用馬爾克斯比照自己的寫作,“有人采訪馬爾克斯,他說小說家天生就是和社會抗爭的,他不管你是啥社會,總是不合作,因為他的思想老是超前,也不是他有意和政府對抗,或持不同政見,而是小說精神決定的,文學的本質是批判,這是天生的一種矛盾。”他說自己“寫作時我的生命需要寫作,我并不要做持不同政見者,不是要發泄個人的什么怨恨,也不是為了金錢,我熱愛我的祖國,熱愛我們民族,熱愛并關注我們國家的改革,以我的觀察和感受的角度寫這個時代。”
在與外國文學大師的比照中,賈平凹得出了“文學應該為社會作記錄”的結論。他認為這種社會記錄:一是要真實,“作品主要寫生活,少加觀念方面的東西,政治評價呀道德評價呀都不可直接堆到作品上”;二是揭露批判現實中的丑惡,宣揚美善理想,探討“人類究竟怎么樣才生活得好”;三是要準確地再現時代精神和民眾心態,“從現實生活中抓當時社會心態問題,抓準了,抓得有力,涵蓋面就大”。
《百年孤獨》可以說在“為社會作記錄”方面是一個典范。布恩迪亞的家族史映照的是整個拉美大陸的歷史。馬孔多世紀是個落后、封閉、被現代歷史遺忘的邊緣的后發展國家或地域的象征或縮影,它遠遠超越了一個地理小鎮的涵義。馬爾克斯通過描寫布恩迪亞家族和馬孔多小鎮的百年興衰,詮釋了拉美大陸百年來的遭遇。賈平凹在《老生》中秉承著這種“文學應該為社會作記錄”的歷史性追求,用秦嶺倒流河旁的各村鎮串聯起來的發展史觀照著中國大陸近百年的歷史。一個村鎮成了一個時代的象征或縮影。賈平凹通過對秦嶺游擊隊及其相關人物和各村鎮的人事變故,真實而客觀地將近百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世道變遷呈現在讀者面前。賈平凹自言這是一次對“民間寫史”的嘗試,但又何嘗不是一次對文學體現歷史性的探求呢?!我們不得不承認,賈平凹在以文學的方式表達生活的深度上,早已走在了中國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的前面。
在強調“想借鑒西方文學的境界”的同時,賈平凹提出了“如何用中國水墨畫寫現代的東西……”,他說:“在具體寫法上,形式上,我盡量表現出中國人的氣派、作派,中國人的味。這足以說明賈平凹對文學體現民族性追求上的自覺。
《百年孤獨》是一部極具鮮明民族特色的魔幻現實主義杰作。馬爾克斯雖然曾受到喬伊斯、福克納、卡夫卡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但他更多地繼承了拉丁美洲本土文學傳統。譬如,對于生與死、現世與來世的看法,如《百年孤獨》中所描寫的那樣,就是拉美印第安人的看法。《百年孤獨》中的阿瑪蘭塔,用全部時間為自己編織精美的裹尸布,她能預測自己死亡的時間,答應全村人,幫他們給故去的親人捎信,致使設在家里的信箱塞得滿滿的,來不及寫信的,她還應諾給捎口信。這看似十分荒誕的情節,竟源于馬爾克斯的真實生活,他就有一位像阿瑪蘭塔這樣的親屬,是個老處女,她預知自己的死期,便坐下來織裹尸布,裹尸布織好了,她便靜靜地躺下來,死神果然前來把她帶走了。就這樣,生與死、人與鬼的界線完全被打破。正如墨西哥作家帕斯所說:“在古代墨西哥人眼里,死亡和生命的對立并不像我們認為的那么絕對。生命在死亡中延續。反之,死亡也并非生命的自然終結,而是無限循環的生命運動中的一個環節。”這不僅僅是墨西哥人的看法,也是哥倫比亞乃至大部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看法。諸如此類,馬爾克斯從各個角度反映了他想表現的拉丁美洲的現實,極具拉美民族性。
賈平凹曾非常坦誠地說過:“拉丁美洲文學中有魔幻現實主義一說,那是拉美,我受過他們的啟示,但并不故意模仿他們,民族文化不同,陜南鄉下的離奇事是中國式的,陜南式的,況且這些離奇是那里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賈平凹在作品中一直在努力建構著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東西。這次《老生》的創作中,我們不說別的,僅就《山海經》的引入,就足以顯見賈平凹的立意與追求。《老生》除了開頭,四個故事和結尾都是先引入了中國上古時期涵蓋諸多內容的奇書《山海經》中的《山經》部分,然后通過飽學之士和孩童的對答解釋,進而引發老唱師的世事聯想。從《山海經》的一山一水到秦嶺山脈的一村一時代,賈平凹有機地將鮮明的中華民族山水人事呈現在讀者面前。
“越有民族性地方性越有世界性,這話說對了一半。”賈平凹這“說對了一半”,實際上是說民族性和世界性是不矛盾的,因為“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關于這一點,賈平凹在其《四十歲說》中有過更詳盡的闡釋:“要作為一個好作家,要活兒做得漂亮,就是表達出自己對社會人生的一份態度,這態度不僅是自己的,也表達了更多的人乃至人類的東西。作為人類應該是大致相通的。我們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替古人流淚,之所以看懂西方的東西,為他們的激動而激動,原因大概如此。”這也就是說,文學除了體現民族性的追求之外,文學還必須體現人類的共通性。
活在世間的人時而都會有孤獨感,而作家的日常寫作也常會有一點孤獨。馬爾克斯非常擅長寫“孤獨”這一主題,《百年孤獨》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孤獨的主題。馬爾克斯說:“《百年孤獨》不是描寫馬孔多的書,而是表現孤獨的書。”不僅作者如此闡述,而且作為讀者的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也深切地體會到了那種人的孤獨、家族的孤獨以及拉丁美洲的孤獨。孤獨是家族的人一個個相繼失敗的原因,也是馬孔多毀滅的原因。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孤獨”,確實寫出了人類共通的東西,引發了人們對人性的深刻思考。
賈平凹也一再強調:“寫作內容要表現一些人類相通的東西”他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人世間的每個人都生活著,生活著的人自然就牽扯進各種關系。于是,《老生》中,有了人與社會的關系,有了人和物的關系,有了人和人的關系,有的緊張而錯綜復雜,有的清白和溫暖,有的混亂和凄苦,還有殘酷、血腥、丑惡、荒唐。那么,人為何而生?“生命有時極其偉大,有時也極其卑賤。唱師像幽靈一樣飄蕩在秦嶺,百多十年,世事‘解衣磅礴’,他獨自‘燕處超然’,最后也是死了。沒有人不死去,沒有時代不死去的。”賈平凹《老生》中對“生”的思考,承載起了對于人類生存本質的關切、對人類命運與現代人精神狀態的思考。
綜上比照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賈平凹的《老生》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在歷史性、民族性和人類共通性的追求上,其文學境界是相通的。從這個意義來說,《老生》和《百年孤獨》都是履行了文學宏大使命的作品。
朱靜宇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注釋:
①孫見喜著:《賈平凹前傳》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頁。
②伊夫· 塔迪埃:《普魯斯特和小說》,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第284頁。
③加西亞·馬爾克斯著 范曄譯:《百年孤獨》,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頁。
④轉引自吳曉東著:《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60頁。
⑤⑥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百年的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談創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頁,第182頁。
⑦林曉云、司空小月著:《荒誕的閱讀快感和通感——晚報讀書沙龍關于〈百年孤獨〉的閱讀體驗》,《廈門晚報》2007年9月2日。
⑧?孫見喜:《賈平凹前傳》第二卷,《制造地震》,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頁,第470頁。
⑨孫見喜:《賈平凹前傳》第一卷《鬼才出世》,第418頁。
⑩夏林主編:《廢都廢誰》,第299頁。
??????孫見喜著:《賈平凹前傳》第三卷,《神游人間》,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頁,第357頁,第252頁,第254頁,第274頁,第277頁。
?孫見喜著:《賈平凹前傳》第一卷《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頁。
???肖夏林主編:《〈廢都〉廢誰》,學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頁。
?帕斯:《孤獨的迷宮》,轉引自鄭克魯主編《外國文學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3頁。
?孫見喜著:《賈平凹前傳》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頁。
?賈平凹:《四十歲說》,見賈平凹《人極》,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頁。
?馬爾克斯:《番石榴飄香》,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