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印象
馮連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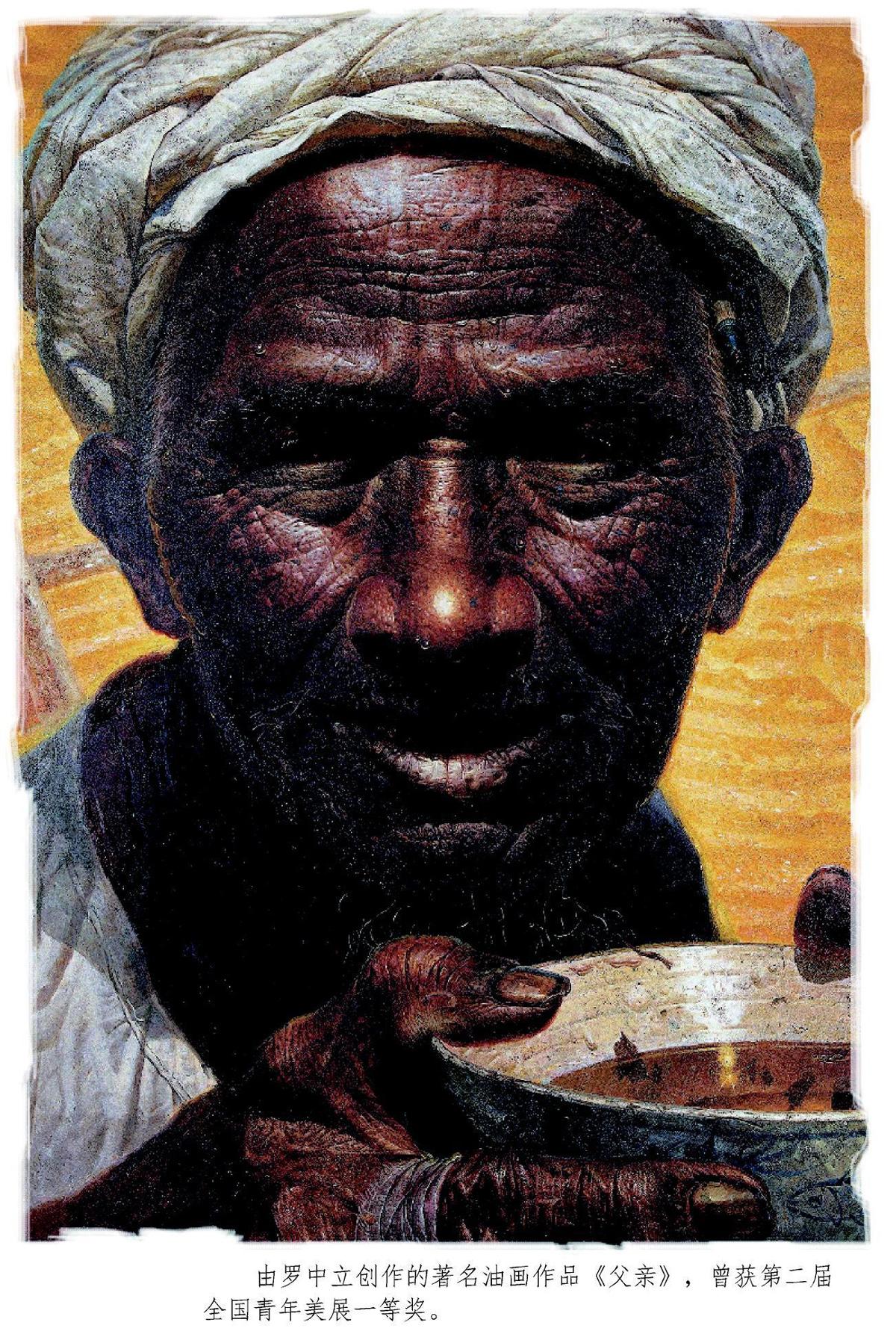
父親離世時,我尚年幼,但父親在我的記憶中并不模糊:細高挑的個子,走起路來慢慢悠悠的;瘦削的臉上深嵌著兩只大眼睛,棕黑色的皮膚顯得人更瘦了。父親總是不停地咳嗽、哮喘。打我記事起,他就像“長”在了醫院一樣,而奶奶、媽媽和我們兄妹六人,則是時常光顧那幾所醫院且心情糟糕透頂的常客。
父親的病由來已久。從日本統治大連到解放初期,父親一直在鋼鐵廠燒制耐火磚,長期的粉塵環境使他患上了嚴重的矽肺病。1958年,父親響應號召,從鋼鐵廠轉到郊區農業社任生產隊長。當時,“大躍進”的口號正喊得震天響,全國上下各個領域都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為了完成任務,父親帶著社員們戰三九、斗嚴寒,拼命地工作,這使他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很快就垮掉了。母親一再叮囑他在家休息,可母親前腳上班剛走,父親就又偷偷摸摸地去工作。反復高燒加上長期的勞累,父親終于一病不起。醫生的診斷結論是晚期矽肺病,基本喪失勞動能力,需終生休養。此后,父親在結核病院一住就是整整一年半。
我八歲那年,正是全國人民普遍挨餓的時期。對這場天災加人禍,處在社會底層的父親似乎有著一種本能的預見和防范。身體稍微好轉時,他就扛著鎬頭出門,到郊區的山山峁峁開地,每天忙忙碌碌的,前后竟然開出百余塊大到兩三米、小如鍋蓋般大小的莊稼地,統統種上了地瓜和苞米。至少有大半年的時間,父親都在忙著蒔弄那些莊稼。瘦弱的他挑著一對糞桶,拄著棍子,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家和山地之間。家里的旱廁總是被父親掏得干干凈
凈。直到有一天,我跟父親一起上山,我蹦蹦跳跳先上了山,等了半天仍不見父親的身影,于是我原路返回去找他,卻看見父親站在山下劇烈地咳嗽,渾身都在顫抖,地上還殘留著一攤未干的血跡。
父親再次住進了醫院。但那年秋天,父親開出的“巴掌地”卻出奇地爭氣,收獲的地瓜和苞米多得堆不下,我和哥哥在屋子里搭了兩層吊鋪才勉強全部放進去。那時,人們大多處于饑餓狀態,左鄰右舍有的餓得全身浮腫,有的誤食有毒的樹葉險些喪命,有的吃代食品得了病,而我們家不僅沒有餓死人,還幫助許多親屬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
父親雖身體羸弱,但他很愛孩子,即使我們犯了錯,他也舍不得戳上一指頭。父親偶爾從醫院回家,為了避免傳染不得不與我們分居、分餐,但他總是千方百計找機會親近我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家都有好幾個孩子。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個不太容易受關注的位次,但父親從來沒有忽略我,而是一直用最細微的舉動關愛著我。寒冬臘月,我的鞋里總是潮乎乎的,每晚我入睡后,父親就找來干爽的苞米葉子,用梳子梳成一絲一絲柔軟的細條蓄進鞋里,第二天,我的腳在冰天雪地里就能享受到一整天的溫暖。如果某天他忘記了這項任務,就會因此而面帶愧疚,偷偷塞給我一樣小玩藝兒以示補償。父親干不了重活兒,哥哥當兵走后,家里挑水的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每次我挑著兩大桶水,走起路來趔趔趄趄的。父親見狀,就從廢品收購站買來兩只小巧的油漆桶,改裝成水桶,從此我肩膀上的紅腫徹底消失。
人們常用高山來形容父親的偉大和父愛的厚重,但我的父親更像是夏天的涼風、冬天的暖陽,讓人為之身心舒暢。父親的手很巧。春天,他給我們扎各式各樣漂亮的風箏漫天去放;夏天,他給我們做小巧玲瓏的木船到河邊漂流;秋天,他扛著鎬,背著籮筐,到收過的莊稼地里撿地;冬天,他給我們做五顏六色的陀螺到冰上撞打。講故事更是父親的拿手好戲,他講的地主拿元寶和窮人比孩子的故事我至今銘記,這是父親對我認識人的價值的啟蒙和照耀。特別是當他自豪地講到,地主拿著元寶可以墊起桌子,但窮人的四個孩子卻可以把桌子抬走時,嘴角露出的笑意近似得意。父親是家里的黏合劑,每次他出院回家,我們家就變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我們兄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樂的孩子。
父親比母親整整大一輪,兩個人的生日只差一天。父親平時沉默少言,母親則是風風火火,脾氣來得快,走得也快。兩個脾氣截然相反的人卻相濡以沫,感情甚好。許多事情,他們僅靠眼神交流就能明白對方的心意。母親的工作是三班倒,父親心疼母親,總是把家里最好的飯菜裝進母親的飯盒。有一年春節,父親給母親的飯盒里裝滿了餃子,可母親下班回來后卻悄悄地抹眼淚。原來,母親的工友發現她的晚飯竟然是餃子,就到領導那里提意見:“救濟戶還能吃上餃子,說明她家的生活根本不困難!”父親為此感到愧疚,不停地向母親檢討:“都是因為我吃救濟飯,才讓你跟著受委屈……”
1968年,父親的病情越發嚴重。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拼盡全力,用他生命僅剩的微弱光芒照亮我們。他趁二哥放暑假,帶著他上街去賣冰棍;他給我編了一只小圓筐,讓我到鍋爐房揀煤核;他耐心地教大姐支鏊子攤煎餅;他無力再去照應山地,就在房西頭開出了三分薄田,種上各類蔬菜,竟然也夠維持一大家子人的日常所需。
為了給父親治病,家中稍微值點錢的東西都處理了。不到五年時間,錢花光了,還欠下了三千元的外債,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啊。病中的父親飽嘗了世態炎涼,但他沒有任何怨言,還表現得異常豁達。他一再對家人講:“不要報怨,這要是在舊社會,咱這個家就得筐要飯、家破人亡……”父親還時常和我們講這樣一個謎語:“弟兄七八個,圍著柱子坐,大家一松手,衣服就扯破。”在父親的潛移默化下,我們兄妹不僅學會了在困境中生存的技能,而且懂得了兄弟姐妹之間要相互扶持、互相幫助——即使只有一塊糖,我們都不會占為己有,而是兄妹幾個輪番品嘗;遇到累活兒、臟活兒,哥哥、姐姐總是搶著去做;一個人在外面受欺負,其他兄妹手拉手登門理論。這種拼命抱團的家風一直延續下來,并且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如今,我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但是對于父親的印象不但沒有隨時間湮滅,反而一次次在夢中、在故鄉的老屋前、在發了黃的照片里變得愈加清晰。透過零零星星的記憶碎片,我依然能感受到父親那份疼愛妻子兒女的心,還有老山東那倔強不屈的德行。
責編/張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