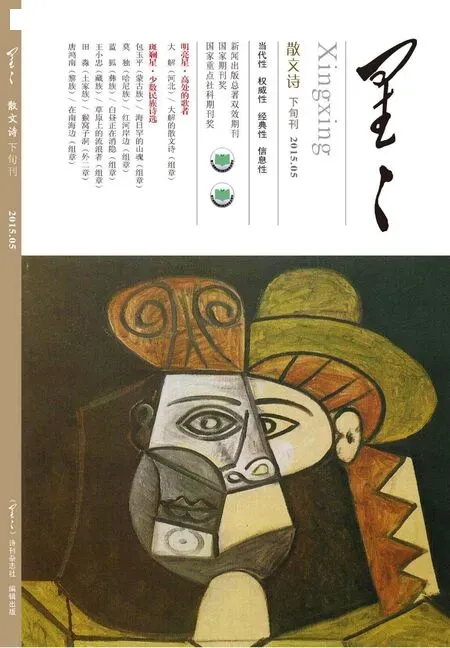風吹故鄉(組章)
王崇黨上海
風吹故鄉(組章)
王崇黨上海
清明雨
那些父親本來應該在的地方,現在都空著。
我看見風嗚咽地圍著那些空打著旋,卷起地上的香樟樹葉,像在拋灑著若干年的紙錢。慢慢地,那些憂傷的風抬著那些空,就像抬著父親的靈柩,越來越遠……
一場適時而下的清明雨,滾燙地下著。
我們兄弟埋放在父親身邊的柳樹棒,在淅淅瀝瀝的雨里,長出了新芽。
風吹故鄉
風吹過屋后的小竹園與吹過莊稼地,聲音是不一樣的;風吹過母親的亂發與吹過村后的墳場,聲音也是不一樣的。
故鄉的每一個物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調弦的樂師,每次都能恰如其分地調出鄉音。
每次我擦拭完父親的牌位,都會恭恭敬敬地放回原處。故鄉在隨處等著你,清晨出去隨便走上一趟,鞋就濕了。
母親已看不見了,但我每次從城里回家她都知道。一次是母親睡著了,我回來后靜靜地立在床前。她醒時,一下子就抓住了我:“這孩子,咋不叫醒娘呢”。
回城時,路過山崗,我聽見風吹過堅實的山壁時,像河流在父親裸露的脊背上歡快流淌;風吹過有空洞的山壁時,像失去老馬的小馬駒在泣聲嘶鳴。
忙 音
我每天都要給一個人打電話。
可是,不是號碼按到一半,突然被事情打斷,就是電話忙音,多少年來一直都沒有打通。
我不知道他為什么這么忙碌。我想問候一下他,讓他幸福的時候要提防厄運,痛苦的時候要想想彩虹和父母,思鄉的時候不要讀李白的《靜夜思》,失戀的時候不要一個人在河邊遛達。
終于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替我撥通了那個號碼。
我看著自己的手機響個不停,淚水嘩嘩嘩地流。
方 言
有方言的人,是有故鄉的人,也是幸福的人。
家鄉的寂靜也是一種方言。
家鄉的寂靜,站著聽與俯下身子聽是不一樣的,只有當你的身心和它緊貼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真正察覺到寂靜從鄉土里泛上來的體溫。
如果你能和草木一起靜立不動,寂靜的方言就會在你身上結滿露珠。
寒冬里,我們提著方言的小火爐,穿過童年的時候,更多跌落的寂靜會從夢里蘇醒過來。
異鄉再大也是航行的船。
在異鄉,我的心總是蕩著的。只有在家鄉,心才是平的,世界也是穩妥的。
漂泊在外的人,很容易與操著方言的老鄉喝個大醉——
醉眼里,對方只是一塊小小的鄉土。
寂寞長出叢叢木耳,每一只都努力豎著,朝著家鄉的方向。
丟 失
我的第一聲啼哭,讓家鄉的寂靜大吃一驚。
慢慢地,我就與家鄉的寂靜融為了一體,成為家鄉寂靜樂器的一個部件,一個發聲的簧片,我的站、坐、臥、側的各種姿勢都參與著寂靜的發聲。
我的漂泊遠離,讓家鄉的寂靜響起連綿的幽謐思念。
在繁華的都市,我走著走著,就丟失了腳步聲,丟失了悄悄話,丟失了喃喃自語,丟失了愛的私語……
那些聲音,要么沒入了噪音的水位下,要么懶得再說出來。
油漆工
有些事物是命定的。
春天正在生長,卻忽然把嫩芽憋了回去,想流淚的人忍住了悲傷。
我到處尋找適合粉刷的東西,母親用破的抹布,父親用舊的木尺,一只半埋在歧途中的鞋子,都被我涂上鮮艷的顏色。
后來我又找到霉黑的王氏族譜,找到孤寡的二胡,胎死蛋殼的雞雛,甚至找到陽春三月剛備好的棺材,我把它們全部刷成好看的顏色,還畫上花草、蝙蝠和仙鶴等裝飾紋樣,畫上神靈的庇護和鄉村的樂器。
我累了,蹲下來,鯉魚一樣在冰冷中彎起身子。
漫山遍野的迎春花忽然開到了我腳下,我假裝很開心很幸福。
爺爺,可能是你在土里翻了個身,突然之間——
我哆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