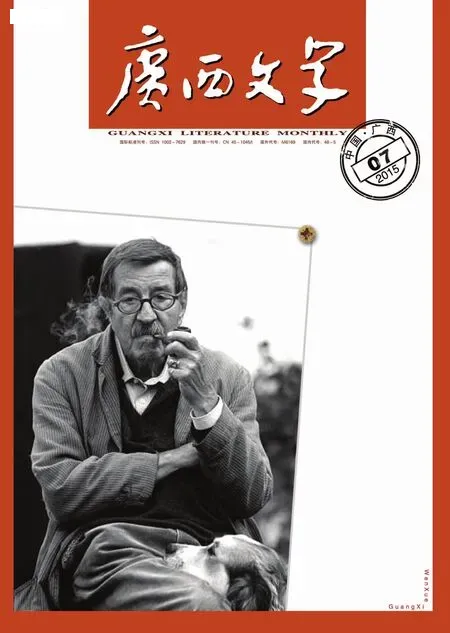馬頭情緣
黃 榮/著

說來我與馬頭是挺有緣的。
因為工作的關系,曾經很多次來到馬頭,但每一次留給我的記憶都不一樣。
20世紀90年代末,剛從學校畢業分配到鄉鎮工作,很巧,我工作所在的鄉鎮就在馬頭的隔壁,于是便有了與馬頭的不解之緣。
應馬頭朋友之約,在一個夏日的下午,下了班,邀上幾位朋友開上自己的摩托車就出發了。在那個時代,摩托車還算是稀有物,年輕人能有一部嘉陵70C摩托車,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行駛在鄉村集鎮上,回頭率極高,況且開摩托車的是一位模樣還稱得上俊秀挺拔的年輕人。幾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大家一邊開著摩托車一邊熱烈討論著某某學校是不是又來了位年輕漂亮的女教師,不知不覺就進入了馬頭的地盤。下了坡,摩托車駛入了一片綠色的林海里,道路兩旁低矮的山坡上一片連著一片連綿起伏郁郁蔥蔥的松樹林,就這樣沖進眼睛里,更確切地說是直撞入了我的眼里。也許是山多樹多的緣故,空氣頓時變得涼爽了起來,一路來的燥熱感也在此時被空氣中的涼意趕得無影無蹤了。一陣陣涼爽的風兒輕拂著臉龐,就像心愛的姑娘的撫摸,有些癢癢但是愜意極了。胯下的摩托車仿佛也被這涼爽的天氣感染了,發動機的轟鳴聲變得輕柔歡快起來。就這樣,來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馬頭街,馬頭街不大,集鎮上的房子傍著一個小山坡依地勢而建,兩排上了年紀的瓦房分別建在道路兩旁,這就是馬頭街。黃昏夕陽的照射下,瓦房斑駁,顯得有些破敗,再加上集鎮不大,因此馬頭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小而偏僻。友人早已備好了當晚的飯菜,啤酒是必不可少的,還有馬頭的魚仔。友人說這些魚仔是從本地河里打撈上來的,原生態,味道極好,看著讓人垂涎三尺。煎得金黃的魚仔,我忍不住就夾起一條送進嘴里,果然是味道鮮美!當與友人說起,馬頭的天氣很涼爽。他告訴我,因為背靠著大明山,再加上有山有水有樹,所以這里的溫度常年都要比外面的溫度低二到三攝氏度,即使是在酷暑,晚上睡覺的時候也要蓋著薄被才行。
因為有這位鐵哥們在馬頭工作,便經常有了到馬頭的時間和借口。一來二往也便與當地人熟識起來,也因為有了跟馬頭人接觸的機會,更清楚馬頭地處偏僻,經濟發展還滯后于縣內的其他鎮份,群眾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但在我的印象里,馬頭人天性樂觀,熱情豪爽,喝起酒來也絕不含糊,能喝一斤絕不喝八兩。每一次到他們家去做客,都會慷慨地拿出家里最好的東西來招待,因此馬頭的河魚,土雞土鴨,還有一些野味就成了我大快朵頤之后最深的印象。與當地人混個臉熟之后,得益于遺傳了祖輩父輩的好基因,每當年輕帥氣玉樹臨風的我出現在主人家,總會有熱情的阿嬸不放過“提豬頭”的機會,熱情招呼著坐下來,然后急切地張羅著要給我介紹張三李四家貌美如花的女兒。在壯家人的婚娶風俗里,豬頭是不可或缺的,在婚娶當天,一個鹵過的大紅豬頭再披上一朵大紅花,是祭拜祖先以保佑新人往后的日子里紅紅火火恩恩愛愛相偕到老的最好信物,這個豬頭最后的歸屬是要拿給媒人的,在媒人們的眼里,“提豬頭”是至高無上的榮譽,“提豬頭”意味著媒人已經把年輕男女培養成了夫妻。或許是年輕靦腆矜持,或許是年少輕狂,我最終還是辜負了馬頭阿嬸們的好意,沒有當成馬頭姑爺。雖然缺少了一段與馬頭姑娘風花雪月的情緣,但是,與馬頭的緣分并沒有因此而中斷,它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抹去的記憶。

百年老屋
就這樣我初識了馬頭。
2013年的5月,一紙公文把我從鄉鎮調回到了縣城工作,距離馬頭遠了,心想再到馬頭的機會可能更少了。但沒曾想,我到馬頭的機會反而更多了!
原來,不甘人后的馬頭人民克服了地理海拔高、氣候多變、日夜溫差大、光照不足、人多地少、氣候陰涼等不利自然條件的制約,利用地處巍峨秀麗的大明山腳下,秀麗的風光和得天獨厚的水資源,大力發展特色農業綜合開發,大作“山”“水”“風”“古”的文章,開發大明山、小明山,再造生態經濟林,利用各村屯荒山荒坡,大力發展山區特色種植業和養殖業,群眾的腰包漸漸地鼓起來了。“美麗廣西·清潔鄉村”活動開始之后,馬頭鎮巧妙避開資源劣勢,依托這山這水獨特的自然資源,全曾村尾雷屯、四明村板亨屯、奮進團隊等先進典型的不斷涌現,一舉走在了全縣的前列。因為開展“美麗廣西·清潔鄉村”工作的關系,我頻繁來到馬頭。
馬頭,對于我來說,不是疏遠了,而是走得更近了。
今年5月,我再次來到馬頭采風。
因為修路的緣故,我們乘坐的客車開得很慢,一路搖擺著前行。也許是大家正襟危坐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太久了吧,車輛一出縣城,縣內的作家、攝影家們就像一群久不出籠的鳥兒,在車廂里熱鬧了起來,就連平時寡言少語的巧哥也變得分外活躍。車輛行進的速度不快,正好可以好好欣賞這一路的美麗風景。

古老的石磨
來到了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全蘇村的蘇溪屯。這個屯我并不陌生,2月的時候,曾經帶著記者來到這個屯,對當地的返鄉農民工在春節期間返鄉之后積極投入清潔鄉村的先進事跡進行深入采訪。第一次到這個屯的時候,感覺它是暖暖的,當我再次踏上蘇溪屯這片土地時,這溫暖的感覺依舊。道路一如既往的整潔干凈,公共場所小孩子、老人三三兩兩悠閑地圍坐在一起,每家每戶的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凈凈井井有條。村莊就坐落在群山環繞的盆地里,不遠處就是大明山,從大明山下來清澈的山水長年從村莊前的小溪流過,溪水靜靜地流淌,不緊不慢。低矮的瓦房和新起的樓房相得益彰,在這里,瓦房沒有因新建的樓房而顯得多余,反而是因為歷經滄桑的緣故而增加了些許歷史的厚重感,新起樓房也沒有因瓦房的存在而顯得突兀,這也許是得益于他們新起的樓房還保持著鄉土味吧,沒有時髦的造型,沒有粉刷上喧囂熱鬧的鮮艷色彩,裸露著的磚頭反而保持著幾分野趣,顯得沉靜低調。村莊的氛圍,和村莊一脈相承沿襲下來的文化積淀就這樣和諧相處著。我喜歡這里,喜歡它的不張揚、不做作,喜歡它的自然隨意。走在這里,再煩躁再急性子的人都會安靜下來;走在這里,你會有少年時村莊的記憶,會尋找到生活在高樓大廈里已經丟失的部分記憶和樂趣。

馬頭清澈的溪水
在村前那棵象征村莊保護神的榕樹下,退休老干部老蘇向我們徐徐講述著關于這個村莊的故事。蘇溪屯原來不是叫蘇溪,因村里出了一位叫蘇希洵的歷史文化名人,為了紀念他就改為蘇溪屯。當年,蘇希洵因聰明過人,早年漂洋過海留過洋,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七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因深受當時的兩廣總督陸榮廷賞識,陸榮廷就把自己的養女許配給了蘇希洵,回國之后他先后擔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廳長、中華民國司法院第一屆大法官。不難想象在這樣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出了這樣一位官至三品四品的人物,是何等的榮耀!但就僅憑這一點來解釋蘇溪屯改名之謎也未免太牽強,以壯家人向來不喜歡攀權附貴的傳統就足以證實我的猜測。因為工作的關系,我走過縣內的絕大多數村屯,在許多村莊的歷史里也曾有過類似蘇希洵這樣的一些人物,但僅憑有所謂的權貴官賈,村莊因此而改名則未聽聞,難道這個蘇溪屯是個例外?關于蘇溪屯改名的來由,村民們也是語焉不詳,我再細翻歷史資料,發現蘇希洵在當時絕對稱得上文化名流,他早年留過洋,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把法文版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譯成中文,著有《現代憲法的趨勢》《羅馬法與中國固有法律之比較》等書。不難看出,與其說他是個官,不如說他是個事業有成的學者更為恰當。當看到他的子孫們在許多年后提起這一位從山村里走出去的人物還是一臉的自豪時,我恍然大悟。知識教育對于這樣一個偏僻的小村莊,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想象,當一個小小村莊的群眾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里沉寂安靜很多年之后,突然間就出現了這樣一位文化人,是何等的驕傲!對文化教育是何等的頂禮膜拜!也許正因為這樣,為激勵后人,當地人就把蘇希洵當作文化的象征,知識分子的代表順理成章地把村莊改了名,在他們的眼里一個改變村莊歷史的文化學者擁有這樣的榮譽是當之無愧的。因此,他們再把蘇村的名字改成全蘇村也就不足為奇,在村民樸素的思想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孫們都能成為像蘇希洵一樣成就一番事業的文化人。這樣樸實的想法其實就是蘇溪屯先人留給全蘇村子孫后代的一筆最為厚重的精神財富。

美麗的馬頭
我們沿著縣里面為建設新農村而鋪設的水泥巷道行走著,細細品味著這個村莊所具有的歷史沉淀和韻味。
在一座紅磚紅瓦圍成的四合院前,老蘇告訴我們,這座房子有上百年的歷史了。“上百年的瓦房?”我一驚,趕緊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鏡架。老蘇又介紹說,在他小的時候已經見到這所房子,那時候家里的老人說這個房子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了,他現在已經年過七十,加起來,這房子至少有一百年了。而且這所房子是用泥漿砌成的,沒有一丁點水泥、沙子、石灰之類的東西。聽到這,人群中發出了一片驚嘆,我趕緊扶了扶眼鏡,仔細觀察這座傳奇般存在的瓦房,這座老房子坐北朝南坐落在蘇溪屯的一處不起眼的低洼地,瓦房沒有雕梁畫棟的精美,有的是經歷歲月沖刷留下的痕跡,有的是精致細膩的做工,看到這房子,我們依稀還能感受得到當時的泥水匠們建造這房子時精益求精的細致。這所百年不倒的老瓦房不禁讓人想到報紙上一則寧波建成僅二十三年的樓房倒塌的消息,這百年后依然堅固如初的瓦房不得不讓人感嘆,我們現代的鋼筋混凝土竟比不上舊時的泥漿?我瞬間凌亂了。
有意思的是這里的大門。有精心用紅磚砌成拱形的大門,有兩塊厚木板做成的大門,有久經歷史沖刷、破舊不堪的大門,有華麗美觀堅固無比的大門。大門對于我們這般普通老百姓來說,不僅僅是起到防盜賊的作用,而且通過這道門才能把家庭與社會清楚地隔離開來。一到了晚上,關起自家的大門,沒有了紛雜社會事務的干擾,沒有了工作上的忙碌,有的只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其樂融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房子有了大門,家才算得上一個完整的家。看得出來,蘇溪屯和壯鄉的許多地方一樣,門還被賦予了家庭興旺發達的神圣使命,或榮華,或富貴,或平安,或健康,或長壽。所以這里的門不統一齊整開向一個方位,有偏東的,有偏西的,有方形的,有拱形的,大門的材料也不一而足,有高端大氣上檔次的不銹鋼門,有低調內斂的木門,還有一些斑駁的鐵門。在這里,大門的朝向、用材、形狀是與這個家庭主人的生辰八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在壯家人的眼里,大門的建造不能馬虎,具體到用的材料,所面向的方位,都要經過風水先生的精心測算,家庭成員的生辰八字一一排列寫在紙上,缺水還是缺木,宜忌用時掐指一算,大門的建造經度緯度,已經清清楚楚地寫在風水先生手中拿著的羅盤指向方位里。看到這些形狀各異、古樸有趣的門,攝影家們都禁不住拿起手中的相機“咔嚓咔嚓”地在門前拍起照來。在一扇青磚砌成的拱形門前,兩塊厚木板組成的大門緊閉,在經歷了無數個烈日的曝曬、風雨洗禮和蟲蟻的侵襲之后,兩塊古色古香的厚門板上刻出了一道道歲月斑斑的痕跡。門前,美女們紛紛拍照,陽光斜射,光影斑駁,笑靨如花。恍惚間,仿佛門打開了,門后一位落落有致的馬頭姑娘正含情脈脈欲語還羞地向我走來。

手抄經書記
全蘇村還有一棵更大的榕樹。因為經常下鄉的緣故,我見到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榕樹,但可以肯定的是,從沒見過這樣的母子樹。說是母子樹,是老的榕樹大部分枝干已經枯死掉。殘留的主干已經被寄生在老樹上的新榕樹緊緊地包裹住,就像長大成年的孩子緊緊抱住風燭殘年的老人反哺報恩。人有感情,想必樹亦如此吧。老蘇跟我們說,這棵樹應該有上百年的樹齡了,在他小的時候,這樹已經長得很大了。平常村民對這棵樹愛護有加,沒有人隨便折枝攀爬,也沒有人隨意拴牛把樹當牛欄,更沒人恣意破壞,也許是感恩于村民的厚愛,這棵樹愈發生機盎然,直聳云霄,像守護神一樣日夜履行自己的職責,靜靜地守護著村莊,護佑著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們。
一個村莊就是一部活的歷史書。

獸面紋提梁銅卣圖片
在前往全樂屯的路上,我們的客車在一片青翠的玉米地旁突然停了下來,正疑惑,同行的老蘇說,這個地方就是逸嶺,發現出土“國寶級”文物——獸面紋提梁銅卣的地方。他說,1974年,幾位生產隊的社員在這附近的逸嶺挖貯糞池,無意中挖出一件色澤晶瑩、紋飾繁縟的青銅卣。他們知道這是件寶物,趕快把青銅卣拿到水溝洗凈,送往公社革委會,后經自治區專家及國家文物局鑒定為公元前1600—— 前1046年商代時期的文物,并確認為一級藏品,現保存在廣西博物館里。當看到我們一臉疑惑的樣子,老蘇又說道,銅卣是古代的一種盛酒器,是商代人用來祭奠祖先和神靈的酒器。老蘇指著不遠處的一棵木棉樹說,那里就是發現銅卣的地方,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就是古時候的驛道,木棉樹那里還有個驛站。腳踩著這片土地,我們已想象不出古時候的驛道是什么樣子,古時候的這個驛站是怎樣的繁華和人來人往。聽著老蘇的介紹,看了這片神奇的土地和不遠處的木棉樹,我心想,在這里發現的這個銅卣一定是古時候征戰的壯士在這里與他心愛的馬頭姑娘離別時一飲而盡的手中酒樽,要不然,這木棉樹怎么像極了在這里默默守候的溫柔多情的馬頭姑娘婀娜的身姿啊。聽到這,原來我們腳下的馬頭這片土地竟是如此的滄桑,還會有多少深埋在地下的歷史秘密呢?我不得而知。時過境遷,古時候曾演繹多少悲歡離合的這片土地,已經化為了村民們賴以生存的一片片肥沃田地。古來征戰幾人回,壯士已經一去不復返兮,只有這棵婀娜多情的木棉樹還在這里守候著,默默等待她的心上人歸來。
人常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很有道理,至少我所接觸到的馬頭人可以證實這一點。
全蘇村全樂屯,韋伯的代銷店成為我們的臨時歇腳點。我們找到韋伯的時候,已是晌午時分,韋伯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一邊對我們說,今天太陽大,天氣熱,還一邊從冰柜里拿出了許多瓶裝的冰鎮飲料來給我們:“來來來,大家都過來喝呀,不夠冰箱里面還有。”我們一行人都面面相覷不敢接過來,因為我們內心都很清楚,這位看上去面慈目祥、樂善好施的韋伯是不會收我們錢的。這從稍后他從貨柜里拿出幾支強力膠水給人救急卻執意不肯收錢,可以證實我們之前的判斷。見我們不肯喝冰鎮飲料,他自覺心里過意不去又拿出自家種的木瓜,仿佛不給我們點東西吃,他就不會心安。盛情難卻之下,我們邊吃著木瓜邊和他交談。
韋伯的代銷店是間平房,應該建造得有些時日了吧,顯得有些老舊。走進代銷店里,雖然開著日光燈,但還是比較昏暗。韋伯代銷店擺放著幾排貨柜,但貨柜上的商品并不多了,只是零零散散地擺放著一些日用品而已。我猜想,韋伯代銷店的生意在以前應該還算可以的,不然不會擺放這么多貨架,現在韋伯的生意已經大不如前了,只是村里人偶爾還有需要,他就一直這樣堅持開著。相比擺放的商品,韋伯這間店更像他個人的成就展廳。店里更多顯眼的地方是用來展示他的藝術才能。一幅幅由他自己書寫的“致富在勤奮,實現靠永恒”“一張白紙能繪新的畫圖”“孝父母是走上天下第一位”韋氏語錄,白底黑字,邊幅上還自己精心地畫上了裝飾的花邊,記錄他的樸素思想。另一面墻上,則是他人生歷程的展示,年輕時獲得過的榮譽獎狀,年輕時的一些相片,還有那個年代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無不有著屬于他的那個時代深深的歷史烙印。在他的這面墻上,還發現了獸面紋提梁銅卣的相片,相片雖已有些模糊,但仍可看出銅卣的精美。

整潔干凈的蘇溪屯
韋伯個頭不高,中等身材,頭發花白但精神很好并且很健談,聲音洪亮。面對著我們一行人侃侃而談,談村莊的傳聞軼事,談自己年輕時的人生經歷。看得出來韋伯在這個村子里很有人緣,一邊與我們交談,一邊還時不時應和著過往村民的招呼。
韋伯的興趣愛好廣泛,而且精力充沛,看上去不像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年輕時他是村里的一名獸醫,現在不但經營著代銷店,還是一名師公,鄉村祈福人。他樂善好施,當我們提出要翻閱他的那些師公經書時,他爽快地答應,并從貨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珍藏的幾十本手抄經書本,他輕輕地拍拍這些經書的封面,遞給我們任由我們翻閱。我們認真地翻閱著這些經過韋伯一筆一畫認真抄寫的經書,從一頁頁經書的字里行間,我們翻閱的仿佛不是韋伯的經書,而是他自己的故事。

韋伯在吹笛
談到盡興處,韋伯還拿出自制的竹笛當場為我們演奏了一段,平時閑暇的時候,他還自己上山砍竹回來制作竹笛、竹簫等樂器賣給村里有需要的人。韋伯的笛子聲一響起,喚起了隨行的作家攝影家黃瓜老師的極大興趣,他隨手拿起笛子也吹上一曲。這時韋伯簡陋的小店里笛聲悠揚,歡聲陣陣。
離開韋伯的小店,我們來到位于全曾村的大明山最高峰龍頭峰腳下。沿著山路往上爬,不遠處的龍頭峰山頂云霧繚繞隱約可見,我們走到半山腰,看見散落的三兩間茅草屋,茅草屋邊是一片開闊的草地,草地上三三兩兩的雞正在悠閑地散步,當我們靠近,它們依然在草地上若無其事地散步著并沒有跑開,仿佛在向我們昭示著這是它們的地盤,我們來或不來,它們就在這里,與我們無關。就在老屋的不遠處,是一條從龍頭峰一路尋來的蜿蜒小溪,溪水純凈、清澈,小溪里光滑圓潤的石頭清晰可見,或大或小,看到這緩緩流淌的清澈山泉水,我們紛紛挽起褲腳下到水中,腳剛一浸入清冽的溪水中,我們奔波一天的勞累燥熱感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隨行的山歌手們禁不住臨水而歌。藍天,白云,綠草,老屋,潺潺流水,巍巍山巒,山歌繚繞,我們仿若置身于世外桃源,也許我們所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也不過如此吧。
車從高處駛下,從車窗看正好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整個全曾村。夕陽西下,太陽的余暉傾瀉在全曾村的大地上,一片金黃。遠處群山環繞,層巒疊嶂。不遠處的村莊,紅磚黛瓦的瓦房和高大聳立的樓房高矮錯落,相映成趣。近處的田地里,一片綠波蕩漾,砂石鋪設的機耕道路蜿蜒曲折盤旋著往前延伸,用鵝卵石鋪設水泥硬化了的水利渠道此時流水潺潺。一幅美麗的田園景象令人陶醉,流連忘返。此時此景,原來在我心中模糊的美麗鄉村的輪廓竟然漸漸清晰:村莊是有尊嚴的,我們的規劃設計應該是因地制宜的,但不隨便不刻意。村莊是有靈魂的,文化的傳承,文化的多樣性,是在繼承中不斷創新發展的,但不追求標新立異。村莊是有記憶的,村莊的建設不是全部推倒重來,而是新老結合,更迭輪回,上百年歷史沉淀的榕樹、老屋、老人、代銷店是村莊活的歷史,休閑廣場、樓房同樣也是在書寫著村莊未來的歷史。村莊是有責任的,干凈整潔的衛生環境,清新的空氣,藍藍的天空,清澈的河水,綠草菁菁,綠樹成蔭。
只有這樣,我與馬頭的美麗情緣,才能和這一路來正在修葺的道路一樣越修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