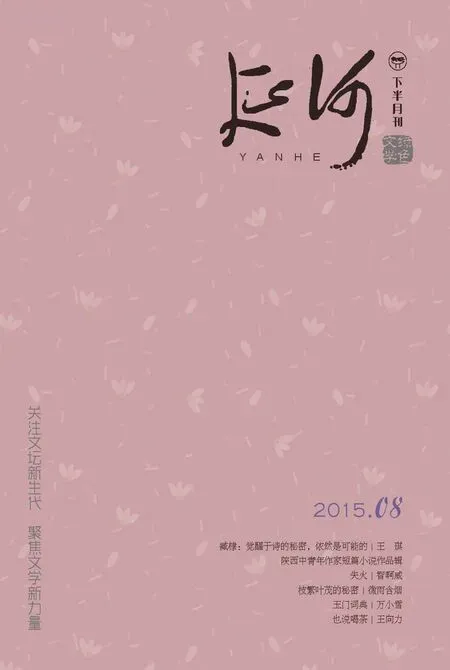十一朵紅玫瑰
云 崗
十一朵紅玫瑰
云 崗
1
中午下班,剛進家門,手機鈴不緊不慢地響了。我以為又是誰約我吃飯,心想早干啥去了,啥時候了,湊人數嗎?便想著如何拒絕。倒不是我這人事多,主要是我一回到家,就不愿意出去了。
翻開手機,卻是一個生號碼。我有點生氣,現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好好一個通訊工具,卻成了行騙的工具。上一星期天,我接了一個電話,電話里放的是錄音,一個女人義正詞嚴地說,法院里有你一張傳票,你必須在x月x日前如何如何,否則將怎樣怎樣。我聽得頭皮發麻,目瞪口呆,以為自己攤上事了,攤上大事了。又一想,自己就是一個主任,還是副的,提拔不到半年,不相干的事倒也干過幾件,卻不至于惹上了官司。心里卻不瓷實,便給法院里的熟人打電話。打了一個,無人接,又打了一個,仍然沒人接,我傻眼了。都說關鍵時候無朋友,看來這話在我身上要應驗了。這不,八字還沒見一撇呢,電話就沒人接了。不接就不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我一屁股坐到了沙發上。這時候,手機驚心動魄地唱開了,我一看,正是法院副院長高峰,他是我高中同學,忙去接。對方說,是夢生嗎?對不起,我剛才洗澡,有事嗎?我感動的眼淚差點掉下來,忙把剛才的情況講了一遍。未待我講完,高峰副院長斷然道:別理他,狗日的是個騙子,我也接到過同樣的電話!
這以后,一看到生電話我就來氣。
我剛準備摁掉電話,卻見來電顯示的地方是老家所在的市,便猜想是不是老家哪個親戚朋友打來的。剛升了職,可不能在父老鄉親面前落下口實。我想了想,便摁下了“接聽”。
“是夢生嗎?”對方是個女的,說話吞吞吐吐。
我說:“您是……”
“我是……容容。”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
我一下子沒有聽清,或者說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問道:“容容,哪個容容?”
“真是貴人多忘事,升了官,連老同學都忘了!”她輕輕笑了一下。
我呆了,比上次接聽到那個假電話還要呆。下意識中我往廚房方向瞅了一眼,只見妻子亭亭戴著圍裙正在炒菜,菜蔬落進油鍋里的滋啦聲甚是熱鬧。我趕忙往門口挪了挪,空著的右手也不自覺地擱在了嘴邊,極力穩定住情緒說:“對不起,這么多年了,不敢相信是你。你好嗎?”
“還行吧,但肯定不如你!”容容輕輕地嘆了一聲,接著說:“前兩天和幾個同學吃飯,他們說有你的電話,我就要了過來。”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說什么好。
亭亭端著剛出鍋的菜出來了,擱到茶幾上,又進了廚房。我們一直在茶幾上吃飯,這樣可以吃飯、看電視兩不誤。只有來了客人,才在餐廳吃。我一見,忙對容容說:“這樣吧,我現在有點不方便,隨后我給你打電話。”待容容說“好吧”后,我趕快摁斷了電話。適好亭亭又從廚房出來,不知道是我的神色不正常,還是她亂咋呼,竟說:“和誰通話,鬼鬼祟祟的?”
我的臉頰有點燙,又慢慢往四周洇。我似乎看見自己變成了紅臉關公,趕忙低了頭說:“一個同學打的,有啥鬼鬼祟祟的。”
“不會是老相好吧?”亭亭睨視了我一眼。
亭亭說話尖酸,近來越發來勁。似乎我已到了懸崖邊,她不疾言厲色的敲打我,我就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卻多少有點煩。
2
下午,我去省城開會。當了這個副主任后,會還真的就多了。雖然我不大喜歡這樣,可畢竟見的人多了,經的世面大了,自己便一天天在變化,可以說越來越像個領導了。但今天我的心情卻無法平靜,無論在什么地方,一睜眼,一閉眼,眼前晃動的都是容容的倩影。我想不到容容會給我打電話。二十多年了,容容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讓我無窮無盡地回味。甚至在反復的回憶中她的面容都有點模糊了。現在容容真的出現了,我卻有一種似夢非夢的感覺。
容容是我的初戀情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背著饃去一個叫高耳塬的地方上高中。高耳塬不大,卻的確高,四圍都是溝,好像從溝里長出來的一個平臺。我現在無法想象我當時的境況,但有一個字很能說明一切,便是“土”。可以說,土到家了!好在大伙兒都一個樣,誰也不笑話誰。
當然也不盡然,容容就是個例外。
容容大名明小容——一個很怪的姓,她來自我現在工作這個市最遠一個煤礦,離高耳塬不遠。當時的礦上有點亂,她爸望女成鳳心切,便把她轉到高耳塬磨煉。容容吃著貨真價實的商品糧,是我們心目中的城里人。她穿著白底碎紅花洋布衫,機器造的平絨系帶方口鞋,扎著兩個翹翹地小刷刷,在“土”堆中自然很顯眼。加之她的皮膚白,說話也很好聽,她在我眼里便愈發鶴立雞群了。
按當時的狀況,我不應該對容容抱有幻想,那有點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味道。我明白這個道理,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有時是有意識地追尋著她,有時是無意識地鎖定了她。到了最后,我的眼睛似乎已經離不開她了,一會兒不見心里便慌亂地好像丟了什么。
容容似乎發現了我的偷窺,有時也回過頭看我一眼,開始是驚疑,繼而含糊不清,最后竟然充滿了迷人的笑意,笑意中又隱含了深不可測的誘惑。每次當我的眼光和她的眼光相撞時,我覺得她的眼光就像一支箭,正嗖嗖地向我射來,方向看似是我的眼睛,中箭的卻是我的心。我的心隱隱地疼了起來,很舒服地那種疼。我趕忙收回眼光,仿佛落荒而逃的敗將。
這一天,我匆匆從教室出來欲上廁所,卻見容容正站在門口。她用書掩住嘴,頭微微低下,上眼皮使勁往上翻,死死地盯住了我。這一瞬間,她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白多黑少,飄忽不定,越發地嫵媚撩人。我呆在了一邊,傻子一樣,不知道該怎么辦。容容“撲哧”一聲笑了,然后擦著我的身子蹬蹬噔地進了教室。我的心隨著她的腳步聲撲通撲通地狂跳,兩條腿雖向前邁著,卻仿佛一個被電腦控制了的機器人,毫無主見。進了廁所,我不知道干什么來了,就那么轉了一圈,又回到了教室。
我知道我完了。但完了的我卻沒有按兵不動。幾天后,我斗膽給容容寫了一封信,信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你等著我,我一定會考上大學!”兩天后,正當我望眼欲穿,生不如死的時候,容容的信來了,信中也有一句關鍵的話:“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大學,到了那時候……”信的落款是“容容”。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父母給我起了個名字叫夢生,現在我真的恍若夢中了。但看著手里真真切切的信,我卻不得不相信我的夢實現了,我覺得我現在擁有世界上的一切!
但好景不長,容容突然不見了,一句話也沒有留就走了。一打聽,她竟然轉校了。我如五雷轟頂,一下子懵了。我恍恍惚惚,覺得整個世界都拋棄了我。待清醒過來,我整個人似乎像害了一場大病,已經沒有人形了。
后來,我考上了大學,又經過了兩次不成熟的戀愛,最終畢業分配到和我們縣相鄰的這個城市。但我沒有忘記容容,曾多方打聽她的消息,得到的結果卻是:她已經結婚了,嫁到了我們那個縣城。她丈夫是干什么的,我自然無心過問。至于容容為什么要對我這樣,我更懶得去想。或許她當時是逢場作戲,或許是她迫于壓力,或許她有難言之隱,誰知道呢?但我卻忘不了容容,每當想起他時,心里都有那么一種難以言說的痛,當然也有一絲隱隱地恨意。百無聊賴之時,好心人給我介紹了亭亭,我一見這姑娘長得挺干凈,走路風風火火地挺利索,當然了,最關鍵的是她多少和容容有點相像,半年后便和她結了婚。
說心里話,當初我和亭亭談不上有多大感情,但二十多年了,亭亭給我生了一個漂亮女兒,和我租過房,借過債,受過苦,可謂含辛茹苦,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在感情上我已經和她分不開了。她的缺點就是嘴碎,這兩年越發絮叨。她常給我說:“你是農村出來的,混到今天不容易呢,千萬不敢在生活上犯錯誤,撇開我不說,出了問題你大,你媽,親朋好友甚至鄉里鄉親的臉往哪里擱?”亭亭的話有點尖刻,但有道理,我自然記在了心里。可現在出現的是容容,是我的初戀對象,這叫我怎么辦?
晚上回來,我讓司機把車開回去,自己步行進了小區。經過中心廣場時,我又想到了容容。我停住腳步,隨意地掃視了一下廣場。廣場本應該是全小區人休憩、娛樂的場所,而今卻成了老頭、老太太們跳健身舞的地方。每天晚上七時整,音樂聲便會準時響起,什么《最炫民族風》《火火的姑娘》《草原情哥哥》《愛琴海》,不一而足,竟然還有《叫聲哥哥你快回來》。老頭、老太太在如此青春歌聲的伴奏下,邁開步子,甩動胳膊,很歡實地舞動起來,仿佛突然之間回到了激情燃燒的歲月,讓人好生感慨。現在,老頭、老太太們已經收兵,廣場上只有幾個人晃悠著,黑魆魆的,越發襯托出廣場的靜。我想了想,掏出手機,拐進了花園旁邊的樹叢里。
五月的夜晚,天空澄凈地像姑娘的眼眸,沉靜,明亮,纖塵不染。空氣中流淌著甜絲絲的芬香,熏的人有一種微醉的感覺。不知名的生靈或含蓄,或迫切地鳴叫著,不知道是在歡唱,嘆息,還是在呼喚心上人。
我左右看了看,然后翻開手機,撥通了容容的電話。說不清什么原因,手指按在“明小容”三個字上時,我心里似乎有一種曖昧的感覺,又隱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沖動。
“你好,夢生!”容容的聲音傳了過來,似乎她一直在等我的電話。
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蹙了一下,忙說:“實在對不起,下午去省城開了個會,剛才才回來,給你回電話遲了。”
“你大忙人嘛,哪會把我們平民百姓記在心上。”
“哪里哪里。”我心里有點熨帖,又多少有點不舒服,便改變話題說,“你怎么樣,還好嗎?”
“這話你好像問過了。”
“是嗎?”我的臉微微有點燙,“我是說你孩子和老公……”
電話那頭稍稍沉吟了一下,然后說:“我兒子上大學了,我老公在縣統計局當副局長。還想知道什么?”
我“哦”了一聲,心里冒出了一點醋意,心想過得不錯嘛。又一想,她丈夫雖然是副局長,卻是個副科,比我整整低一級呢,心里不覺又沾沾自喜起來。便又問,“你會開車嗎?”
“我用我家人的車學了幾天。”
“你家人是啥車?”
“桑塔納。你有車嗎?”
“有啊,帕薩特。”
“帕薩特”三個字一出口我便后悔了,心想咋這么庸俗呢?
接下來我不知說什么好,容容也不再說話,電話里死一般地靜。
我故意咳嗽了一聲,容容說聽著呢。我擰了擰眉頭,然后吞吞吐吐地說:“知道嗎?我曾經找了你好長時間!”
“是嗎,我咋不知道?”
“打聽到你時,你已經結婚了。”
“哦,都怪我爸,其實我……”
“現在好了,終于聽到你的聲音了,我心里很高興。”
“是嗎?”
“咱們離得不太遠,你有空就過來,我有空也過去看你,好嗎?”
“好吧!”聲音淡淡地,略含憂郁。
匆匆進了家門,明亮的燈光讓我很不適應。亭亭看了我一眼,似乎一下子看到了我心里。我的臉不由自主地紅了。
這一晚,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天快亮時方瞇瞪了一會。
3
過了幾天,我去寧波出差,順便去了趟普陀山。在寧波坐上船,望著浩淼的大海,我忽然想到了容容,心想著要是容容一起來就好了,那樣至少我就不孤單了。想到這里,我給容容發了個短信,說:“我在去普陀山的船上,到了那里,我會求菩薩保佑你的!”信息剛發走,手機便“叮鈴”響了一聲。我想,好快啊,就像守株待兔的人,兔子剛碰死,他便提到了手里。我有點激動,忙去看,卻是亭亭發來的短信,問我到了哪里。我有點失望,便把剛才給容容發的短信轉發給了她。亭亭回短信說:“搞那些虛頭巴腦的事干啥,你給我平平安安回來就行。”這時候,容容的短信來了,說:“你好瀟灑,謝謝!”我心里頓時熱乎乎的。
到了普陀山,天氣雖然有點熱,但看著肅穆莊嚴的寺院,意態如生的佛像,蓊蓊郁郁的參天大樹,特別是一對對拉著手的游客,我又一次想到了容容。一時幻想著和容容拉著手上山下山,燒香磕頭,求佛爺保佑我們。想著想著,我的臉上就像開了花,旁若無人的笑了。
自從心里有了容容后,我常常心猿意馬,晚上管不住自己的做那些小動作。每當這時候,我便會臆想出許多平日里根本不敢想的事。
高耳塬有一座大舞臺,前多年縣劇團、鎮劇團都在上面演繹過悲歡離合的人生,蕩氣回腸的愛情,紛紛擾擾的歷史。后來秦腔戲衰落了,舞臺也隨之荒蕪了。誰家的麥草垛竟然堂而皇之地堆上了舞臺。我想象著我和容容溜出學校,心照不宣地走向了舞臺。容容先到,她坐在麥草垛的后面,儀態雖羞羞的,一雙嫵媚的大眼睛卻放肆地撩撥著我。我亢奮的臉發紅,喘著粗氣坐在了容容身邊。容容的頭歪到了我肩膀上。我抖抖索索地抓住了容容的小手……
我還想象著我們去了高耳塬旁邊的溝里。這里太偏僻,太幽謐了,我的膽子一時大得出奇,竟然一把抱住了容容,緊緊地……
我渾身一陣燥熱,仿佛心里燃起了一團火,正在血液里流淌。
我突然想,我要見到容容,緊緊地抱住她,把心里多年沉積的情愫向她傾訴。
一陣風拂過,雖柔柔的,卻一下子喚醒了我。我緊張地向周圍看了看,確信沒有人注意我,方無精打采地向另一個寺院走去。
踏進寺院門,門兩邊站立著四個怒目圓睜,呲牙咧嘴的神像,說是四大天王。天王的腳下踩著一個個小人,代表著“酒色財氣”。其中一個天王腳底下踩著象征著“色”的女人。這女人乳峰高聳,長發飄逸,眉清目秀,算得上一個美女。只因天王的腳踩在了她的胸脯上,她的臉很是痛苦不堪。
我心里不自覺地“咯噔”了一下。
晚上回到寧波,高峰給我打了個電話,很悲痛地說他媽去世了,后天下午入事。
我正發愣,丁鴻的電話來了,問我知道不知道高院長家的事。我說知道了,明天坐飛機回來。丁鴻說那好,明天我到機場接你。
丁鴻過去是個礦工,對了,就和容容一個礦。后來,他不知怎么著就成了煤老板,和高峰成了朋友。我通過高峰認識了他,也成了朋友。

楊雪芳 繪畫
第二天下午,我一出機場,丁鴻果真就在候機廳迎接我。見我出來,他的司機小貴趕忙接過我的拉桿箱,顯出很急的樣子向外跑去。丁鴻先是和我握了握手,然后竟然抱住了我,巴掌還在我脊背上像模像樣地拍了兩下。我覺得很怪,骨碌碌向四周巡視了一眼,見無人注意我們,方也學著丁鴻的樣子,在他的脊背上拍了拍。
外面的陽光很明媚。明光锃亮的小汽車往來穿梭,車頂上泛出的光一閃一閃的,就像鏡子里反射出來的光,既虛幻,又真實。乘機的,到站的,接機的以及機場里的服務人員都穿得很干凈,有些還很時髦。一些看不出是女孩子還是少婦已經穿上了超短裙,露出炫目的大白腿。我感覺生活很美。忽然,我想到了自己回來的目的,心便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我敢打包票,機場上所有的人絕對猜不到我急急忙忙坐飛機回來,又坐上大奔是要去奔喪。
丁鴻堅決讓我坐前邊,自己坐在了后面。我回頭一看,丁鴻旁邊還坐了個女人。這女人長得端莊優雅,打扮得還算得體。
見我回了頭,丁鴻忙嬉皮笑臉地說:“忘了介紹了,這是你弟妹,叫個……舒舒。媽的,拗口的很!”又對叫舒舒的女人說:“這是胡主任,胡哥。”舒舒看了我一眼,微笑道:“胡主任好!”
這女人是我的“弟妹”不假,第幾個?說不清。反正我以前見過的“弟妹”中沒有她。我敢肯定的是,這個“弟妹”也絕對不是丁鴻的老婆。丁鴻的業余愛好是找女人,現在幾乎快成了他的主業。他對自己的戰果很是上心,對每個追到的女人都表現得柔情蜜意,頗有點相見恨晚,“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味道,外人一看,還以為真是兩口子。可這兩口子男的永遠是主角,女的卻你方唱罷我登場,走馬燈似地換,搞得我們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卻不好說什么,只能胡亂應付。這樣,我只得搖了搖手,說:
“哪里,哪里。”
隨便聊了聊外邊的見聞,話題自然轉到了高峰家的事。
我說,老婆不老嘛,怎么說走就走了。
丁鴻“咳”了一聲說,想不開唄,自從高叔走了后,老婆一直想不開,說的話都陰陽不分。
這倒也是。高峰爸前年去世后,高峰媽一夜之間變得瓷瓷的。話雖不多,卻句句不離老伴,什么“死老漢嘴饞的很,死了死了還要吃攪團,那邊沒有人給他攪,嫌潑煩,他捎話讓我去呢”,什么“死老漢又讓我去哩,嘿嘿,他離不開我呢”。聽得人脊背陣陣發涼。
高峰父母親是包辦婚姻。高峰爸是個教師,高峰媽是農民。后來有了政策,他媽便隨他爸進了城。但兩個人很要好,差不多到了恩恩愛愛的境界,外人見了絕對認為他們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忠實實踐者。有時候我突發奇想,假如有一天高峰媽發現老漢有一個情人,她會是什么反應呢?她還會那樣全身心地愛他嗎?她會后悔自己的一生嗎?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會嚇一跳,仿佛黑暗中看到了不該看的秘密。
當然了,高峰爸絕對沒有情人,我只是胡思亂想而已。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后視鏡,鏡中丁鴻和那個叫舒舒的女人依偎在一起,彼此的手還像小青年談戀愛似地握在一起。
一瞬間,我真的弄不明白愛情是個什么玩意。
高峰的老家在高耳塬,就是我們上高中同學的地方。葉落歸根,高峰爸去世后葬回了老家,他媽自然要和他爸合葬。
車子進了高耳塬,遠遠地,我的眼光便搜尋見了我的母校——高耳塬中學。我有點激動,似乎看到了自己朦朧的青春,品味到了自己青澀的初戀。可到了跟前,卻大失所望。學校的圍墻已經坍塌了幾處,仿佛沙漠上的古長城,給人一種滄桑和歷史的感覺。過去的門是大木門,現在已換成了鐵柵門。雖緊緊地閉著,但里面頹敗的景象卻一覽無遺。我知道我畢業幾年后,高耳塬中學就被縣上撤了,改成了什么職中,卻沒有人上,漸漸地,當年一片瑯瑯書聲的地方就被荒草占領了。
我讓小貴停下車,孑然一身走向母校。透過柵欄,我看見校園里雖然荒涼,但當年磚鋪的小路依然延伸著,仿佛雕刻在大地上的一首詩,正在抒發著心中的感慨。我的心倏忽間回到了當年迷離的歲月。恍惚中,我看見容容正風擺楊柳般地走在校園里,我遠遠地跟在她后邊。忽然,容容轉過彎不見了,我急了,忙忙地追了上去。剛轉過彎,容容從一棵樹后閃了出來,死死地盯住了我。我嚇了一跳,莫名其妙的傻笑起來……
“走吧,胡哥,別遙想當年了!”丁鴻在車里笑道。
我驚醒過來,卻一時想不通丁鴻怎么用了“遙想當年”這個詞語。我嘆了一聲,覺得歲月真的無情。
到了高峰家門口,丁鴻囑咐舒舒就坐在車上,不要下來。我看了一眼丁鴻,覺得他人雖有點粗,心卻很細。
高峰家很亂,一副入事前的景象。高峰和他愛人丁莉接待了我們。高峰一臉的沉重,明顯發福了的丁莉卻嘻嘻哈哈的像個彌勒佛。
丁莉和高峰是大學同學,上學時兩人就有了關系。那時候的丁莉雖不漂亮,卻苗苗條條地充滿了活力。畢業后,兩人鬧了點矛盾,便賭咒發誓地分了手。后來,高峰和丁莉高中一個同學談起了戀愛。丁莉知道后氣了個半死。他先是找高峰謾罵、威脅,甚至痛哭流涕,又找那個同學苦口婆心,義正詞嚴,還把她和高峰之間的事全部抖摟了出來。我當時是他倆的調解人,尚沒有認識亭亭,丁莉便對我說,狗日的誰不能找,竟然找我同學,這不是羞辱我嗎。等著,把我逼急了,我也找他同學。說著,飛快地瞟了我一眼。我嚇了一跳,朋友妻,不可欺,我只能逃之夭夭。
不用說,兩個冤家后來又和好了,孩子現在已經大三了。過去的事已經沒有人再提,似乎一切就這么順理成章。
我們先去吊唁故人。一到靈堂,高峰行孝子禮,跪在了靈堂的一廂。丁鴻一見,忙也撲通一聲跪了下去。站在一旁的丁莉欲笑,卻不敢出聲,只得極力地憋著,眼角邊的魚尾紋一時雞爪子似地張牙舞爪起來。高峰惱惱地拉了她一下,她翻了高峰一眼,閃到了一邊。
我在心里嘆了一聲,不自覺地想到了亭亭。亭亭倒沒有丁莉粗陋,可也越來越不講究。有時候在家里洗完澡,她就那么赤身裸體地走出來,把已經變形了的身體暴露在我面前,讓我很不舒服。你還不能說,一說就翻臉。要么說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要么質問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人,嫌棄她這個糟糠了,不行了就離。她啥都好,就是說話讓人難以接受。唉!
我點了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插到了香爐里。在供桌上的蠟燭上點香時,我總覺得遺像里的高峰媽正一眨不眨地盯著我看,似乎窺見了我內心的秘密。我趕忙避開老婆的眼睛,把香插上,然后像丁鴻一樣,跪在了地上。
本想陪高峰坐一會,說一些節哀順變之類的話再走,卻有人不停地找高峰。見幫不上忙,我們只得告辭而去。出了門,丁鴻問我就這么回。我故意做出考慮問題的樣子,然后用商量的口氣說,去一趟縣城吧,我多年都沒有去過縣城了!
丁鴻說,行,我也有此意。

周斌 書法
4
路上,我對丁鴻說縣城有一個女同學,多年不見了,順便去看看她。盡管我說的很淡然,很簡單,似乎一點感情色彩也沒有,丁鴻還是狂笑開了,邊笑邊用食指點著我說:“想不到平日里正兒八經的胡哥也……也……也……”他好像噎住了,半天沒有“也”出口。但誰都知道他要說的意思。我看見舒舒扯住丁鴻的胳膊,仰起臉看丁鴻,丁鴻也俯下臉看舒舒,兩個人睒了睒眼睛,會意地笑了。我的臉一下子紅到了耳根,忙分辨道:
“我不過是尋找一下青春的影子,沒有你想的那么深刻!”
丁鴻這下簡直就是瘋笑了,他捂著肚子說:“還……還……還青春的影子,哥哎,我可以肯定的是,尾巴也不知道丟哪里了。”
接下來丁鴻說了自己的一件事。他說,他上初中時看上了一個女娃,那女娃長得絕對沒啥說,白的很,學習也好。女娃卻沒有看上他,他給她寫信,拋眼色,送東西,人家非但不理他,還罵他是流氓,那段日子他差點就瘋了。后來,她考上了高中,他下井當了礦工,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自然便是狐貍和葡萄的關系了。再后來,他成了煤老板,腰纏萬貫了。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竟然是那個女娃,還說有機會的話想見他一面。他當時差點又要瘋了,忙匆匆趕去見她。可一見面,他幾乎沒有認出她來。他就像大冬天被人潑了一盆冷水,從頭到腳涼了個透。為了不把事情弄的太無趣,他請她吃了一頓飯,然后逃也似地走了。從此后,按丁鴻的話說:“我再也不相信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文人騷客嘴里所謂的狗屁愛情了!”
我笑了笑,說:“那女娃現在在哪里?她找你干什么?”
丁鴻詭秘地擠了擠眼,說:“這個嘛,保密。”
舒舒撇了撇嘴,說:“想不到你還是個情種。”
丁鴻摟住舒舒的肩膀,呵呵笑道:“鬧著玩,鬧著玩。現在我就愛你一個。”
我覺得丁鴻的話是對容容的不恭,對我的不恭,對那個純真年代的不恭,說:“我和你不一樣!”
丁鴻說:“一樣一樣的。我一直認為,每個人干事的目的都一樣,只不過為目的辯護的說法不一樣而已。”
我微微皺了皺眉。丁鴻似乎看見了我的不悅,忙改變話題道:“不管咋說,這畢竟是一次浪漫之旅,雖然沒有準備,但車是大奔,朋友是大款,女秘書是大美女,胡哥,你就大膽地往前走吧!”
丁鴻的話太直白了,卻暗合我的心意。我往后靠了靠,右腿搭在了左腿上。
丁鴻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哥,你約人家了沒有?”
我說:“沒有啊,去了再聯系。”
丁鴻又“咳”了一聲,說:“好我的哥哩,你就會當領導,弄這事真的不行。你不約好,人家不在怎么辦?有事出不來咋辦?約,現在就約。她不是縣城人嗎,讓她訂一家最高檔的酒店。”
我想了想,覺得丁鴻說的在理,便掏出手機,撥通了容容的電話,說:“我現在正往縣城趕,你在縣城找一家高檔酒店,晚上咱們聚一聚。”
電話那頭死一般地靜寂。
我頭上似乎已經漫上了細密的汗珠。
“我哪有錢請你嘛!”
容容終于說話了,我的心“咚”地放了下去。心里卻很不舒服,說:“你就訂個地方,我請你。”
“那就去君再來大酒店吧,聽人說那里高檔。”
“行,你先去訂個包間,我很快就到。”
車子沿著坡道向溝下行駛,我的心也隨之往下沉。到了溝底,陽光停留在崖壁上,周圍頓時陰暗起來,與溝沿上的景色判若兩個世界。穿過一座橋,車子又向溝上爬去,陰暗便一點一點留在了后面。終于,車子爬上了溝,又到了一個塬上。這塬雖比高耳塬矮了許多,陽光卻也艷艷地撒了一地。我的心情頓時又歡暢起來,一時間也理解了容容。是啊,現在生活雖然好過了,可能和丁鴻丁總相比的有幾個呢?容容能那樣說,說明她還沒有被這個世界污染,還實誠著呢,這樣的人如今真的難得呢!
車子進入縣城時,太陽已經站在了西山山巔上,天地幻化成了讓人留戀的胭脂紅。
幾年沒來,縣城已經被改造的面目全非。街道變寬了,樓房砌上了瓷磚,有的刷上了五顏六色的涂料,大街上到處都是五彩繽紛、肆意夸張的廣告牌。但仔細看去,縣城老氣橫秋的神態卻沒有因之消失,讓人咋看咋覺得像一個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老婦人。
汽車導航把我們帶到了君再來大酒店。這個酒店還真不小,應該是三星級的。進了門,我問明女士訂的包間在哪里。挽著發髻的服務員查了半天說沒有明女士訂的包間。我心里有點不快,說那現在給我訂個包間。服務員說就剩下“小宴”廳了,有點小,只能坐六個人。我說就小宴吧,明女士來了就帶她到小宴廳。
坐進包間,點好菜,容容還沒有來,我便給她打電話,語氣里明顯有了責怪的聲調。容容卻什么也沒有說。
丁鴻說:“不急不急,女人比不得男人,出門化妝呀,換衣服呀,擦皮鞋呀,事多得很。”
舒舒“咯嘣”磕了顆瓜子,低頭道:“我就不化妝。”
丁鴻說:“你還年輕,老了也一樣。不過,老了再怎么化也是個老,越化越讓人不舒服,一般沒人看。”
舒舒翻了丁鴻一眼,說了聲“德性”,然后把剝出的瓜子仁塞進丁鴻嘴里。丁鴻夸張地吧唧著嘴,連聲說香。
我受不了這般肉麻,轉過頭想起了心事。我想容容來了我應該說什么話,我們面對時會不會尷尬?如何排除這種窘境?我還想今后我們應該怎么辦……
這時候,包間門推開了,我的心一下子涌到了嗓子眼,咚咚地狂跳。我極力穩住神,卻見進來的只有服務員一個人。服務員落落大方地說,哪位是胡先生?我趕忙站起來說,我就是。服務員笑吟吟地說,剛才來了位女士,她讓我告訴您,她有點事,不能赴約了,請您諒解。另外,她讓我把這束花送給您。
我這才發現服務員抱了一束花,是紅玫瑰,鮮艷美麗的就像姑娘的笑靨。我接過花,只覺一股超凡脫俗的清香悠悠地飄進我的鼻孔,又游進我的胸腔,我似乎有點醉了,心情慢慢地平靜下來。
“這不是涮人嗎?給她打電話,什么意思?”丁鴻憤憤不平地嚷起來。
“呀,整整十一朵紅玫瑰呢!”舒舒說不清是驚嘆,還是羨慕。
我把花擱在餐桌中間,搖了搖手說,啥話都不說了,喝酒。話音未落,手機鈴驚心動魄地響了。我慢吞吞翻開手機一看,是亭亭的。亭亭出乎意料地溫柔,說:
“你咋還不回來嘛!”
◎唐云崗,筆名云崗,陜西蒲城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畢業后分配到銅川市工作至今。寫小說、散文。作品獲全國梁斌小說獎長篇小說一等獎、第三屆柳青文學獎、北方十三省市文藝圖書獎、孫犁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