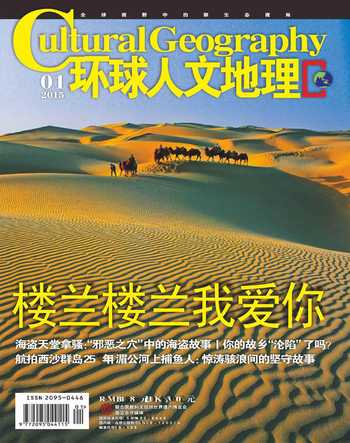你的故鄉“淪陷”了嗎?沖突:在經濟開發和文化流失之間
伯言








編者按:
2014年歲末,著名學者冉云飛的最新著作《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出版,書中薈萃了他十余年來有關巴蜀歷史文化的觀察與思考。作者根據歷代野史筆記,參以正史,輔以詩文,饒有趣味地爬梳巴蜀歷史文化。在整部著作中,作者以文化學者的視野,列舉種種案例,沉思家國歷史,追憶和探尋沉潛的文化,喚醒人們對故鄉的憐惜與保護之情。
在著名學者冉云飛心中,沒有故鄉的人是不幸的,有故鄉而又不幸遭遇人為的失去,則是一種雙重的不幸。“在經濟利益至上的風氣席卷下,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唯有對文化家園有所堅持的文人,用筆墨復活了自己心中的故鄉。”
面對故鄉的文物被毀、古器被盜、老屋被拆、江河被污染等逐漸“淪陷”的現象,冉云飛先生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查閱大量史籍,足跡遍布巴蜀大地,去追尋文化興廢,重新梳理巴蜀文化的歷史鉤沉,其著作《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的問世,再度讓人們看到了那些漸行漸遠的文化。
面對本刊記者的獨家專訪,冉云飛說:“既然我無法阻止那些破壞與變遷,但我可以憑借地下古物、紙上文獻、自我經歷,來建構那過去或即將消失的故鄉,聊以慰藉眾多像我一樣的受傷者。”
“我的故鄉已淪陷”
無法還原的吊腳樓和龔灘古鎮
在有識之士看來,那些舊的歷史遺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傳統——但若以社會的發展來看,許多我們想保留的東西,卻又未必能夠保留下來。
冉云飛的老家在重慶的酉陽,深藏在渝東南的崇山峻嶺之中,那里是神秘的北緯30度線穿過的武陵山區。作為詩人,他用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黑人訴說河流》的名句,來稱頌故鄉那條約一千二百里的河流酉水:“我知道河流像這世界一般古老/比人類血脈中的血流還要久遠……”
“任何一個民族的定居,在對水源的選擇上都是十分慎重而考究的,逐水草而居原非游牧民族的專利,圍繞武陵山區而言,對我們土家民族來說,鄂渝湘的酉水流域是永遠的故鄉。”
重慶境內古老的歷史文化名鎮——龔灘,是冉云飛家鄉的驕傲。古鎮坐落在烏江與阿蓬江交匯處的鳳凰山麓,擁有1700多年歷史。這里蘊藏著土家族的許多精神及物質文明,歷史悠久的冉家院子、西秦會館及不少寺廟,都是難得的活著的文物。
古鎮中最典型的文物,莫過于舉目可見的吊腳樓。吊腳樓的歷史淵源非常久遠,杜甫入蜀時曾寫道:“仰凌棧道細,野人半巢居”。古巴蜀地區多是瘴癘沮洳之地,且森林茂密,氣候比現在還炎熱,因此必須有底層房屋架空的巢居,才能最大程度地擺脫當時的環境對身體的傷害。后來,隨著平原地區氣候日趨干燥,人口越來越稠密,森林砍伐得厲害,巢居的形式便漸漸式微、衰落,只有在山區或一些需要人們爬坡上坎的大城市,還殘留有巢居的影子——這便是今日之吊腳樓。
在重慶、涪陵、萬州等長江沿線城市,以及烏江沿線的小鎮如龔灘等地,尚有吊腳樓的余韻風采。但隨著建筑材料的變更,建筑式樣的西化,大城市偶存吊腳樓樣式,與原來的吊腳樓韻味已經相去甚遠。只有在渝東南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才多少保留了吊腳樓這種“建筑活化石”。
然而,就是這樣一座堪稱“活著的土家族建筑博物館”的古鎮,在現代化的建設大潮面前竟然毫無抵抗之力——在下游修建的一座水電站,注定了原來的龔灘古鎮被淹沒的命運。早在2006年,龔灘古鎮就已經被拆遷,并在下游3公里處進行了復建。雖然有關部門宣稱“修建水電站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經濟,并且古鎮會按照原樣進行復建”——但那1700多年累積起來的神韻,只怕早已在搬遷過程中損失殆盡。
為搜集家鄉那些即將消失的人間愛物,冉云飛曾跑遍了這里的山路,“無法阻止,真有追之莫及的傷懷之痛。”冉云飛痛心地說,如今像這樣喊著‘大開發’的口號,冠冕堂皇地“為了發展經濟”,而罔顧保護傳統文化的行為,并不鮮見。在有識之士看來,那些舊的歷史遺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傳統——但若以社會的發展來看,許多我們想保留的東西,卻又未必能夠保留下來。
成都的“病態”
我們的精神家園怎么了?
“曾接納窮困杜甫的草堂門票愈來愈貴,草堂也愈來愈豪華,甚至還有人準備在草堂里建商業地產,名曰草堂二號……”
在《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沉淪》一書中,從眾多的例子可以看到,在當今的巴蜀大地,但凡可貼上“歷史文化”標簽的元素,似乎都已被開發打造出來,成為吸引一撥又一撥觀光客的噱頭,而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明積淀,也在指縫間悄然溜走。
冉云飛認為,作為四川乃至大西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成都,近年來也逐漸走上了文化“淪陷”的道路。作為2000多年來城址都沒有多少變動的城市,成都以山水之勝、風景之美而馳名天下,歷來吸引著各路人馬頻繁出入,他們在或短或長的羈旅中,不忘將他們所看到的蜀中景致傳達給友人,展示予讀者。但縱觀如今來到成都的各路旅行者,似乎都得到了統一指令,那就是導游們手中小旗子的指揮。一大幫人鬧哄哄地跟著導游,純粹是走馬觀花看熱鬧,那簡單的三言兩語,短短的十多分鐘游覽時間,怎能體會那些古老的建筑、書畫甚至草木里記載的歲月風華?
更令人痛心的是,成都這些年的改造,悄無聲息之間就毀壞了許多好東西。太多的打造、開發,讓這座原本純粹、安逸的天府之國,到處充滿了銅臭,那些慢悠悠的休閑時光,也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夜生活”里變得一塌糊涂。
冉云飛把著名的寬窄巷子稱為“成都最后的孤兒”,曾幾何時,這“孤兒”作為有百年多歷史的孑遺而如此滄桑多難,身歷數朝,愈發顯其不可多得的風致。人們行走其間,舊日風物、人物掌故聯袂而來,動人心懷。可是如今,這“最后的孤兒”也被狠心的父母給典當、賣掉而拆毀了。各色商鋪、各種酒吧會所五光十色的浮華,讓那最后一絲滄桑的味道也蕩然無存……
冉云飛在書中還重現了杜甫草堂的興衰:“公元759年冬,杜甫從甘肅同谷出發來到蓉城。第一次看見繁華的成都,冬天里還有綠樹,一個逃難的窮人,得到當時成都要員嚴武的扶助,在離市中心遠點的地方安身,于是他在浣花溪筑茅屋數間,成就了后世天下聞名的草堂。老杜在浣花溪寫下了他窮愁一生中最快樂的詩篇……但如今,曾接納窮困杜甫的草堂門票愈來愈貴,草堂也愈來愈豪華,甚至還有人準備在草堂里建商業地產,名曰‘草堂二號’……”
阿壩的窘境
開發與保護的矛盾沖突
“我們必須天然地利用現有環境,進行科學而適度的開發,而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保護傳統文化,應該是放在第一位的頭等要事。”
中國的旅游勝地大多位于西部,而西部的旅游核心地非阿壩州莫屬。從上世紀1990年開始,冉云飛就開始探訪阿壩,這里是他最鐘情的地方——神奇的九寨、上天的黃龍、醉人的米亞羅、自然之子牟尼溝、生物天堂臥龍、雪山女兒四姑娘、賞心悅目的黃龍大草原、“羌族生活博物館”桃坪羌寨等,無不閃耀著令人稱奇的魅力,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那些令人心醉的風光與人情,讓我此生不忘。”
然而,到了新世紀后的2011年冬天,當冉云飛再一次深度探訪九寨溝,卻發現與十幾年前的記憶大相徑庭:溝口再也不是簡單清凈的山與水,而是綿延數里的賓館、飯店,河邊的山坡上,樹木被砍伐得厲害,郁郁蔥蔥的原生態樣貌已大不如前……說到這里,他笑道:“幸好當年的冬天人少,九寨溝沒有人山人海,否則,我那大包小包的九寨之行就真的太‘造孽’了。”
冉云飛調查后發現,對景區的過度開發和利用,在西部真可謂舉目皆是,其狂熱程度讓人傷心,不少人在商業面前淪為毀我山川的“旅游瘋子”。比如黃龍大草原、紅原大草原聲名在外的豐茂草場,如今不僅面臨過度放牧、嚴重沙化、鼠害嚴重的危險,而且在每年的七、八月,密集的游人還會帶來植被破壞、垃圾污染等問題,那滿目瘡痍更令人憂心。這種竭澤而漁的方式,會使西部的人文地理、山川風物、民族風情、宗教文物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慢慢遭到侵蝕而逐漸消亡。20年后,在西部廣闊的土地上,這些上天的恩賜、人間的愛物,將以什么樣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實在令人不堪設想。
在這部書中,他不僅提出了對眾多開發項目的質疑,也提出了許多解答方式。冉云飛表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貧窮是勒在西部人民身上的繩索,但要去掉繩索,不是隨意亂剪繩索的某個地方,而是剪掉繩索本身打結甚至是死結之處。從根本上來講,剪掉貧窮這根繩索的死結,不是以人們喪失祖祖輩輩賴以立足的精神和物質的故鄉為代價,來讓他們吃飽飯。這個過程,不能全盤仿效東部發達地區,更不能成為某些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而搞的所謂“經濟大躍進”——“我們必須天然地利用現有環境,進行科學而適度的開發,而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保護傳統文化,應該是頭等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