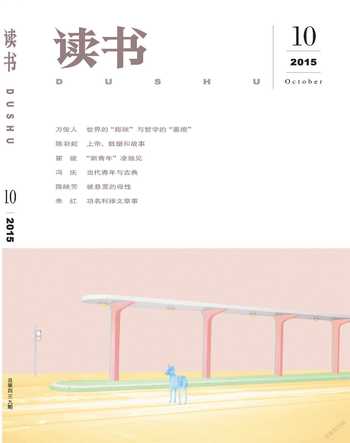松窗長晝憶平生
王振忠
去年五月,復旦大學博物館曾展出一批明人書畫,其一為松石圖,畫面上,枯松一株傲然挺立,左旁題句曰:“清標不受秦皇詔,勁節應嗤沈約腰。”此畫作于“萬歷年新夏”,具體年份不詳,但其言志詠懷,顯然意在彰顯松樹之清標勁節。
一五九三年(明萬歷二十一年),畫作者張瀚寫道:
余自罷歸,屏絕俗塵,獨處小樓。楹外一松,移自天目,虬干縱橫,翠羽茂密,郁郁蒼蒼,四時不改,有承露沐雨之姿,凌霜傲雪之節。日夕坐對,盼睇不離,或靜思往昔,即四五年前事,恍惚如夢,憶記紛紜,百感皆為陳跡。謂既往為夢幻,而此時為暫寤矣。自今以后,安知他日之憶今,不猶今日之憶昔乎?夢喜則喜,夢憂則憂,既覺而遇憂喜,亦復憂喜。安知夢時非覺,覺時非夢乎?……
這段人生感悟冠諸《松窗夢語》一書卷首,讀來令人神馳。著者張瀚時年八十三歲,寫下此話不久,他就溘然長逝,因此,該段絕筆實可視作對個人一生的感喟。當時,張瀚致仕回鄉已十數年,上揭文字是根據退隱蟄居后的周遭環境,回憶平生的經歷見聞,夾雜著個人的今昔感悟,筆之于書。所謂夢語,是指現實與夢幻其實都只是相對而言。此類頗具哲學意味的人生思考,顯然用的是莊周夢蝶的典故。據此看來,此時的張瀚一定想起了個人一生的宦海浮沉……
張瀚生于一五一○年,為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進士,時年二十五歲。此后,他歷任南京工部主事、廬州知府、潼關兵備副使、大名府知府、陜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刑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兩廣督府、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等職。一五七三年為張居正提攜,出任吏部尚書。四年后,因不贊成張氏“奪情”而致仕家居,時年六十七歲。
在明代,官員在任如遇父母去世,一般情況下皆應棄官,家居守制,稱為“丁憂”,待守喪期服滿再行補職。而所謂奪情,亦稱“奪情起復”,意指為國家而奪去孝親之情。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只是不參加吉禮而已。“奪情”是忠孝不能兩全的權宜之計,但后來也成了一些官員戀棧的借口。在明代政治史上,張居正之“奪情”極為著名,對此,《松窗夢語》卷一有所記載:
江陵聞喪之越日,傳諭令吏部往諭皇上眷留意。江陵亦自為牘咨部云:“某日聞訃,請查照行。”蓋諷使留己也。
這是說張居正本應丁憂,但他卻戀棧不去,想盡各種辦法,甚至讓吏部出面挽留他。對此,主政吏部的張瀚認為極不妥當,遂假裝不明白他的真實意愿,主張—應當讓禮部根據歷年閣臣丁憂的恩典,從重加以優恤。這當然得罪了張居正,不久,在后者的指使下,便有數人相繼對張瀚提出彈劾,讓他奉旨退休。得知這個結局,張瀚先是朝北叩頭,以示對皇恩浩蕩的感激,接著前往張居正那兒道別—
張瀚道:“頃某濫竽重任,幸佐下風,見公聞訃哽咽,涕泗交橫,謂公且不能旦夕留,區區之心,誠欲自效于公,以成公志,詎謂相矛盾哉!茲與公別,山林政府,不復通矣。”張瀚的微詞婉諷,在在點中張居正之要害。在他筆下,袖原善舞的張氏聽罷此言,似乎是愧悔交并,不勝凄惶。而隨后拂袖而去的張瀚,則深得時人的嘆賞,有人贈言道:“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十多年后,決絕的張瀚對于此番人事滄桑仍耿耿于懷,他顯然是以枯松自況,說楹外一松“有承露沐雨之姿,凌霜傲雪之節”,前句是比喻皇恩浩蕩,后者則形容自己的為官操守。
對于為官節操,張瀚一向頗為看重。早在他剛中進士不久,就曾前往王廷相的私第拜謁。王廷相是河南儀封人,為人素性端方,言動威儀,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給事中,后因得罪權閹劉瑾,被貶到地方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并巡撫四川,后又升為兵部左、右侍郎,最后升任南京兵部尚書。這位當世名臣曾對張瀚講過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雨后的大街上,有位轎夫穿著新鞋上路,從灰廠經長安街,走路都很小心,總是找一塊干的地方走,戰戰兢兢,怕弄臟了鞋子。后來轉入內城,地上漸多泥濘,一下子踩臟了,此后也就顧不上這雙鞋子了。他說,做人的道理也是如此,失足一次,就無所顧忌,恣意而為了……
此一故事,被張瀚鄭重其事地寫在《松窗夢語》卷一《宦游紀》的開頭,而他對于張居正“奪情”一事的抵制,則書于該卷的卷末。如此編排顯然煞費苦心,可見張瀚認為自己當年的做法是正確的,而這與王廷相的教誨則密切相關。
揆勢衡情,“奪情”事件對張瀚的影響一直是如影隨形。在晚年,他曾追憶某次自杭州北游的經歷:
渡揚子江,登金山寺,繞佛閣七層,高者臨絕頂。……四顧青山,峰巒峭拔,如萬笏朝拱。睹江上舟航,往來迅捷,其行如飛。旦暮視日月之出沒,大如車輪,光焰萬丈,目奪神竦。時江飆乍起,波濤洶涌,雪浪排空,已而風恬日朗,江波澄靜,渾如素練。人生顯晦升沉,亦猶是耳!安得砥柱中流,屹然如金、焦者?
涉歷幾多寒暑,文人的追憶間或亦雜夾著時空的錯位。不過,從字面上看,是時,張瀚站在金山寺前俯瞰長江,但見江面帆檣不斷,櫓槳如織,面對著洶涌而至的波浪觸緒縈懷,平生經歷中的點點滴滴,一一浮現于腦際……或許,數十年宦海沉浮中最令人感慨的,便是湍流馳激,砥柱為難。
因“奪情”事件,張瀚被迫致仕家居,但在此前,他少年得志,“泛覽群書,尤酷嗜左、國、莊、騷,至寢食俱廢,遂燁然成名當世”,二十五歲就中了進士,一生從政長達四十余年,“宦轍所至,幾遍海內”。在這部“隨筆述事”的著述里,張瀚用了八卷的篇幅分三十三“紀”,對一生的經歷見聞做了記述。其中的《宦游紀》、《南游紀》、《北游紀》、《東游紀》、《西游紀》和《商賈紀》等,多根據個人的親身經歷寫成,頗為翔實可靠。
《宦游紀》主要是講張瀚為官的經歷,不過,個中也涉及各地的民情風俗。例如,他提到:
江北地廣人稀,農業惰而收獲薄,一遇水旱,易于流徙。
廬陽地本膏腴,但農惰不盡力耳。年豐粒米狼戾,斗米不及三分,人多浪費,家無儲蓄。旱則擔負子女就食他方,為緩急無所資也。
“廬陽”亦即廬州府(今安徽合肥一帶),其北面就是鳳陽府,上述記載實際上與傳統時代的“鳳陽花鼓”、“鳳陽乞丐”密切相關。對此,張瀚在其后的《商賈紀》中也指出:“廬、鳳以北,接三楚之舊,苞舉淮陽,其民皆呰窳輕言少,多游手游食。”這段話其實源自《史記·貨殖列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在司馬遷的時代,戰國楚地被分作“三楚”,也就是西楚、東楚和南楚,“呰窳”亦即貪懶、不肯力作、委靡不振的意思。及至明代,廬州府、鳳陽府一帶是大批乞丐誕生的搖籃。據清人趙翼在《陔余叢考》中的記述,江蘇各地,每到冬天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乞食,至翌年春季方才離開。他們唱著“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歌”。本來以為這些人是因為災荒而外出乞討,但實際上即使是豐年,他們也照樣外出乞食,形成了一種頑固的風俗。
為了防止“鳳陽乞丐”的大批產生,張瀚在廬江當地開發水利,采取種種措施對逃荒者加以限制。據說,在他的努力下,廬江一帶的灌溉條件有所改善,拋荒現象逐漸減少。不過,倘若我們從晚明時代廬江、鳳陽一帶的實際情況來看,這如果不是張瀚的夸大其詞,那至少也說明此種狀況不會持續太久。廬州和鳳陽二府位于江淮之間,黃河全流奪淮入海以后,此處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因頻遭災荒,當地民眾遂養成一種不事產業、輕出其鄉的習氣,此種現象源遠流長,有其深刻的自然地理背景。
《松窗夢語》卷二的《南游紀》、《北游紀》、《東游紀》和《西游紀》四篇,皆是游記,記錄了他在全國各地的游歷。此外,還有《北虜紀》、《南夷紀》、《東倭紀》和《西番紀》,涉及北方游牧民族及中國周邊(琉球、日本)和西部(吐蕃、回回)等人群的生活習性及其風俗。以《西游紀》為例,篇中馳騖翰墨,遠引旁搜,有不少地理方面的描述。如:
歸州四里之城在高山之上,臨大江之涯,居民半居水涯,謂之下河,四月水長,徙居崖上。
歸州屬湖北荊州府,山水縈回,源流澄澈,此處瀕臨長江,屬三峽地區。上文描述了當地的聚落,人們隨著水位之高低而居住于不同的位置。接著,文中還描寫四川:
蜀城內外,平地僅四十里許,而四面皆高山,天色常陰翳,如晴明和煦、風朗氣清之日絕少。至若白日杲杲、明月輝輝歲不數日,而月尤罕見,故云“蜀犬吠月”。氣候較暖,初春梅花落、柳葉舒、杏花爛,暖如江南暮春時矣。地多二麥,春仲大麥黃,小麥穗,皆早于江南月余。民俗樸陋鄙俚,雖元旦、燈夕,寂然無鼓吹,燈火不異平時。惟婦女簪花滿頭,稍著鮮麗,丑嫫出汲,赤腳泥涂,而頭上花不減也。
此段文字筆觸細膩,饒有畫意。這是杭州人眼中的四川,文中說蜀地有霧的日子很多,節候也較江南要早,風俗比江南更為儉樸,朱門嬌媛,窮巷荊釵,其審美方式亦頗不相同。《西游紀》刻畫陜西為:
氣候寒于東南,惟西風而雨,獨長安為然。……地產多黍麥,有稻一種名“線米”,粒長而大,勝于江南諸稻,每歲入貢天儲。民俗質魯少文,而風氣剛勁,好斗輕生,自昔然已。
此處盡情摹寫,對東南與西北的氣候、物產、風俗皆加以比較。其中,還特別寫到陜西的三原:“三原二城,中間一水,水深土厚,民物豐盛,甲于一省。”在稍后的《商賈紀》中,張瀚還指出:“至今西北賈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可見,三原一帶為陜商重鎮,故而頗為富庶。張瀚又寫到山西蒲州的情況:
渡黃河,即為山西之蒲州,州城甚整,民居極稠,富庶有禮,西北所絕無僅有者。俗尚多靡,中有山陰、襄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門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競為奢華,士夫亦皆高大門廬,習為膏粱綺麗,漸染效法。
張瀚于山川佳處駐足流連,他描述了蒲州的富庶與奢靡,對當地明朝宗室(山陰、襄垣)之活動亦多所狀摹。關于蒲州,在隨后的《商賈紀》中,他還指出:山西“以太原為省會,而平陽為富饒。……獨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賈爭趨”。可見,蒲州一帶煙戶繁盛,市廛輻輳,也是晉商重要的桑梓故里。平陽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臨汾市一帶,靠近陜西,黃河從其西面和南面流過,“平陽富庶甲于秦、晉,以秦、晉財貨多出于途”,當地系山西、陜西最為富庶的地區,為秦晉商人商品流通的重要區域。
《松窗夢語》卷四的《百工紀》,談的是百工技藝以及與此相關的奢靡風氣,其中提到: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是個典型的消費性城市,全國各地大批的商品都匯聚于此。當時,商品主要的來源地是東南一帶,所以從事百工技藝的人群也大多出自東南,其中,以江西、浙江、南直隸、福建、廣東一帶居多。接著,他又指出北京的奢靡風尚對全國的影響:
自古帝王都會易于侈靡,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沿習既深,漸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嘗數游燕中,睹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宮室壯麗,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巨室所羅致而取盈。蓋四方之貨,不產于燕而畢聚于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于趨赴者,為重糈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今也散敦樸之風,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皆百工之為也。
這一段文字是說,北京對于全國的奢靡風習頗有推波助瀾之力,直接的后果便是人們紛紛棄本逐末,從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除北京之外,另一個對全國奢靡風習起引領作用的是蘇州:“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主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這是從地域觀照的角度,提到蘇州對于明代社會風俗的重要影響。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松窗夢語》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卷四《商賈紀》。該卷概括闡述了明代兩京十三布政司的經濟、文化及習俗,指出全國自然資源、經濟地理的布局特點:
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于羅、綺、絹、纻,而三吳為最。……西北之利,莫大于絨、褐、氈、裘,而關中為最。……夫賈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珠璣金碧材木之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然茶、鹽之利尤巨,非巨商賈不能任。……西北在茶,東南在鹽。
在這里,作者以“東南”、“西北”將全國一分為二,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地理布局,并舉例加以說明。他說自己的祖先就是以絲織業致富,而在浙江,不少人皆以販鹽、賣茶發家致富。而在西北,畜牧業則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還分省對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的風俗做了頗為細致的分析。譬如,關于南直隸:
沿大江而下為金陵,乃圣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爭趨效之。廬、鳳以北接三楚之舊,苞舉淮陽,其民皆呰窳輕言少,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賈操巨萬資以奔走其間,其利甚鉅。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
根據張瀚的描述,南直隸風俗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若以現代行政區劃來看,即今江蘇省的江南部分,安徽和江蘇二省的江北部分,以及安徽省的江南部分。這里也提到蘇州引領全國時尚,廬州、鳳陽二府多游手游食之人,這些情況已見前述。至于“煮海之賈”,指的則是鹽商。在明代,淮揚鹽商相當著名,獲利亦甚巨。根據差相同時的《廣志繹》之記載:“維揚中鹽商,其鹽廠所積有三代遺下者。”而在淮揚從事鹽業的,大多為徽州鹽商。在明代,徽州的風俗頗為獨特,“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日偷”。張瀚將以徽州為中心的皖南視作一個風俗區,有著相當的道理。特別是徽州的休寧和歙縣,在明代中葉更以商賈眾多聞名遐邇,以致官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注意到這種風俗。據明人吳子玉的《丁口略》一文指出:因休、歙之人多精于商賈榷算,故政府對當地的課稅要高于徽州府的其他四個縣。對此,雖然“休、歙二縣民甚苦之”,一些地方人士也疾聲力呼,要求取消此種不平等的重賦,但都沒有什么結果。在此背景下,這種政策導向,無疑更刺激了徽州人計覓錙銖,紛紛外出經商。從《太函集》、《復初集》和《大鄣山人集》等明人文集來看,南直隸安慶府、池州府、太平府、廣德州、寧國府等地,皆是徽商麇聚之區,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徽州風俗的影響。
除了南直隸外,張瀚對浙江風俗的描摹也相當精彩。他將浙江風俗分為三個部分,即杭嘉湖、寧紹溫臺和嚴衢金華。犀照之下,可謂無微不察。此種劃分,與同時代其他人文地理著作(如《廣志繹》)之描摹也大致吻合。
二十多年前,譚其驤先生曾撰文呼吁應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指出,中國人“對人文地理現象的記錄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書于二千多年前的《禹貢》,而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卷末所載的‘域分’、‘風俗’中,對戰國至西漢各地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農商工礦各業的盛衰和風尚習俗的差別,都有極其生動具體的敘述”。不過,漢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視了人文地理的記述,有關人文地理現象的文獻東鱗西爪,這種情況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觀。對此,譚先生特別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學衍義補》、章潢的《圖書編》、謝肇淛的《五雜組》以及王士性的《廣志繹》,都是這方面頗為出色的論著。在他的倡議下,上述諸書都受到歷史地理學界的重視,有的還出版了專門的研究論著。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松窗夢語》中最為系統、最有價值的是《商賈紀》。在我看來,《商賈紀》無論是謀篇布局還是行文措辭皆是在刻意模仿《史記·貨殖列傳》。事實上,在明代,《史記·貨殖列傳》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張瀚并非絕無僅有的一位。在徽商的桑梓故里,成書于十七世紀初的萬歷《歙志》,卷十就是《貨殖傳》,其卷首提及:
太史公傳《貨殖》,班氏非之,謂其失受命之旨,乃亮之者,則曰太史公得罪,而漢庭諸公卿無有能為端木、子皮其人者,故發憤而為此,以為若皆白圭、烏倮耳,豈可與圣門高弟、霸國英臣等埒哉?其然是或然矣,凡史與志不必有此,而邑中不可無此。因嘗反覆《貨殖傳》,而以當今之世,與邑中之人比之,蓋亦有同與不同焉。
在編纂者謝陛看來,為商賈之鄉歙縣修志,不能沒有“貨殖”各傳。為此,他仔細研讀了《貨殖列傳》,并將歙縣的現實與之相對照,從物產、城鎮、人地關系、商人構成、社會觀念和價值觀變化等諸多側面,詳細分析了兩者的不同。而在福建,何喬遠所著的《名山藏》中也有《貨殖記》,他指出:“余覽傳記,得富者數人,仿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從“貨殖”一詞的本義來看,此處的“貨殖記”與“商賈紀”同義。
除了篇目之外,在寫法上,《史記·貨殖列傳》較為系統地概述了“山西”、“山東”、“江南”和“龍門碣石以北”各區域的經濟特點及其相互聯系,深刻地指出了形成區域間差異的歷史淵源和環境因素。而《商賈紀》也注重區域的劃分、區域特征和人地關系等方面的觀察與研究,將經濟與文化、風俗諸因素綜合起來加以考察。另外,從作者的生活年代以及作品的成書年代來看,張瀚的《松窗夢語》作于一五九三年(明萬歷二十一年),王士性的《廣志繹》自序于萬歷丁酉,即一五九七年(萬歷二十五年),而謝肇淛的《五雜組》則出版于一六一六年(萬歷四十四年)。個中,無論是作者的生活時代還是著作的成書年代,皆以張瀚的《松窗夢語》為時最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賈紀》對人文地理現象的系統描述,標志著《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相關傳統在明代的全面復興。
張瀚出生于工商業者之家,雖然他在《商賈紀》中也引用《周書》的說法:“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用,商不出則三寶絕。”不過,他的總體思想落后于時代。在張瀚之前,江南一帶早已出現“崇奢黜儉”的主張。此類主張認為,“俗奢而逐末者眾”,奢侈可以提供諸多就業機會,令販夫走卒易于為生,因此,當政者應“因俗以為治”,毋須強力禁奢。在這方面,張瀚的立場頗為保守。在《百工紀》中,他說自己在廣東蒼梧,某年燈夕,屬下的封川縣送來一盞紙燈,以竹篾為燈骨,又以花紙作為裝飾,看上去似乎并不太值錢,但此類奇技淫巧,“束縛方圓,鏤刻文理”,需要專精此業的工匠花費數十天的功夫方能制成。燈夕剛過,門隸就想將之毀掉,張瀚痛惜“積月之勞毀于一旦”,急忙制止。這讓他想起自己家鄉的風俗,浙江“燈市綺靡,甲于天下,人情習為固然。當官者不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游之樂者”。接著,他又發了一通感慨,說倘若賈誼再世,看到這種現象,不知要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
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樸茂之風。以撫循振肅于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
《松窗夢語》卷七有《時序紀》和《風俗紀》,其中有不少都與張瀚的故鄉杭州之風俗相關。在這一卷中,張瀚時常強調,“余遵祖訓不敢違”、自己“世能守之”云云,以此凸顯作為文人士大夫的守禮循規。在張氏生活的時代,世當承平,俗隨世變,“金令司天,錢神卓地”,社會風尚極其奢華。殘軀老邁的張瀚,疾聲力呼反對其時的奢靡之風,但他生活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十六世紀末期,安享著錦攢花簇輕裘肥馬,卻窮思極想,希望整個社會重返太祖高皇帝的時代,這豈非荒唐可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