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鐵轉軌的人生
韋星
“如果我主動賣給你的,折舊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給一個很低的價格不說,最后還給我打個八折、九折,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呀?”岑慧嬌的老公楊秀統說,他至今想不通。
“我把她們身上的各個旮旯,全罵了一遍”,陸樹洲說,“沒錯,每個旮旯,都罵遍了!”
陸樹洲罵的是平果縣國土局的幾個公職人員。這天是7月30日下午,他罵完后,從國土局611辦公室直接下樓—不坐電梯。陸樹洲認為有官員欺騙他。
和陸樹洲想法差不多的不只他一戶。全長710公里的云桂高鐵,盡管途經平果縣只有二十幾公里,但改變的卻是600多戶家庭的命運—平靜的生活,一下子被改變了。因為八成以上的拆遷戶,他們所能拿到的補償總額,都不足以在安置地購買新的宅基地來建房。
這一切,皆始于那條高鐵干線。
從迅速崛起到很快消失,馱層屯是其中的代表。
25年前,廣西平果縣馬頭鎮雷感村馱層屯村民的居住地還是一片荒坡荒地。當時,最早到這里居住的,是一個叫張顯明的老師。張是鄉下的一名教師,退休時,他希望到縣城居住。可1990年,平果縣還沒有房地產,購地自建,成了唯一的渠道。
張顯明托人在馱層屯找到了一塊地,買下后建房居住。這里距離縣城大約有7公里。“當時,不通水、電,建房需要攪拌水泥的水,都是到比較遠的地方,一擔擔去挑的。”潘愛菊說。
潘是張顯明的兒媳婦。她記得,直到1995年,這一帶才有3戶人來建房居住:一戶是一個姓潘的老師,另一戶是個叫黃彩珠的人。黃彩珠1995年來這里建房居住,他此前在果化鎮糧所上班。
這個村莊可以追溯的歷史,不過20來年光景。首批進駐的村民,是當時在社會上,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教師、糧所干部。1995年,黃彩珠一個月的工資才500塊錢。建房的地皮,加上給中間人的介紹費,總共花掉他10400元。
進入2000年以后,來這里買地建房的人,逐漸增多。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有打石頭的、發豆芽的、賣菜的、踩三輪的,也有專門來養豬的。他們身上的共同標簽是:進城務工人員。
早前,潘愛菊去廣東打工4年未歸。有次回來,發現連路都找不到了,村子完全變了模樣。
這期間,伴隨中國鋁業廣西分公司在平果縣發展,馱層屯也有了一個“城市化”的村名—鋁城大道左一巷。
2003年4月,平果縣所屬的百色市,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下山、進城、入谷”運動,主要是運用勞務輸出和異地安置的辦法,引導山民到城鎮(城市)、右江河谷一帶落戶就業。
當時的力度很大。按計劃,百色市打算用5~10年的時間,把全市農村50萬富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出去。為此,官方通過培訓農民工,讓他們掌握謀生技能,以更好在城鎮就業、創業、落戶。
這樣背景下,地方政府給了進城人員足夠的包容,鼓勵他們進城落戶。這時,鋁城大道左一巷迎來了最為快速發展的時期。截至高鐵拆遷前,這一帶已有200多戶村民。
但進入2011年,村民陸續收到風聲:高鐵要經過鋁城大道左一巷。2013年,風聲變成了現實,大批的工作組輪番進村做工作。
云桂鐵路建設,平果縣路段涉及的拆遷戶有600多戶,占到云桂鐵路拆遷量的52%。重壓之下,平果縣將拆遷任務,逐一分解到教育局、民政局、商務局等30個單位。
“包片、包段,每個單位包10~20戶。”云桂鐵路平果縣征地拆遷協調辦公室(以下簡稱高鐵辦)副主任阮家杰告訴《南風窗》記者。
一開始,工作組進村宣傳的車輛,每天喇叭里都傳出“先安置,后拆遷”的聲音。廣播后,是實地走訪。
平果縣拆遷辦副主任凌維康來到陳美玲家里,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阿姐啊,你好嘞,我要是有一套像你這樣的房子,我天天殺雞吃。”陳美玲當時也琢磨著,如果按市場價,她的房子至少應該可以拿到30萬元的補償。
工作人員進村宣傳時,說的也都是:以地換地,非法變合法。
因為不管是在城郊,還是在平果縣偏遠的鄉村,村民建房一般都不辦證。即便這次拆遷涉及的600多戶村民中,有證的,也不過100多戶,剩下的都是沒證的。
這樣,工作組的人就特別強調:“沒證,就是非法的,你們的宅基地需要去繳納每平方米30元的罰款。這樣,原有宅基地合法了。屆時,到了新安置地,才可以以合法對應合法,成功置換。這是以地換地的前提。”
這樣,村民心里估摸著:拿著房屋建筑的補償款,到位于龍居社區的安置地就可以直接建房了。
不過,補償標準很低。比如岑慧嬌的房子,混合結構,每平方米只補償690元,而她附房屬于磚木結構,每平方米補償只有300元。
當下,平果縣的房價已是每平方米近3000元。300元一平方米的補償標準,確實讓很多村民難以接受。
這還不夠,村民的房子還要被折舊。如岑慧嬌的房子,綜合成新率是92%,這意味著她磚木結構的房屋,折舊之后,每平方米實際拿到的價格是276元。
“如果我主動賣給你的,折舊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給一個很低的價格不說,最后還給我打個八折、九折,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呀?”岑慧嬌的老公楊秀統說,他至今想不通。
阮家杰說,平果縣對房屋建筑面積的補償標準,和是否合法沒有關系。即便證件齊全,也是按標準進行。
問題還在于,評估公司派來評估的人,故意將拆遷戶的面積縮水。而房屋的水電、水管,甚至是地基,都不列入可補償的范疇。
在黃彩珠的家里,記者看到,1995年,當時的平果縣土地管理局確認他家建房的占地面積是88平方米。但20年后的今天,這一房屋的占地面積卻“縮水”為80平方米。
20年前罰款時,按88平方米來處罰。20年后補償時,卻按80平方米來補償。此外,房屋的補償款,算賬也能“算錯了”,補償金額比實際應付的,少了100多塊錢。
超低補償款,加上被動折舊,村民之所以還是接受了,因為“沒有辦法”。
但這些都不是核心問題。核心問題是,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地價補償過低,一平方米只有100.47元。而政府安置給村民的宅基地地價,又是太高—最高的,每平方米達1305元。
扣除繳納每平方米地基30元的罰款后,村民實際拿到的地基補償款是一平方米70.47元。即便在20年前,這點補償,也連當初買地的成本價都不夠。阮家杰說,“這是因為他們是違法的”。但即便證件齊全,原有地基的補償價,也遠低于新安置地的購買價。
張榮蘭的房屋,屬國有劃撥用地,證件齊全。政府給他的地價補償是580多元一平方米,但他到新安置地向政府購買的地價是700多塊錢(劃撥用地)。劃撥對應劃撥,但張榮蘭卻為此多掏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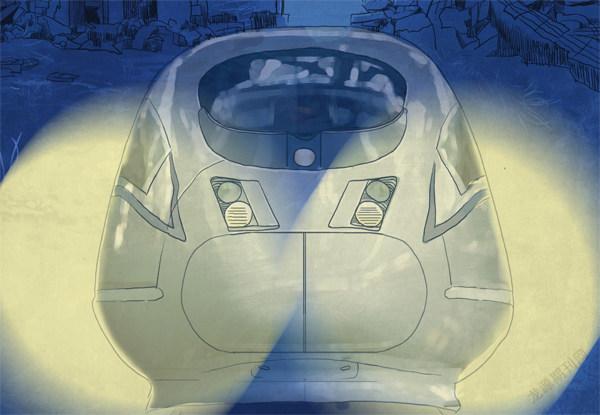
張榮蘭說,他不愿意拆遷,因為他之前的房屋位于一家工廠附近,做早餐、小賣部等生意,異常火爆。可拆遷后,他還需要出高價買一個和以前相比,并不太好的位置。曾經以地換地的承諾,變成了低價征收村民的宅基地,高價賣給村民安置地。
7月29日下午,阮家杰也向《南風窗》記者承認,“當初,工作組為了做工作,肯定會說一些讓他們(老百姓)心動的話”。
對此,平果縣國土局監察股股長易俊也有耳聞。但他說他沒有全程參與,所以也不清楚是哪個說的。
對村民反映:房屋已推倒,土地也已供給高鐵建設使用,為何還要繳納每平方米30元的違法用地罰款?
易俊承認:原本,這筆費用應該在建設時就開罰了,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推遲了。如今,工作的推進幾乎是同時進行,所以出現一些房子即便已經拆了、地也已交了,但還要去繳納違法用地罰款的情況。
類似的罰款是,房屋在去年甚至前年已拆,而今村民要在新的安置地購買宅基地時,也要先繳納過去因沒有辦證而違法的建筑罰款,每平方米建筑面積按57元收取。“這是為了創收而罰款”,黃牡丹說。
村民和平果縣某些政府工作人員并不是身處一個平臺。
一份在2013年年底簽訂的《云桂鐵路平果段征收房屋建(構筑物)設施拆遷安置補償協議書(自建)》上,記者注意到,里面的表述有“按照一戶一宅的原則,高鐵辦在統一規劃安置回建的宅基地上,安排一塊宅基地給村民,回建后按有關規定給予辦理相關手續”、“原主房(宅基地)占地地價和安置地地價待定,安置地號待定(確定后另立補充協議)”。
高鐵辦是平果縣政府下設的一個臨時機構,工作人員從各單位和部門抽調過來。他們在和村民簽訂協議時,涉及核心利益的問題,沒有盡量明晰。等村民簽訂協議、政府拆了房后,他們才告訴村民:你們老的宅基地地價是一平方米100元左右,而政府安置地地價是1300元左右。
“補償款到手還沒暖,又全部轉給他們了”黃彩珠說,他今年80歲了,沒見過這么干的。
“如果當初工作組把話說清楚了,村民肯定就不肯拆房子了”,阮家杰說,“但高鐵是重點工程,不管怎樣,都要全部拿下”。
但問題是:“拿下”之后,如何善后?
對此,平果縣國土局辦公室主任韓惺告訴《南風窗》記者,所有關于安置以及繳納相關費用等,都是依法依規進行的。
7月29日上午,在高鐵辦,很多前來討要過渡費的村民遭到了阮家杰的拒絕。
過渡費,本是高鐵方對支持高鐵建設的村民,在還沒來得及獲得安置的情況下,讓村民出去找房子租住,高鐵方給村民支付租金。2014年的過渡費,當時因拆房需要,已支付了—每平方米4元。
房子拆了以后,自2015年起至7月底,村民就沒能領到過渡費。因為高鐵辦要求他們:要領過渡費,必須接受政府給他們每平方米100.47元的老宅基地補償款,并把錢領走。這種捆綁的模式,遭到村民拒絕。“扣除每平方米罰款30元后,一個平方米實際補償70元,而他們賣給我們的是一平方1300多元”黃牡丹說,地價相差18.5倍。
7月30日,阮家杰答應將過渡費支付給村民,不再捆綁。
陸樹洲花了10多萬元,交了新宅基地的地價后,平果縣國土局給他出具了一張“僅供內部使用”的收據,收費名稱是“建設用地費用”,收據上的會計、出納、經手人,均沒有工作人員的簽名,只有縣國土局的公章。
交完這筆費用后,工作人員讓陸樹洲填寫一張《自愿交款書》。陸樹洲對這很不滿,“協議說好先建房,再完善手續,現在不交錢就不給建房,我這哪里是自愿交款的?”
交款后,有朋友提醒陸樹洲索要發票時,他手里揚著一張粉紅色的收據,瞪大眼睛說:“這不是發票嗎?!我去找她們!”冒著大雨,陸樹洲慌慌張張騎上摩托車,趕到了縣國土局,將負責辦理的女工作人員,罵了一頓。在其他村民面前,此刻的他,就像剛打了勝仗歸來的小孩,臉上洋溢著“終于雄起一回”的快感。
聽罷,村民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