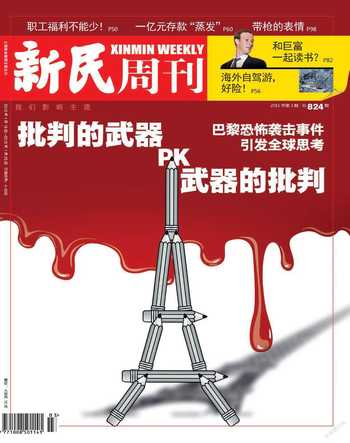歷史學家的可信度
劉洪波
寫歷史與講故事是不同的兩個行當。講故事的是說書藝人,寫歷史的是歷史學家。兩者間有粗疏與精致之別,更有史觀、史識的差異。
即使說書,也是不無史觀和史識的,忠孝節義、君臣綱常,便是史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史識。這是很堅強的東西,關公的紅臉和曹操的白鼻子,如影隨形。
歷史學家不同,史料要多,史實要準,史識要獨立,史觀有自覺,史思要深邃,還有所謂史膽、史感,如此等等。歷史學是知識生產的一個門類,這樣一講,門檻就立起來了,譜也擺起來了,可信、嚴肅、高貴等屬性也站起來了。歷史既然是一門學問,也就有其邏輯結構,歷史關節的敘述建立在諸多史實的相互參證之中。歷史重視但討厭孤證。孤證首先就要面臨是否可靠的質疑,質疑通過,才考慮能否足以修正某個結論。
近年來,《蔣介石日記》得以公開。很正常地,它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雖然直接讀到日記的人還很少,但談論民國歷史、國共關系時,引證它的人很多。這當然是歷史學家的功勞,歷史學家去檔案館里抄錄日記,見到來自當事人的先前未曾見到的記載,不免興奮,希望憑日記去“尋找真實的蔣介石”,從一般情理而非從歷史學家來要求,也不算過分;若以為一套日記就可以真實復原某個人,那就情同兒戲了。
《蔣介石日記》是真實的,這個判斷有多重含義,一是日記真為蔣介石所寫而非他人偽托,二是日記中的行止或心跡流露真切而非虛飾。前一點,現己確證;后一點,歷史學家試圖確證,但不無疑問。日記里記了每天做什么事、在里面罵人,這可以說真實;但某事是怎樣做的,為什么這樣做,為什么罵人,就是個人角度。個人角度,即使代表真實的認識和意圖,也未必符合客觀事實。個人角度還有可能是自證合理。
日記為誰而寫,也是一個問題。日記可能僅僅是面向自我的內心,永不公開;日記也可能是“暫不公開”但終將公開的“起居注”。即使永不公開的日記,當其不是“記過即焚”而是日積月累,也可能形成一種萬一面對某位讀者的“寫作自覺”。如果日記記錄時已有“終將公開”的預感或準備,那就更有可能埋伏解釋或交代自身的“導向”。
如果更加徹底地看,文字記錄心跡和行為,但從心跡、行為到文字,未必是如實的,未必是不經修飾的。任何記錄,不僅無法完全還原實際行為和心理過程,而且很容易在“文字轉換”中進行事實和心情的剪裁、取舍和修飾。一本日記是否真實,與它是不是真實的歷史,并不相同。
對于一個時代來說,歷史固然與大人物的細行小故、臨事決斷、心跡意愿分不開,但歷史終究不在宮幃或總統府里,而在天下蒼生和時代走向之中。《蔣介石日記》中是否看得到那一時期人民的生活狀況,從介紹和引用來看,沒有見到。當然,這原本也不是日記必須承載的內容,甚至怎樣看待外交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長都“內舉不避親”也不必有,怎樣用嫡系、門生和旁枝來區別治理也不必有,四一二、皖南事變等也可以基本不記。但如果這些都沒有,日記還能還原真實的蔣介石嗎?更重要的是,既然記錄是選擇性的,誰能保證這只體現于選擇記哪些事之中,而沒有體現在被記的事情記哪些、怎么記、從什么角度記、用什么方法記呢,《蔣介石日記》可以作為直接取信的史實嗎?
《蔣介石日記》從日記被確認為史實,這有一段距離;從確認史實到采納寫史,這又有一段距離;從采納寫史到據此斷史,這更有一段距離。《蔣介石日記》一出,歷史據此重斷,這需要在史實準確、史識獨立、史觀自覺上產生多大的跨越才能做到?
不只《蔣介石日記》,其實任何人的任何個人記錄,當其進入歷史學的視野時,都同樣要成為史實、史識和史觀的審驗對象,而不是直接信錄,否則歷史學家的可信度就跟說書藝人相當,但演義是說書藝人本行,歷史學家又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