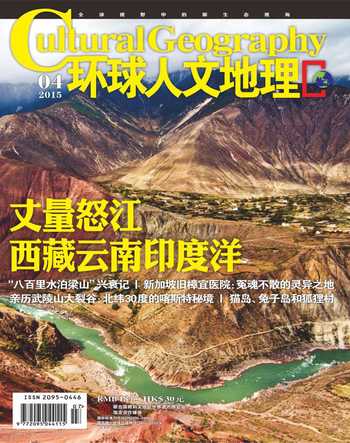氣候變化導致心理抑郁
麥克?華萊士
幾年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卡米拉·帕梅森因為嚴重的“職業抑郁”,想完全放棄自己對氣候變化的研究。這則消息出來后令人震驚,因為帕梅森在他的領域頗有建樹:在2007年,她作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CPC)第三工作組的研究者,與阿爾·戈爾共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2009年,她又因為對于氣候變化對全球物種的研究與影響,成為《大西洋報》提名的27名“勇敢的思想者”之一,同樣獲得這個提名的還有美國總統奧巴馬和Facebook的創始人扎克伯格。
可是即便獲得了這么多提名,她還是因為受夠了自己的工作帶來的情緒而倍感抑郁,她說:“我感覺根本沒有人在乎我在氣候上的重大發現,我做這么多有什么意思?”最終,她因為這種情緒而結束了自己在美國的生活,舉家搬回了丈夫的老家英國生活,成為普利茅斯大學的教授。
帕梅森絕不是第一個因為氣候變化而抑郁的人,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全球變暖心理學認為,隨著風暴越來越強烈和干旱持續時間越來越長,氣候變化最終將對人類的心理產生嚴重的影響,而對于一般的環保主義者,尤其是對于環保領域的科學家,氣候變化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焦慮情緒,并導致抑郁。
氣候學家在日復一日“末日景象”的研究中,會發現自己被卷入了一個更為龐大、包含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討論的旋渦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且對于像帕梅森這樣的一線科學家,這個問題可能更嚴重,因為能夠理解和處理大量氣候數據的能力,不代表一定能接受這些結果所衍生的情緒,當他們的研究成果遭遇現實世界在氣候問題上的集體失靈,以及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壓力,你就可以想象他們的心情。
國家野生動物盟的心理學家里瑟·范·蘇斯特蘭,發明了一個叫做“創傷前應激障礙”的術語來描述這種情緒:在最壞的結果發生之前做準備,并因此而導致精神上的極度痛苦。蘇斯特蘭說: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高度專注,而且這種專注遠遠超越了工作范圍,它不同于家長里短的煩惱,當你專注于此,你就很難再關心家里的各種費用是否都繳納了,棒球裝備是否合適,孩子在學校是否成績好等小問題。尤其讓人沮喪的是,當你因為即將到來的氣候災難而努力奮斗時,卻發現周圍的人都在裝聾作啞,當你把信息傳遞給某些人,他們卻不相信你。這就像醫生對病人做了全身檢查后,確定這個病人需要手術,而病人卻看著醫生說“我不相信你”,這種感覺足以讓人發瘋。
因為焦慮,很多氣候學家和活動家都會把自己的情緒帶入他們的發現,這成為氣候變化否認者所批評的重點,他們會抓住這一點,極盡所能地告訴人們應該拒絕這種不理智的科學。這就使得很多氣候學家即使不面對聚光燈,也要經常克制自己的情緒,并因此而感到壓力巨大。著名氣候活動家麥克·提德維爾說:“你不可能在朋友家的雞尾酒會上直接大談海平面上升的惡果,這種既想表達實際想法,又要壓制表達沖動的情緒,是所有氣候學家和活動家們都需要承受的重負。”
那么,氣候學家們該如何應對這種壓力呢?蘇斯特蘭提供了幾種“氣候創傷生存貼士”——冥想和治療,以及特別強化工作和生活的邊界。不過,蘇斯特蘭也強調,保持誠實也是一樣重要的,不要以為自己堅不可摧,大方地接受自己的處境會讓自己更加堅強。
2014年3月,《本報》的布蘭亭·默克發表文章認為,也許現在可以切實討論全球變暖的緊迫性,而不再是采用“僅僅是事實”這樣的詞匯,他認為,在合適的時候,科學家應該可以用一些情緒化的語言,譬如爆粗口來表達意見,因為世界上沒有什么比粗口更能表達焦急和緊迫性,默克這樣形容:“我們需要他們不斷地提醒這些并不深奧的道理,不管聽上去有多么粗魯或者不適。”
雖然氣候變化心理學還是個非常年輕的領域,但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也許,現在應該讓這些氣候學家來講述他們的內心情感,或者至少讓那些精神健康研究機構更加積極地探索氣候變化心理學,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需要人們更多的支持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