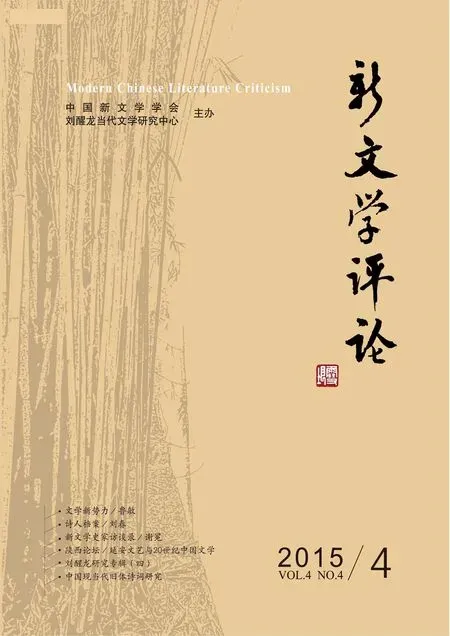浪漫是希望的一種
———論劉醒龍的中短篇小說創作
◆ 陸 琰
浪漫是希望的一種———論劉醒龍的中短篇小說創作
◆ 陸琰
從1984年在《安徽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黑蝴蝶,黑蝴蝶……》以來,劉醒龍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被他自己劃分為三個階段,“《黑蝴蝶,黑蝴蝶……》、‘大別山之謎’,是盡情揮灑想象力的時期。以《威風凜凜》為代表,直到后來的《大樹還小》是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現實的魅力吸引了我。第三個階段是從《致雪弗萊》到《圣天門口》”。
自1992年開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全面展開,經濟體制的變化直接影響了社會交際,文壇充斥各類描述市場經濟及社會生活改變的小說,與80年代類型化的改革小說不同,90年代的現實主義小說的敘述視角重新回歸社會底層,尤為關注農村社會的矛盾沖突和發展方向。90年代是劉醒龍創作的第二階段,他以“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中鼎力量受到廣泛贊譽。“現實主義沖擊波”宣稱“要把小說定位在普通讀者的層面上”,“要站在大眾的角度上,弘揚一種‘平民意識’”。而出生于農場干部家庭的劉醒龍,對平民生活的描寫貫穿他的創作,被稱為優秀的平民代言人,“他基本上承擔著為中國現代社會平民們代言的角色和任務”。
而在劉醒龍的小說觀中,他認為中短篇小說依附于時代,如果它不和時代的某種東西引起一種共鳴,它很難興旺下去。《白菜蘿卜》(《江南》1994年第3期)、《分享艱難》(《上海文學》1996年第1期)、《挑擔茶葉上北京》(《青年文學》1996年第3期)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的發表讓劉醒龍登上創作新高度的同時,很好地描摹了那個時代百姓的生存狀態。
一、平民化視角下艱難生活的反映
90年代現實主義小說表現出一種平民化傾向,它像一面鏡子,直接反映凡間俗事,瑣碎生活逼迫人們拋卻虛無縹緲的理想,扎根現實,不管你是農民還是市民,無論你是工薪階層還是機關要員,你都必須耐下性子應付艱難世事。而伴隨洶涌的市場經濟大潮一并席卷社會的還有貧富差距加大、社會道德日益淪喪等問題,在對物質生活的追逐中傳統價值觀被重新建構。同時,窮困加深了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無力感。“劉醒龍無疑是表現這一歷史時期矛盾沖突的出色作家”。劉醒龍創作于90年代的中短篇小說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從農民、工人到基層鄉村干部,然而這些人物的生活基調有一個相同點:艱難。
《黃昏放牛》里曾經的“鐵姑娘”秀梅如今只能落得一個女兒出嫁無法準備豐厚嫁妝、有病沒錢醫治的窘迫結局,她直言就算改革,發財的也不是全天撲在田里的種田人。瘦干干的小腳沒有鞋穿、風大且涼的日子里卻只能穿著背心短褲……幾個細節就逼真地勾勒出《鳳凰琴》中大山深處界嶺小學的艱難處境。《火糞飄香》中吳四歌一出場就嚷嚷自己已經兩天沒吃上飯了,其生存狀態之窘迫可以想見。
除了再現改革時期貧困農民的生存狀態,劉醒龍的作品中也記錄了容易被人忽視的“城里人”的艱難生活。《白菜蘿卜》里,“城里人”也會在沒錢買菜的情況下去撿廢棄的白菜幫和爛了半截的蘿卜,而曾經那么美好的周玲在生活的重壓下更是走上“歧途”:“女兒戶口在城里,我必須讓她待在城里。為了女兒,我一切都可以忍受!”《音樂小屋》中的環衛工人萬方因卓越的口琴演奏技巧而被小男孩邀請到家里授課,女主人回來,因為他那“不體面的職業”對他百般辱罵,萬方居住的隔間和二樓僅有幾步臺階的距離,卻像是永無交集的兩個階級。而萬方的舍友陳凱為了獲得這個城市的尊重更是不得不使出苦肉計,自編自導一出平民英雄救人的戲碼,其生活之艱辛不言而喻。
除了簡單描繪平民生活外,劉醒龍在其作品中也對平民生活如此艱難的現狀進行了自己的思考,撰文諷刺了改革并未切實關注民生,僅僅流于注重改路名等表面工作,抨擊了精神生活建設未與物質生活改善同步等問題。
舊體制的變化,不良風氣泛濫,讓被傳統文化道德理念浸潤的人們精神受到腐蝕,在現世物欲橫流的社會面前愈加手足無措。《黃昏放牛》中胡長升就直言,改革讓麻將和婊子出來腐蝕社會主義,而德權的一席話更是點破了世道的變更:“往日那一套全作廢了。如今誰的錢多誰就當勞模;誰會搞歪門邪道賺錢,就讓誰當干部。”《民歌》中小園為了在比賽中勝過柳柳,先假意與其交好,然后再設計讓袁副書記糟蹋柳柳,并利用此事件逼迫柳柳退賽。年輕女性往往是“溫柔”、“善良”等優秀品質的代言人,而小園卻為了一己私利,工于心計、步步為營;《農民作家》中華文賢與楊主任合謀,偷盜孫仲望家的牛,排擠他,侮辱孫仲望的妻子,只為將孫仲望創作的劇本《偷兒記》據為己有;《火糞飄香》中吳支書賣酒摻水,邱丙生賣茯苓片子摻紅芋干,兩人還堂而皇之地聲稱“現在什么都是假的,我這酒也不能太真了”。善良、信義、仁慈、勤勞等傳統道德在利益面前逐步被人們忘卻。
而社會生活艱難的根本性癥結之一——腐敗問題也在劉醒龍的作品中得以體現。《路上有雪》苛捐雜費是鄉民背井離鄉的直接原因;《挑擔茶葉上北京》中的“冬茶”事件更令人發指,“放開了采幾畝地才能得一斤活芽葉,茶樹被凍死凍傷,來年必定減產減利”。如此違背采摘茶葉的規律只為巴結上司,以謀私利,文中最后,石得寶只能滿腹心酸看著被欺騙的父親走向自家的茶園;《秋風醉了》里的王副館長兢兢業業完成本職工作,只求升為正館長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不料因為自己不懂察言觀色遲遲不得如愿,幾經波折后無奈萌生退意,回家守著老婆孩子,反而獲得了“各方面都成熟了,適合擔任館長一職”的評價,如此諷刺的結局深刻地批判了社會的腐敗現象。
艱難時世,人心不正,眾人舉步維艱。劉醒龍,這位“社會的書記員”將自己的責任心,對于普通百姓乃至整個民族命運的關心、思考灌注在筆尖。
二、寄寓希望的浪漫化表達

詩意的情節呼喚人性向善,批判世間丑陋。《分享艱難》中,嫖娼被抓的嫖客主動為因洪澇災害而流離失所的百姓送來善款,在強奸田毛毛被寬恕后,洪塔山賣掉了自己的桑塔納轎車為鄉村教師發工資,并積極談成生意改善鎮里的經濟狀況,一派祥和中,鎮里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壞人都受到了洗禮,走上光明的道路。《民歌》里,“民歌”、“藝術”被富于了精神支柱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古九思的靈魂家園,還撫慰了所有經受苦難的心靈,而文末柳柳擺脫畏懼心理,重新歌唱,這樣的設計直接消解了文章的悲劇色彩,卻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了讀者的心靈。


三、充滿具象的風俗畫描寫
劉醒龍生于黃州,在英山縣度過自己青少年時代,自幼便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劉醒龍早期作品“大別山之謎”系列小說全面展現了楚地風情,可以說大別山是劉醒龍的精神家園,鄉土文化是劉醒龍小說的靈魂,而這一顯著的特點在其90年代的中短篇小說中并沒有消失,反而通過劉醒龍愈加成熟的創作技巧呈現,作品中隨處可見鄉土風情,卻不單單局限于鄉村之間。




爺爺說:“伢,你不懂。威風會長的,長出來就不得了了。”

——《威風凜凜》

——《黃昏放牛》

——《秋風醉了》
方言的使用不僅彰顯了地域特色,也更加堅定地表達了劉醒龍從平民視角描繪百姓生活的決心,用鄉親們的語言寫鄉親們的事。
劉醒龍發表于90年代的現實主義中短篇小說使其攀登創作高峰,以平民的視角關注社會改革時期發生的各種尖銳矛盾體現了一個作家的人道主義情懷,凸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責任感,他以深情的筆觸敘寫“小人物”的生死歌哭。主觀浪漫主義的介入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性批判力度,但為劉醒龍的小說注入了脈脈溫情,給讀者希望與慰藉。同時,劉醒龍的作品搖曳楚風,展現了湖北的地方文化特色。“自古楚地出人才”,劉醒龍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為當代文學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①周新民、劉醒龍:《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劉醒龍訪談錄》,《小說家評論》2007年第1期。
②談歌:《作文與做人》,《北京文學》1997年第9期。
③談歌:《小說與什么接軌》,《城市熱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
④賀仲明:《平民立場的現實審察——論劉醒龍近期小說創作》,《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5期。
⑤周新民、劉醒龍:《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劉醒龍訪談錄》,《小說家評論》2007年第1期。
⑥段崇軒:《90年代鄉村小說綜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
⑦劉醒龍:《劉醒龍文集》,第3卷“疼痛溫柔”,群眾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頁。
⑧劉醒龍:《劉醒龍文集》,第4卷“鄉村彈唱”,群眾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頁。
⑨劉醒龍:《劉醒龍文集》,第4卷“鄉村彈唱”,群眾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頁。
⑩王澗:《另一種聲音:90年代的鄉村小說》,《當代文壇》1999年第6期。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