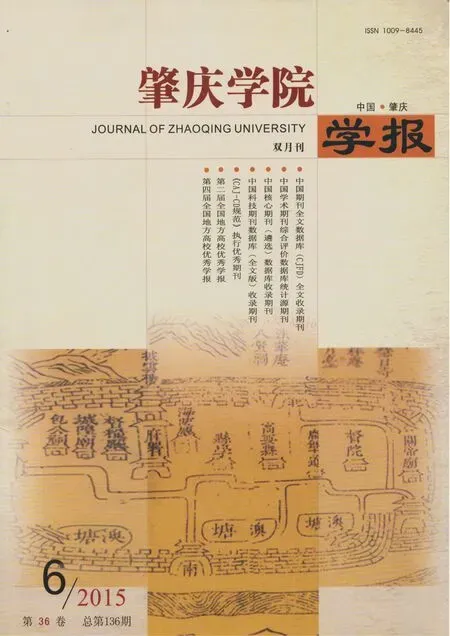漢英詞語理據對比
趙曉華(肇慶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漢英詞語理據對比
趙曉華
(肇慶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詞語理據指事物或現象獲得名稱的依據,是人對事物或現象的某些特征的概括。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但同時又兼具理據性。任意性和理據性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兩個概念,不可將任何一方絕對化。語言理據具有民族性,各民族語言發生、變化、發展的動因各不相同,理據的隱顯、強弱程度有別,因此,有了對比的理由和可能。探究語言理據,揭示創造和發展語言符號的動因,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對于語言學習、語言教學和翻譯也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任意性;理據性;英語;漢語
“詞的理據(motivation)指的是事物和現象獲得名稱的依據,說明詞義與事物或現象的命名之間的關系”[1]62。語言符號既具有任意性,又兼具理據性。語言理據具有民族性,各民族語言發生、變化、發展的動因各不相同,理據的類型,隱顯、強弱程度有別,因此也就有了對比的可能與理由。探究語言理據,揭示創造和發展語言符號的動因,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它可以使我們對語言的研究由表及里,知其然并能知其“所以然”,從而使人類對語言現象的理解提高到一個更高的高度。本文僅以英語和漢語為例談談詞語的理據,希望能夠對英語學習、英語教學及英漢互譯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一、任意性vs理據性
關于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理據性之爭,已進行了兩千多年,至今仍無定論。從古中國、古希臘哲學家關于唯名論和唯實論的辯論,到后來的自然派和習慣派的互不相讓,其間雖然不斷演繹引申,但是語言符號與其所指的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爭論的核心。概括地說,古今中外學術界的意見基本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任意論,認為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不可論證;另一派是理據論,認為其間有必然的聯系,可以論證。以下兩節詩很好地反映出兩派的不同意見:
1.What’s in a name?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
Act II,Scene 2
2.’Tis not enough no harshness gives offence,
The sound must be an echo to the sense.
Pope:Essay on Criticism
在Shakespeare看來,人們叫做rose的花朵,如改用其它名稱,其芬芳依舊。而Pope則認為只是不作刺耳之聲是不夠的,音必須是義的一種回聲。
在現代語言學界,普通語言學的奠基人洪堡特(Humbolt)是理據說的大力倡導者。他強調語言與思維——認知能力的關系,認為人類對事物的感知,都必然會轉移到語言的構造和使用上來。“詞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Abdruck),而是事物在心靈中造成的圖像的反映”;“語言結構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相似,語言通過其結構激發人的最高級、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動,從而幫助了人深入認識自然界的形式特征”[2]。而結構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則極力主張任意說,認為這才是語言符號頭等重要的原則。由于這位語言學家的巨大的影響力,在隨后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任意論在論爭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在20世紀后半葉,隨著功能主義和認知科學的興起和發展,不少語言學家對語言符號的音、義關系有了新的認識,理據說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烏爾曼(StephenUllmann)、海曼(JohnHaiman)、斯洛賓(Slobin)等一批語言學家認為,自然語言象似性具有遍布性,在語言中占有支配地位,布達哥夫甚至進而提出任意論是“虛構的原則”。從此,將任意性視為語言符號的頭等重要的原則的觀點開始受到全面的挑戰。
我們認為:首先,任意性和理據性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兩個概念,無論是任意性還是理據性都有其相對性,不可將任何一方絕對化;語言符號既存在任意性,又同時存在理據性,二者矛盾統一,相輔相成。事實上,就連索緒爾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各種語言常包含兩類要素——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對地可以論證的”,“語言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里面有相對的道理……在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一點自然聯系的殘余。”[3]
其次,語言理據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語言其發生、發展、變化的動因各不相同,民族文化因素對詞的概念意義的形成和詞義的引申、發展起著很關鍵的作用。
二、詞語理據的分類
語言中的詞語、單句和復句大致分別記錄了人的認識中的概念、判斷和推理。語言中的詞正是以表示概念為其天職,詞與概念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密不可分的聯系。“語詞的理據性是人對事物和現象的某些特征的捕捉”[4]。語言理據有廣俠之分。廣義理據指整個語言系統發生、發展的動因,其范圍涉及語音、語義、語用和句法等各個層面。狹義的理據則指語言的某一單一層面的理據。本文重點討論的詞語理據屬于狹義理據的范疇。
關于詞語理據的類別,有各種各樣的劃分方法。如Ullmann在其《語義學》一書中把詞的理據分為三類,即:語音理據(擬聲理據)、形態理據和語義理據[5]。其中,他認為擬聲理據屬“絕對理據”(absolute motivation),而形態理據和語義理據則屬“相對理據”(relative motivation)。許余龍考慮到漢語中詞的文字書寫形式與詞義的聯系,認為除此之外還應該有一種理據,即文字理據[6]。陸國強將詞語理據分為:(1)擬聲理據,(2)語義理據,(3)邏輯理據[1]62-72;嚴辰松則把語言理據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外部理據(external motivations),另一類是內部理據(internal motivations)[7]。他認為內部理據應包括語音、形態、語義理據;外部理據指擬聲、擬象、臨摹、省力理據。王艾錄,司富珍在對漢語的語詞理據進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從構成類別、性質類別、造詞類別和顯隱類別等不同角度對復合詞的理據類別做出了更為詳細的分類[8]100-113。他們提出,從構成類別的角度,詞語理據可分為詞外理據(文化理據)和詞內理據(語文理據)。詞內理據主要從內部形式入手,探究反映語詞的若干兩兩相對的構成要素相結合的理據。他們更進一步把詞內理據分為三層:1.詞內表層理據——音義結合的理據(語音理據);2.詞內中層理據——內部形式與理性意義結合的理據(語義理據);3.詞內里層理據——語法結構與語義結構結合的理據(形態理據)。另外也有學者從性質類別的角度分為原始理據和民俗理據;從造詞類別上分為直感和非直感兩種;從顯隱類別上分為顯性理據和隱性理據,等等。本文贊同王艾錄、司富珍兩先生的分類方法,但限于篇幅和為了敘述方便,只選取一種角度,即構成類別的角度對比英漢詞語語音理據、語義理據和形態理據的異同。
三、漢英詞語理據對比
(一)語音理據對比
詞語的語音(擬聲)理據主要體現在詞的語音形式與詞義的對應關系上。具有擬聲理據的詞即擬聲詞。一些擬聲詞是直接模仿某一客觀事物的發聲而產生的,從這些詞的發音,我們可以聯想到它們的所指,這類擬聲詞被稱為基本擬聲(primary onomatopoeia),如英語的meow,cuckoo,buzz,crack,growl,hum,plop,squeak,squeal,bleat,croak,whistle。在漢語也有此類擬聲詞,漢代《釋名·釋樂器》有“箏,施弦高急,箏然也。”“鐃,聲鐃鐃也。”誠如劉師培所論:“古代造字,慮字音展轉失其真讀也,乃以字音象物音。例如,火字之音為呼果切,即象風火相薄之聲。水字之音為式軌切,即象急湍相激之聲。雹從包聲,瀑從暴聲,霰從散聲,亦猶是也。”[9]除單音節詞以外,雙音節詞如“丁丁”,伐木聲;“嘭嘭”,水湍急聲;“齟齬”,鋸木聲;“嘰咕”人饒舌不休聲等。這類語言符號與所指有自然的聯系。還有一類擬聲詞并不能引起音與音之間的聯想,而能引起聲音與某種象征性的意義之間的聯想,這類擬聲詞被稱為次要擬聲(secondary onomatopoeia)。Bloomfield發現,在英語中以sn-開頭的詞常常表示:1.呼吸聲(breath-noise),如sniff,snuff,snore,snort等;2.動作的迅速分離或移動(quick separation or movement),如snip,snap,snatch等;3.爬行(creeping),如snake,snail,sneak,snoop等。英語中聲音與動作發生聯想的詞還很多,如muffle,tremble,toddle,tumble,crumple,等。此外,英語中有些詞的組成部分帶有強烈的象征性含義,有時通過元音或輔音的替換重疊也可達到擬聲的效果[1]62-64。而在漢語中,“聲象乎意”“因聲求義”,已經成為漢語使用者普遍的語言認知心理。清代學者陳澧就認為“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則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如口酸之形,說‘苦’字若口食苦之形,說‘辛’字若口食辛之形”[10]。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的擬聲詞多是動詞,可直接做謂語,如:1.The dog barked the whole night.(那條狗叫了一個晚上)2.A twig snapped under my feet.(一根樹枝啪地一聲落在了我的腳下)3.He made audiences howl with laughter.(他引得觀眾哈哈大笑)等。而漢語的擬聲詞自成一類,一般做狀語(有時也做定語、謂語、補語、獨立語等),后面經常要加“地”,有時加“一聲”。如:1.海水啪啪地拍打著堤岸。2.相機咔嚓咔嚓地響個不停。3.啪嗒一聲,一塊墻皮掉了下來。了解英漢擬聲詞的語法、語義特點對于英漢互譯有直接的現實意義。
(二)形態理據對比
詞的形態理據是指一個詞的詞義可以通過對其構成成分的分析而獲得。如果根據詞的形態,能剖析其組成成分,或能從其組成成分的意義推出整詞的意義,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詞的形態理據強,反之則弱。不同語言對形態理據的運用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如果一種語言的合成詞的數量多于單純詞,則該語言的形態理據性就強。其實,這也是當初索緒爾說德語的理據性比英語強的原因。
索緒爾之所以下結論說德語的形態理據性比英語強,最弱的是詞匯語言漢語,是因為他認為單純符號是絕對任意的。事實上,也未必盡然。我們要承認單純符號的“可論證性”要明顯弱于合成符號。例如,人們無法解釋為什么英語把房屋、車船等的出入口稱作“door”,把一種氣味芬芳、莖部有刺的花叫作“rose”。但解釋不出只是對現代和常人來說的。從詞源學的角度看,這些詞在歷史上可能都曾經是可以分析的。如,enemy在英語中是個單純詞,與法語的ennemi同源于拉丁語的inimicus(敵人)=in(非)和amicus(朋友)。可見,“敵人”在拉丁語中是個可分析的合成詞而到了法語、英語才變成了無可論證的單純詞。又如,英語的companion來自拉丁語cum=with+panis=bread,所以companion(伙伴)就是一個你很喜歡,甚而至于愿意與其分享面包的人。另外,像英語中表示一周七天的詞語除了Sunday外原來都是可分析的復合詞。在漢文化中,人們原把放食物、酒具、茶具的家具統稱為“幾”,在成語“窗明幾凈”中我們還能看到這一原始意義的遺跡。當“桌子”這一事物出現后,人們依據“桌高于幾”的特點,徑直將此物稱為“卓”,后來為了區分卓(高)和卓(桌子),也為了突出桌子的木質義類,就在“卓”字的左邊加上木字旁,寫作“棹”,后來又改寫為“桌”。現在,“幾”當家具講,只出現在“茶幾”“幾案”等有限的幾個詞語中。由此可見,由于歷史的發展,許多詞語形態發生了分合變化或詞義的轉變,因此許多詞語的理據逐漸喪失或變得模糊,而難以探究。但是“難以探究決不能成為否認理據存在的理由”[8]13。因此,與其說德語的理據性強不如說其理據更呈顯性化。而英語則由于從古英語到現代英語拼寫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之大量吸收外來詞和新詞的復古化使其理據逐漸被掩蓋,為一般人所不識。
索緒爾一方面肯定語言符號的絕對任意性,同時也承認其相對可論證性,也就是相對任意性。他說的相對任意性就存在于合成詞之中。德語的理據性之所以比英語強,因為很多具有形態理據的德語合成詞所表達的意義在英語中是由不可分析的單純詞或新古典復合詞表達的。如下表1所示。

表1
從以上例詞可以看出,德語的新詞往往可以“望形生義”,而英語則不行。索緒爾當初之所以判定漢語為(形態理據)最弱的“詞匯邏輯語言”,是因為他只看到漢字既無內部形式,又無詞尾或內部曲折變化等作為語法或語義標志。其實,漢字造字以象形字為基礎,以指示字、會意字相輔,最終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形聲字為主體、以部首為統率,有的字以類相從的構字方法。現代漢字絕大部分都是形聲字,在形聲字中形旁表示意類,聲旁表示讀音。“凡木之屬皆從木”“凡水之屬皆從水”,這樣“松、柏、楊、柳、桃、李、梅”等一望而知都與樹木有關;“江、河、湖、海、洋、池、深、淺”都與水有關。隨著詞匯的發展,漢語逐漸從以單音詞為主發展到了以雙音詞和多音詞為主。但在組詞方法上,漢族人仍然沿用了造字的方法,即先確定一個類屬大名,然后加以個別區分。如把各種各樣不同的交通工具都統稱作“車”,然后再把不同的車分別叫做“汽車、火車、自行車、手推車、救護車、出租車”等等,而這些不同的車在英語中分別是“car,train,bicycle,barrow,ambulance,taxi”從字面上你根本看不出和車有什么聯系。難怪嚴辰松認為“與英語相比,漢語詞匯具有更高的透明度”,“由于漢語大部分詞匯的組成部分清晰可辨,詞內部的理據暴露無遺”[9]。即使是單音節的單純詞也有派生,(如上面提到的由“卓”到“桌”,以及由“立”而派生出的“位”)和合成(形聲字,如江、貸、材、芬,等)。只是這些理據深藏不露,一般人看不出來或感覺不到。
(三)語義理據對比
詞語的語義理據實際上是一種心理聯想,由詞語的基本語義加以引申或轉喻而產生。人們選擇用哪個符號來表達一個新生概念時,往往是有理據的。如英語的calculate來自拉丁文中的calculus (pebble小石子兒),因為古羅馬人用小石子兒作為一種計程的工具。glass作玻璃杯解釋來源于其制作材料。英語中有很多詞匯,通過對其詞義加以引申,就可用來喻指其他事物,如coat:a coat of paint(一層油漆);bonnet:the bonnet of a car(引擎蓋),veil: a veil of mist(一層薄霧),foot: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山腳下),teeth:the teeth of a saw(鋸齒),等等。許多新詞語的產生也是通過對舊詞語的引申和類比而得來的。如a red letter day比喻喜慶吉祥的日子,通過反義類比得出了a black letter day(倒霉不幸的日子);blog(博客)源自船員記錄的航海日志(blog);citizen(公民)一詞衍生出netizen(網民),甚至antizen(蟻族—異族),等等。
漢語的語義理據比英語的更顯而易見。漢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發展完善起來的,而象形字本身就是對事物形狀的描繪。象形字雖然在漢字中占的數量不多,但它是構成漢字的基礎,指示、會意、形聲字都是在它的基礎上發生、發展的。從象形字“日”+“月”,我們得到一個“明”;兩個“人”一前一后,有了“從”;刀鋒上加點兒,表示“刃”;“眉,目上毛也”,并由此衍生出“楣”(近前各兩,若面之眉也);由“山峰”而到“駝峰”,等等。漢字的音、形、義有著天然的聯系,以致國人習慣“望文生義”。
四、結語
從語源的角度看,象形文字是人類語言文字的共同起點。只是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絕大多數語言,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道路,致使在語言的音、義結合的層面,其理據性變成隱性,為多數人所不察。但在形態和語義理據方面則呈顯性。而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其在字形和字義的理據關系上呈顯性,但由于沒有詞形變化,在語法形態理據上則“最弱”,以致被索緒爾歸為“詞匯邏輯語言”。不論是采用表音文字的英語,還是沿用表意文字的漢語,都起源于象形文字,因此都是有理據的,只不過是理據的類型不同,強弱、隱顯程度有差異而已。
[1] 陸國強.現代英語詞匯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3.
[2]Wilhelm von Humboldt.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un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胡明楊主編.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33.
[3]F.de Saussure,Coursede lingguistique générale,1916中譯本[M].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麟祥,葉蜚生,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05-107.
[4]許晉.語言符號任意性和理據性的再闡釋[J].內蒙古社會科學,2003(1):116-117.
[5]Ullmann.S.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M].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2:128.
[6]許余龍.對比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137.
[7]嚴辰松.語言理據探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 (6):2-9.
[8] 王艾錄,司富珍.漢語的詞語理據[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9] 劉師培.原字音篇下[M]//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241.
[10]陳澧.東塾讀書記?小學[M].上海:中西書局,2012:178-179.
[11]嚴辰松.漢英語詞匯透明度對比[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0(3):74-76.
(責任編輯:姚英)
A Contrastive Study of Motivat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Contrastive Study of Motivat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ZHAO Xiao-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
ract:The motivation of words explains how things got their names and how the sounds,the forma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words are related to their physical identities.Linguistic signs are arbitrary,and non-arbitrary. These two principles co-exist in harmony.Neither is absolute.Motivations of words vary in degree and opaqueness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That makes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the motiva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possible.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s of 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ds:arbitrariness;motivation;English;Chinese
H031
A
1009-8445(2015)06-0040-05
2014-11-14
趙曉華(1964-),女,吉林農安人,肇慶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