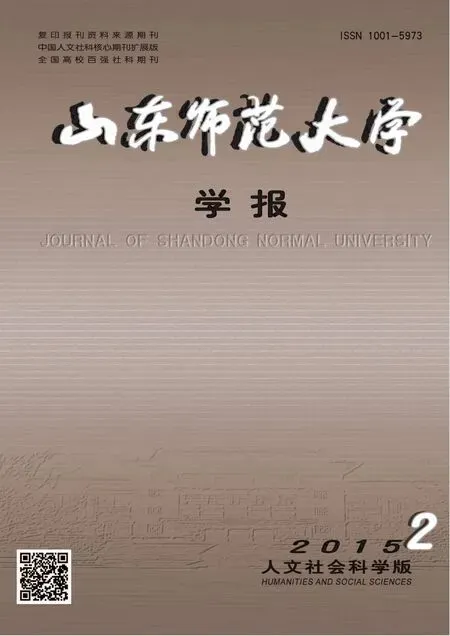作為修辭的歷史
——論渡也的詠史詩*
楊學民
( 南京曉莊學院 文學院,江蘇 南京,211171 )
作為修辭的歷史
——論渡也的詠史詩*
楊學民
( 南京曉莊學院 文學院,江蘇 南京,211171 )
從話語修辭的視角看,渡也的詠史詩可以分為三大類:轉喻型詠史詩、隱喻型詠史詩和反諷型詠史詩。轉喻型詠史詩可以分為深層隱喻性轉喻型和表層隱喻性轉喻型。前者是轉喻在表層話語中占支配地位,深層原型與表層敘事形成了隱喻關系;后者是部分詩節或意象凸顯出來,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與詩歌形成隱喻關系。隱喻型詠史詩包括比興式隱喻型和擬人式隱喻型。反諷與隱喻話語都具有雙重意義,但隱喻注重的是兩層意義的統一,反諷看重的是雙重意義之間的對立。渡也創造反諷詩歌的方式很多,有言語反諷、語調反諷、結構反諷和戲擬反諷等。詩歌修辭的目的在于意義建構,渡也以多種話語修辭創造了豐富的意義空間。
詠史詩;歷史;反諷;轉喻;隱喻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2.003
一、引言
詠史詩以歷史為歌詠對象,借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歷史遺存抒情達意,追求詩、思與史的圓融一體,是詩歌史上的一種重要類型。在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詠史》命篇的是東漢班固,但詠史詩的起源卻可以追溯到《詩經》,《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大明》等可以說是最古老的敘史、詠古的詩篇。東漢以后,詠史詩漸成風氣, 名篇佳作琳瑯滿目。經唐宋至晚清,歷朝不衰。白話新詩的興起以反文言詩歌為前提,力倡“不模仿古人”①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1917年第1期。,但古人詠唱歷史的傳統在新詩史上并沒有絕跡。即使是“五四”時代精神的歌手郭沫若,也沒有與“歷史”斷裂,也寫下了《我想起了陳涉吳廣》、《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等托古言志的詩作。“五四”以后,現代詠史詩雖不如古代詠史詩那樣波滾浪涌,但也似一股溪流,時有浪花漣漪。《七子之歌》(聞一多,1925年)、《古墻》(穆旦,1937年)、《長恨歌》(洛夫,1972年)、《漢城景福宮》(羊令野,1976年)、《古羅馬的大斗技場》(艾青,1979年)、《紀念碑》(江河,1980年)、《杜甫》(西川,1989年)等都是中國新詩史上詠史詩的名篇。
臺灣詩人渡也自中學時代開始詩歌創作,筆耕不輟,產量甚豐,出版有《手套與愛》(1980年)、《陽光的眼睛》(1982年)、《憤怒的葡萄》(1983年)、《最后的長城》(1988年)、《落地生根》(1989年)、《空城計》(1990年)、《留情》(1993年)、《面具》(1993年)、《不準破裂》(1994年)、《我策馬奔進歷史》(1995年)、《我是一件行李》(1995年)、《流浪玫瑰》(1999年)、《地球洗澡》(2000年)、《攻玉山》(2006年)等14部詩集,詩作1000余首,其中詠史詩100余首。主要篇目見表一。
渡也出入文史,出版有古典文學論集《分析文學》和《渡也論新詩》等學術著作,對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及詩學皆有比較精深的研究,其詠史詩既承續了以往詠史詩的神髓和修辭方式、詩歌意象等詩歌元素,又進行了多方面的創新,顯示出不同的時代精神、美學風貌以及臺灣地域的歷史文化特色。

表一
詠史詩是歷史客體與創作主體在審美意義上的融合,從歷史、詩人或主客關系視角分類研究詠史詩也就成為了詠史詩研究的常見模式。例如,有學者根據把握歷史的角度將古典詠史詩分為史傳體、史贊體、情理體和懷古體,進行研究;*韋春喜:《漢魏六朝詠史詩探論》,《中國韻文學刊》2004年第2期。也有學者把詠史詩分為寫實型、意象型和意境型等三種形態,分別描述分析其特點。*章建文:《論古代詠史詩的基本形態》,《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研究渡也詠史詩的學者也習慣性地根據歷史題材內容將其作品分成了三種類型:歷史人物與事件、民俗采風與鄉土文化、古董文物與生活用品。*林怡汝:《渡也新詩的詠史特質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臺灣中興大學,2007年。以往的詠史詩研究雖然有助于讀者理解詠史詩的思想情感內容、類型特點等,但卻忽略了對其詩歌話語特色的探討和深入研究。本文擬從話語修辭的視角,探討渡也詠史詩話語的意義建構方式以及借歷史所表達的情感寄托和意義探詢。
二、渡也詠史詩的三種基本類型:轉喻型、隱喻型和反諷型
文學是一種話語實踐活動,是說話人在一定語境中通過某種文本與受眾之間的對話交流。詹姆斯·費倫在研究敘事話語時把敘事話語的修辭過程更加具體化了,他認為“作為修辭的敘事”“這個說法不僅僅意味著敘事使用修辭,或具有一個修辭維度。相反,它意味著敘事不僅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動,某人在某個場合出于某種目的對某人講一個故事”*[美]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作為修辭的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頁。。詩歌雖然是一種抒情文體,話語建構方式不同于小說敘事等,但它同樣是一種話語實踐活動和修辭過程,在話語活動中,傳達知識、情感、價值和信仰等意義。在詠史詩的話語修辭實踐中,歷史作為重要修辭元素參與了作者與讀者的對話過程,或者說詩中的歷史已經修辭化了。
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首先提出了“句段關系”與“聯想關系”這一組概念。認為語言都是以這兩種關系為基礎的。 “一方面, 在話語中, 各個詞, 由于它們是連接在一起的, 彼此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系, 排除了同時發出兩個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要素一個挨著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這些以長度為支柱的結合可以稱為句段。”“另一方面, 在話語之外, 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合起來, 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它們的所在是在人們的腦子里。它們是屬于每個人的語言內部寶藏的一部分。我們管它們叫聯想關系。”*[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70-171頁。雅柯布遜則把“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引入到了詩學領域,提出了相對應的轉喻和隱喻概念。他認為,“對話的延伸是沿著兩個不同的語義學途徑進行的:或是通過話題的相似性,或是通過接近性,一個話題可以引出另一個話題,對于第一種情況,隱喻方式可謂是最切合的術語,而轉喻方式則是最適合第二種情況的術語,因為它們各自在隱喻和轉喻中找到了自己最凝練的表達”*[美]羅曼·雅柯布遜著,周憲譯:《隱喻和轉喻的兩極》,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著:《激進的美學鋒芒》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17頁。。在正常的話語中,轉喻和隱喻共同參與話語運作,由于作家個人偏好、時代風尚、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轉喻和隱喻在不同文體、作品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對詩來說隱喻是快捷方式,對散文來說轉喻是快捷方式。”*[美]羅曼·雅柯布遜著,周憲譯:《隱喻和轉喻的兩極》, 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著:《激進的美學鋒芒》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21頁。“在俄國抒情歌謠里,隱喻的結構居支配地位;而在英雄史詩里,轉喻方式則占有優勢。”*[美]羅曼·雅柯布遜著,周憲譯:《隱喻和轉喻的兩極》, 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著:《激進的美學鋒芒》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19頁。在雅柯布遜看來,隱喻和轉喻不只是語言層面上的修辭格,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建構文本世界的轉義方法,深刻地制約著詞語、句子、語段和篇章的修辭活動。但影響詩歌話語的修辭方式不只有隱喻和轉喻,在隱喻和轉喻之外還有一種修辭方式,它既以轉喻和隱喻為基礎,但又是對轉喻和隱喻的超越,那就是反諷。
如果說渡也的詠史詩話語有隱喻和轉喻的共同參與,這只是為雅柯布遜的詩學多提供了一個例證。一個詩人的詩歌話語特點不在于話語的共性,而在于其獨特性,具體而言在于在不同語境之中,根據修辭目的而對隱喻和轉喻以及它們與其他修辭方式的獨特調配。根據詩歌話語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修辭方式的不同,我們把渡也的詠史詩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轉喻型、隱喻型和反諷型。當然每種基本類型又包含著亞類型,從某種意義上說,渡也詠史詩的個性主要體現在這種綜合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修辭方式的亞類型身上。
三、渡也的轉喻型詠史詩
從現代認知語言學角度看,“轉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認知模型內,出于交際的需要,語用者用一個認知域啟動另一個認知域的操作過程”*李勇忠:《語言結構的轉喻認知理據》,《外國語》2005年第6期。。它在話語中有兩個顯著特征,一個是喻體與本體之間具有替代關系,部分替代整體或整體替代部分;另一個則是話語流存在著“鄰近關系”,話語主要依靠因果或時間先后秩序流動。可以說,所有的詠史詩都具有轉喻性質,因為詩歌無論如何地細致描摹,無論篇幅多長,都無法完整地呈現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只能掛一漏萬,只能以部分代整體。轉喻是歷史實現轉義的基礎。在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生平事跡為題材的敘事性詠史詩中,轉喻占有支配地位。渡也的《宣統三年》、《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最后的長城》、《我靜靜眺望祖國江山》、《王維的石油化學工業》、《殉國的梅花》等,從整體來看都屬于轉喻型詠史詩。它們都選取了一個歷史片段作為歌詠對象,如《宣統三年》選擇的是武昌起義,《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歌唱的是革命先驅方聲洞的生平歷史。這只是從詩歌題材與歷史本事之間的關系來說的。深入到詩歌文本內部來看,其詩句、詩節的線性連續也是轉喻性的。任意舉出《宣統三年》幾個詩節,就可以展現這種轉喻型詠史詩話語的基本運行機制。
宣統三年,春天/郵傳部大臣盛懷宣大叫/鐵路國有!鐵路國有!/各省都搖首反對/鐵路也抗議/樹在風中嘆息//宣統三年春天,鴉片依然茂盛/依然成為百姓的三餐/割地、賠款依然是流行病//樹在風中低頭嘆息/清兵在每一條街道/在黨機關,用子彈/射入革命黨人的嘴巴/刺穿革命黨人的頭顱*渡也:《最后的長城》,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第5-6頁。
從詩句來看,第1節第1句“宣統三年,春天”與接下來的第2、3句構成轉喻關系,后兩句是宣統三年發生的事情,是所有事件中的一件,它們之間存在著部分與整體以及時間的關聯。而接下來的“各省都搖首反對/鐵路也抗議/樹在風中嘆息”又是前面詩句的結果,構成因果關系。而從詩節之間的關系來說,在“宣統三年春天”這一認知框架內,3個詩節在語義層面存在著鄰近關系,依據轉喻思維,通過話題的鄰近關系向前推進。因此可以說,《宣統三年》在詩歌與歷史、詩句與詩句、詩節與詩節等不同話語層面上均依據轉喻思維或轉喻修辭在建構詩歌話語。《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最后的長城》、《我靜靜眺望祖國江山》、《王維的石油化學工業》、《殉國的梅花》等詠史詩也是如此。
與散文甚至同樣以轉喻為主要修辭方式的敘事詩相比較,渡也的詠史詩對轉喻的運用也顯示出了特別之處,那就是善于在轉喻話語中經營“留白”,留出了大量“空白”讓讀者共同參與詩歌創作。朱光潛先生說:“無窮之意達之以有盡之言,所以有許多意,盡在不言中。文學之所以美,不僅在有盡之意,而猶在無窮之意。”*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94頁。而無窮之意正來自于文學中的“空白”。 轉喻、隱喻等其實是比喻的一種,都回避直言,自然也就留出了“空白”和想象的空間。創設“空白”的文學方式很多,渡也創設詠史詩“空白”的常用方法主要有:敘事序列轉喻、情節轉喻和結構轉喻。敘事序列是基本的敘事單位,是幾個動作依據常規邏輯而展開的過程,比如“握手”序列一般包含著“伸手、握住、松手”三個動作。如果在語境中,只敘述三個動作中的一個或兩個,或以“握手”替代整個序列,就形成了轉喻。渡也詠史詩中的敘事序列轉喻不勝枚舉。僅以《殉國的梅花》中的幾個詩句為例:
三十一歲那年/你僅僅留下一篇最痛心的絕命書/便毅然躍入東海/你是不偷生的梅花/也只有一朵新化的梅花/默默飄入大森灣/才能催促中國所有的梅花醒來……*渡也:《不準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第29-30頁。
如果我們把“你僅僅留下一篇最痛心的絕命書”這個敘事序列補充完整,足可以寫成一篇小說。按照常規生活經驗,它應包括“準備紙筆、鋪開紙張、拿起筆來、書寫絕命書、停筆、出版、發行”等,而詩人卻以整體代部分的轉喻修辭完成了一個敘事序列。
情節轉喻處于比敘事序列更高的話語層面上,一個情節包括多個事件和敘事序列。情節和敘事序列的轉喻機制一樣。《殉國的梅花》共選擇了三個情節:陳天華東渡求學、書寫《警世鐘》、未覺醒的留學生在海邊猛然醒悟。而每一個情節都只有不多的幾個詩句。在“你僅僅留下一篇最痛心的絕命書”和“便毅然躍入東海”兩句或兩個情節之間留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情節、故事?但都被省略了。迅疾的敘述更凸顯出了壯士決然以死來喚醒國民的意志。
詩歌結構在敘事性較強的詠史詩中主要以故事情節為結構單元,而形成一個整體。結構轉喻是說在詩歌話語結構層面上,一部分情節代替生活的全部。同樣以《殉國的梅花》為例,該詩是以革命烈士陳天華東渡日本留學,參加革命,為喚醒愚昧的國民而蹈海的事跡為歷史背景的,可以想象,陳先烈在日期間的所作所為,肯定不會只有詩歌呈現的三個主要情節,甚至可以說絕大部分事件都被省略了,而僅僅選擇了這三個最凸顯的情節組成了詩歌的有機結構,形成了結構轉喻。
通過對《殉國的梅花》中的敘事序列轉喻、情節轉喻和結構轉喻的簡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轉喻在詩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學功能。首先,轉喻創造了詩歌的“空白”和讀者參與的空間,在疏朗的字里行間,言外之意冉冉升起。其次,轉喻有助于調節詩歌的節奏,使節奏更加緊湊。痖弦在評價渡也的詠史詩《宣統三年》時認為,詩人“以簡明的意象、朗誦的語氣、快速的節奏、戲劇的動感統攝全詩,把先烈熊秉坤這段驚心動魄、迅雷狂飆般的歷史場景,形象而生動地表現了出來”*痖弦:《抒大我之情》,渡也:《最后的長城》,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第3頁。。其中的“快速的節奏、戲劇的動感”這種美學力量的形成與渡也善于運用轉喻修辭密不可分。最后,轉喻可以說成為了渡也詠史詩“宏大敘事”的有力支撐和基礎。
如果詠史詩僅僅靠轉喻思維來運作,也易流于流水賬、散文化,詩味寡淡。可喜的是,渡也的轉喻型詠史詩并沒有只滿足于轉喻的運用,而是有意或無意地融合進了隱喻,實現了隱喻與轉喻融合的多種方式,形成了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和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
(一)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
所謂的深層隱喻性轉喻,是說詩歌的表層話語轉喻占支配地位,但始終有隱喻修辭參與,一邊敘事一邊激發詩歌深層的原型。深層原型與表層話語敘事形成了結構性相似而構成隱喻關系。渡也對原型批評理論是熟悉的,他在《詩中的原型》一文中曾以此理論方法討論過覃子豪的兩首詩《過黑發橋》和《追求》。他認為:
所謂原型模式,亦可以簡稱為“原型”(Archetype) ,它和神話有著密切的關系。神話足以將一個部落或者國家結合于那個民族所共有的心理與精神的活動范圍之內。雖然各個民族都擁有其自身的神話,反映在傳說、民俗與觀念之中,盡管神話皆因各個民族所有的其相異的文化環境而構成不同的特殊形態,然而,一般而言,神話是普遍的。非獨如此,許多相異的神話中亦具有相似的主題(theme) 。在時空距離均極遙遠,更確切地說,彼此完全沒有任何歷史影響與因果關系的各個民族的神話里反復展現的某些心象,泰半亦含有一種共通的意義。換言之,可導引相似的心理反應而發揮相似的文化功能來。這種主題與心象均稱作“原型”。它是不斷地反復呈現在歷史、文學、宗教或民俗習慣里,以致于獲取很顯著的象征力的一種普遍的隱喻意象、題旨或主題模式。一言以蔽之,“原型”便是“普遍的象征”(universal symbols)。*渡也:《詩中的原型》,《渡也論新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第93-94頁。
渡也不只是用原型批評理論評論別人的詩作,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也自覺不自覺地激發、建構原型,以增強詩歌的隱喻功能和象征意義。《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最后的長城》、《我靜靜眺望祖國江山》、《道光年間》等詠史詩,都屬于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歌詠的是革命先驅方聲洞戰死沙場的壯舉;《最后的長城》贊嘆的是林則徐抵制鴉片而被謫貶的史實;《我靜靜眺望祖國江山》詠嘆的是王安石變法的努力和挫敗。從整體來看,它們擁有共同的原型——“陰”勝“陽”,是“陰”戰勝“陽”的英雄悲劇。
整部文學史從上古樸質的文學一直寫到現代深奧精良的作品,在這過程中,在研究這些作品時,我們“應該是探索以審美創造來承載心靈史的那個過程,激發并復活過往文學所創造所遺留的那些不朽結晶的不朽魅力”*賈振勇:《文學史的限度、挑戰與理想——兼論作為學術增長點的“民國文學史”》,《文史哲》2015年第1期。,這樣我們才有機會瞥見原來文學是呈現于原始文化中的較為局限和簡單的程序系統逐步演變而成的復雜體系。如果這樣,那么探索各種原型便成了一種文學上的人類學,它涉及諸如儀式、神話和民間傳說等文學前的形態如何滲透到后來的文學中來的問題。*[加拿大]諾思羅普·弗萊:《文學的原型》,吳持哲編:《諾思羅普·弗萊文論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85頁。
這意味著渡也詠史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文化中的神話、儀式和民間傳說,以及以往的文學史中。渡也詠史詩的英雄悲劇原型也就與中國遠古神話《夸父追日》、《精衛填海》等以及后來的“屈原投江”、“霸王自刎”和大大小小的英雄悲劇等形成了一個“秋天的故事”系統。弗萊說:“凡是習慣于從原型角度思考文學的人,都會發現悲劇乃是對犧牲的模仿。悲劇是一種矛盾的結合:一方面是正義的恐懼感(即主人公必定會墮落),另一方面則是對失誤的憐憫感(主人公墮落,太令人惋惜了)。犧牲的兩種成分同樣構成一個矛盾體。”*[加拿大]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批評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310-311頁。古代神話《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刑天舞干戚》的內在矛盾都是陰陽對立,承載的原型可以說是“陰”勝“陽”。逐日的夸父是一個失敗的悲劇英雄,方聲洞、林則徐、王安石、陳天華等何嘗不是悲劇英雄呢?
從上面的論述來看,渡也的《永不回頭的方聲洞》、《最后的長城》、《我靜靜眺望祖國江山》、《道光年間》等詠史詩,可以說是《夸父追日》等神話在新時代的置換變形,其深層的原型作為潛在的中介使這些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與無數文本構成了互文關系,極大地擴充了詩歌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蘊,使詩歌內蘊變得異常豐厚。進一步來說,文學原型的“啟動”具有為現代人尋找精神家園,拯救現代人靈魂失落的功能。正如榮格所言:“人類文化開創以來,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蟄伏在人們的無意識中,一旦時代發生動亂,人類社會陷入嚴重的謬誤,它就被重新喚醒……每當意識明顯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種虛偽傾向的時候,它們就被啟動———甚至不妨說是‘本能地’被啟動———并顯現于人們的夢境和藝術家先知者的幻覺中,這樣也就恢復了這一時代的心理平衡。”*[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榮格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43頁。渡也在進入后現代的臺灣書寫這些具有“夸父”精神的英雄史詩,贊美祖國歷史上的悲壯英雄,標舉崇高的旗幟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對于當代臺灣人文化心理確實具有“補鈣”的意義。在英雄消失的后現代主義時代,渡也歌詠英雄,也許有悲壯氣概。
(二)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
與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不同,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的兩種比喻修辭的融合直接發生在詩歌話語表層,隱喻直接投射在轉喻話語鏈條上,比如《道光年間》:
道光年間/有一顆星向江南馳去/擊中英國領事義律的傷口/這顆星/連鴉片也怕它//中國所有的尊嚴/都集合在它身上閃爍/在它走過的每一條路上/它在清朝喊了四十年/中國要鍛煉身體/沒有一只耳朵在聽/甚至我的學生在臺下埋頭/準備專業科 目期末考/用力將這顆星推到墻角//我在講臺上/喊了兩個小時/淚終于流下來/淋濕了在課本里揮汗奔波的/林文忠公的官服*渡也:《落地生根》,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第103-104頁。
這是詩集《落地生根》第一輯“講師日記”中的一首詩,整體看來是敘寫“我”的一個講課場景。“我”所講述的先知先覺者林文忠公喚醒國人戒絕鴉片,強身健體卻不被回應的故事,是講課場景的一部分,屬于轉喻話語鏈條上的一段,所以整首詩屬于轉喻性話語。但令人贊嘆的是,林文忠公的故事與“我”講課場景卻有內在的一致性,構成了隱喻關系,都可以說是啟蒙而不被理解的故事,現在的“我”與古代的林文忠公都是孤獨的先知形象,是跨越時空的知己。讀者在詩句間不難體會到敘述者“我”和林文忠公的那種無奈、失望、悲憤的情緒。
轉喻性詠史詩中的部分片段凸顯出來,獲得相對的獨立性,與詩歌整體構成隱喻關系,一方面拓展了作品的意義空間,另一方面也豐富了詩歌的修辭技巧。前面列舉的《宣統三年》也可以說是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請看其中的兩個詩節:
好/大家約好臂纏白巾/縱火為號/宣統三年,八月十九/辛亥雙十/李鵬升如約在塘角放火/“革命的心我也有/革命之火/我也有”//塘角雜貨店主說著/立即點燃煤油/茂盛的火光在空中飛舞/宛如一盞明燈/照亮每一個百姓的臉/百姓的夢/照亮全中國的土地*渡也:《最后的長城》,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第7-8頁。
這兩個詩節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事件,是武昌起義歷史事件的一部分,但卻與武昌起義具有相似的結構。武昌起義是封建帝國的一盞明燈,是革命先驅點燃的一把熊熊烈火,是毀滅封建制度的第一縷光明,而李鵬升和雜貨店主燃起的燈火對于武昌起義而言是起義的信號,革命之火,劃破了暗夜,引發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照亮全中國的土地”。“塘角放火”事件與辛亥革命互相映射,形成隱喻關系。
建構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的方式多種多樣,除了上述方式之外,渡也也喜歡使用隱喻意象以使詠史詩在話語表層形成隱喻修辭與轉喻修辭的互動,使詩歌具有了雙層結構。例如在《永不回頭的方聲洞》中,詩歌話語在以轉喻思維敘述革命英雄方聲洞的生平事跡時,有一些隱喻意象像點點星火一樣不時地在詩行間閃爍跳躍,比如“梅花”、“黃花”、“鴉片”等意象。請讀下面詩節:
……辛亥年的春天/梅花仍舊盛放/黃興、趙聲、胡漢民等人一致說/朝所有不低頭的梅花說:/該是時候了/這一句話/雖然輕聲,簡短/雖然隔了重重的冷冷的海洋/但是留日同志的耳朵都收到了/留日同志的心都聽到了……九次痛楚而美麗的戰役/不幸的同志均已化作無言的/勇猛的黃花/一去不復還/大丈夫方聲洞豈能不去/靜靜寫成幾封絕筆書/心中涌起一江狂奔的巨流/方聲洞就頭也不回地/流去了//去吧,為了成為一朵灼亮/英挺的黃花*渡也:《最后的長城》,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第28-31頁。
僅以“黃花”為例,據統計,“黃花”意象在該詩中共出現了6次。 “黃花”是“菊花”的代稱,是漢語詩文中常用的意象。意象的多次重復就構成象征或者說象征性隱喻。“黃花”的隱喻意義實際上成為了一個一言難盡的意義叢集。在此,我們可以在大家熟悉的詩歌中探詢其常見意義。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離騷》(高潔品格)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飲酒》(隱逸之意)
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醉花陰》(感傷之態)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毛澤東:《采桑子·重陽》(戰斗精神的化身)
當“黃花”意象攜帶著積淀在自己身上的意義叢集:高潔品格、隱逸之意、感傷之態、戰斗精神的化身,進入詠史詩《永不回頭的方聲洞》之后,“黃花”的品格、意義就與以方聲洞為代表的革命戰士的品格、信念、行動等產生了隱喻性映射,革命戰士與“黃花”合為一體,革命戰士的精神品格獲得了充實和升華。“梅花”意象在《殉國的梅花》、《永不回頭的方聲洞》等詩篇中也具有同樣的功能。
四、渡也的隱喻型詠史詩
就詩歌的數量而言,渡也的大部分詠史詩屬于隱喻型詠史詩,因為畢竟隱喻或“相似的原理構成了詩的基礎”*[美]羅曼·雅柯布遜著,周憲譯:《隱喻和轉喻的兩極》,[法]福柯等著,周憲譯:《激進的美學鋒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21頁。。“隱喻涉及兩個不同領域之間的互相作用。在這一互相作用過程中,其中某一領域(源領域)的結構關系和相關特征被映像到另一領域(目標領域)。這一映射的結果是兩個、甚至是三個以上心理空間中概念之間的整合。而這一映射和整合過程發生的基礎是相似性。……由于隱喻同時涉及兩個不同領域,因此隱喻話語具有雙重影像的特點,它是隱喻話語之所以形象、生動和意猶未盡的主要原因所在。”*束定芳:《論隱喻的運作機制》,《外語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2期。隱喻思維滲透到了渡也詠史詩的詞語、詩句、詩節或詩篇等諸多話語層面上,與轉喻一起發揮著建構詩歌話語、表情達意的作用。在隱喻與轉喻的共同作用下,詩歌話語形成了不同的聚合或組合方式,即詩歌類型。渡也的隱喻型詠史詩大體可以分為比興式隱喻型詠史詩、擬人式隱喻型詠史詩。
(一)比興式隱喻型詠史詩
比、興屬于中國古典詩學范疇。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詞也。 比興在思維方式上與隱喻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礎上的兩個領域的相互作用。渡也的詠史詩特別是《流浪玫瑰》《攻玉山》等詩集中的詠物之作大多運用比興思維或者說隱喻思維結構成篇。比如《雙魚鼻煙壺》、《三寸金蓮》、《彰化的長江》、《宣德香爐》、《木刻神像》、《綠釉油燈》、《青花磁盤》、《五彩磁碗》等。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雙魚鼻煙壺》來理解這類作品的話語建構機制。
它們緊緊擁抱著/想必是萬年前的情侶吧,想必是/萬年后的你和我//在千度高溫下煎熬成型/這淺青,瓷的,雙魚鼻煙壺/我們的愛/也如此燒成吧/啊,就不要變形//將它們細心放在心中/兩尾魚仍然緊緊擁吻著/一萬年的擁抱/啊,不要碰撞/因為愛/容易碎裂*渡也:《流浪玫瑰》,臺北:爾雅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第3-4頁。
這首詩有3節,每一節都首先描述了“雙魚鼻煙壺”的一種特征,而緊接著讓時間推進到了千萬年后的今天一對情侶的情感狀態。比如第1節:“它們緊緊擁抱著/想必是萬年前的情侶吧,想必是/萬年后的你和我”,而這一詩節與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結構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詞也”。先言之物與后言之詞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似,構成隱喻關系,雖然先言之物與后言之詞之間存在著時間、空間等方面的差異,但畢竟相似性得到了凸顯,成為了相互激發的基礎。《雙魚鼻煙壺》的第2、3節的話語結構與第1節一樣,無大變化。由此可以看出,這首詩話語整體運作機制是:先以部分代整體的轉喻修辭分別抓住“雙魚鼻煙壺”某一特征進行描述, 這有助于在不同維度上豐富詩歌的內涵,展示吟詠對象的多層面特征,然后通過隱喻修辭把先言之物投射到另一個領域,從而在整體上使詩歌作品形成隱喻性的雙層結構話語,讓歷史獲得新的生機,“雙魚鼻煙壺”此時已經不是古董鼻煙壺了,而成為了一種愛情理想,一種深摯愛情的象征。《木刻神像》、《三寸金蓮》等詩歌的話語運作機制與《雙魚鼻煙壺》相比,并無太大的差異。《木刻神像》在今昔對比中,思考了神與信眾之間的關系,昔日被膜拜的神像,現在降格為膜拜者,他們膜拜的是一切金錢拜物教的神靈。詩人借木刻神像的現代遭遇,發出的是對現代人信仰失落的慨嘆,人文關懷之情彌散在字里行間,不絕如縷。
(二)擬人式隱喻型詠史詩
雖然擬人式隱喻型詠史詩也涉及到轉喻與隱喻的融合,但與前文論述的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和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不同,也不同于比興式隱喻型詠史詩。表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是詩歌的部分凸顯,形成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隱喻;深層隱喻性轉喻型詠史詩是因詩歌深層結構即原型而與古代神話和前文本形成隱喻關系;比興式隱喻型詠史詩是在詩歌話語以轉喻方式展開的過程中,通過詩句與詩句或詩節與詩節之間的隱喻而形成的整體隱喻詩。而擬人式隱喻型詠史詩內部不存在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隱喻;不依靠原型鏈接后文本與前文本之間的隱喻關系;也不需要在轉喻詩句、詩節旁邊安排比興而形成隱喻繼而形成整體隱喻詩。它只是在轉喻式地鋪陳詩歌話語,描述歷史物象的諸多特征時,依靠擬人隱喻就把整首詩歌轉變為隱喻型詩歌,把人的特征賦予給歷史物象,進而使詩歌話語轉變成隱喻性雙層話語,使所詠事物似物非物,似人非人,極具隱喻色彩。比如《土罐》、《犁》、《太師椅》等詩篇。請看《土罐》:
茫然張開不會說話的大嘴/獨自蹲在鄉村角落/春去秋來/陪王家孩子游戲/送李家女兒出嫁/眼看所有的主人被塵土帶走/土罐漸漸衰老無力//春去秋來/默默裝過陶工的心意/裝過糖、米,裝過水/裝過凄涼/從來沒有裝過/恨//茫然睜著不會流淚的眼睛/獨自蹲在鄉村溝中/被愛和溫暖遺棄/被計算機遺忘的土罐/滿臉都是風化的時間//春去,秋來/數十年的酸甜苦辣/肚子寬大的土罐/不皺眉頭/一口飲下*渡也:《留情》,臺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64頁。
在這首詩中,古董陶罐本為一無生命的物體,但渡也把它寫得活靈活現,它無腳卻可以東奔西走,無舌卻可以張口說話,具有七情六欲和酸甜苦辣,顯然已經擬人化了。擬人是一種隱喻,它作為一種隱喻思維方式,是基于人與事物之間的某種相似性,把人類這一領域中的心理活動、言語行為特征投射到事物領域中。《土罐》正是基于擬人隱喻而建構的詩篇。讀者在閱讀這首詩時,依據土罐的擬人特征和個體體驗可以幻化出不同的形象,土罐是母親的化身抑或是地母、父親、鄰家大嫂的隱喻,無論是何人,她一定有著寬容無私的胸懷,悲天憫人的心境,無私奉獻的品格,是值得贊頌的人。
五、反諷型詠史詩
反諷(irony)概念源于古希臘喜劇的一個角色類型,即佯裝無知者,后來演變成了一種修辭格,其基本涵義是“言此而意彼”。鼎盛于20世紀中葉的“新批評”派對反諷理論進行了更加深入、具體的探究,并廣泛用于文學批評。克林斯·布魯克斯在《反諷——一種結構原則》一文中集中表述了他們對反諷的看法:反諷就是“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反諷作為對于語境壓力的承認,存在于任何時期的詩、甚至簡單的抒情詩里。”*[美]克林斯·布魯克斯:《反諷——一種結構原則》,趙毅衡:《“新批評”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336、345頁。趙毅衡解釋得更加明白,認為“反諷的形式機制,是一個符號文本不表達表面的意義,實際上表達的是正好相反的意思,這樣的文本就有兩層意思:字面義與實際義,表達面與意圖面,外延義與內涵義。兩者對立而并存,其中之一是主要義,但是究竟何者是反諷的主要意義,在形式上不一定有定論,要看解釋情況而變化”*趙毅衡:《反諷:表意形式的演化與新生》,《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總之,反諷的兩個突出特征是:反諷生成于語境當中;反諷是兩種相反、相對的元素之間的張力,雖然張力形成的技巧、方法等多種多樣。
從前文分析的詩歌作品來看,渡也的隱喻型詠史詩的源域與目標域之間雖然存在著張力,但作者凸顯的是張力之間的統一性,而有意忽視了兩個域之間的沖突和差異。大致從詩集《不準破裂》(1994年)以后,他詩歌的格調越來越顯示出反諷氣質,更加追求張力中的對立和錯位,面對歷史,表現出一種顛覆歷史的沖動。《屈原之一》、《自殺未遂的屈原》、《憤怒的屈原》、《屈原之二》、《渡也與屈原》、《五柳先生傳》、《戲贈杜甫》、《戲贈李賀》、《糯米、豬肉、花生》、《屈原與計算機》等詩作已經脫去了端莊、沉郁、憤激的情調,而顯出譏諷、“山寨”、戲弄的氣質。《屈原與計算機》把2000年前的大詩人置放到了計算機時代,這種并置就顯得有些突兀和怪異,然而更怪的是當今詩壇亂象:
如今詩壇/比春秋戰國還亂/凡是新奇,就是/萬歲/凡是憂國憂民就是古代/古代詩人的事/唯感官剌激/和新潮/才是詩的*陳啟佑:《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第135-136頁。
詩人在描述詩壇現狀時的語調流露著譏諷之意,而兩個“凡是”所引導的詩句明顯存在著邏輯沖突,讓人覺得話里有話,能指與所指之間出現了錯位。這是典型的語調和言語反諷。
渡也詩歌的反諷多種多樣。再看另一首反諷詩《母系社會》,這首詩的前面大部分都以夸張的語調描述母系社會男人與女人的關系:
這是愛的新石器時代/我們像羊的耳朵一樣聽話/像豬的性器一樣努力/每年春天/我們——七個男人/一起盼望女人為我們/生一大堆兒女/就像大地懷孕/懷孕快樂的農作物一樣
但在詩歌的結尾,筆鋒一轉,繼續寫道:
這是愛的新石器時代/在香甜的黃河流域/不懂政治的黃河流域/肥美的半坡村/圓形的茅屋內/我們甜甜地睡著了,夢見/舊石器時代*渡也:《我是一件行李》,臺中:晨星出版社,1995年,第93-94頁。
如此行文,就使詩歌在結構上形成了“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對立,屬于結構反諷。不管更久遠的“舊石器時代”是什么模樣,但它是“我們”的夢想,而不是現實的“新石器時代”,夢想與現實存在著極大的反差。反諷的意義不只在于顛覆“新石器時代”的性別之間的關系,而更在于反諷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是意義叢生的空間。顛覆女人統治男人的時代,并不直接滑向男人統治女人的時代。無論誰統治誰,總不會改變“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在這首詩中,讀者一方面能體會到詩人對“新石器時代”男女關系的不滿,對女性主義、女權主義走向極端的譏諷,一方面又能體會到詩人對男女之間公平、和諧關系的向往以及對淺薄的女性主義的警覺。
《戲贈杜甫》、《戲贈李賀》、《戲弄孟浩然》、《糯米、豬肉、花生》等詩歌的反諷品格主要源于戲擬。《糯米、豬肉、花生》前兩節以端莊、沉郁的語調描述屈原投江,但自第三節開始語調變得粗俗、滑稽,兩種語調之間產生了齟齬和相互消解,更有意味的是詩的最后一節,“我”也開始了模仿屈原投江的壯舉:
我也要投江/投詩之江/何時我才會浮出每個人的心湖//搶占屈原的位置/端午節我也要吃粽子/紀念在龍舟上寫詩的我/一面吃/一面懷念糯米、豬肉/花生*渡也:《攻玉山》,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年,第67-68頁。
當讀者讀完這最后一節時,在比較之中,“我”的投江舉動馬上會變成一出滑稽劇。“糯米、豬肉和花生”所暗示的口腹之欲與關乎靈魂的詩歌共處一起時,“詩”也顯得“非詩”,糯米、豬肉和花生似乎煥發出了靈光。在這首詩中,詩歌戲擬的前文本與后文本之間有著比較完整的對應,而在《戲弄孟浩然》等詩歌中,并沒有如此對應的詩節,它們主要以戲謔的話語重寫前文本,而實現顛覆前文本、與歷史對話的目的。據《唐才子傳校箋》載:
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詩工五言。隱鹿門山,即漢龐公棲隱處也。四十游京師,諸名士間嘗集秘省聯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眾欽服。張九齡、王維極稱道之。維待詔金鑾,一旦,私邀入商較風雅,俄報玄宗臨幸,浩然錯咢伏匿床下,維不敢隱,因奏聞。帝喜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再拜。帝問曰:“卿將詩來耶?”對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命放還南山。*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62-366頁。
《戲弄孟浩然》源此故事而起詠。讀者只看后面兩節就可以體會反諷意味:
我敢說孟夫子日夜所想的/盡是榮華富貴/究竟他還想些什么/也只有他心里有數//其實他躲在床下/怕見唐玄宗/這種苦肉計未免造作/我操/隱居鹿門山更是騙人的把戲/可憐李白受他蒙騙最深/你只要看他那首《贈孟浩然》/就會明白*渡也:《憤怒的葡萄》,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138-139頁。
反諷的闡釋離不開語境(包括文本內語境和文本外語境)。《戲弄孟浩然》中的“孟夫子”“他躲在床下”、“唐玄宗”、“隱居鹿門山”等話語符號時刻提醒著讀者注意前文本的存在,但這些話語符號卻是在新語境之中,被新語境所擠壓和扭曲,顯示出來不同于其在前文本中的意義。“他躲在床下”成為了苦肉計,“隱居鹿門山”則變成了騙人的把戲。這就使這一系列行為在新語境中產生了新意義。《戲贈杜甫》和《戲贈李賀》等也以戲擬的方式實現了反諷。戲擬不能炒冷飯,它成功的關鍵在于前文本與后文本之間要有張力,張力越大反諷意味越強。
六、結語
從橫向來看,渡也的詠史詩主要有三種基本類型:轉喻型、隱喻型和反諷型。而從縱向來看,渡也的詩歌創作經過了早期的“描寫自我的階段”,到20世紀80年代初,他自覺“拋棄整個象牙塔,踏入社會,進入廣大的群眾里。挖掘人類的問題,甚至能進一步解決人類的困境”*渡也:《沒有喜悅的創作》,《臺灣的傷口》,臺北:月房子出版社1995年,第95頁。。其詠史詩的創作也就出現在詩人的興奮點“由內向外轉”以后,話語修辭也從隱喻修辭中逃脫出來,而進入了轉喻和反諷階段。僅就詠史詩而言,以1994年出版的詩集《不準破裂》為標志,后來的詩歌話語愈來愈顯示出反諷的氣質。
修辭中有四格:隱喻、提喻、轉喻、反諷。“任何一個修辭格否定了其余三者,而反諷是總體上否定后的上升。隱喻(異之同)→提喻(分之合)→轉喻(同之異)→反諷(合之分)。”*趙毅衡:《反諷:表意形式的演化與新生》,《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但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上來說,渡也詠史詩話語中的隱喻、轉喻和反諷都是難以徹底割裂開的,它們甚至在同一首詩中都是交融在一起的,存在著張力關系。渡也詠史詩的話語修辭之所以顯示出不同的修辭類型,出現向反諷的轉向,這與臺灣文學場域的變遷、歷史語境的變化以及詩歌主體性的流動等內外諸多因素都有關系。渡也詩歌的風格越來越傾向于反諷,這一方面反映出他對歷史、現實和人性的認識越來越深透和辯證,看清了世界的反諷本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渡也詩藝更加成熟和豐富;同時也折射出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特征。
History as Rhetoric:On the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by Mr. Duye
Yang Xue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rhetoric, the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by Mr. Duye are to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the metonymic, the metaphoric, and the ironic. The metonymic is further to be divided into the deep metaphorically metonymic and the surface metaphorically metonymic. Within the former, metonymy is dominant in the surface discourse, and the deep archetype and the surface narration come into a relationship of metaphor; while, within the latter, certain stanzas or images are highlighted and gain a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come into a relationship of metaphor with the poem. The metaphoric consists of the analogically metaphoric and the personified metaphoric. The discourse of irony and that of metaphor both bear their dual meaning respectively, but, while metaphor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its two-fold meaning, irony lays stress upon the antagonism between its two layers of meaning. A lot of methods are employed by Duye in writing poems of irony, such as that of parole, of parlance, of structure, and of parody. For, poetic rhetoric aims at meaning construction, so Duye has created a wealth of meaning by making use of many sorts of discourse rhetoric.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history; irony; metonymy; metaphor
2015-02-12
楊學民(1963—),男,山東陽谷人,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教授,博士。
I227.3
A
1001-5973(2015)02-0017-12
責任編輯:孫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