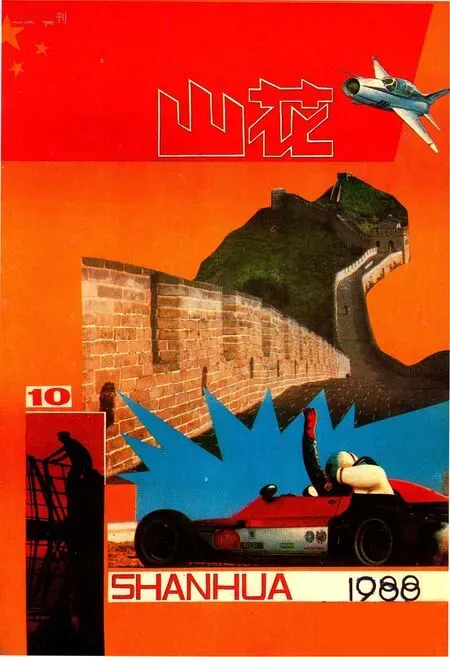嚴歌苓長篇小說的史詩性品格發微
周巖
“史詩”有著復雜的內涵,它源自于西方,隨著歷史的發展,史詩這一概念已經超越原本的題材和體裁的界定。而“史詩性”作為一種審美范式,也逐漸成為評價長篇小說的一種審美標準。“史詩就是史、思、詩的統一,即史的真實性、思的深邃性和詩的感染力的統一。”[1]嚴歌苓是享譽世界文壇的華人作家,她的作品無論是對中西方文化的獨特闡釋,還是對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審視,都折射出復雜的人性和深沉的哲思。她的《雌性的草地》《扶桑》《人寰》《小姨多鶴》《陸犯焉識》《一個女人的史詩》等多部長篇小說等更因其個人氣質呈現出獨特的史詩性品格。
對歷史真實的呈現
歷史是一種無言的存在。“人的生存與發展,主要不是在純粹自然性的環境中展開的,而是在人化的自然環境與人類在歷史的發展中所創造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展開的。這就意味著人的存在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及其產生的可能性的影響,其復雜性遠非動物所能企及。”[2]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都有特定的歷史的真實背景,在濃郁的歷史性的線條書寫中給人物的活動提供了真實的背景,時間和空間的跨度極大。《雌性的草地》講述的是“文革”動亂年代,《扶桑》書寫近代海外華人的血淚史,《人寰》關注的是“反右”和“文革”的歷史,《一個女人的史詩》跨越解放戰爭、“反右”、“文革”及“文革”結束后的歷史,《陸犯焉識》涉及“文革”前后幾十年,《小姨多鶴》歷經抗戰勝利到改革開放。
我們不難發現,“文革”的歷史在其筆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為“文革”親歷者的嚴歌苓,童年時代的記憶成為心中不可抹殺的印痕。在“文革”歷史淡出現代人的視野時,她不厭其煩地用她細膩的筆觸撫摸著這道印痕。《雌性的草地》在激情燃燒的“文革”歲月里,一群年輕的姑娘被放逐于中國西北荒涼草原上的一個軍馬場,小說以小點兒的視角來表現女子牧馬班這一女性集體在特定時代中的人性的荒誕。羞于告人而又終于大聲宣布私生子的柯丹,永遠留在草地上的17歲的女紅軍,那個吹著口哨的開康拜因的女墾荒隊員。歷史將獻身的機遇給了她們,她們以肉體與靈魂為代價,捧上了所謂“理想”的祭壇。而這一“理想”,最終被認清為罪惡。她們雖年輕,卻有著“終將殉道的先兆”。
《人寰》中父親同賀叔叔存在奇妙的朋友關系:父親是知識分子,賀叔叔是農民出身,他們的生活本不存在交集。然而賀叔叔在“反右”運動中保護了父親,父親耗費半生精力為賀叔叔寫書;“文革”中父親打了賀叔叔一個耳光,賀叔叔的寬容使父親內心愧疚,從而更把為賀叔叔寫書作為唯一追求。在女孩眼中,賀叔叔是特定的時代理想的化身和特定的政治審美情趣集于一身的英雄人物。強烈的政治氣候使女孩過早成熟,女孩對賀叔叔的模糊而曖昧的情源于對他的恨。小說講述的非正常年代的人們的非正常的情感糾葛,揭示了一定時期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對人的命運的無情戕害。
與傳統的傾力于謳歌與贊美的史詩性小說不同,嚴歌苓長篇小說中的歷史是想象與淡化的歷史,其講述的重點不在于歷史本身,而是再現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關系,于歷史的滄桑中演繹人物悲歡離合的人生,并為主人公的思想與行動提供某種可能。在嚴歌苓的小說中,歷史的存在有著特殊的意義,人物存在于歷史的大環境當中并與其發生一定的互動,有的是被動承受,有的是主動響應并試圖改變。歷史不再是被敘述的主體,它只是一個舞臺,是小說中被邊緣化的角色。歷史“因為它不再可被直接感知,所以只能被想象而不是被簡單地提及或論斷”。[3]她沒有對歷史進行強烈的政治反思和批判,這滲透的是嚴歌苓對宏大的歷史敘事的解構和深沉的政治意識的疏離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獨特的審美觀照。
嚴歌苓雖然長期旅居海外,但是中國歷史對于她是不可回避的存在。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她對中國歷史感受更深刻。她的長篇小說中的“中國記憶”展示和對中國歷史的書寫也是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尋,體現了難以釋懷的家園情結和文化鄉愁。經歷過非常的文化、人生的放逐和心靈的震蕩之后,嚴歌苓不再惆悵、彷徨,更多的是淡定和從容,既是反觀中國歷史,也是感悟人生。“文學與歷史學質上全新的結合將成為21世紀智力生活的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4]嚴歌苓長篇小說中文學與歷史的結合有利于華文文學審美價值的提高,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
對人生終極價值的思索
嚴歌苓在反映中國歷史風貌及發展趨勢的同時,超越現實的時空界限,將她的筆觸由歷史范疇延伸到人類的精神層面。傳統的恢宏的歷史敘事悄然隱退,“人”得以真切的還原。嚴歌苓的長篇小說是一個跨文化的生命對人生的參悟。在她的字里行間,那種對人生意義和終極價值的艱難追尋,那種對人生根本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諱的揭示,如同一個哲人的睿智,閃爍著生命哲學的光芒。
《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馬班的行為雖然是荒誕而可笑的,但她們尊重并承認自己的價值存在,她們曾有的對夢想的追逐和對青春的留戀是圣潔的。嚴歌苓為她們已逝的花樣年華唱出一曲凄婉的悲歌。“人的生命有著另一種存在方式;人的生命在超越有限生命之后才獲得無限存在。總有一天人們會認清,肉體實際上是束縛了生命,只是生命短暫的寄存處,而不死的精神是生命的無限延續,是永恒。恰如星辰隕落卻將光留在宇宙。那光便是星的升華的存在。”[5]
《一個女人的史詩》是一部女性成長的史詩。中國當代小說中不乏對女性成長的關注,如楊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就是由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崇高的無產階級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熱情的青年革命者的典型,她的成長代表著那個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走過的一條曲折艱難的道路。與之不同,在《一個女人的史詩》中,愛情成為貫穿近半個世紀、數個不同年代的唯一主題。部隊女演員田蘇菲具有相互交織的雙重身份:革命女性身份和世俗女性身份。在波瀾壯闊的時代回望中,嚴歌苓運用濃郁的溫情筆墨書寫的是田蘇菲作為一位世俗女性追求并保衛愛情的故事。田蘇菲革命的初衷以及革命的過程失卻其特有的莊嚴與崇高,帶有鮮活的日常生活的色彩。歐陽萸的才貌雙全和憤世嫉俗使其甘愿一生堅守,無怨無悔。她為了保衛愛情,去郊區釣蛤蟆、給劇團書記送禮、在舞臺上忙碌。歐陽萸的不堪經歷和風流成性反而激發了田蘇菲對愛的癡狂。她對愛情的執著使她生命張揚、內心飽滿,煥發出個體生命和人性的熠熠光輝。《娘要嫁人》講述的是齊之芳與三位男性的愛情糾葛,身為消防員的丈夫在一次執行任務時意外身亡,留下三個年幼的孩子,芳子在希望找人分擔撫養孩子的艱辛和追求自己愛情的邊緣苦苦掙扎。她雖為有三個孩子的寡婦,卻并不想草草一生,她想得到的是完美的愛情。兩性之間真摯的愛情是圣潔的,當然也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愛情的最高境界是精神上的一致。年輕貌美的她與“右派”戴世亮的情是心有靈犀的,與老干部李茂才的情是平淡溫馨的,與肖虎的情是感人至深的。在齊之芳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了她對善良人性的尊崇和堅守,還看到了她對母親的社會身份的拷問。她沒有因為母親角色而放棄自己的女性身份,沒有因為滿足最基本的物質需求而遮蔽自己對情感的真切追求,沒有因為外界的惡語中傷與謠傳喪失對美好人性的展示。正是在這種人生的掙扎與追尋中使她在白發蒼蒼之際終獲圓滿的愛情。《娘要嫁人》正是通過齊之芳20余年的“嫁人”歷程,深刻地揭示出人類愛情理想的最高境界——精神世界的相通。
《陸犯焉識》中的陸焉識曾有留美經歷,精通四國語言,天資聰慧,風流倜儻。他敢于張揚自己對自由的追求,他渴望自由、害怕失去自由,為著足夠的自由,他逃離繼母為他安排的婚姻而留學美國,在抗戰期間與韓念痕相愛,在建國初期鋃鐺入獄。出獄后他原有的家庭已沒有他的位置,但他自愿在瑣碎、矛盾的家庭生活中盡心照顧失憶的妻子,完成了對自由靈魂的自我反芻與救贖。
正如《陸犯焉識》中的思考“活下去為什么?不跑為什么要活下去?”嚴歌苓小說中的形象似乎都很執著與固執,無論時代如何動蕩,歷史如何變遷,他們總有自己心中想要的東西,有著較強的自我意識。“逃離”與“追尋”是嚴歌苓小說中主人公的共同特征,“逃離”是為了“追尋”。嚴歌苓在其小說中并不追求主人公的人生的政治意義,在“政治”的底色上呈現出“繁華”與“蒼涼”無情轉換的歲月中個體的生命可能觸及的高度。嚴歌苓的小說之所以具有史詩品格,也正是源自于她對歷史文化和復雜人性的深刻透視,而非人物的政治性體現。她傾向于以個人為主體的歷史書寫,在歷史的變遷和人物的命運中折射出歷史的多層面和人性的多元性。
優雅的詩性展示
“詩性”主要指作品的藝術性而言,“史”與“詩”(藝術性、文學技巧)的結合。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多種敘事相互交織,語言細膩富有韻味。
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在敘事上往往是多元的。《雌性的草地》以近乎原生態的身體敘事與女性敘事剖析并闡釋對自然人性和女性生命的尊重。 沈紅霞的掙扎、老杜的變異、柯丹的母性展示、小點兒的美麗與邪惡,這種種敘述無不張揚著嚴歌苓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一個女人的史詩》融合了歷史敘事、女性敘事、人性敘事三種視角來書寫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田家四代女性雖然生存于不同年代,經歷過不同的時代流轉和世事變化,但她們的心性卻如此相通。這樣一個整體是嚴歌苓對中國女性原生態品質的完整表達。《娘要嫁人》所蘊藏的女性敘事、母性敘事、歷史敘事,展現出人性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以及嚴歌苓的理想追求。《陸犯焉識》家族敘事、歷史敘事、人性敘事交錯,以陸焉識個人的生活來展現歷史的豐饒,反思知識分子的情感世界、自我心理和人性的復雜。無論采取何種敘事,嚴歌苓始終站在人性的高度對待其小說中的人和事,于理性地審視和平靜的敘事之中流淌著無盡的激情。
嚴歌苓長篇小說的語言美麗含蓄、耐人尋味,既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又留給讀者拓展想象的空間。異質文化的碰撞使嚴歌苓深愛中國文字的魅力,在中國文字中自由穿梭。《娘要嫁人》中的齊之芳經歷喪夫之痛后,“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由柴、米、油、鹽、醬、醋、茶組成的瑣碎現實人生,終讓齊之芳在不知不覺間,將往昔和丈夫之間種種舉案齊眉的恩愛記憶塵封在了心底一角。”“就在齊之芳跟肖虎之間的曖昧感覺逐漸升溫之時,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十年亦不知不覺地降臨人間。”[6]嚴歌苓不經意的語言將故事的情節加以延續,同時也蘊含著對語言背后的文化意識的回歸。《小姨多鶴》的語言有一股縈繞至終的原始的誘惑力。“小環的圓臉上總掛著兩個潮紅的腮幫,一對微腫的單眼皮,把很密的睫毛藏在里面,因此什么時候見她,她都是一副剛剛醒來的樣子。她嘴巴很厲害,但也特別愛笑,笑起來左腮上一顆酒窩,嘴角挑上去,露出一顆包著細細金邊的牙齒。”[7]簡單多趣的文字將這個伶牙俐齒、聰明能干、尖酸刻薄又善解人意的賢內助潑婦形象躍然紙上。
結 語
從舞蹈演員、軍人到旅美作家,嚴歌苓本人的經歷更像一部耐人尋味的長篇小說和電影。嚴歌苓的孜孜以求的嚴謹與不懈使她的長篇小說成為中國當代小說一抹沉靜而又耀眼的風景,嚴歌苓在其長篇小說中融現實主義的真實描繪與浪漫主義的文學想象于一體, 史、思、詩統一,其所具有的史詩性品格使其長篇小說充滿彈性與張力,有利于進一步豐富和深化當代文學的史詩寫作傳統。
參考文獻:
[1]王又平.反“史詩性”:文學轉型中的歷史敘述(上)[J].荊州師范學院學報,2001,(3):45-48.
[2]張治庫.生存與超越——人的存在與發展的文化性解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
[3][美]海登·懷特文.舊事重提:歷史編撰是藝術還是科學[A].書寫歷史[C].陳新譯.陳啟能,倪為國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25.
[4][俄]S.A.艾克什穆特.歷史與文學:“異化帶”[A].書寫歷史[C].賈澤林譯.陳啟能,倪為國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72.
[5]嚴歌苓.雌性的草地[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45.
[6]嚴歌苓.娘要嫁人[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56.
[7]嚴歌苓.小姨多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
作者簡介:
周 巖(1979— ),女,河南鶴壁人,文學碩士,鄭州旅游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