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揭秘(之三)
侯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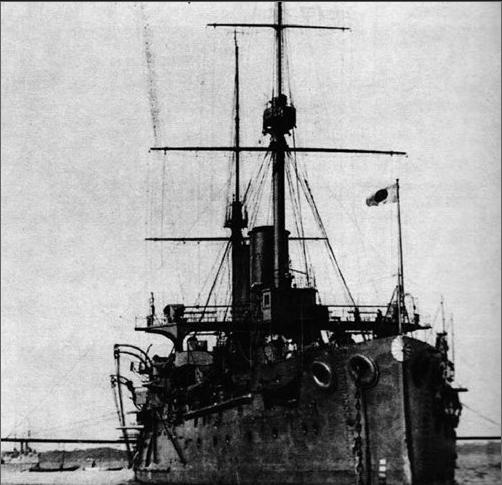
2014年元旦,日本華文媒體《新華僑報》發表《從一個甲午到另一個甲午的“危機”》,文章對中日圍繞釣魚島問題,持續了兩年的紛爭和摩擦,表示擔憂。文章聲稱,新的甲午年中日似乎又站到了戰爭的邊緣。
對中日在21世紀發生戰爭的擔憂,是一個普遍現象。國內外媒體,在整個2013年度,已經多次發表類似言論。
《新華僑報》的文章剛剛發表一個星期,國內媒體《環球時報》發表《打贏同日本的“輿論甲午戰爭”》,對日本外務省計劃邀請一百多名駐華記者訪日,向他們宣傳日本與中韓領土爭議立場一事,反應敏感,說“中日輿論戰看來面臨全面升級”。文章分析了日本在這次輿論戰中的目的,指出“日本會千方百計把中日沖突描繪成它同一個威脅世界的集權大國之間的斗爭,從而喚醒西方主流輿論對它的同情,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情結主導西方輿論界對中日沖突的態度”。文章提醒國內同行,要講大是大非,不作枝叉之爭,“緊緊咬住”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和他的歷史觀不放,抓住日本與德國對二戰態度的巨大區別不放,從而打贏這場“輿論甲午戰爭”。應該說,這篇文章的戰略視野比較開闊,提出的問題也切中要害。
說起來,這次中日間的輿論戰,從2012年4月,日本提出“購買”釣魚島的那一刻就打響了,幾經舌劍唇槍的較量,至今越發激烈。我們可以預言,以后還會更加激烈。至于何時偃旗息鼓,眼下很難估計。
《環球時報》的文章說,在這場輿論戰中,日本會以其豐富的輿論資源和技術優勢,同歐美社會進行溝通,爭取更多好感。還說,“日本做這些事的手段多、也更靈活。它的輿論引導能力、制造熱點能力都接近世界一流水平”。這段話讓我想到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戰爭中的輿論戰,日本就是以多種靈活的手段,以豐富的輿論資源同歐美社會進行溝通,成功地將大清帝國妖魔化,把那場戰爭渲染成文明對野蠻的戰爭,從而贏得全世界的普遍好感。而大清帝國,在輿論戰場上,時時處處被動挨打,毫無還手之力,比軍事戰場敗得更慘。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應該銘記這一慘痛教訓。
當年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已經認識到輿論戰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利用媒體攻勢取得國際輿論的支持,等于拿下戰爭一半的勝利。而大清國的棟梁之才李鴻章,對此毫無認知,等于先把一半的勝利,拱手讓給日本。
宗澤亞先生在《清日戰爭》一書中說:“清日戰爭作為近代戰爭所表現出的一大特征,是重視媒體對戰爭的作用。通過媒體向國際社會陳述自國的戰爭立場,求得列強支持。媒體成為作戰國主張戰爭合法性和為戰爭行為狡辯的重要工具。”嚴格說來,這個總結,只是針對日本一方而言。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大清的輿論,別說主動出擊,連“防御”的能力都沒有。所以,我對那場“甲午輿論戰爭”的梳理,只能取名為“日本的輿論戰略”。
現在,我們來看看日本的輿論戰略是如何展開的。
三個層面的攻勢
讓人郁悶的是,從中日雙方宣戰的那一刻起,日本就占據了輿論的制高點,從此一直居高臨下,直到戰爭結束。
日本的輿論攻勢,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宣戰書,二是外交戰略,三是媒體戰略。
先說宣戰書。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與大清北洋艦隊,在朝鮮豐島海面打了一場遭遇戰,嚴格說是日本不宣而戰。李鴻章于7月28日致電總理衙門,說日本先開戰這事,咱們得通知各國,讓他們都知道,不是大清去挑釁日本的。電文強調,朝鮮是大清藩屬國一事,“文內輕筆帶敘,斯我先派兵非無名”。這些都是實情,談不上擺弄手段。談得上擺弄手段的,是建議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暫停日本通商,日貨不準進口”。7月30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介紹了大清向朝鮮派兵和日本先行開戰的相關事宜,后說在這種情況下,大清“不得不暗籌決意辦法”,暗示要向日本宣戰。8月1日,光緒帝下旨宣戰,還是李鴻章的思路,大意是說,朝鮮是大清的藩屬國,前些日子出現內亂,俺大清派兵前去戡亂,這事跟日本沒關系,它不應該派兵,更不該不宣而戰,俺大清不能容忍這事,現在決定打它個小倭。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這份宣戰書影響到后來的主流教科書,對甲午戰爭的起因,沿用的還是這種解釋。當時的清廷,更是恪守這一“中央精神”。
日本對大清的宣戰書,前后經過六次重大修改,字斟句酌,其中第三、四、五稿,都包含對朝鮮宣戰內容,鑒于朝鮮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將日軍進攻朝鮮王宮一事,解釋為兩國士兵間的摩擦,是偶然事件,才在第六稿刪去對朝鮮宣戰內容。現在史學家公認說兩國是同日宣戰,這與事實略有出入。真實的情況是,7月31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向各國公使遞交日清戰爭通告書,實際上就是宣戰書。8月1日,宣戰書內容在內閣引發爭議,不斷進行修改。8月2日,內閣通過宣戰詔書議案,呈請天皇簽發。9月10日,內閣通過決議,日清戰爭開戰日為1894年7月25日,宣戰日為1894年8月1日。這就是所謂“同日宣戰”的歷史依據。
明治天皇的宣戰書說:“朝鮮乃帝國首先啟發使就與列國為伍之獨立國,而清國每稱朝鮮為屬邦,干涉其內政……朕依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使朝鮮永免禍亂,得保將來治安,欲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國,以協同從事,清國反設辭拒絕。”等于說日本師出有名,為的是推動朝鮮獨立,維護朝鮮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清國染指,這也是為東亞和平盡力盡責。
史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兩份宣戰書,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日本的宣戰書,更勝一籌,占領了道義高地。這樣說不算錯,只是過于籠統。我的看法是,日本提出朝鮮獨立問題,撓到了西方各國的癢癢肉,讓它們感覺很舒服。大清這邊,從李鴻章到總理衙門,再到光緒帝,都在意淫,以為西方各國默許大清跟朝鮮的藩屬關系。真實的情況,是日本跳著腳反對,美國也給大清施加壓力,提出讓朝鮮獨立,其他各國跟朝鮮簽約時,對藩屬關系不置一詞,實質上存有腹誹。何況那時候,大清跟越南的藩屬關系,因中法戰爭之敗,已經土崩瓦解。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呼吁,自然更能喚起西方的共鳴。
再說外交戰略。
在輿論戰方面,大清談不上有外交戰略,還是一如既往,就事論事,給各國公使發個照會之類。可笑的是,當時大清駐各國的外交官,絕大多數不懂外語,英語、法語、德語,管你什么語,咱不會說,更聽不懂,愛咋的咋的。更可笑的是,大清駐美國公使楊儒,把精力都用在美國國務卿葛禮山的老婆孩子身上,經常“親密接觸”,送點小禮品啥的,利用“枕邊風”進行外交,化公為私。
日本則完全相反,奉行積極外交策略,駐各國外交官,都精通所在國語言,有些口語較差,但可以運用當地語言寫作,達到報刊發表水平。其中兩位外交官更是表現出色。一個是駐英國和德國公使青木周藏,另一個是駐美國公使栗野慎一郎。青木戰前擔任外相,戰爭爆發后,“下放”到歐洲。他的主要任務,是把歐洲輿論控制在有利于日本的范圍內。青木在化解“高升號”外交危機上,有過出色表現。栗野是哈佛大學畢業生,英語不在話下,外交手段也非常健朗。他的做法跟大清駐美國公使楊儒形成鮮明對比。為達到本國外交目的,栗野天天去美國國務卿葛禮山辦公室拜訪,暢談國際事務,從“公誼”入手,表達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把葛禮山對大清的好感削掉了很多。此外,他還經常組織外交人員和學者,為美國報刊撰稿,闡釋日本所作所為的“合法性”以及大清對東亞和平的威脅等等。(據雪珥先生吐槽,他翻遍甲午戰爭期間《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西方所有大報,沒看到一篇大清官方或個人發表的文章。)青木和栗野更突出的貢獻,是聯手促成日本政府和軍方允許外國武官隨軍觀戰,同意西方媒體隨軍采訪,此舉讓戰爭期間日本的形象得到彰顯。而大清不僅拒絕西方媒體隨軍采訪請求,作戰中,清軍還把兩個迷路的西方記者砍了頭,鬧出不少丑聞。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媒體戰略。
在軍事上,日本早在戰爭爆發之前的6月5日,就成立了戰時大本營。在輿論戰方面,也同樣設立了“總指揮部”。也是在公開宣戰之前,日本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記者豪斯,擔任媒體戰的“總指揮”。這豪斯是個搞宣傳的行家里手,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的策劃下,戰爭初期,美國報刊發出的聲音,絕大多數有利于日本,塑造了日本的“文明”形象。
《清日戰爭》說中日甲午之戰,“是在國際社會的注目和監督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帶有濃厚的新聞色彩,透明度較高”。還說“媒體的近代化,推進了戰爭的明朗化,引導國際社會知曉和理解戰爭”。這個分析是中肯的。這個現象的出現,完全是源自日本對媒體的高度重視。而日本運用、利用媒體的柔軟手段,更是為日本的形象錦上添花。
當時,大清的主要媒體,影響比較大的有《申江新報》(也稱《申報》)《萬國公報》《字林滬報》《上海新聞畫報》《點石齋畫報》等,不超過十家,還都是外資創辦。由于清政府對媒體的種種限制,不能派記者隨軍采訪等等原因,媒體根本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轉載外國報紙的報道,做外國報紙的傳聲筒,再就是把小道消息或者前線故意的虛報,當作事實大肆宣揚,頻頻搞笑。當時日本國內的媒體,有《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讀賣新聞》《中央新聞》等六十六家之多,派遣一百一十四名記者、十一名畫師、四名攝影師隨軍采訪;批準外國媒體《紐約世界》《倫敦時報》《黑白畫報》等大報記者十七人隨軍采訪。除了媒體,軍方也派出自己的攝影師隊伍,組成寫真班,戰后出版《日清戰爭寫真帖》三大冊。這些照片現在有好多出現在網絡上,對了解甲午戰爭以及晚清社會,都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雪珥在《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中介紹,當時的日本媒體,引進了西方觀念和運作方式,被稱作“第四種權力”,相對獨立,不受政府任意干涉。相反,媒體對政府行為,有時能形成巨大制衡,可以批評政府的某些做法“因循誤事”。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國民新聞》竟然揚言,要是政府向清國屈服,“國民將趨于反動,乃至大大地反動,而且也將使國民的輿論沸騰起來”。就是這樣的獨立媒體,戰爭期間,卻能主動配合政府,美化戰爭,美化日軍,有效地凝聚了日本的民心士氣,顯得特別“主旋律”。
有意思的是,大清的新聞媒體,盡管是外資創辦,在戰爭期間,也是特別“主旋律”,自覺過濾素材,對大清不利的事情咱不報,對大清有利的事情咱使勁報,有時用力過猛,對日本極盡諷刺挖苦。比如,北洋艦隊舊艦操江號被日軍俘獲后再利用,《申報》《字林滬報》等先后發文,說什么日本把“既小且舊,為中國所不甚愛惜”的破船當寶貝,還為這等小事奉告祖先,是“言詞夸誕欺及先人”云云。這等諷刺挖苦,今日讀來,心中別有滋味。
李鴻章在戰后出訪美國,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中國辦有報紙,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這是實情。不過,李鴻章不提清政府對報紙的嚴加管制,只把棍子打到報紙的屁股上,也著實有點冤枉。
關于戰爭的西方言論
延至今日,國內史學界一致認為,甲午戰爭是一場由日本發動的,對大清的侵略戰爭。當時的日本媒體卻認定,那是一場文明之戰、解放之戰和救亡之戰。文明之戰指的是,先進文化戰勝了落后文化;解放之戰指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日本是來解放中國光復中原的,把滿清這個“蠻夷”趕走;救亡之戰指的是,日本必須先拯救中國,才能解救整個“中華”,讓黃種人團結起來,攜手對抗西方的壓迫。由宗方小太郎起草、日軍在大清國土上到處張貼的《開誠忠告十八省豪杰》,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當時的西方觀察家和媒體,對戰爭性質的判斷,跟大清的自我認定南轅北轍,而且偏向于日本的觀點,普遍認為,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尤其是美國媒體,親日傾向最為明顯,甚至把日本人稱作“東方美國佬”,或者東方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而把清國人看作“東方黑鬼和猶太人”。
我從相關史料里,抄錄部分西方觀察家、記者和主要媒體的言論,借此重溫那場對大清而言的輿論噩夢。
之一,《紐約先驅報》認為,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于整個世界,它一旦失敗,將令這一隱士之國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
之二,《舊金山檢查者報》發表社論,指責大清將朝鮮控制得如此死板,“這個可憐的國家似乎并不存在,它的一千萬人民的任何野心都會被輕輕撣去,這是中國的一個毫無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之三,《紐約世界》隨軍記者觀察報道,“日本軍隊擁有超出想象的諸多優秀之處,令我感慨備至。其一,他們是一支沉默的軍隊,部隊在行進中始終保持肅然寂靜,沒有奏樂、沒有旌旗招展、沒有喧嘩,組織井然、軍勢威嚴、沉默有序、疾行向前……其二,日軍不但擁有與歐洲諸國比肩的武器、器械、兵法、組織和統轄部隊的軍官,而且擁有完整的野戰醫院配置體系……其三,日本軍夫的膽量令人感嘆……其四,日軍縝密的作戰規范值得贊譽……”
之四,一個不知名的外國記者手記,“兩周前隨軍參加了平壤戰斗。日軍從漢城向平壤進軍,一路跋涉之艱難,文筆無法言表。沿途群邑的村鎮已經被清軍盡數掠奪,居民四散逃離,部隊向當地居民求食求水,竟然找不到一個人影。朝鮮山多,道路崎嶇,部隊所到之處常常是人跡罕見的未開墾地。武器、彈藥、輜重由隨軍的軍夫搬運,過山開路、渡河架橋,憑借馬背和人力把重武器運往前線,士卒們克服疲勞和艱難,生氣勃勃到達平壤。這是一支英武的軍隊,服裝端正、紀律嚴明、武器精銳。經過辛酸跋涉之苦,沒有挫傷他們戰斗的勇氣,在平壤激戰中表現出無畏的武士精神。”
之五,《泰晤士報》發表言論說:“日本的軍功不愧享受戰勝者的榮譽,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認日本為東方一個方興未艾的勢力,英國人對于這個彼此利害大體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興島國人民,不可絲毫懷有嫉妒之意。”
之六,英國隨軍觀戰武官尹庫魯說:“黃海海戰是特拉法加大海戰以來,全球范圍內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海戰。這場海戰對于海軍學生而言,顯然可以獲得諸多教益。清國海軍不出外洋,沿著近海游弋是敗戰的主要原因。”
之七,某外國武官評價旅順戰役,說:“此間聽聞旅順口戰斗中,許多關于清軍怯懦表現的報告,實令我難以置信。清軍最終沒有堅守自己的陣地與日軍戰斗到底,從清軍在陣地上留下極少的尸體數,可以證明這個事實……清軍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怯懦,戰局常常并非敗勢,兵士就會先行丟棄陣地和武器逃跑。旅順口作戰前的金州防御,亦見清軍怯懦之相。攻防當日,清軍金州防御兵力八千人,日軍兵力一千三百人,結果清軍防線不堪一擊,尚無多少傷亡便大舉遁退,還遭到日軍長距離的追擊驅散……日軍戰術規范,井然有序,在敵陣面前攻擊態勢嚴謹不亂,可見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
之八,法國記者卡雷斯考和拉露的觀察報道,“我們隨軍詳細觀察了日軍的作戰行動,得出日軍是世界上值得贊譽的強大軍隊的結論。榮城登陸作戰時,萬余兵卒和數千軍夫井然有序,完成龐大的登陸行動。我等上陸后,日軍已經展開安民行動,布告清國居民不要驚慌,日軍絕不騷擾民眾。近村的一民家大門上竟貼有‘此家有產婦,不要入內驚擾的日語大字條,著實令人嘆服……有一件印象深刻的戰地觀察,日本兵對勇猛抵抗的清國俘虜表現出仁厚的優待,對病人、負傷者給予人道的治療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愛心在這場戰爭中被展現給了世界。而清國軍隊之殘酷刑法令今人悚然,對日本俘虜斬首、斷肢、切睪,實乃野蠻人之行徑。”
之九,英國旅行家、游記作家伊絲貝拉女士手記,“清日戰爭爆發時,我正在清國滿洲旅行。宣戰后的形勢日趨險惡,清國各地人心惶惶。失去制海權的清國,赴朝軍隊不敢繼續在海上運送,只能從滿洲和朝鮮接壤的國境地帶通過。各路大軍經過奉天附近時,紀律渙散,每日有百十人竄入奉天城內,強搶民家財物,甚至升級到團伙掠奪。常聞清軍散兵半夜闖入小旅店無錢住宿,強行掠奪,令店內狼藉才棄之而去。清軍敗退后,日軍進入滿洲,軍隊紀律森嚴,工作秩序井然,毫無倨傲不遜之行為,旁觀者一目了然,肅然起敬。”
抄錄以上文字,從情感上說,對我是一種折磨;從理性上說,也讓我知道,大清之敗,是命中注定。一個處在中世紀的國家,跟一個近代國家交戰,勝敗毫無懸念。同時我也理解了,日軍為什么叫囂來一次“直隸會戰”,打到北京去。
最后我還想再引用一段伊絲貝拉的手記。這位英國女士,目光犀利,在當時就透視到大清戰敗的一個重要緣由。可嘆后世國內史家,對此大多置若罔聞。
伊絲貝拉說:“日清戰爭,日本成功地運用了近代宣傳媒體作為輔助戰爭的武器,在歐美國家之間巧妙進行政治公關,讓全世界相信日本對清國的戰爭,是拯救朝鮮于水深火熱、為朝鮮爭取獨立解放的文明戰爭。日本媒體的公關混淆了視聽,使日軍成為發動正義戰爭的一方。而清國孤陋寡聞,忍氣吞聲,全然不知應該運用媒體的作用揭露日本的謊言。”
化解輿論危機的手段
無論何事,主觀上的高度重視,并不意味在客觀上就不會遇到棘手問題。日本在輿論方面,就遇到過兩次大麻煩,說是危機,也不過分。一次是擊沉高升號商船,另一次是旅順大屠殺。
豐島之戰,日本軍艦浪速號擊沉英國商船高升號,激起英國媒體和軍方的強烈反應,憤怒譴責日本的暴行,強烈要求政府對這種侮辱和藐視英國國旗的行為進行報復。英國政府也照會日本公使,向日本提出嚴正抗議。在此情形之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對海軍的行為大加斥責。
對此次輿論危機的化解,日本主要采取的是外交手段。其外交手段非常靈活,先低調取守勢,然后高調轉守為攻,這兩手都取得絕佳效果。
先是向英方承諾,一旦查實是日方責任,日本政府會向英國賠償全部損失。這種表態,或多或少會緩解對方的激烈情緒。接著不斷向英方提交日本的“調查報告”,同時也向英國媒體和大清媒體提供信息,以混淆真相。
日本在外交上表現突出的,有兩位外交官,一位是駐英國公使青木周藏,另一位是日本駐英公使館聘用的德國籍法律顧問希伯特。
青木面對英國的官方壓力非常持重老道,一方面不斷重申日本政府先前的表態;另一方面,再三強調,“更加精確和完善的報告,會使事實逐漸澄清”。他提供給英國政府的相關文件,大多不是正式的照會,為自己的回旋留下足夠的余地。
希伯特的表現,更有可圈可點之處。他十分擅長從英國利益入手來說服英國。在中日開戰之前,他就向英國外交部遞交《在朝中日爭端備忘錄》,說“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家們不難理解,英日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在關系到雙方利益的時刻,應該把相互對立的問題或歷史問題放在次要的位置”。這段話意味深長。當時“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家們”,包括非外交家,普遍對大清抱有好感。
宗澤亞在《清日戰爭》一書中全文抄錄希伯特跟英國外交次長巴魯奇的一次會談。會談中,希伯特就每一個細節問題,為日本進行辯護,并且經常圍繞國際法展開討論。這次會談非常精彩。希伯特化解了巴魯奇的每一次指責,使巴魯奇的態度越來越趨于緩和。巴魯奇的結束語是:“英國政府對這件事,眼下不會采取任何處置方法。本官在拿出最終處理意見之前,不能不等待更充足、更詳細的報告。”史學家認為,這是英國政府淡化高升號事件并轉化態度的第一個信號。
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英國國際法領域的泰斗,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和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先后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認為日本軍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合法的。這兩篇文章對平息英國輿論的極端情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后日本緊緊抓住大清租用高升號的合同條款,以及事發前清軍已經“占領”高升號的說法,高調進行反擊,終于化險為夷,把賠償的責任推到大清頭上。可以想見,此時的日本媒體,也會群起鼓噪。
對旅順大屠殺的輿論危機,日本采取的是外交手段和媒體手段雙管齊下的方法,更多的是借助媒體的力量。
我想按時間順序,簡要敘述事件發生的過程,這會讓讀者對日本的反應速度和應對手段的變化,看得更清楚。
最早向外界披露旅順大屠殺真相的,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托馬斯·克溫。1894年11月30日,托馬斯從旅順來到日本后,約見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陳述旅順大屠殺事件,后又發出種種質問。會見結束后,陸奧立刻指示日本駐西方各國公使,密切關注所在國的輿論動向,收集媒體反映,迅速報告日本外務省。其實那時候,事件真相還沒有見報。
12月3日,托馬斯從日本發出的電訊在《泰晤士報》發表,電訊中,也包含了他與陸奧談話的內容。這篇電訊并沒有引起太大反響。
12月12日,美國《紐約世界》記者克里曼從日本發回的電訊,在《紐約世界》發表。13日《紐約世界》以“日軍的殘虐行為”為題發表社評。針對正在美國上議院審查中的《日美條約改訂協議》,開始出現反對批準的言論。
12月15日,日本國內《時事新報》《日本》發表社論,對大屠殺行為進行辯解。陸奧向駐各國公使傳達應對這一事態的統一口徑,提示媒體不要操之過急,不要跟歐美媒體強硬對抗,必須講究策略。
12月16日,陸奧委托豪斯,給《紐約世界》送去日本的官方聲明,列出八條辯解理由。
12月17日,《紐約世界》頭版發表日本政府的聲明,同版發表多篇評論文章。其他媒體也轉載了日本政府的聲明。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的聲明表示歡迎。克里曼電訊的真實性受到質疑,《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批評克里曼的虛假報道。18日,美國上議院公開審議《日美條約改訂協議》,沒有一個議員提出異議。
12月19日,克里曼的旅順大屠殺長篇紀實寄達《紐約世界》編輯部。20日,《紐約世界》配上插圖,全文發表,大標題是“旅順大屠殺”。這一詳細報道,成為全美最轟動的新聞。歐洲各國媒體也相繼轉載。美國對日本的好感瞬間崩潰。
12月25日,日本政府再次發表聲明,為大屠殺做辯解,指責克里曼的報道是捏造的。
1895年元旦過后,在日本政府籌謀下,日本媒體對外媒報道進行全面反擊,把克里曼的長篇紀實,當作惡意誹謗來共同討伐。這次討伐一直延續到馬關和談、中日休戰才停止。
這個過程中,還有加拿大《旗幟》記者威利阿斯的報道和演說,也引起很大關注。一個日籍美國留學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責克里曼和威利阿斯。有史料揭示,日本當時收買《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等媒體,為日本作袒護之辯。
日本當然知道,僅僅依靠口水來扭轉形象是不可能的,還是化被動為主動更好。1895年2月12日,北洋艦隊投降,隨后日軍在威海表演了一場大型的“行為藝術”:給受傷清軍提供醫療服務,釋放所有俘虜,對自殺的北洋艦隊首領丁汝昌給予禮遇,準許北洋軍艦康濟號載運北洋高級軍官護送丁的靈柩離開威海。這些都是在西方記者和軍事觀察員的目光下表演的,通過媒體公開報道和私下傳播,大大扭轉了日本的形象。英國那個國際法泰斗胡蘭德,說這是日本作為成熟的文明國家的標志性事件。
可惡的是,在此期間,大清政府沒有發布一次正式聲明,好像旅順大屠殺跟它無關。大清媒體也只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有史家評論說,大清實際上是認同日本的戰爭行為,換個位置,它也會這么干。這充分說明,大清跟文明國家之間的距離,很遠很遠。說它野蠻,也不算苛責。
大清媒體的假新聞
大清媒體針對甲午戰爭的報道,有不少假新聞。究竟多少,難說。在我的閱讀范圍內,至少有四個比較大的假新聞。那些假新聞,無一例外,都被日本媒體拿去作為調侃譏諷的材料。
第一個假新聞,“豐島海戰大捷”。這是甲午戰爭的第一戰,小道消息說北洋艦隊擊沉了日本軍艦,弄得朝野一片亢奮,大談倭奴小國不堪一擊,各媒體爭相報道大捷新聞。《上海新聞畫報》煞有介事刊登《倭艦摧沉圖》,有聲有色描繪豐島戰事,說大清北洋艦隊的濟遠和廣乙等艦,與日本艦隊激戰,大敗日本艦隊。
第二個假新聞,“牙山大捷”。葉志超虛報戰果,朝廷得到消息,牙山之戰清軍大勝,媒體歡呼雀躍,紛紛報道。當時上海赫赫有名的媒體《點石齋畫報》發表一篇圖片報道《牙山大勝》,說:“牙山離海口不遠,向為華兵戍守之所,此次葉曙卿、聶功亭二軍門之督兵援高(即高麗)也,駐守期間,頗得形勢。乃倭人不知利害,突于六月二十五六等日,有倭奴之名亞希瑪者,聞中國六軍將到,深恐四面受敵無處逃生,遂率倭兵四千余人前來攻擊。時華兵僅二千余名,各奮神威,短兵相接,無不以一當十。鏖戰良久,我軍大獲勝仗,斬獲倭首二千余級,刃傷倭兵不計其數。倭兵官見勢不佳,急調占據韓京之兵回陣助戰,而兵鋒既挫,依然敗北而逃,倭兵死亡枕藉,滿目瘡痍,有自相踐踏者,有長跪祈求者,悲慘之形動人憐憫。華軍聲威大震,奏凱而回。是役也,我軍以少勝多傷亡無幾,而倭兵已死傷過半矣。若待厚集雄師大張撻伐,吾恐倭人皆不知死所矣!”我的天,太能吹了,還“各奮神威”呢,還“以一當十”呢,這比后世文學盛行一時的浪漫主義,還要浪漫百倍。
第三個假新聞,“平壤大捷”。這個假新聞跟“牙山大捷”如出一轍,不再詳述。可述的是,大清媒體的忽悠,竟然連累了英國的路透社。這家通訊社,素以快速報道和世界各地報刊廣為采用而聞名,這回不知犯了哪根神經,竟然采信大清媒體上的娛樂新聞“平壤大捷”。真相澄清之后,美國媒體不再輕信路透社,轉而依賴合眾社提供的新聞。
第四個假新聞,“大清抗日娘子軍”。這是得知清軍前線屢戰屢敗之后,上海坊間傳出的消息。還是那個《點石齋畫報》馬上跟進報道,圖文并茂,雷死人不償命。報道說,左寶貴戰死沙場之后,其遺孀“痛夫情切”“號召巾幗中之有須眉氣者”,組建一支娘子軍,要奔赴前線,“為夫報仇”。更八卦的是,報道還說這事驚動了紫禁城,光緒帝發話:“中國堂堂之上邦,滿朝文武,與左軍門報仇者何患無人。何必使婦人從軍,為外邦見笑耶?”
平心而論,大清媒體制造的假新聞,不應該由媒體承擔全部責任。連政府上下都聽信前線將領的信口雌黃,媒體又能怎么樣呢?媒體之過,只在于放大“謠言”。
我的猜測,當時的大清媒體,還會制造一個更大的假新聞,“黃海海戰大捷”。我的猜測有一個堅硬的理由,黃海海戰之后,北洋艦隊上奏清廷:“擊沉包括吉野號在內的數艘日艦,日本聯合艦隊已經失去海外作戰能力。”這玩笑開得太大了。清廷被這玩笑逗得非常開心,下旨嘉獎丁汝昌。海戰六天之后,英國遠東艦隊司令官拜訪李鴻章,告知日本聯合艦隊一艦未沉,受傷戰艦也已經修復,再次駛入清國近海尋求戰機。李鴻章聞言震驚不已,絕不相信。依正常思維,這六天當中,大清媒體能對此次“大捷”表示沉默么?
雪珥在《絕版甲午》中說:“假新聞對中國的形象造成進一步的傷害,美國《輿論》雜志對波士頓到舊金山的主要媒體編輯進行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日本贏得了普遍的尊重,并被多數人視為平等的文明國家。”
參考書目
1.《六十年來中國和日本》,王蕓生編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2.《清日戰爭》,宗澤亞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
3.《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澳大利亞〕雪珥著,文匯出版社,2009年。
4.《大東亞的沉沒:高升號事件的歷史解剖》,〔澳大利亞〕雪兒簡思著,中華書局,2008年。
(照片摘自《1904-1905,洋鏡頭里的日俄戰爭》,圖為朝日號戰艦)
責任編輯 鐵菁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