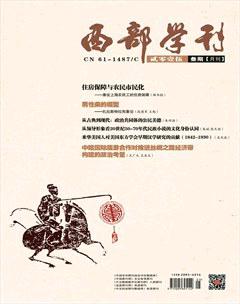詩性的追溯
摘要: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注重歷史的敘事功能,即賦予文本以統一性和融貫性,從而使研究對象得以解釋并被賦予意義。海登·懷特是敘事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在對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哲學著作進行研究后,他力圖揭示一種歷史想象的深層結構。他的思想并非無源之水,尤其是其歷史書寫理論極具結構主義風范的分析模式,借鑒了多位思想家的理論精華。本文旨在彰顯懷特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的形成軌跡,追溯其理論根源。
關鍵詞:海登·懷特;敘事;闡釋;結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歷史哲學發展至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敘事學轉向,意味著將研究對象定位在歷史著作上,懷特所提出的“元史學”實際上就是指稱一種敘事層面上的歷史。歷史著作在懷特看來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被發現的部分,也就是歷史事件;一是被建構的部分,就是史學家所應用的三種策略(情節化(倫理層面)、形式論證(認知層面)、意識形態蘊涵(倫理層面));一是詩性的比喻預構。他討論的重點是后面兩點,旨在探索史學著作中的詩性結構。懷特認為,在“元史學”中,敘事的理解和闡釋成分往往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消解了再現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或合理地解釋它何以如此發生的原因的權威性。他進一步分析出史學家應用三種解釋策略來達到解釋效果,每種解釋策略又有四種可能的演說模式,同時,四種比喻預構策略——隱喻、提喻、轉喻和反諷,與史學家在其著作中使用的種種解釋模式相互呼應,從而構成史學家的風格特征。盡管懷特的史學觀念驚世駭俗,幾乎改寫了歷史真實性的面目,但他的思想并非無源之水,尤其是其歷史書寫理論極具結構主義風范的分析模式,更是借鑒了多位思想家的理論精華。本文旨在彰顯懷特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的形成軌跡,追溯其理論的詩性根源。
一、歷史的闡釋——敘事主義的形成
首先要清楚的是,歷史通過書寫來傳達,那么歷史學家的寫作過程必然包含兩個步驟:去除史學家認為多余的歷史事實和填補歷史資料欠缺的空白部分。因為,歷史學家所能獲得的材料和文獻不是過多就是過少,這也就意味著它無法簡約闡釋成分。
懷特對歷史敘事性的論述首先集中在對歷史闡釋性的肯定上。闡釋不同于解釋,解釋傾向于強調歷史的客觀成分,而闡釋則更關注史學家的主觀因素,懷特認為二者相互對立。蘭克及其追隨者所進行的歷史解釋是尋求解釋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為文獻中報告的事件提供準確詳盡的重建,他們只描述歷史現象但不探究歷史何以如此的原因,壓抑闡釋的沖動,以盡可能的“客觀”精神對歷史進行再現。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對闡釋的排斥是激起懷特寫作《元史學》的關鍵因素。
一個歷史敘事不能全然由充分解釋構成,其中充斥著既定事實與假定事實。黑格爾、德羅伊森、尼采和克羅齊拒斥這種解釋觀念,他們把闡釋看作歷史修纂的靈魂,并且各自確立了四種闡釋模式。黑格爾區分了“原始性”歷史和“反思性”歷史,得出史學家本質上的詩性理解能夠被納入意識之中,并轉化成一種有關整體過程的喜劇式想象,他將這種反思性歷史修纂分為普遍的,實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德羅伊森明確指出,“歷史方法的本質是一種理解的研究,是闡釋。”[1]22他區分出了歷史書寫的四種可行的闡釋策略:因果的,條件的,心理的和倫理的。尼采堅持認為,歷史修纂中闡釋是必要的,這是由歷史學家所努力達到的那種“客觀性”所決定的。他在《歷史的使用與濫用》中提出四種再現歷史的方法:紀念的、古物收藏的、批判的和他自己所用的“超歷史的”方法。而克羅齊則提出四種不同的哲學立場:浪漫主義的、唯心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和批判的。
無論如何劃分,他們的一致認為,歷史學家本身參與了歷史敘事的建構。我們面對這種建構,需要將史學家的自身經驗與其所應用的闡釋策略區分開來。在《野性的思維》中,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指出,任何歷史敘事的形式一致性只含有一個“騙人的綱要”,這是歷史學家強加于大量材料之上的,這些材料只能在最廣延的意義上才能稱作“數據”。也就是說,歷史事件本身只是一些無序零散的材料,而史學家為了達到某種闡釋效果才構建了一種連續性。列維-斯特勞斯在這一建構中看到了歷史事實概念的二律背反——每一個“真實發生的事”都可以化解為“無數的個人時刻”。所以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歷史事實決不是“給予”歷史學家的,而是由歷史學家本人“借助抽象手法,仿佛在無限倒退的威脅之下”“建構”的。[2]70
至此,闡釋性已經成為歷史哲學中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解釋和闡釋并不體現主體與客體的分立。伽達默爾認為,“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不是一個客體,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一種正當的釋義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有效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歷史叫做效果歷史。理解本質上是一種效果歷史的關系。”[3]267伽達默爾所說的歷史理解正是歷史的闡釋性,他反對研究歷史的“科學客觀主義”態度,在他看來,歷史學家無法置身于歷史之外對其進行研究,理解者總是帶著某種成見去理解。而且,我們理解歷史的過程實際上也參與了歷史。同時,伽達默爾也反對黑格爾和狄爾泰等人的純粹主觀主義態度。他認為,“歷史先于我和我的反思”。[3]267所以,在伽達默爾眼中,歷史既不是客觀對象,也不是絕對精神和生命自我的體現,它是一種主客體的交融。“在一切理解中,都有這種效果歷史的力在起作用,無論我們意識到它還是沒有意識到它。”[3]268伽達默爾認為,理解就是與傳統對話的過程,同時由于傳統先于理解而存在,理解也受制于它。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將文本稱為“歷史流傳物”,目的是突出其歷史性。解釋者與文本之間存在歷史形成的時間與文化的距離,因此需要解釋。文本與解釋者構成了一種歷史流傳物與當代讀者之間的關系。歷史流傳物并不外在于解釋者,而是與解釋者不斷對話和交流的準主體。
伽達默爾對歷史文本的關注,以及他對歷史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討論實際上已經打破了歷史嚴格的學科限制。當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轉向歷史文本,歷史的闡釋性和文本化便凸顯出來,蘭克等人標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很難再成為歷史的先在屬性。懷特的歷史哲學便開始于這種對歷史的學科地位的質疑之上。
“懷特希望一種更理性地對概念屏障的顛覆,這與尼采的歷史和神話之間區別的‘隱喻式的抹殺相聯系,它可以提供一種方式——返回歷史與神話創造性地內部活動的思維方式。”[4]63懷特想要通過隱喻方式將理性與非理性、歷史與神話之間被科學實證方式切斷的聯系重新建立起來,就如懷特自己所說,“寫作歷史就不僅要接受理性的指導,而且要在‘與理性相關的最廣闊視野之下,運用歷史可能提供的與‘非理性相關的任何知識,在生活與藝術二者中促進理性的事業。”[5]69在歷史學科地位的探討中,歷史學家對歷史、科學和藝術之間關系的認識和處理與歷史主義危機的發生有著密切聯系,懷特思想的構建也需在澄清三者關系的基礎上進行。面對歷史學的危機,懷特認為,“這一代歷史學家所要完成的最棘手的任務就是揭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歷史學科的性質,率先消除歷史在各學科中的自治性,并幫助把歷史同化到一種更高級的知識探索之中,又由于這種知識探索是建立在對藝術與科學的共性而非差異的認識之上,因此可以正確地說,它既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2]35
二、歷史與詩的內在聯系——情節結構的形成
顯然,懷特對歷史的藝術性或者詩性的部分更感興趣。他想要重建的歷史與神話之間的聯系,在諾斯羅普·弗萊那里尋找到了最豐富的資源。懷特稱贊弗萊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自然文化歷史學家”,在《弗萊在當代文化研究中的位置》一文中,他聲稱“弗萊的文學理論對文化研究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動作用。”[6]29他也不諱言自己借鑒了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對文學情節結構的分類理論。在弗萊理論的基礎上,懷特找到了返回歷史的神話源頭的途徑,形成了自己的歷史書寫理論中的情節化模式理論。
歷史需要通過敘事呈現,歷史學家對過去的建構溝通了歷史與詩學之間無法抹殺的聯系。黑格爾將詩看作是對世界的隱喻式理解,歷史則是一種散文性表達。但是,“他將詩性意識本身歷史化了,并在歷史意識框架內把詩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從而將歷史與戲劇和詩歌緊密聯系起來,達到一種詩與戲劇的歷史化以及歷史的詩化和戲劇化。”[2]65維柯將文化研究置于隱喻理論的框架內,在一種“詩意邏輯”中發展起來,這給予歷史研究以重要啟示。維柯認為,用隱喻來表達陌生事物并對其進行分類,可以凸顯事物與詞語之間的張力。例如,一旦將雷與憤怒等同起來,其他事物就可以分有憤怒的某些特殊性質。由此可以得知,歷史學家在歷史敘事中應用隱喻表達便可對事物加以命名,從而獲得所需要的意義。
在這一點上,諾斯洛普·弗萊堅持認為,歷史學家不應該把一個結構強加在他的數據上,他必須“誘導地收集事實,努力避免道聽途說的結構,除非是他親眼所見或確信是他親眼所見的事實。”弗萊認為,一種歷史闡釋與一首詩的虛構一樣,可以說是作為對世界的合理再現而對讀者產生吸引力的,對那些“分類前的情節類型或原型的故事形式”具有隱含的吸引力,而這些類型或形式限定了特定文化的文學稟賦的形態。[7]162因此,歷史學家就與詩人沒有了本質區別,他們可以通過為歷史事件提供解釋的形式將意義類型嵌入敘事之中。
弗萊在榮格的原型理論基礎上,將原型的定義從心理學領域引入文學范疇,從而建立了以“文學原型”為核心范疇的原型批評理論。他在《批評的剖析》中認為,文學批評走向科學的途徑是建立“整體觀”意識,也就是重構那些已經失去的聯系之間的關系,比如藝術與科學。弗萊極力倡導對各類文學研究應著眼于它們相互關聯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體現了人類集體的文學想象。弗萊認為西方文學的敘事結構模仿了自然界循環運動。春、夏、秋、冬所形成的自然循環在弗萊看來可以與文學敘事的結構模式的四種基本類相對應:喜劇—春天的敘事結構,浪漫劇—夏天的敘事結構,悲劇—秋天的敘事結構,諷刺劇—冬天的敘事結構。這四種敘事結構模式從神話原型而來,再發展到以某一敘述為主,繼而轉化為喜劇、浪漫劇、悲劇、諷刺劇。等到現代劇出現,它表現出了“回歸”神話的趨勢。弗萊認為,這體現了一種文學發展的循環。
弗萊的思想可以引申出,歷史中的闡釋包括可以構建情節結構所需的各種成分,而歷史學家能夠通過對這些成分的編排,架構出特殊種類的故事,從而顯示該事件的性質。由此便可以從歷史學家的敘事中分辨出悲劇、喜劇、羅曼司和諷刺劇等不同形式。而這樣的架構也說明歷史學家在面對歷史材料的時候,他們所謂的發現實際上包含著對于情節的預期敘述。在歷史敘事中,故事之于情節,就如同對過去“所發生事件”的解釋之于對敘事中包含的整個序列時間的“意義”或“意指”進行的概括描寫。[8]30所以,按照弗萊所言,歷史著作至少有兩個闡釋層面:一個是歷史學家以編年史事件為基礎架構故事層面;另一個是歷史學家用基本敘事技巧循序漸進地講故事。
懷特正是從弗萊的小說理論中獲得歷史敘事所套用的情節結構模式,將其應用到自己的歷史詩學理論中。“順著諾斯羅普.弗萊在其《批評的剖析》(下文簡稱《剖析》)中指出的線索,我至少鑒別出四種不同的情節化模式: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5]9他認為,這些情節化模式也是史學家賦予歷史著作以美學意味的方式。懷特在分析19世紀歷史寫作中的四種存在論中,分別對米什萊、蘭克、托克維爾和布克哈特的史學著作進行剖析,指出他們如何應用情節化、形式化和意識形態化從歷史過程中獲取意義。米什萊將歷史過程視為一種本質上的美德對抗極端邪惡而進行的斗爭,根本上是一種自我認同,體現出了浪漫劇的特點;蘭克作為歷史主義的代表,將客觀性以及批判原則應用于解決歷史中的各種沖突使其獲得一個和諧的結局,因此也就形成了蘭克歷史著作中的喜劇性主題;托克維爾的著作具有一種悲劇內涵,他不允許自己相信歷史的普遍意義;在布克哈特那里,歷史陷入了反諷,代表著英雄時代和信奉英雄主義的能力的消逝。歷史充斥著憂郁,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希望。
三、結構主義“骨骼”與后結構主義精神
對懷特歷史哲學的詩性追溯,最終落實到語言問題上。從哲學領域興起的語言學轉向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語言學轉向起源于分析哲學,1955年,懷特在《分析的時代》的序言中這樣解釋使用分析哲學這個概念的原因:“在充分認識到任何標題的危險性之下,本書旨在簡要地記載這樣一個事實,即20世紀表明為把分析作為當務之急,這與哲學史上某些其他時期的龐大的、綜合的體系建立恰好相反。我認為有用的是抓住本世紀一個最強有力的趨勢來標志這個世紀,而不是去捕捉這一世紀的本質。”[9]5歷史與語言建立起密切關系來自結構主義,而懷特一直聲稱自己是一名結構主義者,主要原因就是他將歷史和語言的關系作為歷史事實建構的基礎。
懷特認為,結構主義分為兩個對立學派:“實際上,我們應該區分結構主義運動中的兩個派別:實證主義派,索緒爾、皮亞杰、哥爾德曼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屬于此派;末世學派,拉康、列維—斯特勞斯、巴特以及福柯本人屬于此派。”他還指出了這兩派的區別:“實證主義者方面一向注重意識結構的科學確定,憑此,人們形成他們對所居世界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他們構想與世界達成一致的實踐形態。他們的結構概念主要是(結構)功能主義的,或實用主義的。末世學派方面則關注意識結構用以真正遮蔽世界現實的方式,并且通過那種遮蔽(concealment)而有效地使人們在不同的,雖不說是相互排斥的話語、思想與行動世界中受到割裂的形態。”結構主義的實證主義派是整合性的和科學性的,而末世學派則是播散性的和反科學性的。[10]141懷特對歷史文本的詩性比喻結構的分析充分體現了其科學性的結構主義的一面。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話語的“轉向”上:“從一個組織層面向另一個組織層面的轉向,從序列的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轉向,從描述向分析或從分析向描述的轉向,從比喻向原由或從事件向事件的環境的轉向,在同一話語內部從一種體裁常規向另一種的轉向,等等。”[2]304懷特根據新古典修辭理論的四種基本轉義——隱喻(以相似性原則為基礎),換喻(以臨近性原則為基礎),提喻(以作為事物整體中各部分之間的同一性為基礎)和反諷(以對抗性為基礎),展現出歷史學家建構話語并轉義為書寫的基本模式。“歷史話語中包含的隱在的、二級的、內涵的意義是對構成其顯在內容的事件的闡釋。由歷史話語產生的這種闡釋賦予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序列事件以形式的連貫性,也就是虛構小說中情節結構的那種連貫性。”[2]301歷史書寫與文學共享的一個基本層面就是語言。
20世紀下半葉,法國和美國的文學批評從結構主義走向了后結構主義。巴特、德里達和福柯等人將后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引入歷史學。羅蘭·巴特在《歷史的話語》中提出問題,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在話語結構上是否不同。巴特的表述意圖很明顯,即歷史不是再現而是重建,它在本質上是想象的。德里達與福柯更是認為,人類陷入了語言的牢籠。
福柯的理論深深影響了懷特理論的建構,福柯認為話語的意義不源自歷史書寫者的意圖,而是來自文本所出的社會歷史結構,這樣話語就為文本與歷史搭起了橋梁,而話語的關鍵作用在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中舉足輕重。一方面,懷特的研究方法受到福柯知識考古學式研究的影響;另一方面,懷特也受到福柯話語權力理論的啟示:既觀照到語言學層面,也不忽視社會歷史領域。
福柯對人類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切入點是話語,即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和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體社會機制等的關系。福柯的話語理論又稱話語實踐理論。話語實踐特指社會中的具有權威性的主體以一種社會能夠普遍接受的方式言說的話,這些話明確要求社會承認其真理性。而福柯考察的重點不是這些話語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而是討論它們的言說方式以及它們在某時某地的出現有什么樣的意義。懷特將語言視作福柯著作中隱秘的主人公。因為,福柯極度唾棄再現真實性的目標,而是把這些再現的全部努力視為一種對語言本質的根本誤解的結果,世界并非可以毫無懸念地一一再現,而是如語言本身一樣,是不透明的,并存在神秘性。受這種考古學式研究方式的影響,懷特也將自身的研究從對歷史內容的探討上移開,轉向關注某一歷史時期的歷史話語的意義,關注歷史學家采用不同的書寫方式意味著什么。他不像實證主義歷史學家一樣挖掘歷史真相,反而更關心歷史學家是在什么樣的觀念指導下,采取何種策略進行歷史書寫。
福柯還認為,在歷史話語的表層與其深度之間權力悄然建立。福柯正是在消除這種差異的意愿中展開其思想的。他認為,哪里出現這種差別就證明哪里存在組織權力的作用,而且,這種差別本身便是權力所擁有的用來掩蓋其作用的最有力武器。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是話語分析的一種方法,對傳統的歷史決定論提出挑戰。歷史研究的復雜性不是因果律和邏輯關系可以概括的,這兩種思維模式容易造成滋長對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導致對人的主體性的盲目崇拜,掩蓋歷史與真實的關系。所以,他要考察的不是事物的本來面目,而是關于事物的話語如何形成。福柯的著作呈現出一種去中心化的形態,這是對傳統的語言透明性的批判。他說,他自己的話語“遠沒有確定它從中言說的基點,而是回避它據以發現支持的基礎。”它“要力圖實現一種非中心化,不給任何中心以特權……它不打算成為一種起源的回憶錄或真理的存儲器。相反,其任務是要制造不同……它不斷制造變異,它是一份診斷書。”[11]205福柯為什么要做這樣一種嘗試?他接著補充道,“為了表明,言說便是做某種事——某種不同于表達一個人所想的事;轉達一個人所知道的,而且是某種不同于玩弄一種語言結構的事。”[11]209話語遠比單純地作為反映“事實”的鏡子所能承擔的更多,隱藏在其背后的權力系統的運作始終被人們無批判地承接下來,而實際上,語言是不透明的,它沒有能力揭示主體。福柯致力于揭示蘊藏在各種區別中隱含的權力,他在《瘋癲與文明》、《詞與物》和《臨床醫學的誕生》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即是通過彌合“詞與物”的區分所造成的斷裂從而掌控話語的消解。這些書試圖證明,瘋癲與心智健全、疾病與健康以及真實與錯誤之間的區分始終是不同時期在社會權力中心占優勢地位的話語模式的一種功能。
福柯拒絕邏輯和傳統敘事,他否認西方思想中所標榜的連貫性。在他看來,歷史中存在著斷層,而連續性、一致性以及因果性都不過是人類理性的烏托邦構想。這也就意味著,在無序的歷史背后,主體發揮著能動地組織起零散事件并賦予其聯系的作用。“連續的歷史是一個關聯體,它對于主體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這個主體保證把歷史遺漏掉的一切歸還給歷史……,將歷史分析變成連續的話語,把人類的意識變成每一個變化和每一種實踐的原主體,這是統一思維系統的兩個方面。”[12]15
懷特的思想深受福柯影響,他在《元史學》中就指出歷史的無序性,而史學家就是通過四種比喻手段建立起歷史的連續性。而且,通過作為后結構主義者的福柯,懷特認識到了以語言為基礎同時超越語言的歷史重寫。作為現代語言,已經“遠不像經典結構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穩定。與其說它是一個定義明確而界限清晰的結構,其中包含著能指與所指組成的對稱單位,它現在開始更像是一張無邊無際的蔓延的網,其中各種成分不斷地交換和循環,其中沒有什么成分是可以被絕對規定下來的,其中每個東西都被所有其他東西牽扯和貫通。”[13]112
結語
實證主義史學所營造的歷史真實性幻象破滅之后,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都在積極探索一種人文學科研究的方法,懷特所提倡的元史學應運而生。他探討的目的不是如何確定歷史的真實性,而是在對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哲學著作進行研究后,揭示了一種歷史想象的深層結構。然而,懷特的史學觀念也因其相對主義傾向而飽受詬病,但是他的這一次叛逆絕不偶然,從其理論形成的軌跡以及史學發展總的脈絡來看,黑格爾、馬克思、尼采、福柯、弗萊等人都從正向或反向為元史學的誕生提供了靈感和思想助力,懷特具有后現代主義特色的歷史哲學正是在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尋找到了其詩性的故鄉。
參考文獻:
[1]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歷史知識理論[M].胡昌智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M].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3]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4]Frank Ankersmit, Ewa Domanska and Hans Kellner, Cultural Memory in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5]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M].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4.
[6]Hayden White,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ed. by A. A. Lee and R.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
[7]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8]Brian C. Fay and Richard T. Vann,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6.
[9]海登·懷特.分析的時代:20世紀的哲學家[M].杜任之譯.商務印書館,1985.
[10]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1]Michel Foucault ,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translated by A.M.Sheridan Smith,Pantheon books,New York,1972.
[12]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13]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
作者簡介:白春蘇(1985-),吉林四平人,南開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