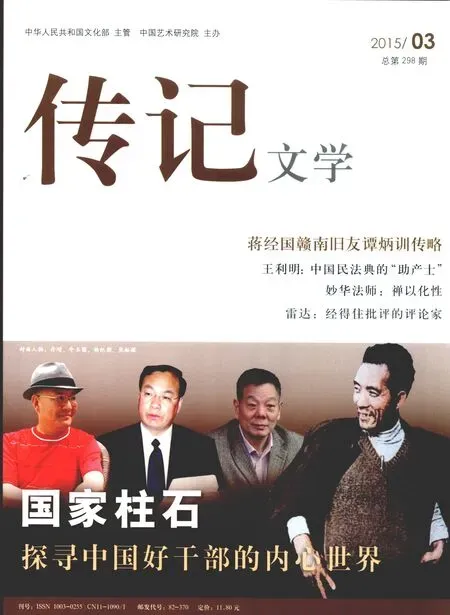焦裕祿的最后歲月
文 吳志菲
焦裕祿的最后歲月
文 吳志菲

當年心系災民,治水封沙,奈何天太無情,萬里黃河流濁淚;此日夢圓蘭考,豐林茂草,如是地能載德,一抔厚土護蒼生。
令人感慨的是,焦裕祿最后魂歸之處竟是曾經的黃河故道,而焦裕祿紀念園就建在黃河故道的河灘上。墓碑上有焦裕祿的照片,照片上焦裕祿的臉龐清瘦堅毅,眼睛凝視著遠方,仿佛要實踐自己臨終前的愿望:“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離家17年后的第一次探親
1964年元旦,蘭考縣委放假一天。焦裕祿卻沒有休息,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一頁連一頁地翻閱治“三害”資料。他的肝病已十分嚴重,瞞天瞞地但瞞不了他自己。早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之時,他的腹中便像開鍋似的翻攪、響動,這肝氣郁塞的癥狀,他卻用一根布條捆住了肋腹,以土法子壓迫病痛。那種辦法如今已經失靈,疼痛來自于肝部——右肋之下,他的壓迫止疼法也便改良,改用了秫秸稈、雞毛撣桿、鋼筆、鞋刷等硬物頂壓。
這天,他帶著剛剛翻閱完文件的新思考,騎著自行車來到了城關公社的韓村,找到6位有經驗的農民座談,檢驗自己的思考。之后,他來到村西南地搞起臺田試驗。
焦裕祿親自規劃,畫好邊,拿起鐵锨和大家一起挖了起來。挖了一會兒,火燒般的肝痛襲來。焦裕祿做出休息片刻的模樣,以锨桿頂住肝部,咬緊了牙關。但是,一切的掩飾動作都不能瞞住熟知他的人。大家一齊勸阻他不要再挖,要送他去看病。他做出輕描淡寫的樣子:“不要緊,咱們眼下吃點苦,受點累,挖掉窮根,子孫后代才有好日子過!”
挖了一晌,到午餐時,焦裕祿說回縣委有事,就騎著自行車走了。下午修臺田的社員剛到地里,焦裕祿又來了。直到天黑,把臺田樣板修好,他才高興地離去。以后,韓村群眾按照這塊樣板田,又修臺田100多畝,莊稼獲得了好收成。
身邊人這期間注意到:無論開會、作報告或聽匯報之時,焦裕祿總是右腳踏椅,抬高右膝,頂壓肝部。而且,他棉襖的第二、三個扣子總是不扣,以左手探入懷中,或握一支筆,或持一茶缸蓋、一根秫秸棍,硬硬抵住肝部。他坐椅右側的被頂出來的大洞,令人望而心痛。縣委和上級領導都很關心他,屢屢勸他住院治療,他都以一條聽來令人信服的理由硬生生地予以推辭:“病人最好不要住院,一住院,耳朵聽的眼睛見的都是病,人進到了病圈子里,輕病也轉重三分,倒不如堅持工作,工作的樂趣可以驅除疾病的痛苦,這樣對戰勝疾病反而有利。”
1月26日,焦裕祿在開封地委參加會議,肝病突然加重,以硬物頂肝的土法也失效了,疼得滿頭全是汗珠。地委領導命令他立即住院治療,他說:“年初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現在不能住院。”
一位有名的中醫為他開了個藥方,焦裕祿一看每服藥要花30元錢,嫌太貴沒有買。縣委的同志瞞著他取了三服藥,竟挨了他的批評:“蘭考是個災區,群眾的生活很苦,吃這么貴重的藥,誰咽得下去?”他執意不再買第四劑藥。
每到夜深人靜,焦裕祿拖著體力、精力透支的身子回家,把茶缸蓋悄悄藏入被窩,頂壓肝部的劇疼。疼痛實在難忍之時,他干脆穿衣起床,把煙嘴含在口中,點燃一支劣質的香煙。妻子徐俊雅知道,他又要工作了。
焦裕祿加夜班時,疼得難受就發狠地吸煙,常常將煙嘴咬碎。徐俊雅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你要是疼得厲害,我就找醫師給你打一針吧?”焦裕祿故作輕松道:“深更半夜的,吵醒人家不好,沒有多疼啊!”俊雅含了眼淚勸他:“你一天天瘦了,鐵打的人也要歇一歇。”焦裕祿淡淡地笑了,“反正睡不著,還不如做點事情,還能忘掉疼痛。這樣也好,工作的時間反倒多了……”
1941年,焦裕祿的父親因家貧又愁悶而上吊自殺,這時焦裕祿只有19歲。1955年,焦裕祿在他的干部檔案自傳中是這樣敘述他的母親的:“母親李氏63歲,住山東家種一畝地生活,完全依靠我和愛人工資。我除經常向家寄錢供母親生活外,母親農閑時有時也到我處住三兩個月。”
1963年農歷的年根兒,經上級黨組織批準,焦裕祿帶著妻子與兒女回山東省淄博市北崮山村探望老母親,這是他參加革命后離家17年的第一次探親。
臨行前,焦裕祿到蘭考縣政府大院找縣長程世平。程世平以為有什么大事要商量,便把他讓到了煤火爐旁,讓他暖和暖和。焦裕祿說:“老程啊!今年春節你打算回家過年嗎?你要是回家,我就值班看門。你要是不回去,你就值班看門。我已經好多年沒回山東家鄉看望老母親了,今年春節前打算領著老婆孩子回去一趟。”程世平說:“那你就準備準備回去吧!我沒打算回家,你放心地走吧!我看門。”
焦裕祿笑了,說:“那好。老程,我還有點小事兒,能借給我點錢嗎?三四百元就夠了。”程世平知道,焦裕祿夫婦平時省吃儉用,因為要贍養老人,撫育6個子女,有時還接濟窮困群眾,日子過得相當緊巴。可沒想到他一個十五級干部連回老家探親的路費也湊不夠。于是問:“不大夠吧?是不是多帶一點?”
“夠了夠了,連工資一共500多塊,足夠用的。錢,我回來就想法還給你,路上能節省的就節省了。”焦裕祿有些難為情。
爐火燒旺了,程世平因穿得厚,身上有點熱了。可他發現焦裕祿偎近火爐去烤火,身上還打哆嗦。程世平一驚,問道:“老焦,是不是又犯病了?”焦裕祿說:“沒有,就是有點冷。”
程世平知道他的肝疼時不時地發作,只是咬牙挺住,從來不吭一聲。于是,順手摸了摸他身上的衣服,又是一驚:“大冷天你穿個空心襖,怎能不冷?連件秋衣也不套,八面透風,還不凍壞了!”焦裕祿苦笑一下:“老程,咱沒衣服往里套啊!”
程世平說:“買布做一件嘛!”焦裕祿答:“沒布票,錢也緊,將就著過吧,許多群眾連棉衣也穿不上啊。”程世平說:“沒布票我給你找,無論如何也要做件內衣。不然,老娘見了心里啥滋味?”便硬拉著焦裕祿,冒著風雪來到了街上,買了一身價錢便宜的處理布。
就這樣,一家大小上路了。路上帶著饃,買碗開水都算計著。一路上,焦裕祿指著一塊塊烈士碑對孩子們講革命烈士的故事,教育孩子們要珍惜眼前的生活。徐俊雅這才明白焦裕祿把孩子全部帶回老家的良苦用心。
“我爸從蘭考買了些鹵豬肝、鹵豬耳朵啥的拿回老家。我奶奶還舍不得吃,拿著供在院子里的祭桌上。我兩個弟弟饞,就去偷著吃。”二女兒焦守云回憶道,“正月十五送花燈,奶奶把白蘿卜的頭兒削去,挖個坑,放上根棉花繩子,舀上些豆油,點著了滿家照照,石臺、磨盤、雞窩,旮旮旯旯的,說不招蟲子,照照小孩的眼睛,說看得遠,最后把花燈送到井邊的石頭縫里。”
山東博山的雪下得深,一家人團聚,老宅里的年味愈發濃厚。“那年雪很大,到大人的膝蓋那么深。博山過年的民俗很講究,從小年開始到正月十五,每天做啥都有安排。過大年,我們一家又都回去了,那就更熱鬧了。”焦守云難忘老家過年時的味道。
焦裕祿的侄媳婦趙心艾這樣回憶二叔最后一次探家時的情景:“見到二叔是在1964年,他一家人回來過年。那時候俺剛訂婚,見到他時都不敢說話。他很瘦,臉色難看得很。”
恰逢春節,按山東風俗,給剛訂婚的侄媳婦一些壓歲錢本是“在理”的事。被問及此,趙心艾卻不好意思地搓起手來,“俺娘家人說他二叔在外面當官,保證給個三五塊的壓歲錢。結果,一分錢都沒有,回娘家還落一頓笑話。”
其實,這個在蘭考當縣委書記的二叔,哪有富余出來的壓歲錢。快上門的侄媳婦不清楚自己的二叔全家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回家的路費盤纏都是賒借的。
村里人聽說有大官從外地回來,很多人都很好奇,紛紛到焦家爭睹大官的風采。可站在鄉親們眼前的大官卻讓人“大跌眼鏡”—— 回家過年的焦裕祿穿著一個很破舊的大衣,甚至在肩膀上還有個大補丁,下身穿著藍粗布褲子,腳上是勞動人民最尋常的膠鞋——這模樣,還不如村里普通村民穿得好呢。
大年初一,家家拜年。焦裕祿逐一拜訪在村里幼時的伙伴、一起吃苦受累的鄉親、并肩作戰的民兵戰友。在北崮山當過多年村支書的陳壬年在晚年還記得,焦裕祿“還沒進俺家大門,他就喊我。我看他穿著一件磨得發亮的大襖,還說他咋穿成這樣,他說咱們干活出力的不就是這樣”。陳壬年還說,“1953年,他在洛陽工廠里的時候,就給我寫信,讓我發展初級互助組,搞農業生產大聯合”。
焦裕祿對家鄉的一草一木有著深厚的感情。焦裕祿在陳壬年家坐了一個多鐘頭,給他提出兩條建議:一是抓封山造林,“咱北山上光禿禿的,得綠化綠化,在崮山上種些桃樹什么的,開了花也好看,有人會來參觀,村民們也有些收入”;二是抓水利,“可以讓各個生產隊挖幾個蓄水池,割完麥子種玉米的時候,挑水養苗不怕旱”。并鼓勵陳壬年說,“應該在村里發展副業,栽個桑樹養個蠶,40多天就摘繭”。
在崮山橋西頭,有一處北崮山村人極愛湊一起曬太陽的地方。“我爸在那兒跟鄉親們講一些外面的事。他說,再過不長時間,在崮山橋東頭的大槐樹上,架一個大喇叭,什么時候想聽戲,那里面都有。”焦守云回憶道。
“我爸身體那時候就不是很好了。你看他在梧桐樹底下照的那張照片,就缺一顆牙,所以他喜歡吃酥脆一點的煎餅,軟的太筋道,反而咬不動。”焦守云記憶中父親愛吃老家的煎餅,“我奶奶每次都是把煎餅放干了疊起來,去看我爸的時候帶上,能吃好長時間。有時候都長了一層薄薄的綠毛,他就拍拍再吃。”
“我記得老家的廚房沒有窗戶,天稍微晚一點就啥也看不見了。我奶奶在小油燈下,不是紡線就是攤煎餅、納鞋底,小油燈的燈頭兒在那跳啊跳。她是個熱心腸,針線活兒在十里八鄉都是出了名的。我爸的很多布鞋都是她親手做的。”焦守云回憶起奶奶時說,“她來看我們,回老家的時候,只要能拿得動,我爸總會給她捎上點白面。我爸可能覺得,老家生活不好,只有過年才有白面吃。”
村民王成茂在82歲高齡之時還依然清楚地記得1964年春節焦裕祿最后一次回到老家過年時的情景。王成茂說,鄉親們見他沒什么架子,聊著天就插科打諢取笑他:“你看看你穿的喲,怎么看都像是在油坊里干活的,說你是個大縣官誰信哩!”
在家鄉度假期間,焦裕祿曾率領全家老少,由侄子焦守忠帶路,來到了位于村西北角,岳陽山與崮山之山腳交匯的去處——焦家的老林地。在北風的呼號聲中,在松濤的低吟聲中,開始燒紙化錢,寄托對于父親、祖父、列祖列宗的哀思。焦裕祿指認一個個的墳頭,向妻子、兒女介紹著名字和與每人的血緣關系。告訴妻子兒女他們都是窮死的、苦死的,如果能有今天的日子,他們本不該在那樣的歲數病亡或自縊。對孩子們說:“你們知道爺爺是怎么死的嗎?是因為對生活無望而上吊死的。那時候,咱們全家吃的都是清水煮野菜。你們的大哥哥叫小連喜,也是在逃荒討飯路上死的……那孩子要是還活著,今年該有20歲,一個真正的山東大漢了……”
生命倒計時的忙碌與情懷
在老家待了半個月,返回蘭考后的焦裕祿工作起來還是一如既往地忘我。正如1964年3月14日他在縣常委生活會上講:“……在蘭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沒有說活一天就要干一天),但最苦惱的是自己身體不好,肝疼,扁桃體腫大,現在又多了個腿疼,工作搞不上去……生活上問題不大,春節回老家借了300塊錢,這個月可還100,爭取3個月還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時對下邊的同志批評不夠恰當……”
既然知道自己身體不好,為啥還不去看病啊,為啥還豁出命來干?!“他太清楚了,包括回老家,他都覺得是和他們永別去了。”焦守云說,“怎么樣治水,怎么樣治沙,蘭考的情況全部在他腦子里裝著,誰都不可以替代的,所以就這么玩命地干。”在焦守云的印象中,父親的心中只有群眾,他寧可自己累死,也不愿讓百姓餓死。
春節剛過不久,焦裕祿把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叫到辦公室,指著一份《人民日報》說:“你看,《人民日報》正在討論縣委領導班子思想革命化的問題,我看咱縣委決心領導群眾除掉‘三害’,就是思想革命化的一個具體表現,你到河南日報社匯報匯報,看看,能不能突出地報道一下,鼓鼓群眾的勁兒。”
于是,劉俊生找到河南日報社總編輯劉問世,向他詳細地介紹了蘭考除“三害”的情況和焦裕祿的建議,劉問世聽后當即表示:“我們商量一下,再向省委請示,再答復你們。”
10多天后,河南日報社把劉俊生召到鄭州。劉問世高興地告訴劉俊生:“省委領導同志認為你們縣的除‘三害’搞得很好,同意發蘭考縣一個專版。你回去,轉告縣委負責同志趕快組織人員撰寫文章,20天內把稿件送來。圍繞除‘三害’斗爭方面的,請縣委書記寫一篇文章,你們再寫一篇通訊、幾條消息,可以配發些照片、詩歌……把版面搞得活些……”
回到縣委,劉俊生向焦裕祿匯報了河南日報社的版面策劃。焦裕祿聽后,說:“好!這是省委對我們的關懷,這是報社對我們的鼓勵。我們要組織寫作力量,盡快地把材料整理好!”這時,劉俊生提出幾個骨干通訊員名單請他審定,焦裕祿看后隨即表示:“可以!現在就通告他們到縣委辦公室來開會。”
在焦裕祿主持下,召開了一個骨干通訊員會議。在會上,他作了一番鼓勵后,又讓劉俊生傳達了河南日報社發蘭考專版的具體意見。接著,幾位骨干通訊員各自認領寫作任務。最后,焦裕祿說:“縣委的文章,由我來寫。我想寫的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除掉‘三害’保豐收》。”他略停一陣后,隨即又說:“把題目改成《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吧!”
3月16日,縣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焦裕祿要同志們搞“四擺”——擺成績、擺變化、擺進步、擺好人好事。還搞“兩找”——找差距,找原因。搞“一樹”——樹各種標兵。搞“兩訂”——訂規劃,訂措施。在講到如何開展比、學、趕、幫活動時,他講道:“比,比1963年各項指標完成情況,比勤儉辦隊,比愛國,比奮發圖強,比自力更生,比收入,比鞏固集體主義,比共產主義風格,比實事求是。學,學先進思想,學生產管理,學技術革新,學‘三老’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趕,趕的目的就是比。幫,自愿結合,一個先進帶一個后進。”晚上,他通宵達旦寫材料。他仍然在與肝病“賭氣”:“你越怕它,它越欺負你。”
3月17日,焦裕祿出席公社黨委委員以上干部、縣直機關全體黨員會議。他講了三個問題:一、堅決糾正工作一般化現象;二、立即行動起來,全面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三、切實改進領導作風。講到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問題,他激動起來,越講越有勁。突然,他的肝部劇烈地疼痛起來,豆大的汗珠閃閃滾落。同志們都勸他休息一下,明天再講,他稍微停息了一下,疼痛一過,繼續講下去。
3月18日,焦裕祿召開縣委擴大會,主要研究生產救災、春耕生產、種植經濟作物等問題。最后研究了如何抓好典型問題,他列舉了大量的典型事例、典型單位和個人。大會開了一整天,焦裕祿十分激動、亢奮。
3月19日上午,縣委擴大繼續進行,研究了群眾生活安排和改進領導方法等問題,開封地委副書記延新文參加了會議。
延新文在會上講:“到蘭考后,下去看了4天,把你們縣的大部分地區都看了。總的印象是,蘭考正在變化,向好的方面變化。干勁大,信心足,不但有規劃,而且有行動。變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縣委領導思想比較明確,摸透了縣里的情況,下了決心,方法與措施都對頭,都具體。如壓沙,原來聽到了消息,總考慮行不行?壓了沙會不會再被風刮起來?下大雨會不會沖走水土?顧慮重重。這次看了,確實不錯,這條路走對了!”“蘭考縣委的同志很好,去年雖然困難很大,但在困難的情況下辦了很多事情。別的地方不敢干的事你們干了,效果很好。從去年看,你們的態度是積極的,沒有被困難嚇倒,大家的精神狀態很好。”“蘭考過去要飯的多,聞名全國,現在轉變過來了,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地委很注意你們的做法,并且大力推廣你們的經驗。”地委副書記的話,無疑對焦裕祿來蘭考的工作情況是一種肯定,與會者沒有想到這似乎在提前給這位鞠躬盡瘁的縣委書記在致美好的悼詞。
3月20日,焦裕祿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公社、縣直機關的干部調整問題。
3月21日,焦裕祿和縣委辦公室干部張思義騎自行車去三義寨公社檢查有關工作的落實情況。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后一次騎車下鄉。
焦裕祿看著路邊的每一行樹木、每一道溝渠、每一片莊稼,都露出愛戀的神情,像老人看著可愛的孩子。在一個上坡的地方,他實在蹬自行車上去不了,下車蹲在了地上,以手撫肝。張思義建議:“你的身體的確不行,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突然,焦裕祿站了起來,推起車子向前走去:“事情等著我們去辦!”他沒有更多的解釋。張思義語言直率:“焦書記,你的病很重了,萬一出了問題……蘭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焦裕祿聽后,笑了起來:“我一個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黨和36萬蘭考人民才是改變災區面貌的力量嘛!再說我這病,我就不信治不好!”
他們好不容易來到了三義寨公社,公社書記看到他臉色不對,氣色不佳,明知他病又犯了,卻不敢說病,只說不忙談工作,請他先休息一下。焦裕祿不容商量地道:“我不是來休息的,還是先談你們的情況吧!”
公社書記只得開始匯報。焦裕祿氣喘吁吁地記筆錄,字寫得歪歪扭扭,筆在手中掉下了幾次。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齊聲相勸。焦裕祿卻站起來,執意要到下邊去看看。
剛剛走出了大門,一陣強烈的疼痛襲來,幾乎使他昏倒在地。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回縣城治療。
可是,百忙中的他只要肝痛減緩,就要東奔西走,根本不能按時到醫院打針。為了不使治療過程中斷,醫院安排一位上下班經過縣委的護士順便為他打針。他又意識到這是享受了特權,待注射了兩次之后,他便堅決謝絕了這個“特殊照顧”。終于,這個忘我的人,這輛鋼鐵坦克的主機重創了,需要緊急救治。焦裕祿被強行送往醫院。醫生的診斷是客觀的:“病情嚴重,必須立即轉院治療。”
3月22日,縣委決定于當日12點鐘,派人護送焦裕祿去開封治病。但是,焦裕祿改變了這一日程,他詳細地部署了縣委的工作,找這個同志談談,找那個同志問問,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躺上了床,開始面對墻壁“過電影”,明天將要離開蘭考,是生離是死別他自有感覺。
在蘭考的最后一夜——在他肝疼難忍之時,在兒女熟睡、妻子準備入院諸物之時,再披衣而起,奮筆疾書。在把總題目《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寫于稿紙頂端之后,又列下了粗線條結構的4個小標題(或提要):一、設想不等于現實;二、一個落后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出來,先進的事物看不見;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
寫著寫著,肝又疼起來了,無論是茶缸蓋、雞毛撣、鋼筆管的頂壓都無濟于事,寫作實在無法繼續下去……
再說,有關《河南日報》的專版寫作任務落實后,大家都積極深入基層,開展了采訪和寫作活動。不多久,幾位通訊員把各自的稿件送到劉俊生手中。
3月23日上午,劉俊生得知焦書記要去外地治病。于是,拿著稿件趕到書記的辦公室——一是請焦書記再審閱一下所收上來的這些稿子,二是看他的文章寫好了沒有。
劉俊生走進他的辦公室時,只見焦裕祿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著一個茶杯頂著疼痛的肝部,右手執筆在寫文章。他見劉俊生來到跟前,放下手中的筆,側著身子對劉俊生說:“俊生呀!看樣子,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來越嚴重,肝部這一塊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劉俊生看著他那清瘦的臉色,望著他那因肝部陣痛時時顫抖的身體,又瞅見他為了壓迫止疼肝部在藤椅上頂出的那個大窟窿……為難地問:“那怎么辦?”焦裕祿交代說:“你先把寫好的稿子給河南日報社送去……我的文章讓張欽禮書記寫吧!”
劉俊生呆呆地望著桌子上鋪開的稿紙,上面寫著文章的題目《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下面有4個小標題(或提要)。劉俊生清楚,這篇文章凝結著焦書記的心血,充滿著焦書記對蘭考人民的無限熱愛。可是,焦書記剛剛開了個頭,病魔就硬逼著他放下了手中的筆。
當天,成群的蘭考縣委機關干部、群眾都來給外出治病的焦書記送行。焦裕祿謝絕了那輛美式舊吉普車護送,也謝絕了架子車、自行車的載送,而是氣喘吁吁地彎著腰,緩慢地走向火車站。他努力地揮揮手,勸同志們回去,不要遠送。
臨上車之前,焦裕祿把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叫到面前,以深沉的低聲一字一頓地說道:“除‘三害’是蘭考36萬人民的迫切要求,是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你一定要領導群眾做好!我看好病回來的時候,還要聽你全面匯報除‘三害’的進展情況呢!”卓興隆噙淚頻頻點頭。這一走,竟是永別。
將辦公室安在了醫院
很快,焦裕祿住進了開封醫院。人進了病房,心卻留在了蘭考,口中念叨、囑咐的仍是蘭考的除“三害”工作。醫生對病人負責,勸他既來之則安之,好生休息,好生養病。他苦笑了一下,說:“不行啊!蘭考是個災區,那里有許多工作在等著我,我怎能安心躺在這里休息呢?”
肝疼,腰也疼起來,于是烤電治療,烤得皮肉起了水泡。病情有了大致的診斷結果,地委領導決定,送他到鄭州的醫院再行診治。焦裕祿說什么也不愿意:“我的病沒有什么了不起,災區那樣窮,何必把錢花在這上頭?在這里診斷出病情以后,我還是回到蘭考去,可以一邊治療,一邊工作嘛!”
地委領導得知他的態度,多次派人到他床前,反復說明:“叫你去鄭州,是為了盡快地治好病,使你能更多地為災區人民服務。”他終于同意了組織上的決定。
進入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現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后,被診斷為“肝癌早期”。徐俊雅看到了這個診斷,如雷擊頂,焦裕祿察覺到了她神情的變化,笑著問她:“你怎么啦?”徐俊雅回答:“沒什么,只是想孩子了……”焦裕祿沒有再說話,他大概已經明白了一切,因為鄭州大醫院的醫生要他轉院到首都北京。
于是到了北京醫院,專家會診,專家剖開了他的腹部,確診結果觸目驚心,上面寫:“肝癌晚期,皮下擴散。”交給焦裕祿看的是虛擬的一份,上面寫:“慢性肝炎,注意休息。”他本人早有惡性病的判斷。專家搖頭表示:“只能采取保守療法,無能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還有20多天的時間……”這樣,焦裕祿又被送回到鄭州的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當年焦裕祿在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時,趙自民是河南醫學院醫療系的一名學生,正在醫院實習,他跟隨學習的醫生就是焦裕祿的主治醫生。那個時候,趙自民曾詢問過焦裕祿的病情,為焦裕祿做過病歷記錄。
“當時只知道他叫焦裕祿,是個干部。”50年后,趙自民回憶說,焦裕祿住院時,肝病已經很嚴重了,雖然身為縣委書記,但他為人和氣,當時住在大病房里,沒搞一點兒特殊。“我作為實習醫生,按照醫生的安排,問問病情,做做記錄,雖然只做了這些工作,但留下了永久的記憶。”
在鄭州住院時,來看望焦裕祿的人絡繹不絕。每次見面,他總是告訴同志們:“不要來看我,自己病了不能工作,花了國家的錢,還麻煩同志們看我。”“都不要來回跑了,耽誤工作,我心里很不安哪!”他似乎有問不完的話,多是問除“三害”工作的進展情況。他告訴護送他的縣統戰部負責同志,應該快一些回蘭考,向組織匯報他的病情,叫同志們團結一致,治服“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惦記著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趙家樓的莊稼淹了沒有,秦寨的鹽堿地上麥子長得怎么樣,老韓陵地里的泡桐樹栽了多少……5月4日,焦守鳳到鄭州探望病重中的父親,只見他嘴唇干裂,臉黃如紙,說話要用很大的力氣,仍然上氣不接下氣。
門外暴雨如注,疾箭般的雨點射在窗上。焦裕祿見到女兒的第一句話就是無限憂愁的念叨:“小梅,咱蘭考淹了沒有?你把咱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焦守鳳含淚搖頭。可是,他不相信,便勸徐俊雅回蘭考一趟,看看莊稼到底淹了沒有。
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時候,焦裕祿仍在努力學習,閱讀書報,也就一張報紙他也需間斷幾次才能看完。徐俊雅與護士都勸他多休息,不要看書報了,他總是說:“有病更應該學習,病人有了精神食糧,才能正確地對待疾病,戰勝疾病。”
就在焦裕祿病重期間,他看到除“三害”初見成效,勞動人民將要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曾激情滿懷地想接著寫完那篇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可是,這篇文章剛寫了一個開頭,他的病情就惡化了。焦裕祿對辦公室的同志交待說:“看樣子,我的文章寫不成了,讓張欽禮書記寫吧!他寫好稿子署他的名字也行,署俺倆的名字也行。”
5月初,劉俊生到河南日報社去送稿。一位編輯告訴劉俊生:“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個叫趙文選的打電話找你,說你們縣的縣委書記在那里住院,他找你有事叫你到那去一趟……”
當天,劉俊生趕到醫院,找到隨同焦裕祿治病的趙文選。趙文選告訴劉俊生:“焦書記讓我往河南日報社打電話,找你好幾次,他想問你些情況……”
劉俊生來到焦裕祿的病房,看到他半躺半坐地歪在病床上,瞇縫著眼。劉俊生輕輕地喊了一聲:“焦書記!”焦裕祿看到劉俊生來了,抬起放在胸前的手,指指凳子,示意讓劉俊生坐下。劉俊生看著焦裕祿蠟黃消瘦的面孔,看著他說話少氣無力的緩慢情景,很難過。一個多月不見面,焦書記怎么變成這個模樣?
焦裕祿說:“我想問問……咱縣除‘三害’斗爭那組稿子……報社發不發?”劉俊生回答:“這次,我到報社送稿,專門問了這件事。總編室的同志告訴我:‘蘭考的專版,暫時不發了’……”
焦裕祿同志問:“什么原因?”劉俊生說:“編輯告訴我——蘭考挪用了群眾的救災款,省里通報批評了你們。那邊,省委通報批評您,這邊,我們報社表揚您,太不協調。以后發不發由省委來定。”
焦裕祿聽后,表情凝滯,用低沉的聲調一句一停地說:“這說明,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好……發不發,這是省委的事,報社的事……發了,對我們是個鼓舞;不發,對我們是個鞭策……”
據縣長程世平回憶:“當年焦書記動用救災款買代食品、副食品和議價糧,完全是從干部群眾的實際困難出發,是一種應急措施。沒想到被人打黑槍。他救出了干部群眾,自己卻受了牽連,于他的確很不公平!”
在醫院,焦裕祿沉默了一陣后,又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前幾天,一連刮了幾場大風……又下了一場大雨……沙區的麥子打毀了沒有?洼地的秋苗淹了沒有?”劉俊生告訴他:“咱縣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作用了,連沙丘旁的麥子都沒有打死,長得很好。洼地的秋苗也沒有淹……”
焦裕祿問:“老韓陵的泡桐栽了多少?”劉俊生高興地告訴他:“林場里育的桐苗,全都栽上了,都發出了嫩綠的新芽,看樣子都成活了。”
焦裕祿又問:“秦寨鹽堿地上的麥子咋樣?”劉俊生說:“我剛從那里采訪回來,群眾看到深翻壓堿后種的小麥,都高興透了,形容說:今年的小麥長得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樣,這邊一推,那邊動彈,鉆進一只老鼠都跑不出來……”
由于問話太多,太激動,太疲勞,焦裕祿竟然昏迷了過去。等他醒來,一把拉住身邊的劉俊生的手,說:“剛才,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蘭考的小麥豐收了。你這次回去,一定請人捎一把秦寨堿地上的麥穗來,叫我看一看。”劉俊生點頭稱是。
這時,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端著一碗面湯走來……接著,一位護士拿著針管走來……趙文選拉了拉劉俊生的衣角,劉俊生領會了他的意思,只好和焦書記中斷談話,說了聲:“焦書記,您休息吧!我走了。愿您早點康復!我們在蘭考等您!”焦裕祿含淚緩緩揮手……
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張欽禮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焦裕祿用他那干瘦的手握著張欽禮的手,兩只失神的眼睛充滿深情地望著他,問:“我的病咋樣?為什么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張欽禮遲遲沒有回答。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張欽禮最后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里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張欽禮,說道:“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斗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
不久,醫院連續兩次發出了病危通知。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建民和省委副秘書長苗化銘、開封地委組織部部長王向明趕到醫院看望他,他已處在昏迷與搶救之中。
從昏迷中蘇醒后,焦裕祿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會有多少了,便嚴肅、認真而又溫和地告訴醫護人員:“不要給我使用那么貴重的藥了,應該留給比我更需要的、更有希望的同志。”
臨終前幾天,焦裕祿從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塊手表交給焦守鳳說:“小梅,爸爸沒讓你繼續讀書,也沒給你安排一個好工作,爸爸對不起你。這塊舊手表是爸爸用過的,送給你作個紀念。你要好好工作……按時上下班。”焦守鳳哽咽著說不出話。于是,焦裕祿將目光轉向妻子,囑咐妻子不要向上級伸手。
隨后焦裕祿,又對焦守鳳說:“小梅,你們姊妹幾個,數你大……是大姐姐……以后要聽媽媽的話,幫助她……帶好弟弟妹妹。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也作為送你的禮物……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后來,這塊手表與這本《毛澤東選集》成為焦裕祿紀念館的重要藏品。
1964年5月14日9時45分,因患肝癌晚期而不治的焦裕祿與世長辭,終年42歲。焦守鳳接受采訪時說:“我爸去世時,只有我媽(徐俊雅)和縣委的一個干事(李忠修)在現場。”
一個人的逝去與一個城市的感動
1964年5月15日,焦裕祿追悼大會在鄭州舉行,河南省委領導、開封地委、蘭考縣委領導和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學生前來泣送、哀悼。
5月22日,蘭考縣舉行追悼大會。追悼大廳的大門兩側擺滿了花圈。韓陵村的老農以泡桐樹枝做花圈,有人以鮮花青草做花圈,更多的是青松翠柏的枝葉所做的花圈和紙布花圈。劉俊生負責登記花圈,計數竟至千余。焦守鳳回憶說:“兩場追悼會我都參加了,我抱著我小弟弟,領著二弟等參加的。”
過年時借的錢還沒還清,焦裕祿就這樣走了,撇下家中的老老小小。焦守云回憶說:“父親去世時才42歲。我那時11歲。那一天,我記得特別清楚,在院子里玩,我還模仿老太太在唱戲,突然聽到我媽哭,哭得特別厲害。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兒,趕緊往家跑,我姐抓住我,把我頭上的紅頭繩抹掉了。她想給我找個白布扎一下,沒找到,最后找了個綠頭繩。我媽把我拉過來,說:‘守云,你以后可得好好學習。’這時候我才迷瞪過來,覺得爸爸不在了。我母親那時才32歲,帶著6個孩子,精神上的痛苦和身體上的疲勞可想而知。”
焦守云說,大伯焦裕生給父親寫的挽辭是“鳥戀失翼”,落款是“裕生叩首”。不過,后來焦裕生應蘭考縣委辦公室的留言請求時,又揮毫正楷,寫道:“為人民忘軀英魂尚在,黨育你未忘饑苦人民。”手跡被蘭考縣檔案館保存。
焦裕祿為蘭考人民鞠躬盡瘁,蘭考人民更是崇敬愛戴焦裕祿。當焦裕祿病重住院的消息傳開后,四鄉八村的老百姓曾涌到縣委,都來問焦裕祿住在哪家醫院,非要到病房去看看他不可,縣里的干部勸也不聽。有個叫靳梅英的老大娘,聽說焦裕祿去世了,冒著大雪大黑天地摸到縣城,看見宣傳欄里有焦裕祿的遺像,就坐在馬路上不走,愣愣地看著遺像一動不動。
正當蘭考的封沙、治水、改地斗爭初步取得成效的時候,焦裕祿永遠地離開了。其實, 他那篇沒有完成的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種下的是一個幸福蘭考夢。他走之后,蘭考的黨員、百姓努力用汗水灌溉這個夢。
言行雙表率,生死一沙丘!焦守云回憶說:“爸爸臨終之前最大的心愿是死后能夠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他的遺體起初只是就地埋在遠離蘭考的鄭州郊區的鄭州市烈士陵園,一直到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組織上才決定把我爸的遺骨遷回蘭考,當時我們省還第一次動用了專列把父親靈柩運回蘭考,葬在城北關黃河故堤沙丘。”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準焦裕祿為革命烈士。2月26日,根據焦裕祿生前的遺愿和蘭考人民的強烈愿望,河南省委決定將焦裕祿的遺體從鄭州遷葬于蘭考。當天,一輛護送焦裕祿靈柩的專列到達蘭考,火車站人山人海,街兩邊掛滿了挽聯。
此前,河南省委指派省委秘書長苗化銘負責遷葬事宜,指派省府秘書長趙致平親赴蘭考負責安葬工作,首要問題就是按照焦裕祿的遺囑,埋在沙丘上。
埋在哪個沙丘上?起初有人提出,埋在焦裕祿親自領導群眾封閉過的沙丘最合適,位置在東壩頭的張莊南地。于是,趙致平領著蘭考縣委領導去現場查看,發現這里踞縣城18里地,又沒公路,考慮如安葬這里會給今后的紀念活動帶來很多困難,便提出有沒有靠近公路近的沙丘。這時,有人提出在蘭荷公路旁的城關公社高場北地的沙丘適合,于是大家隨即去現場視察。這里雖有沙丘,離縣城還是有10多里地。
根據蘭考縣委原副書記張欽禮回憶,有一次起大風,他和焦裕祿查風沙,曾到縣城北的黃河故堤上,故堤上有個土牛,是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勞動人民一筐筐、一擔擔把黃土堆在大堤上,以備黃河決口之用,群眾叫“土牛”,這里是縣城的最高處。當時他和焦裕祿站在土牛上,可以看到風沙的起落。焦裕祿說:“人有人路,風有風口。”又轉臉對張欽禮說:“老張,這個地方站得高,看得遠,真是個好地方,如果我死了,就埋在這里吧!”當時張欽禮認為是句玩笑話,并沒在意。于是,墓區選定在這里。
火車站離墓地也就幾里地,數萬群眾扶棺前行,整整走了兩個半小時。這一天,對蘭考人民而言是一個淚水浸泡的日子。“蒼天含黛,大河嗚咽”,蘭考人民以淚洗面,迎回了“被蘭考活活累死”的焦書記。
據參加過焦裕祿葬禮的劉杰回憶,送葬那天,街上到處是人,街道樹枝上掛滿了布條。上萬群眾披麻帶孝,恭候棺木到來,有的婦女還挎著裝滿雞蛋和饃饃的竹籃。
當棺木在東邊出現時,靜候的群眾不顧一切地涌上前去,齊刷刷地跪倒在地,放聲痛哭。棺木前面的人,退一步,磕一個頭;撫摸著棺木的人,一邊隨著棺木移動,一邊泣不成聲地說:“焦書記,你不能走啊!”遠離棺木的人則揮動著雙臂高聲呼喊:“焦書記,讓俺再看你一眼啊!”
在墓地,遠離的群眾跪成一片。有十幾個人不顧一切地跳進焦裕祿的墓穴,周圍立即圍起兩道人墻,他們死活不肯讓焦裕祿的棺木下葬,他們舍不得他們的好書記,紛紛表示要替他而去。蘭考縣領導深情地勸說著:“鄉親們,焦書記為咱蘭考人操盡了心,他太累了,就讓他好好歇息吧!”跳入墓穴的人,悲哀地放聲大哭,最后,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才離開了墓穴。
棺木下葬時,拽繩的人怎么也不愿放下繩子,硬是一點一點地往下放。當繩子剛一松手,成千上萬的人立即從四面八方向墓穴沖去,他們痛哭著,呼喚著:“焦書記,您回來呀!”接著又虔誠地再次跪下磕頭,捧起一把把黃土輕輕撒向棺木。就這樣,蘭考人民用手中的黃土將焦裕祿與蘭考的大地融為了一體。14年后,“萬人送葬”的場面出現在電影《焦裕祿》的開頭。
當天,一對夫婦抱著一個小孩趕到了焦裕祿墓前,哭著說:“焦書記,您睜眼看看吧!這就是您救活的小徐州呀!焦書記,您放心,等娃長大了,俺一定教他像您一樣去做人!”
原來,這個孩子就是焦裕祿曾救過的張徐州,那對夫婦就是張傳德夫婦。焦裕祿去世后,張徐州的父母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張繼焦,取繼承焦裕祿精神之意。
張繼焦日后成為了焦裕祿烈士陵園管理處副主任、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副館長。“我和焦書記結下的是一輩子的緣分。”張繼焦說,如果當年不是焦裕祿伸手相救,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張繼焦,“宣傳好發揚好焦裕祿精神,對我來說義不容辭。”
焦裕祿是1962年冬天到蘭考的,而當年蘭考的老百姓食不果腹,絕大部分背井離鄉,出去逃荒要飯。也是在這一年,因難以忍受“三害”之苦,張繼焦的父母從蘭考逃荒到了江蘇徐州,途中生下張繼焦,并取名張徐州。按當地風俗,產婦不滿月不能進別人家,由于無處安身,張繼焦的父母只好抱著剛出生6天的孩子,扒火車返回了家徒四壁的蘭考老家。
回家不久,張徐州患上重病,家中無錢醫治,父親就把他放在筐子里丟在了路旁。正在查找風沙口的焦裕祿,發現孩子還有氣息,趕緊到大隊給縣醫院院長高芳軒打電話,要他們好好給孩子治療。他還不放心,又寫了一封信,讓孩子的父親張傳德帶上到縣醫院去。孩子住院期間,焦裕祿曾3次電話詢問病情。經過25天的治療,小孩吃得白胖,病全好了。
日后,張繼焦就稱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為媽媽,并像親生兒子一樣經常照顧徐俊雅,又因為張繼焦比焦裕祿的6個子女年齡都小,人們都稱他是焦家“老七”。
如今,張繼焦雖然根本記不清焦裕祿當年的模樣,但是他對焦裕祿卻有著十分特殊的感情。“我的生命就是焦書記給的,我也是他家的‘老七’,我比他家6個孩子都小。從剛記事起,父母就反復講述焦書記救我的經過,經常告誡我要知恩圖報。因而直到現在,當年的細節還深存我的腦海,記憶猶新。其實,焦書記在蘭考工作時,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命。他冒雨去村里救出因房屋坍塌困在里面的老人,冒雪給貧困戶送棉被,他治理‘三害’讓無數人不至于餓死。這么年來,我忠實地做好一名焦裕祿陵園的守護者,如同那棵焦桐樹一樣,與焦書記始終在一起。”
據焦守云回憶:“我爸的去世,使我媽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轟然倒塌。埋葬我爸的時候,她肝膽欲碎,幾次往我爸的棺木上撞擊,被身邊的人死死拉住,我們姊妹幾個連驚帶嚇,一個個圍在我媽身邊嚎啕大哭。”
從此以后,焦守云每天都看到母親的眼淚和艱難的生活,“還有無休無止的報告會,身上別的數也數不清的毛主席像章。她幾乎每天都要給去作報告,作一場報告就回來哭得稀里嘩啦的。”
在當時的焦裕祿烈士陵園內,豎有焦裕祿烈士紀念碑。然而,這塊烈士紀念碑在“文革”期間同樣遭到了災難,先是被推倒,之后林彪的死黨又下令將上面的碑文磨平,重新改寫,添上了“副統帥”的題詞——為了醒目,還專門涂了紅漆。
20世紀90年代,學習焦裕祿再次被提起,焦裕祿烈士陵園才得以重建,命名為“焦裕祿紀念園”。1993年5月,紀念園主體部分完工。
整個紀念園主要紀念建筑物有革命烈士紀念碑、焦裕祿烈士墓、焦裕祿同志紀念館等。墓碑位于紀念碑北側墓區最高處,由大理石雕砌而成,碑高2.75米,正面鐫刻“焦裕祿烈士之墓”,碑背面為焦裕祿生平簡介。墓蓋由漢白玉外鑲。墓后有屏風墻,鑲嵌著毛澤東主席的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讓焦家后人欣慰的是,焦裕祿的陵墓所在地如今已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