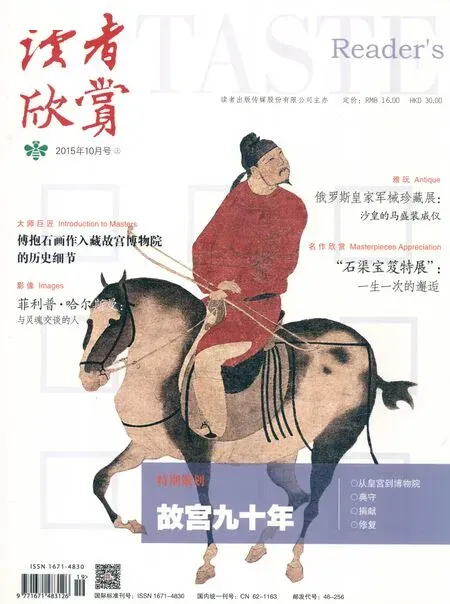隨口潛伏的美好
語言學家趙元任記錄過一段軼事。他去耶魯大學拜訪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薩丕爾問了他幾個關于他的家鄉話常州話的問題,大約一個鐘頭之后,薩丕爾把常州話的音位系統搞清楚了,接下來幾乎要跟趙元任講常州話了。這仿佛只是個語言天才的故事,但我至今依然記得趙元任在文章里寫下這個故事時的腔調,不盡是趣聞,不全是仰慕—這個本事趙元任自己也有,而是一種對于共同研究的學問的尊崇和會意。
我記得當年曾經跟隔壁宿舍同專業的李倩不止一次地討論過這個故事,自然,我們說起這些偉大的語言學家時,有著飽滿的仰慕,還包括我們對于語言學這門學問強大力量的嘆服。那時候我的好朋友、作家周曉楓正在北大做訪問學者,她翻了翻我正撓破頭寫著的論文,問我:“你成天念念有詞的,到底在研究什么?”我翻著白眼,努力用一個作家能理解的話告訴她:“我在研究‘藍棉布門簾和‘棉布藍門簾的區別。”曉楓翻了一個更大的白眼:“這有什么好研究的?‘藍棉布門簾比‘棉布藍門簾藍,‘棉布藍門簾比‘藍棉布門簾棉嘛……”其實,她說得也對,兩種語序人們都能接受,但是它們強調的重點不一樣,不過可接受的多種語序,不只是語感的區別這么簡單。
“然而這有什么用?”這基本上是李倩和我這種學語言學的人,在跟人勉強解釋清楚研究內容之后遇到的第二個問題。語言學有什么用?能換什么?能拉動GDP不?能創業融資不?
坐地鐵的人每天都會聽到“下一站:北京站”“北京站就要到了,下車的乘客請準備”。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車廂廣播不會把第二句放在第一句講,它們的順序從來不變?
為什么說“看一看”“等一等”,不能說“高一高”、“大一大”?你如果覺得“看”和“等”是動詞,“高”和“大”是形容詞,那為什么就沒怎么聽說過“死一死”?“孩子大一大就好了”也是一個中國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句子吧。再深想一下,我們普通人判斷什么是動詞,是不是先想一下這是不是表示動作的詞,而印歐語系,比如英語中的動詞,是根據它在句中的位置分類的,那么中文的動詞和英文的動詞是一個東西嗎?
明星現在都自己做自己的狗仔,不僅要自爆吃喝拉撒,也會在社交平臺上去回應別人對他們生活的猜想。分手信、道歉信滿天飛,如果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它們,你不僅能看到道歉的誠意,也能看到明星預設的歪理,以及推過于人的滑頭。而在從旁助拳的明星親戚們發的微博上,你還能看出完全不符合他們的方言背景、用語習慣的公關痕跡,甚至能推測出代筆者的大致年紀……
李倩的《回鍋肉和香菇菜心的語言等級》于輕描淡寫中傳達的,恰恰就是這些脫口而出的話語背后的語言學解釋,而它的基礎,是7年嚴格的語言學訓練,以及無須為論文和職稱操心的放松心態。前一點決定了它的準確,后一點決定了它的好看。
人類發明了這么多學問,它的出發點,大約是滿足人的好奇心。“有什么用”這種思路,在人們還沒那么從容,相對比較緊張的生活狀態中才會出現。美好的東西沒什么用,但我們隨口問出的一切,都有來自某一種學問的精妙解答。在吃喝不成大問題的人群中,“有趣”比“有用”高級得多,而且“有趣”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能解決比“有用”更為復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