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頌》譯后記
《西風頌》系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名作,寫于1819年。當時詩人正浪跡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附近的亞諾河畔,忽見西風乍起,有感而發,遂成千古絕唱。
該詩由五章構成,每章是一首十四行詩,這是一種比較特別的十四行詩,叫三韻體(tersa rima),由四組三行詩(tersets)和結尾一組兩行詩構成,韻式是aba bcb cdc ded ee,此種韻式的特點是環環相扣,藕斷絲連,回響不絕。意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特別擅長這種詩體。雪萊在意大利用這種體寫詩,也有對但丁表示敬意的意思。仔細審視原詩的韻腳,我們會發現有個別的地方貌似押韻,但似乎并不押韻,最突出的是最后一組兩行詩的韻腳:Wind——behind。這是西方詩歌中特有的一種押韻方式,叫眼韻。顧名思義,也就是看著像押韻,但讀起來韻音并不相同。就此例而言,若要在譯文中體現,其實也不難,譯成“……風哦,/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也不是不可以。漢語詩中雖沒有眼韻的押韻傳統,但“哦”和“嗎”倒是具有視覺效果相近(口字邊)和句法功能相同(語氣助詞)的特征,用來體現英語的眼韻,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只是考慮到漢語讀者對于押韻的期待心理,同時考慮到英語詩中的眼韻也往往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主體韻式的需要,故在翻譯時還是采用常規的押韻方式來體現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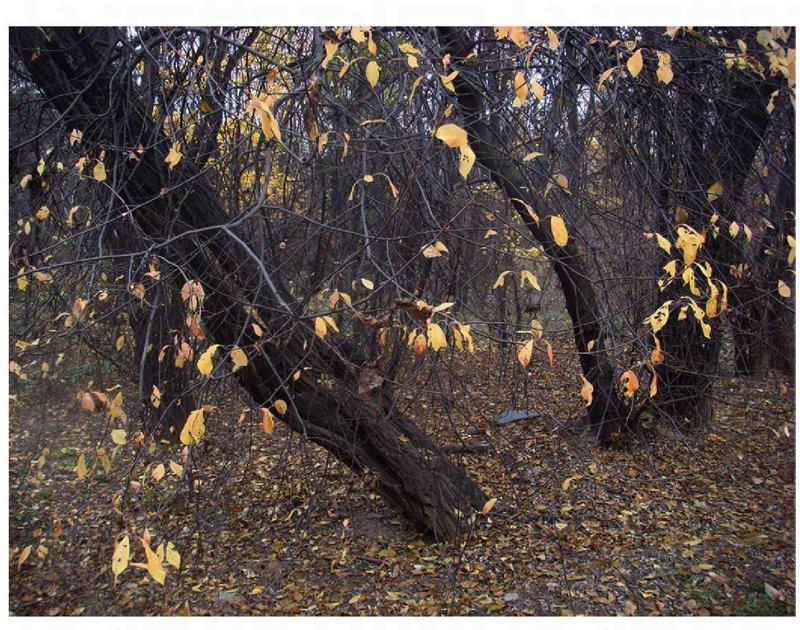
原詩的節奏結構是抑揚格五音步,這是十四行詩的主要格式,但其中也有幾行是11個音節,甚至還有一行是12個音節。從英語詩律學的角度看,格律詩多一個少一個音節,是很正常的結構行為,往往不影響主體音步的計算。英語格律詩的分析基本上是以主要格律為依據,其主體音步基本上都是抑揚格的,即一個輕音和一個重音構成一個音步。個別出格的地方總會找到辦法或理由來讓其順著主要格律來做解讀。如兩個重讀音節或兩個單音節的實義詞并列,就會在分析時將處于“抑”音位置上的音節做次重音來定位,以滿足抑揚格的需要。音節數不夠時,積極的辦法是在不發音的元音之上標出發音標記,如第七行的wingèd,e在這個詞中原本是不發音的,但此行音節數就達不到10個,因此詩人在這個字母上加了一個撇點,就人為地造了一個音節出來;消極的辦法,就直接省掉一個音節,但在分析的時候,往往會將缺一音節的音步當作一個完整的音步來看待,這種少一個音節的所謂缺省音步多發生在詩行的第一個音步和最后一個音步,但行中音步缺省音節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此外,英語格律詩在出現音節數超標時,則往往會在有些音節組合上做短音快滑,在此情況下,多出一個音節的音步單位的時間長度往往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所以總體上不影響主體格律的節奏定位。就此詩的翻譯而言,由于11和12音節的詩行在原詩中不是規律性出現,因此翻譯時就沒有給予這些詩行以相應的體現了,還是按“以逗代步”(關于“以逗代步”的詩歌翻譯方法,詳見王東風“以逗代步 找回丟失的節奏:從The Isles of Greece的重譯看英詩格律的可譯性理據”,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6期,和王東風“《希臘群島》重譯記”,載《譯林》2014年第5期。)的方式來統一體現。所謂“以逗代步”,是筆者提出的一種詩歌翻譯方法,主要是指用漢語的“二字逗”,即兩個字一個音組,來體現英語格律詩中的雙聲音步,如抑揚格,因為抑揚格與“二字逗”一樣,也是雙聲節奏單位。
原詩之中還用了大量的修辭格,最突出的修辭格是比喻,僅比喻詞like就用了八次。英語比喻詞遠不如漢語豐富,主要就兩個like、as,另外還有幾個帶as的組合,如as if、as though。筆者在翻譯時,沒有刻意用漢語豐富多彩的比喻詞去做美化。以明喻為例,譯文用了八個“就像”,以體現原文由like所構成的一個明喻鏈。從語篇的高度看,此類重復具有文體建構的重要意義,它可以視為是作者的一種文體偏好,也可以視為是作者為了營造某種特殊的效果而有意留下的語言痕跡。不過有些利用語言本身特征去建構的修辭格,則極難在翻譯中體現,最突出的是“頭韻”,如該詩伊始就“嗚嗚”地刮起了“西風”:wild West Wind;詩中還有“嘶嘶”的氣流快速流動的聲音:skiey speed / Scarce seemd。對此,譯者只能望“音”興嘆了。詞語和詞形的重復可以產生前景化的修辭和文體效果,語義的重復也同樣可以造成前景化的效果,如該詩對于“枯葉”這個意象的營造就采用了同義重復的修辭手段,用了三個不同的形容詞來描寫這一意象。這三個詞分別是:dead、decaying、withered (leaves),不可否認,這三個詞語與“葉”搭配,都可以譯成“枯葉”,但文體學則認為,意思相同或相近但用詞不同的表達方式,其文體價值是不同的。就此詩而言,這三個形容詞的使用,除了其他潛在的解讀之外(如詞語成色的豐富性等等),對筆者來說,有一點體驗是很明顯的,即這三個形容詞實際上是從三個不同的側面來描寫了“枯葉”的形態。因此,筆者在翻譯這三個組合時不敢怠慢,也分別采用了不同的偏正組合,即“死葉”“朽葉”和“枯葉”。
胡適認為,好詩只要有思想有情感就可以了,不必糾結什么形式,用什么格律。筆者不以為然,以這首Ode to the West Wind為例,此詩之所以在世界詩壇獨放異彩,并非僅僅是有思想有情感,更重要的是這思想和這情感是被詩的形式完美地體現出來的。如果這首詩是用散文體寫的,它也絕無可能大放異彩于詩壇。正是由于這首詩強烈的節奏感(由均齊的音步節奏來體現)和豐富的聯想性(由大量的比喻和借代來體現),才使得這首詩所攜帶的思想和情感得到了最大化的宣泄,也才使這首詩具有了感人至深的思想、情感和聲音沖擊力和穿透力。同理,如果我們在翻譯中不把這些使思想情感變成藝術的東西以藝術的形式體現出來,那么從藝術的角度看,就還是有缺陷的。以往這首詩的翻譯,雖然已經有了多個杰出的譯本,但也有瑜不掩瑕的地方,那就是節奏的體現還不夠到位,主要是因為大家用的是散體來翻譯,沒有把原文以雙聲音步建構的均齊節奏感體現出來,此次重譯就是要在節奏上進一步接近原詩,希望這節奏的加入能把這首名詩的詩意進一步地提煉出來。
(王東風,博士,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