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彪西和《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
任海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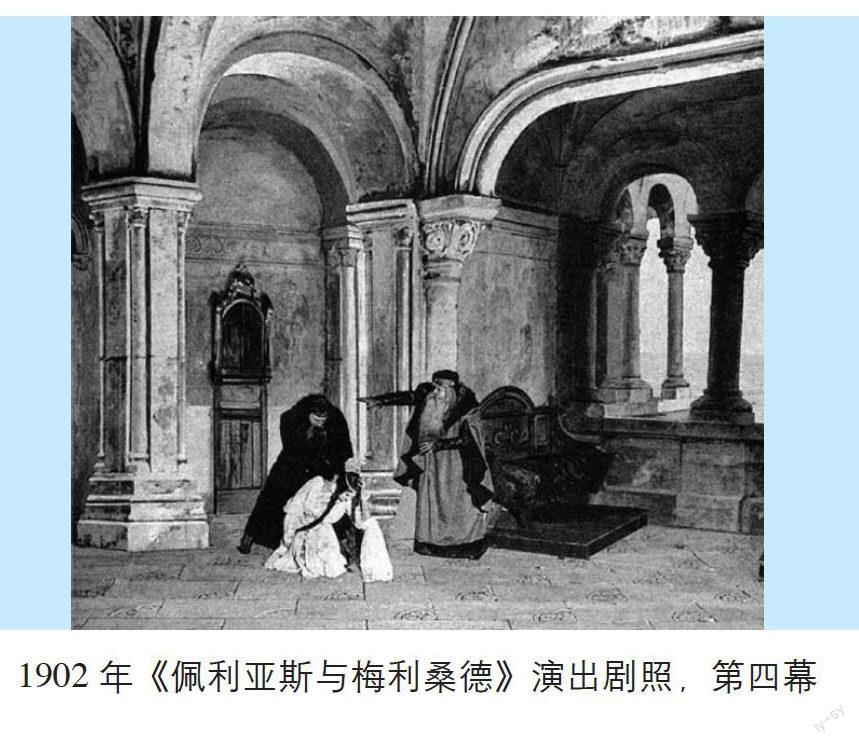
說起德彪西(1862-1918),人們的腦海中也許即刻會跳出:印象派作曲大師。其實這是不準確,至少是不全面的。首先,德彪西本人并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其次,當時就有一些評論家為此展開過爭論,其中一位叫蘇瓦雷的更是明確指出:“德彪西根本不是印象派,相反,他是徹頭徹尾的象征派音樂家。”由此認為,德彪西的音樂并非與印象派畫家莫奈、雷諾阿同宗,而是與象征派詩人馬拉美、魏爾侖同緣。
那么,為什么一般人都會認為德彪西是印象派呢?這主要是緣于德彪西年輕時曾有當畫家的志向,而他獨特的音樂風貌、朦朧多彩的畫面感與色彩感,與印象派的繪畫特色,從藝術欣賞上來說,又頗有相通之處;況且,當時法國印象派畫風正開始風靡全球,于是人們就順勢給德彪西的音樂風格貼上了標簽:印象派。
客觀而言,德彪西的器樂作品,比較靠近印象派的風格;他的戲劇作品,比較接近象征派的風格,比如本文要談的歌劇《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印象是畫風,象征屬詩風,只是為了便于理解德彪西的音樂而提示的一種說法而已。如果要取一位法蘭西音樂的杰出代表,德彪西無疑名列前茅,而他的《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不僅是法國歌劇的瑰寶,更是歌劇藝術史上的奇葩。
如果說,二十世紀以來最為成功的綜合藝術是電影,那么,電影以前,最為成功的綜合藝術則是歌劇。歌劇就是以前的電影。雖然它不復當年的風光無限、備及榮光,但其經典文化的品位和地位,依然像一位雍容華貴、歷經滄桑的老貴族。你如果到了紐約、倫敦、柏林、米蘭、巴黎、慕尼黑……最醒目的城市地標,必定有歌劇院。
歌劇起源于十六世紀末的意大利,十七世紀中葉傳到法國。由于音樂文化傳統(包括語言發音)的不同,意大利歌劇如同大哥,令法國小弟一直處于尷尬的地位。直到十九世紀,出現了以邁耶貝爾(其實是德國人)、古諾、托馬斯、馬斯奈、比才等為代表的法國歌劇,以其抒情性、大場面、經常伴有芭蕾舞表演等,逐漸開始形成了有法國特色的歌劇。然而,就在此時,瓦格納橫空出世!
瓦格納的出現,猶如航空母艦,橫沖直撞,具有極大的震撼力,歌劇界從此一片“唯瓦是從”,就連威爾第—與瓦格納同年出生的意大利歌劇巨擘,也為此震驚,并在“潛移默化”中受其影響,比如說他晚年的《奧賽羅》和《法斯塔夫》。所以,當這股瓦格納熱潮浩浩蕩蕩涌向法國樂壇,可以說是勢不可擋,巴黎甚至創辦了《瓦格納評論報》,馬拉美、魏爾侖等都在上面發表了贊美瓦格納的詩文。而此時年輕的德彪西,剛獲得了在作曲界頗具分量的羅馬大獎,也對瓦格納崇拜得五體投地,一八八八年和一八八九年,德彪西曾兩次到瓦格納歌劇的圣地—拜羅伊特朝拜,沉迷于瓦格納的音樂。但是,自小學音樂時就有反叛精神的德彪西,在極度的沉迷后,很快就醒悟過來。他在第二次從拜羅伊特歸來后,對自己的老師說:“我對瓦格納即使有佩服的地方,但也不想效法他。我在思考新的戲劇表現形式。” 德彪西認識到,恢宏龐大只屬于瓦格納、屬于德意志,法蘭西需要的是屬于自己的音樂藝術—優雅詩意、細膩精致、含蓄節制。他的這一音樂美學理想,終于在《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中得到徹底體現。
事情的開始似乎有些偶然。一八九二年夏季的一天,德彪西在意大利逛商店,碰巧發現了比利時象征派戲劇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劇本《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買回來后一口氣讀完,興奮之下當即寫下了幾句音樂和主題。他本能地感覺到,這部戲適合自己長期以來想要嘗試的戲劇音樂的探索。很快,通過朋友的介紹,德彪西登門拜訪梅特林克,請求授權使用劇本。當時名聲遠超德彪西的梅特林克知道后,一笑了之:我對音樂一竅不通,如何決定?后來在德彪西朋友的一再鼓動下,梅特林克終于欣然答應了德彪西的請求,并大度表示,德彪西在創作音樂時,可以根據需要對劇本進行刪節。
于是,時年三十歲的德彪西,開始創作《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為這部歌劇居然花去了十年時間,至一九○二年才完成,是他畢生投入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可謂是殫精竭慮,精益求精。文學上有“一本書主義”,德彪西一生創作完成的歌劇,也就是這部《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但它“以一當十”,在歌劇發展史上是一部劃時代的巨著,是現代歌劇的發軔之作,對后世影響深遠。
《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是一部五幕十二場抒情戲劇,唱詞基本照搬原來的話劇臺詞。這是一出象征派的劇作,情節和人物關系充滿了隱喻,這是理解該劇的要點。我們且來解讀一下劇情。
第一幕,關鍵詞:相遇。
這里的相遇,是指阿萊蒙德(虛構的國家)國王阿克爾的孫子、同母異父兄弟戈洛和佩利亞斯分別相遇梅利桑德。
某天,戈洛在森林中打獵時迷路,碰到了同樣迷失在森林中的梅利桑德(她是一位來自于一個遙遠國度的公主)。她先是驚恐,后跟隨戈洛一起上路。在路上,他們結婚了(戈洛之前曾有過一次婚姻)。半年后,戈洛帶梅利桑德回到自己的王國。他們兩位為什么會結婚?是個空白。從后來劇情的發展來看,是否有這樣的隱喻:人世間有多少青年男女,是在“迷路”的情景中匆忙結婚的,當他們成熟后,才明白當初彼此并不是出于愛情而走到一起的。他們后來的婚姻出現危機,與此有關。
而當梅利桑德見到青春朝氣、意趣相投的佩利亞斯,真正的愛情開始萌發。
第二幕,關鍵詞:動情。
第二幕一開始,舞臺上有一口古井。佩利亞斯和梅利桑德在互相嬉戲,探望古井戲玩。劇中,多次出現古井場景,是否暗示:人生之謎,就如這深不可測的古井?
佩利亞斯詢問梅利桑德認識戈洛的經過,但梅利桑德岔開話題,在古井旁拋玩起戈洛給她的結婚戒指。她明明知道在古井上空拋玩戒指有掉落井下的危險,但她還是在井邊上一次次拋玩—果然,戒指掉進了井里,她是否潛意識里已不想要戈洛的這枚戒指?而就在這邊梅利桑德的戒指掉進井里的同時,那邊的戈洛打獵受傷。危機同時出現!
梅利桑德在照料受傷的戈洛時,向他哭訴,她想離開這里。戈洛說:誰欺負你了?是老國王阿克爾?是母親吉尼維夫?梅利桑德一一搖頭—當戈洛問到佩利亞斯,梅利桑德下意識地驚呼:“佩利亞斯!”只是戈洛沒察覺。接著,戈洛發現梅利桑德丟掉了自己給她的結婚戒指,非常暴怒,命令她和佩利亞斯一起去尋找戒指。
這無意中又給倆人提供了相處的機會,但已經掉進古井的戒指如何能找到?倆人漫無目的地走進一處洞穴,看到的是三位奄奄一息的老年乞丐……這又是一個令人玩味的隱喻。
第三幕,關鍵詞:高潮。
第三幕中有全劇最經典的場景,也是西洋歌劇中最為經典的場景之一:梅利桑德在城堡塔樓(大約有二層樓高)的窗口唱著一首古老的歌,佩利亞斯聞聲而來,他跳躍著想握住梅利桑德的手,但夠不著。這時,梅利桑德的長發如瀑布般從窗口傾瀉而下。佩利亞斯握住長發,柔情萬種地撫摸親吻:“你聽見了我的親吻了嗎?我的吻沿著你的長發向上攀沿。”
佩利亞斯將梅利桑德的長發纏繞在塔樓旁的樹枝上,激情纏綿的音樂,令全劇達到高潮。這一場景的經典意義,可與羅密歐朱麗葉的陽臺相會相媲美。這時有鴿子驚飛,預示不祥,果然,戈洛突然出現!逮個正著!
戈洛警告佩利亞斯,梅利桑德已經懷孕,不要胡來,要他離開梅利桑德。
戈洛又從與前妻生的兒子小英尼沃德口中了解到,梅利桑德與佩利亞斯經常見面,甚至親吻,更加氣急敗壞。
第四幕,關鍵詞:佩利亞斯之死。
憤怒的戈洛當著老國王阿克爾的面,揪住梅利桑德的長發,暴烈地一邊將其往兩邊猛甩,一邊怒罵。這個場景,與第三幕佩利亞斯親吻梅利桑德長發形成鮮明對比。
傷心的佩利亞斯要去遠方,他約梅利桑德在古井旁會面,向她告別。暮色中,兩位戀人緊緊擁抱,互訴衷腸。一直在暗中窺視的戈洛趕到,用長劍刺死佩利亞斯,并追趕亂中逃脫的梅利桑德。
第五幕,關鍵詞:梅利桑德之死。
驚嚇受傷的梅利桑德早產了一個嬰兒。她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奄奄一息。自殺未遂的戈洛開始反悔自己的過激行為。他在床邊問蘇醒過來的梅利桑德:你愛佩利亞斯嗎?梅利桑德明確回答:是的。但他似乎不明白,也不相信,梅利桑德為什么會愛上佩利亞斯,于是又一遍遍問梅利桑德這個問題。梅利桑德沉默,不再回答。這里的沉默意味深長。
老國王阿克爾說:“別再打擾她……這個人的靈魂是安靜的。人的靈魂喜歡獨自離去。”
遠方隱隱傳來鐘聲。梅利桑德悄無聲息地閉上了眼睛……
一出愛情的挽歌結束。
《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的劇情并不復雜,但充滿隱喻和象征,象征著人世間愛情的難得、脆弱、易逝。德彪西為此譜寫的音樂非常奇特,獨一無二。傳統的意大利、法國歌劇,管弦樂對唱詞、詠嘆調主要起伴奏、烘托的作用,即歌唱為主,管弦樂伴奏為輔;瓦格納的樂劇(這是他對自己的歌劇—主要是中后期歌劇的定義),是大交響樂的概念,音樂與唱段既互相競爭,又融為一體—從整體的觀念而言,音樂更趨主導地位。德彪西的《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則獨辟蹊徑,別開天地,其管弦樂與唱詞、唱段好像是一種水與舟的關系,它們同步前進,不分主次,你載我行,我行你載。如果習慣欣賞以往的歌劇,初聽德彪西《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也許會覺得不習慣。只有反復聆聽,才能體會到其獨特的微妙精妙之處。
這部歌劇的演唱,既不像詠嘆調,也不似宣敘調,而是近乎說話口語的方式,頗似一種音樂的朗誦。這種連綿不斷似唱似說的唱法,進一步消解了自意大利歌劇誕生以來,唱段(詠嘆調)處于重要或競爭地位的歷史,也有別于瓦格納的樂劇,在音樂與戲劇的綿密結合上,作了新的探索,如注重臺詞語言中自然的音樂韻律,以表達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動。連綿不斷的“無終旋律”雖然離不開瓦格納的影響,但表現形式和內涵顯然已經超越了瓦格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事實,進行比較:傳統的意大利歌劇,可以出大把的詠嘆調集錦唱片;到了瓦格納,明顯減少;而到了德彪西的《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幾乎難以有獨立的詠嘆調或獨立的重唱,這說明了德彪西對戲劇音樂的獨特貢獻—臺詞、音樂、劇情、人物內心活動的徹底“無縫接軌”,水乳交融,這對開啟后來勛伯格、貝爾格等的當代音樂、當代歌劇,居功至偉,影響深遠。當時有位法國作曲家但第,也是瓦格納的崇拜者,一開始不喜歡德彪西的這部歌劇,但后來卻大加贊揚:“臺詞的音響演繹與語言的抑揚頓挫驚人的貼切。音樂豐富多彩的色彩波浪般浸透了原劇,提升了它的構思,揭示了它的意蘊,加強了它的表現力,而這一切總能使臺詞或字透過音樂的流動因素得以呈現。”畢竟是同為法國人,還是理解了自己同胞的心思,評價恰如其分。
德彪西在《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中的創新,并不是一夜之間的空穴來風,早在之前幾年,德彪西就說過,以往“音樂戲劇里唱得太多了”;激情的音符要節制;力度要有變化;音樂要從“語言見絀的地方開始”,這種音樂要“表現語言難以表達的東西”,“好像來自太虛幻境,并隨時會回去”。《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出色踐行了德彪西的音樂美學理念,尤其是他提到的 “好像來自太虛幻境,并隨時會回去”。這樣的音樂感覺實在是太奇妙了,我每次欣賞這部歌劇,對此深為贊嘆。
針對瓦格納音樂無休止的喧囂,德彪西還特意提出音樂中的“沉默”理念,認為“沉默作為一種表現手段,恐怕是突出樂句感情的特有方式”。在《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中,德彪西多次運用,別出心裁,比如在表現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互相吐露愛慕之情的表白時,并沒有出現以往歌劇中澎湃喧囂的管弦樂,器樂幾乎靜默無聲,只有男女主角獨唱聲部在輕聲細語—真是“于無聲處聽驚雷”。
德彪西反對瓦格納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瓦格納樂劇中大量的主導動機太過明顯(主導動機恰恰是瓦格納樂劇的主要特色),認為這是另一種程式化,并且調侃道:“你認為在作品里同一種感情可以表現兩次嗎?如果可以,那么作者要么是缺乏思考,要么給人以懶惰的印象。”
不得不佩服德彪西的百步穿楊。在當時一片瓦格納熱潮中,沒有人敢這么說,也沒有人會想到這么說。藝術形式的創新,往往就是這樣:新的,轉眼就會成為另一種陳舊。那么在《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中,有沒有類似的主導動機呢?因為在一部長達兩個半多小時的歌劇中,如果沒有相應的音樂主題、動機,豈不要“一盤散沙”?聰明的德彪西自然明白,但他的做法與瓦格納不同,他的動機非常隱蔽、朦朧,甚至有些支離破碎、行蹤不定,難以與劇中人物“一目了然”地對號入座。他并不是如瓦格納那樣清清楚楚:一個動機,代表一個角色、一種情緒。《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中的動機要含蓄得多,它們更多的是代表人物在劇中的處境,也就是說,他將動機更自然、更隱而不露地融化在全劇中。比如劇中出現的“森林”、“命運”、“梅利桑德”、“佩利亞斯”、“戈洛”、“噴泉”、“喚醒的欲望”、“戒指”、“愛的表白”,等等。說實話,你要聽明白這些動機,不花些時間和精力,是很難一下子就聽清楚的—其實,德彪西要的就是這種朦朧效果。既難以一耳了然,又引發你探究的興味。如果歸納起來,是否可以這么說:瓦格納的主導動機顯得比較“機械”,德彪西的主導動機則更加“靈動”。
所以,說到底,德彪西與瓦格納之間,是一種影響、繼承、變化、突破、發展的關系。他們相輔相承,無法涇渭分明地割裂。瓦格納音樂思想的精髓—音樂與戲劇緊密相連融為一體,肯定是啟發了德彪西的創作思維。也許,正是因為瓦格納的“不可一世”,才“刺激”了德彪西的創新,要為一向自傲的法蘭西人挽回面子,由此成就了一部歌劇史上的杰作。因此,是否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瓦格納,也就沒有德彪西—沒有“敵人”,也就沒有勝利者。
總體而言,《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就像一首雋永淡雅的詩,節制而不濫情,溫文爾雅,娓娓道來,即使是抒情性戲劇性達到極至的場景(如第三幕中經典的長發瀑布、愛之激情),也不過分渲染,縱情馳騁,而是穩穩地控制在自己的法度內。法蘭西式的含蓄優雅,法蘭西式的精致細膩。欣賞這部歌劇,就像口含一粒青橄欖,需慢慢品、細細嘗,千般滋味就在其中……
《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一部真正的獨一無二的法式歌劇。
關于《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最后想作一些延伸。在西方,就如同羅密歐與朱麗葉、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那樣,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也成為了著名的愛情悲劇題材,引起作曲家的興趣。除了德彪西將它寫成歌劇,也有其他一些作曲家為此譜曲,比較著名的有:芬蘭民族樂派的代表西貝柳斯,西方現代音樂的巨擘勛伯格,德彪西的前輩、法國作曲家弗雷。有意思的是,雖然出于同一題材,但音樂風格大異其趣。西貝柳斯低暗深沉,猶如北歐的巖石般冷峻,也是一種詮釋愛情悲劇的色調;勛伯格為此而作的同名交響詩,是他的早期作品,晚期浪漫派風格,音樂語言深受馬勒、理查·斯特勞斯、瓦格納的影響,幾乎就是后者《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翻版,奢華熱烈,濃墨重彩;弗雷的同名組曲共由四首組成,典雅溫情的法式韻味,比較接近德彪西,其中的第三首《西西里舞曲》,膾炙人口,流傳甚廣,成為音樂會上的保留曲目。當然,說到《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第一位的代表人物還是德彪西,這部歌劇幾乎成為他的代名詞,以致讓人幾乎要忘記,它原來是來自于梅特林克。梅特林克的《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早已謝幕,而德彪西的《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令其“復活”,令其永恒,成為音樂經典,至今仍在上演。此種情景頗似威爾第與小仲馬的《茶花女》、威爾第與雨果的《弄臣》之間的關系。再次證明了哲學家叔本華的精辟論斷: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音樂處于最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