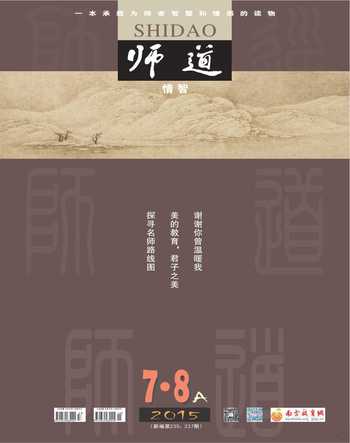職校四年
茅衛東
寫下這個題目,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此刻,我已經向學校提交了辭職報告,離開學校干回了編輯這一行。
一
“你在職校當老師,屈才了!”
“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媒體多了一個好編輯!”
熟悉不熟悉的朋友都對我的這一選擇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認為編輯這個工作更適合我。這與四年前,朋友們得知我離開中國教師報回到紹興老家,在一所職業學校當了老師后的反應很是一致。當時,我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么要離開中國教師報?”然后就是或同情或鼓勵:
“你不當編輯記者跑到職業學校當老師,是不是很有失落感?”
“報社少了一個好編輯,學校多了一個好老師!”
我承認,職校四年,我干得很不開心。不過,失落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更沒有認為自己必須在哪個位置上,不該出現在哪里。盡管現在許多人——這其中也包括職校系統的各級領導與職校普通教師——對職校和職校生有看法,我的觀點是,不偷不搶,學點技術以后能夠自力更生,這樣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我尊重職校生,同樣也尊重我自己的選擇,屈才、失落,只是朋友們出于對我的關心而產生的想當然的看法。
因此,當我自己的孩子由于成績太差上普高無望而選擇我任教的這所職校時——我們當地有四所職校可供選擇——我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從沒想過這是給我丟臉而讓他選擇其他學校。而且,他選擇的是幼師專業。一個一米八四、體重超過兩百的男生以后要去當“男阿姨”,或許對很多人來說,這也只能是一個“別人家的孩子”的選擇。我問他:“你知道幼兒園老師要做哪些事情嗎?”兒子說,知道。“你覺得你喜歡做那些事情嗎?”兒子說,喜歡。“現在幼兒園老師的收入很低的。”兒子說,能干自己喜歡的工作最重要,收入以后再說。那就OK。
講這個事,只是想說明,我對職校和職校生并沒有成見,我對自己到職校當老師的選擇也沒有后悔。
我就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如果去當兵,我一定會踏踏實實做一個優秀士兵,但不會想到以后一定要當將軍。做了教師,我最大的快樂就是看到學生在成長——我指的是在我的影響下的成長,而不在乎職稱,不在乎是不是名師。所以,在職校,我沒有失落感。當有學生懷疑我也和許多人一樣看不起職校生時,我告訴他們,我兒子和你們一樣就在這個學校就讀。
人的成長,不論身心,都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環境。我以為,教師應該是一個安靜中助人成長同時自己也得到發展的職業,但現在,這一職業太鬧騰了。許多校長抱怨,現在什么部門都可以干預學校工作,教師自然也無法安靜地工作,因為各種材料的準備,各種活動的配合,最終是需要教師來完成的。
再說職稱評聘。歐美國家和中國的臺灣、香港的中小學都沒有職稱評聘這個事,而我們這塊工作倒是越做越精致。以前中小學職稱只有初級、中級和高級三檔,據說有些聰明而勤奮的教師三十多歲就高級職稱到手,從此馬放南山,得過且過。領導們看不下去了,將這三檔職稱又細分為四等,一共三檔十二等,每一等級的晉升都有年限規定。這樣,拿到高級最高等,差不多也可以退休了。這樣的制度安排,倒是讓人活到老,爭到老啊。但是這種制度的設計者們有沒有想過,當一個教師一生的努力就是追求外在的評價和認可,這究竟值得贊許還是認人悲嘆?
其實,又何止教師如此,校長們也同樣在為爭這個級搶那顆星而東奔西跑上竄下跳。
當教育中人已經無法靜心思考孩子們的成長,無法靜心思考自己的職業倫理,當教育的一切都為外在規定所捆綁,甚至淪為名利場時,這樣的教育還能剩下多少教育的意味?此時的教育者還能享受到多少教育工作本身帶給自己的樂趣?
這樣的鬧騰中,學生只能成為教師和學校手中的工具,成績差、沒有特長的學生自然不受教師待見;而教師也只能成為校長和學校的工具,應試水平不夠、抓學生不狠的老師當然評不了優秀拿不到職稱。同樣,重點學校看不起普通學校,普通高中看不起職業中學,而教師群體羨慕編輯這一行,也都不難理解了。
我想,之所以很多朋友會覺得我當年離開報社回到學校會有失落感,認為我在職校當老師是屈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教育被扭曲得太嚴重了,現在的教師——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師太沒有職業尊嚴了。
如果你只關心“這條小魚在乎”,你愿意看見皇帝沒穿衣服,也就無所謂失落,無所謂屈才。
二
扯到這兒,或許會有人質疑:那你為什么在職校干了四年又離開了?
這四年里,我帶出了一批學生(11外貿5班,11級學生中入學成績最低的幾十個學生組成的一個班),我給學生上過心理健康、職業生涯規劃、職業道德和法律、哲學與人生、政治經濟生活、現代禮儀等課程;同時,為兩個專業部的同事講過教育寫作,也在區職校政治教師教研活動上做過講座,給退役軍人培訓班講過課,還連續三年為本專業部就業班學生作實習前的指導,針對本校文化課課程改革向學校提交一份數千字的書面建議。個人通過培訓考試獲得了國家心理咨詢師二級、國家職業指導師二級兩本證書,出了《重建教師尊嚴》《心平氣和當老師》《教師職業生涯十大誤區》和《怎樣的愛才合適——做一個不過分的家長》四本教育類小書,共發表了大概七十篇左右的文章,寫有百萬字的工作日志,也算沒有虛度這四年時間,對得起學生和自己。
關于職校經歷,之前我寫過三篇相關文章《白天不懂夜的黑——我在職校這三年》《三年班主任,一地雞毛》以及《還在教育的邊上》,拙著《心平氣和當老師》里也有專門一章《職校工作日志選》,這里就不再重復敘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網絡搜索找到相關文字。
我就說說為什么堅持不下去而選擇離開。
2014年12月12日下午,在三聯韜奮圖書館的一次研討會上,錢理群在總結發言時說,“告別的時刻到了”,因為“我已經不理解當代的青年了,……網絡時代的青年的選擇,無論你支持他、批評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因為我已經不懂他們了。”
雖然錢理群老師比我年長許多,我也沒有錢老那樣豐富而坎坷的經歷,但是讀到這段話,還是心有戚戚。
是的,和錢理群先生一樣,我也看不懂現在的職校生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理解他們的,但他們并不需要我。“無論你支持他、批評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這些話,也正是我的感覺,是我想說的。
剛到職校時,我還偶爾可以準備好PPT給學生講講時政新聞,還可以讓學生提出他們感興趣的話題然后進行課堂討論。慢慢地,新的一批學生對校園外的世界不感興趣了,網游、八卦、韓劇、鬼片這些除外。我開始剪輯《職來職往》《非誠勿擾》這樣的熱門節目,和學生討論求職、交友等我以為很實際的問題。開始也不錯,越來越多的學生慢慢習慣了先看片斷再發言討論這樣的教學模式。但新一批學生來了,他們愿意看視頻,卻不想討論。
職校四年,真的非常能夠體會到“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覺。這是一個教育者不應該說出來的話,所以我知道我不應該再待在學校了。在給學校的辭職申請中我這樣寫道:“曾經我以為職校學生有許多是處于迷茫之中,我可以對他們有所幫助。可是四年下來,我發現越來越多的職校生其實并不迷茫,他們只是不想努力。學生懶,這是我作為教師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也正因為這樣,四年時間我曾嘗試過對話式教學、游戲式教學、案例討論、視頻觀摩討論,但幾乎毫無效果。”
我知道習得性無助,也看過《熱血教師》《死亡詩社》《放牛班的春天》《超脫》等教育電影,或許就像有朋友說的,我不應該有太強的引導意識,而是應該從和他們一起嗑瓜子一起吃飯一起踢球開始。的確,從心理咨詢角度來講,有一種方法是幫助一個人回到原點,快速重新成長一遍。在這個過程中看清楚一些問題的本質,同時滿足自己當年未曾滿足的愿望。如此,或許就會產生一個全新的自我。
但每次想到這里,我就感覺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沒有能力幫助這么多人重新成長一遍。內心深處,我甚至對這種方法很有抵觸。或許,這是我的一大局限。
我們紹興有個“偷白鲞,咬奶頭”的故事。一位母親從小對孩子百般嬌慣,兒子小時偷人家白鲞,母親不以為怒,反而稱贊。結果兒子長大后成了江洋大盜,被判極刑,臨刑前借口再吃母親一口奶咬掉了母親的奶頭,表達對母親“養而不教”的惱火。
故事中這個兒子的做法,完全是推卸自己的責任。一個人的行為習慣和小時候的家庭教育當然是有極大的關系,但人不是只生活在家庭里,更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自己的行為與他人利益發生沖突,這其實是每一個人自我成長的好機會。每個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沖突中慢慢學會爭取、妥協、聯手......
不得不承認,在職校生面前,我越來越沒有存在感。四年里,愿意參與教學討論的學生越來越少,愿意和我課后交流的學生越來越少。到最后,我在課堂上給學生介紹電影,他們很感興趣,巴不得上課就看這片子了。放學回家,卻沒有人愿意自己去網上找來看。
在我離開學校前后兩個月里,學校發生了三起家長進校毆打教師的事件,幸好都沒造成大礙,但對教師的心理影響應該不小。都是局內人,不用我多說,相信大家自有感受。
其實,我最喜歡做的,就是教書。站在講臺上,看學生輪番上陣言語激辯;回到辦公室,翻開學生隨筆看他們或談觀感或發議論或寫心事;再找機會,一起外出踏春賞雪搞調查做公益,多好的事……
責任編輯 黃佳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