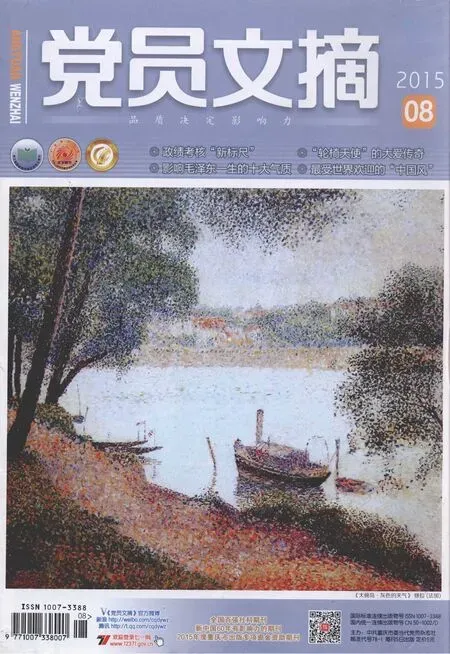尋找嘎麗婭:倒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
2015-05-30 10:48:04王漢超袁泉
黨員文摘
2015年8期
王漢超 袁泉

編者:17歲的嘎麗婭消失在戰火的煙塵里。
一寸山河一寸血。歷史不是空洞的,它之所以厚重,是因為由無數個鮮活的生命書寫而成。
一個17歲的女孩,帶著我們從冰山一角看到歷史的宏大。歷史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為每個民族的歷史都有許多令人尊敬的英雄。
時代呼喚“發現嘎麗婭”。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尊重我們的價值觀,尊重我們的精神堅守。
這正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動力源泉。
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漸漸傳開。
8月11日,她走進黑龍江綏芬河日軍要塞勸降。
她是嘎麗婭·瓦西里耶夫娜·杜別耶娃,身上流淌著中俄兩國的血液,人們習慣叫她張嘠麗婭,大人疼愛地叫她嘎拉。
8月11日,嘎麗婭的母親菲涅和弟弟張樹烈目送她離開,再也沒能等到她回來……
那一年,嘎麗婭17歲。
2009年,嘎麗婭“重生”。
綏芬河市民用青銅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鐫刻著:“我們的友誼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我們將銘記過去,展望未來。”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給綏芬河市民回信中的一段話。
一次寫入歷史的折返
天長山就在城北,但對于綏芬河,那是一個巨大的謎。
南起吉林琿春,北至內蒙古海拉爾,在曾經“滿蘇”“滿蒙”近5000公里的“國境線”上,日本關東軍當年筑起龐大而隱秘的軍事工事,進可攻,退可守,隨時準備對蘇開戰。
侵略者盤踞中國東北14年,苦心經營要塞就達11年。將綏芬河鎮北兩座山峰命名為天長山、地久山,寓意不言自明。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