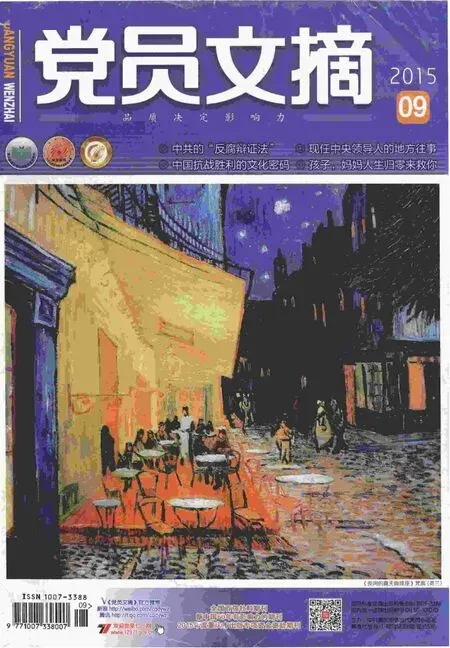誰(shuí)都可以是天使
豐高飛
兩年前,我和太太從北方的一座小城辭職來(lái)到杭州。太太在一家報(bào)社做編輯,我則繼續(xù)做著我的老本行——電臺(tái)DJ。
我們借住在朋友的一棟老宅里,院子里有一扇鐵門,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鎖,院子里的每戶人家都有鐵門鑰匙。我們家的鐵門鑰匙一直以來(lái)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樣形成的習(xí)慣,每一個(gè)住在院子里的人從外面回來(lái),哪怕是大白天,也要順手把院門鎖上。
事情發(fā)生在那個(gè)炎熱的午后。
那時(shí),我做的是下午3點(diǎn)檔的一個(gè)音樂(lè)節(jié)目。我通常是在直播開(kāi)始前的半個(gè)小時(shí)趕到電臺(tái)。在夏天我有午睡的習(xí)慣。太太那天正好在報(bào)社拼版,中午不會(huì)回來(lái)。
平時(shí)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過(guò)了頭,醒來(lái)的時(shí)候離直播只有半個(gè)小時(shí)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來(lái),走到院子里,看到鐵門上的大鎖,這才想起鑰匙在太太的手上。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還有其他人,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整個(gè)院子里只有我一個(gè)人。
我手忙腳亂了起來(lái)。院墻很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墻”,房間里又沒(méi)有裝電話。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腳。我站在鐵門邊,像是一個(gè)渴望自由的囚犯。
然后,通過(guò)鐵門縫隙我看到了他。他是一個(gè)正好從弄堂里經(jīng)過(guò)的小乞丐。他還是一個(gè)孩子,不會(huì)超過(guò)10歲。他穿著一條臟兮兮的短褲,頭發(fā)零亂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緊緊地抓著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裝滿了寶物。
我喊住他,我想請(qǐng)他去巷口給我太太打個(gè)電話。在我開(kāi)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應(yīng)該先給他一點(diǎn)零錢作為報(bào)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