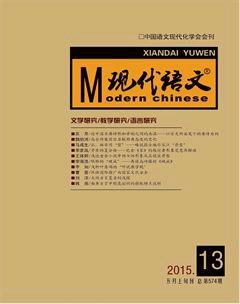艱難的“破戒”
李海浩
摘 要:本文借鑒秩序與個體的關系、日本人論相關觀點,對島崎藤村《破戒》主人公瀨川丑松覺醒后挑戰秩序的過程進行了分析。秩序的強大力量使瀨川四面樹敵、內心負疚、受內心異己壓迫、逡巡猶豫,直到退至墻角才真正行動。他的破戒頗具日本特色——平衡各方、避免直接沖突,以向學生和同事“懺悔”的形式向覺醒的內心贖罪。雖千難萬險但結局并不堪憂,絕望中有希望。
關鍵詞:內心 秩序 艱難破戒 “懺悔” 希望
引言
《破戒》無疑是追求近代自由、探索近代自我的作品。[1]瀨川丑松明知自己正確,卻一再猶豫,莫說光明正大地行動,卻常常表現得好像自己犯了罪。是什么束縛了他前進的腳步呢?
在筆者調查范圍內,以往對《破戒》的研究主要涉及對創作背景特別是當時日本社會歧視“新平民”狀況的實證考察、西方基督教“懺悔”意識對作者的影響以及社會批判意義等方面,但對破戒過程的艱難及最后結局的考察似仍有余地。為此筆者欲借鑒秩序與個體的關系、日本人論的相關觀點解讀《破戒》。
一、服從秩序
破戒的敵人不是特定的個人,而是業已形成的秩序。挑戰秩序難在何處?尼采指出,在權威面前人不許思考,更不用說批評,所能做的惟有服從。[2]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發現,人類長期進化形成等級社會,服從是在這種社會生活的先決條件。且人有與生俱來的服從潛力。[3]人類無法像計算機那樣進行嚴謹的邏輯推理,在一定時期內處理的信息又是有限的,因此常放棄邏輯思考,根據已有圖式進行直覺判斷。已有圖式一旦形成基本不會改變,即便這種圖式不可信或者本來便是錯誤的。[4]這意味著,秩序一旦確立便會產生強大的約束力,即便其本身帶有一定缺陷甚至犧牲了部分人的利益。面對權威,服從總是大多數人的選擇。20世紀60年代的米爾格拉姆實驗[5]發現,日常生活中負責且正直的“好人”“無不麻木地屈服于權威的命令,做出了無情而嚴重的行為”[6]。
挑戰秩序的難度可想而知。尼采寫道:“任何微不足道的變動都不得不付出精神上的和肉體上的血的代價。”突破習俗只有一條路——自己動手創造習俗。[7]
(一)四面樹敵
權威系統建立的基礎是所有人都被放在一個等級結構的某個位置。[8]《破戒》就發生在這樣的等級社會。而且,日本人相信秩序和等級制度,在服從準則,而非企圖修改或反抗準則的情況下顯示勇氣和正直,認為性格的堅強顯示于服從而不是反叛中。[9]士農工商的底層是一致被歧視的“賤民”,綿延數百年浸透人心。盡管有極大的不合理性,大多數人還是持贊成或中立立場,其中甚至包括部分受害者。瀨川一家就默默忍受,從未想過改變。恰如尼采所述,傳統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權威,聽命于它不是因其內容有益,而是因為它是命令。[10]
于是覺醒的瀨川丑松發現面前除了少數“衛道士”,還有包括中間派、受害者在內的大多數人。他仰慕豬子蓮太郎,但先要面對父親的告誡,叔父反復提醒遠離“新平民”,好友土屋銀之助也勸他遠離豬子思想。周圍對“新平民”的歧視令他不寒而栗,目睹大日向遭逐后瀨川深受打擊。
哀憐、恐怖、千々の思は烈しく丑松の胸中を往來した。病院から追われ、下宿から追われ、その殘酷な待遇と恥辱とをうけて、黙って舁がれて行くあの大盡の運命を考えると、さぞ籠の中の人は悲慨の血涙に噎んだであろう。(?破戒?)
覺醒的瀨川成了“孤家寡人”。
(二)內心負疚
挑戰秩序是“罪”,要受道德譴責。尼采指出道德是對習俗的服從,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因為所有原始狀態的人類都把“惡”與“自由”“個人”等當做一回事。[11]汪民安認為在上述標準下,善惡是針對個體對待習俗的態度而言的。遵從習俗為善,反之為惡。這種標準制造出一大批服從性的道德愚民,阻遏了新的想象和行動。[12]于是“道德成了創造更新更好習俗的絆腳石”[13]。里克爾分析創世神話指出,“上帝”只賦予人有限的自由,構成價值權威。創世后權威成了禁止,人只知道強制限定,突破限定便是墮落。[14]可見人對權威、秩序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僅會服從。任何突破,哪怕是正義的都觸犯禁忌。秩序一旦形成,任何挑戰都會成為“罪行”。
瀨川只不過追求新社會已經賦予他的權利。但是,一個行動不是傳統使然,而是出于其它動機,如對個人有利,那么連行動者本人也會覺得它是不道德的。[15]可見即便他人尚未覺察,只要與現行秩序悖離,行為主體也會受到內心譴責。這正是瀨川擔憂的。尼采指出,由于被人——確實也被他們自己——目為壞蛋和害群之馬,那些不可多得的人才忍受的痛苦是難以想象的。他們“不得不背負起良心的十字架”。[16]瀨川正是如此,他由自慚形穢發展到鬼鬼祟祟,不時感到有人跟蹤“正在作惡”的自己,隨時可能被戳穿身份。
誰かこう背後から追迫って來て、自分を捕まえようとして、突然に?やい、調理坊?とでも言うかのように思われた。こう疑えば恐ろしくなって、背後を振返って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破戒?)
沉重的內心負疚讓瀨川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三)內心異己
覺醒的人有雙重傾向——掙脫舊秩序實現破戒,與屈從舊秩序維護既得利益。文中這句話耐人尋味。“自分だって社會の一員だ。自分だって他と同じように生きている権利があるのだ。”這當然可以理解為瀨川欲消除對“新平民”的歧視,實現真正的平等。不過,遵從父戒隱瞞身份同樣可在現秩序下實現上述愿望。一個愿望有兩種矛盾的實現方式。一方是豬子大義凜然,一方是父親諄諄教誨,瀨川在中間猶豫不定。得知豬子病后瀨川偷偷寫信一節很有象征意義。
寢床へ入ってからも、丑松は父と先輩とのことを考えて、寢られなかった。(?破戒?)
兩種形象、兩條道路、兩個力量將他拉向相反的方向。結果還是苦惱地原地踏步——和豬子靠攏的設想沒能實現,只寫成一封普通的問候信。
書けるものなら丑松も書く。それを書けないというのは、丑松の弱點で、とうとう普通の病気見舞いと同じものに成って了った。(?破戒?)
如上述引文寫信失敗由于瀨川本身的弱點,他自己也是前進的障礙之一。
傳統社會加諸人的種種束縛在長期歷史過程中會逐漸化為人內心世界的一部分。黑格爾指出,“奴隸感覺到自為存在只是外在的東西或者與自己不相干的東西”“在陶冶事物的勞動中則自為存在成為他自己固有的了”[17]。里克爾認為創世神話中蛇的形象也可能是我們并不清楚意識到的我們自己的一部分。[18]巴特勒在福柯觀點基礎上再進一步,“權力將自己強加于我們,因被其壓力弱化,我們最終將內化或接受它的條款。”[19]父戒(背后是舊秩序)最初對瀨川僅是天外之音,然而如上述論斷一樣深入內心,形成內心異己——好比奴隸意識中的自為存在。
忘れるなという一生の教訓のその生命——喘ぐような男性の霊魂のその呼吸——子の胸に流れ伝わる親のその血潮——それは父の亡くなったと一緒にいよいよ深い震動を丑松の心に與えた。
?忘れるな?(略)その熱い臨終の呼吸は、どんなに深い響となって、生殘る丑松の骨の髄までも貫徹る(略)亡くなった父が丑松の胸中に復活る(?破戒?)
內心異己要求服從舊秩序,隱瞞身份的瀨川也是舊秩序的受益者——教師工作體面,深受學生擁護,校長也要敬他三分。他還認為目前的社會地位是他與風間志保維系情感的前提。既有秩序與個人利益緊密結合,內心異己成為破戒的強大敵人。福田清人等也認為破戒的最大阻力來自自欺欺人的生活,而這對瀨川本身是有利的。[20]
父親去世,瀨川好不容易邁出行動的一小步[21]時,父戒竟從心底而來!
「隠せ」
という厳粛な聲は、その時、心の底の方で聞こえた。急に冷たい戦慄が全身を伝って流れ下る。さあ、丑松も少し躊躇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先生、先生」と口の中で呼んで、どうそれを切出したものかと悶いていると、何か目に見えない力が背後に在って、妙に自分の無法を押止めるような気がした。(?破戒?)
內心異己的突然出現令其措手不及,一次吐露內心的機會就此錯失。可見,內心異己的威力非同小可,只要還有妥協希望便很難克服。打破舊秩序首先必須清除內心異己,需要進行反復激烈的思想斗爭。這樣內耗便占去了相當的時間與精力,使他難有余力挑戰秩序,只能終日徘徊。
二、中間路線
意欲破戒,可既留戀既得利益,又不想觸犯眾怒,更不愿背上破壞秩序的罪名。四面樹敵、內心負疚、內心異己,瀨川步履蹣跚。只有被形勢逼至墻角,“懸崖上的生活”再無可能時,內心負疚才會減輕,內心異己才行將就木,覺醒的人才有可能行動。
在此之前,對立雙方反倒保持微妙的平衡。校長有意排擠瀨川,但在高柳利三郎傳播謠言前也沒抓到什么把柄。勝野文平提出瀨川身份問題時,他起初還表示懷疑。舉步維艱的瀨川也曾想到“中間路線”。
少年の昔の楽しかったことは。(略)もう一度丑松はそういう時代の心地に帰りたいと思った。もう一度丑松は自分が穢多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てみたいと思った。もう一度丑松はあの少年の昔と同じように、自由に、現世の歓楽の香を嗅いでみたいと思った。(?破戒?)
重返懵懂時代做個“快樂的傻子”,一切苦痛都會煙消云散。不過,上述思緒轉瞬即逝,最后浮現在眼前的是風間志保:
終には、あの蓮華寺のお志保のことまでも思いやった。活活とした情の為に燃えながら、丑松は蓮太郎の旅舎を指して急いだ(?破戒?)
正是風間與豬子“合力”將瀨川拉回正軌。對風間的思念是感性的青春萌動,對豬子的仰慕是對新秩序的理性追求。這股合力把瀨川帶離了中間路線。
三、破戒
(一)“懺悔”——似是而非
破戒前的平衡終究是“火山口上的蓋子”,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土崩瓦解。高柳把謠言傳得沸沸揚揚,校長蠢蠢欲動。瀨川本來對舊秩序不平,此時又面臨傷害,可謂已退至墻角。再不行動必然身敗名裂——落下“下賤”“虛偽”名聲并遭驅逐。
瀨川最后的“懺悔”表面順理成章,實則大有文章。“懺悔”前提是犯罪,那他犯了什么罪過呢?看下文似乎是“隱瞞真實身份,忝居教師之列”。
?もしその穢多がこの教室へやって來て、皆さんに國語や地理を教えるとしましたら、その時皆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略)実は、私はその卑賤しい穢多の一人です?
?今まで隠蔽していたのは全く済まなかった?(?破戒?)
但其內心并不覺得“賤民”當教師有何不妥,他后悔的是沒在豬子生前向其吐露心聲。如此“懺悔”可謂表里不一。
這實際正反映了破戒之難。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人生由“忠”“孝”“人情”等若干規則詳細的圈子構成。評判一個人不從整體出發而是具體到特定圈子中分別評價,人需要在各個圈子之間保持平衡。[22]放到瀨川身上,他涉及職場、家庭[23]、朋友三個圈子。此外還新建了一個圈子:近代理念及青春萌動要求自由、平等并挑戰舊秩序。由于遲遲未付諸行動,這個圈子可視為“內心圈”。
本尼迪克特指出沒有“惡”圈子,人在具體圈子中按規則行事都是行善,且是在服從準則,而非企圖修改或反抗準則的情況下顯示勇氣和正直的秉性。性格的堅強顯示于服從而不是反叛之中。[24]瀨川果然試圖遵循所有圈子的準則,破戒也不過是按內心圈準則行事。這似乎可以解釋平野謙提及瀨川的矛盾——一方面有慷慨悲壯的精神,另一方面卻虔心懺悔。[25]這是因為他在分別按內心圈和職場圈的要求行動。
不難發現同一行動在上述圈子的評價截然相反,這樣保持平衡便十分困難。
職場圈中身份暴露,校長逐客。既然無法在學校立足,索性魚死網破公開身份,遵守現秩序“被迫”出走,以悲情換同情。瀨川受學生擁護,社會對豬子式的行動也非一味排斥,要求開除瀨川的議員也承認像豬子那樣公開身份反倒喚起人們的同情,為人接受。瀨川“懺悔”表明身份并請辭,在學校自上而下公布驅逐決定前占領了道德高地。這種遵守秩序前提下的“悲情”正是博取同情的利器。按前面本尼迪克特的觀點,日本人給予“勇氣”“正直”的正面評價,其前提是服從秩序。教人屈從悲慘命運的故事在日本是顯示進取心和堅定決心的故事。日本小說與戲劇結局很少皆大歡喜,對主人公自我犧牲的憐憫與同情在觀眾中暢行無阻。[26]瀨川的行動恰好如此,必然獲得好評與同情,學生們甚至為他集體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