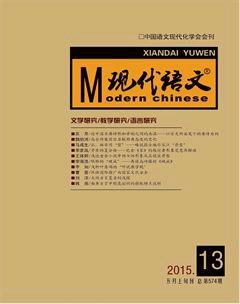論中國古典詩歌和帝制之間的共謀
蘇芹
摘 要: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探尋出的“相關宇宙論”出發,以唐詩為例,提出了在中國古典詩歌和帝制之間存在著共謀的觀點。本文通過對宇文所安這一觀點的剖析探尋出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立場,借此可為當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宇文所安 古典詩歌 帝制 共謀
一、引言
在中國,古典詩歌一直被視為最高文學成就,詩歌使中國文學史幾乎變成了一部詩歌史,它讓中國變成了一個未被超越和不可超越的詩的王國,也正是因為古典詩歌,詩性文化成為了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古典詩歌在中國用途廣泛,從孔門詩學的“興觀群怨”(《論語·陽貨》)到后來儒家理論的“溫柔敦厚”,源遠流長幾千年,詩歌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文學形式,“詩教”構成了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的基本精神。學者林語堂曾言:“中國的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蓋宗教的意義為人類性靈的抒發,為宇宙的微妙與美的感覺,為對于人類與生物的仁愛與悲憫。……詩又曾教導中國人以一種人生觀,這人生觀經由俗諺和詩卷的影響力,已深深滲透一般社會而給予他們一種慈悲的意識,一種豐富的愛好自然和忍受人生的藝術家風度。”[1]雅潔可敬的古典詩歌、怨而不怒的古代詩人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認識。
心好中國古典詩歌的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用他的異域之眼,透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視角卻看到了在中國古典文學和帝制之間存在著一種共謀。“這種共謀在那種為帝制代言及御用的文學的公共形象中較為常見。在明顯的私人詩文中,這種大一統帝國的價值仍然得到表現。”[2]人們都普遍了解文學和社會的關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在古代,受儒家濟世懷抱和用世思想的嚴重熏陶,詩人們的政治理想大于其文學理想,他們沿著儒家為他們設計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的康莊大道積極入世、賦詩言志,流自肺腑的高風亮節贏得后人無限的贊譽與敬仰。但宇文所安卻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探尋出的“相關宇宙論”出發,結合中國詩歌的創作背景和詩賦取士的對象來闡述詩歌與帝制之間合謀主張,通過言之有據又不無思辨地演繹、推理和猜測,去重新衡量帝制下的中國古典詩歌,帶人進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閱讀新體驗。
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相關宇宙論
關于中國古典詩歌所隱含的相關宇宙論,宇文所安是在《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一書中通過對杜甫的《旅夜書懷》和華茲華斯的《威斯敏斯特橋》的比較后提出的,這種對比直接顯示出了中西詩學觀念的差異:中國的古典詩歌包含有真實自然性,西方的詩歌則體現了超驗隱喻的意義,中國的古典詩歌較之西方詩歌具有“非虛構”的特點。宇文所安這一命題的提出源自他的一種宇宙認識論——相關宇宙論。在宇文所安看來,自然宇宙是一個過程、事物和關系的系統,系統之間相互聯系,這種相互關系由“類比”這一原則制定,在漢語中最貼切的詞就是表示“自然的范疇”的“類”。“類”是中國人從自身的感官經驗出發,通過“直覺”和“聯想”推導出的某種共通的結構或功能的對應,它代表了一種宇宙秩序,讓世間萬物之間有一種聯系,即一切事物都只能在與另一個事物的聯系中得到理解,它們在同一時刻既是不同的,又是相應的。宇文所安以《淮南子》宇宙起源論中的“天/地、陽/陰”為例來說明宇宙中行動和事件被秩序化,且宇宙一直沿襲著“相關物的形成(陽/火/日)”和“對立物的形成(陽/陰;火/水;日/月)”這兩種基本衍生線變化,宇宙起源論改編了自然的結構,人們通過“相關物”和“對立物”的類比去了解自身所棲居的世界,由此形成一種宇宙認識論。他又從詞源學的角度追溯到書寫文的最初形式,即《易》的三卦畫和六卦畫這種最基本的圖式,作為文字的“文”可以理解成為天、地合一,它最初是被當作與祖先交流的一種媒介,他還引劉勰的《文心雕龍·原道篇》來解釋文學為之“文”,是作為某種潛在秩序得以顯現的審美圖式,或者說“文”就是某種潛在秩序的外部形象。宇文所安筆下所強調的“文”都與祖先崇拜、宇宙法則有關。而“文”的顯現是通過作為人的意識、思想和情感場合的“心”來完成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通過“物”到“心”再到“文”,使“感物”成為“感應”,一種“同情的共鳴”由此產生。詩人是宇宙三才者之一,擁有敏感的“心”,“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4]。“文”代表了宇宙秩序顯現過程的圓滿和充分實現的形式,詩人通過對宇宙世界的體驗,察知其內在秩序,并加以真實記錄使之得以顯明,這是一種從內在意義到反映意義的認知活動。比起物理學家心中的“宇宙”,宇文所安筆下的“宇宙”更接近于哲學家眼中的“宇宙”。“哲學家說到‘宇宙時,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體,相當于中國古代哲學家惠施所說的‘大一,可以給它一個定義,乃是:‘至大無外。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5]。
但另一方面,宇文所安也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中雖然包含了自然與人事的不斷整合,或宇宙秩序的圓滿顯現,卻體現了詩歌與帝制之間的一種共謀。因為,在人類意識中并不存在某種先天的秩序體系,它們都是后天學習和教育獲得的,沒有哪個過程不具有功利性,每個對宇宙秩序化的體系后面都潛伏著經濟和政治動機,帝國要把這種宇宙秩序帝制化,并且使人們相信宇宙-帝國體系的普遍性和永久有效性,為了不讓這些真實的動機暴露出來,為了鞏固、維系這種后天習得的宇宙秩序體系,中國古代的帝王都借助“文”的宣傳和教化力量,因為“文”是對宇宙的認知和察覺,“文”中蘊含著宇宙結構相互聯系的普遍法則,“文”是宇宙秩序的顯現過程和實現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并非由歷史進化或神圣權威創造出的任意符號構成,而是通過對世界的觀察而呈現。所以,“文”既是一種方法論,一種信仰,也是一種權利,一種實踐。“只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什么曹丕(187-226)能夠把文學理解為統治者最有意義的事,為什么經歷若干世紀,直至20世紀,皇帝或者當權者(毛澤東、蔣介石等),除了作為知識精英之外,還一再以書法家和詩人的身份出現”[6]。文以載道,古代帝王都擅長把“文”引導和貫穿在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情感和政治觀念中,通過“文”的感染和陶冶,建立起了一個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狀態緊相關聯的帝制宇宙。對詩人而言,一方面,他是“天、地、人”三位一體宇宙中的一部分,是自然之人,他用“心”通過“文”去認知宇宙中的“類”,并借助詩歌使這種潛在的宇宙秩序顯明化。“為感天動地,為喚醒神靈,只有詩才是合適的手段”。但詩人也是社會之人,通過自然投射到社會,詩人就成了文(與武相對)人或仕人,他們努力將自我置身于秩序化的帝制宇宙中,無論是積極尋求入仕,還是無奈厭世退隱,他們都是在用帝國政治上認可的詞句去理解和表達人類精神的深層情感。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被確定為權利機構的中心,詩人和統治者的關系被確定為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山盟海誓的集體。
三、中國古典詩歌與帝制之間的共謀
帝國需要詩歌讓宇宙秩序帝制化,或讓詩歌的“相關宇宙論”為自己的帝國體系塑形,使得臣民相信宇宙-帝國體系的普遍性和永久有效性;詩歌作為一種自然的“文”也要在帝制宇宙中求生存、謀發展,在互惠的關系之下,帝制承認詩歌,詩歌承認帝制。宇文所安以被后人視為古典詩歌高峰階段的唐朝為例,認為無論是唐朝的宮廷詩、應試詩,還是隱逸詩、山水詩,都是為了得到統治階層的贊許而言說的,它們之中蘊含有帝王的威嚴、力量和意志。
其實,宇文所安選擇唐詩來闡述其觀點的重要原因就是科舉制度在唐朝的確立和執行,這一措施對詩歌的發展影響重大。首先,在以楊隋和李唐為首的關中門閥取得了全國政權后,門閥士族已走向下坡,非身份性的世俗官僚地主日益得勢,官階爵祿替代了閥閱身份,成為唐代社會最高榮譽所在。唐帝國為了鞏固其政治,制定和執行了通過科舉從庶族地主和大家族的遠支中選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門大族對仕途的壟斷,大批不用賜姓的進士們,由考試而做官,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而這種決定士子前途的考試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風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創作;與此同時,古代的帝王都知道,詩既是樂,也是禮,詩中含有“類”“心”和“文”的力量,帝王以及由他所代表的中央不但要成為政治的獨裁者,還要成為文學的獨裁者,唐太宗的一個宣言就是最好的印證:“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詩又是一個人才能的標志和價值彰顯的手段,英才借此得以被發現和提拔,因此愛詩和懂詩對帝國政體的維持很重要。顯然,帝王們已經掌握了一種驅盡天下人才為其效力、盡忠的最佳辦法,那是一種“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太宗語)的得意與自信。其實詩歌根本不能證明應試者服務大眾的能力,只能說明他們持有或接受了帝王政權的觀點,并用其認可的措詞來理解和表達對這個世界的情感——詩是一種忠于中央政府的象征行為。在為帝制代言的應試詩中修辭活動受到嚴格限制——政治化的合法情感、只關注外界可以關注的方面、將所有物體和事件納入到一個平行化的帝制宇宙中來。在其他種類的詩歌中,帝國意識也以種種面貌體現在詩歌中。在詩歌話語領域中牽涉到的所有可能與朝廷產生沖突的敏感話題或禁忌都被朝廷過濾或中和掉了,政府支持在詩文中設立一套替代之物,用另一套知識分子術語來平衡這種破壞欲。詩人對于那些可能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的趣味和激情也一定是訴諸沉默或平庸的替代物,由此宇文所安總結出“詩的概念存在于科舉考試的運用中,存在于行卷中,存在于將詩作為史傳的替代物而使自己留名于后世的觀點中。”
另外,宇文所安還在對唐詩的解讀中,提出了兩個概念“宮廷詩”和“京城詩”,在初唐,詩歌創作的中心是在宮廷和王府。宮廷詩主要包括宮廷宴會詩、宮廷詠物詩、科舉考試中的應試詩、朝臣之間的酬贈詩以及其他涉及各種公務禮儀活動而制的應制詩。宮廷詩有著矯飾、拘謹的形式,雅致、華彩的內容,在內容上也多是為了歌功頌德、娛樂消遣,宮廷詩的流行正好說明了文學其實只是宮廷玩物,虞世南、上官儀這些專門的語言大師仍是皇帝弄臣,處于“徘優蓄之”的地位。詩人們爭先恐后地利用詩歌作為對帝國忠誠的肯定,從而獲得賞識和提升,那些堂哉皇也的煌煌詩篇,也不過是歌功頌德、點綴升平之作,再加上一點所謂“諷喻”之類的尾巴以娛樂帝王而已。盛唐詩由宇文所安稱之為“京城詩”的現象所主宰,它是上一世紀宮廷詩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詩涉及京城上流社會所創作和欣賞的社交詩和應景詩的各種準則,……京城詩雖然不像宮廷詩那樣受到嚴格的規范限制,我們在其中仍然看到了詩體和題材規范的強烈意識。與宮廷詩一樣,京城詩很少被看成是一門獨立的藝術,而是主要被當作一種社交實踐;人際關系和社交關系的網。”他將京城詩放置在宮廷、王府、權臣、朋輩這四種社會背景下對唐詩重新進行解釋。在他眼里,有些詩人在忙于求仕的同時,也寫寧靜的山水詩,但對于熱中奔競的自己或同流,只是起了清涼劑的作用,詩里的自然并不與他們的真實意緒發生密切的關系,盡管他們追求玄遠,但仍然心念功業。在宇文所安看來,李白擁有“逸人”的聲譽,這也是皇帝喜歡他的一個重要因素,他的狂誕行為并不是如同某些傳記作者所說的是蔑視權位的真實表示,他“渴望被賞用,表示樂于進入宮廷,當他被迫離開時,他發出了激烈的抱怨。狂野本是對他的期待,他并非有意地要對皇帝挑戰”。孟浩然在歷史上是一位“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李白《贈孟浩然》)的人物,但在宇文所安看來,這種輕視官府生活的形象實際上是進入官府生活的一條途徑,他的不少詩歌都表明他希望獲得那種可以謀得一官半職的賞識,比如在《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的委求援引、《歲暮終南山》中的自怨自艾,都深刻傳遞出了詩人求仕心切、功名未就、宦途渺茫的憂慮焦急。在《彭蠡湖望廬山》詩里,詩人望著廬山,“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表達了其超脫隱逸的思想,但又以“我來限于役”表示因公事無法立即歸隱;然而作為妥協,他承諾“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表達他將來要來廬山歸隱的思想。這似乎印證了“大多數盛唐詩人或者官府任職,或者希企進入仕途,許多著名詩人所表達的對于仕途的厭棄并不真切,當誘人的任職機會出現時,他們幾乎不會有放棄的實際行動。”對詩人而言,無論是中國儒家讀書仕宦的傳統熏陶,還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的強烈誘惑,自身在宇宙中的價值和地位終究難以擺脫帝制的影響,如陳子昂在《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三)》中所哀嘆地那樣“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詩人的才華文采就是被統治者用來點綴升平,增飾“治績”的,作為人就不免為帝王所轄,名列朝班,喪失了在政治上抉擇的自由,即使有隱遁之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終仍難逃統治者的掌控。詩歌是一種獨白和社交的特殊形式,是一種行為,但這個行為不是自吟自唱,仍是為了被認知,被認知就是一種針對其他人的行為,是一種公共行為,“它總是令讀者進入帝國政府這個最大的公共的語境。沒有領會政府和出仕對人的生活和想象施加的特殊情感力量,中國文學傳統和文明就不可能被理解”。
宇文所安還認為,中國的詩歌中只能表現出兩種處境——入仕與歸隱。這種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得到了印證。在中國,儒道互補是兩千多年來的一條基本思想線索,儒家思想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道家則強調人內心自然自動的秉性,表面上看,兩者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但實際上它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補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態以及其藝術意念。”當一個詩人供職于朝廷,他會發揮儒家正統的詩歌功用,是為帝制代言及御用文學的最佳形象,談及他的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他的思維是政府思維,他的語言是政府語言;當他迫于工作壓力或受到政敵排擠而渴望隱逸時,即使心懷濃郁的怨傷情緒,但在表現形式上仍然溫柔敦厚、哀而不傷,無論是陳子昂的“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的滄桑感喟,還是王維的“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的憤懣不平,詩人們都不會敵視中央政權,更不會想著付諸行動去改變現實世界,他們一方面消極避世,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自我心理調節,“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王維《歸嵩山作》),“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早發白帝城》)。詩人“對外部世界現狀的反抗心理,最通常是化為隱居遁世者所抱定的一聲響亮的‘不——逃避現實,拒絕有所作為,據不參與社會,心中不存期盼。他的最高信條是:‘讓而不爭。”而當一個詩人真正厭世而選擇退隱開始寫私人詩歌時,詩人的隱士身份和詩中的“隱逸”語言都能充分說明兩點:第一,在隱遁與服務政府的二選一中,詩人選擇前者完全是出于一種純粹向往心靈寧靜的個人傾向,它解除了與當地經濟和政治利益任何明顯的聯系,在帝王眼里,地方利益總是對中央政府構成基本威脅,成為謀反的最潛在力量,于是,詩人的這種選擇仍是在間接地向帝王及其中央政府權威表達順從。第二,在西方,宗教是一種獨立的權利因素,它幫助人們認識到一種不依賴權力中心的個人地位,但在中國,尤其是在唐朝,道教、佛教和儒家一起成為了帝王實現帝國統一的工具,中國的文人對帝王及其中央政府有一種精神上的依賴性,當一個詩人放棄儒家傳統的入世思想尋求辭官歸隱,他信奉道教、清凈無為或者皈依佛門、大徹大悟,在他們的山水詩、玄言詩里充滿了寂靜主義和日常瑣事美學,他們對世俗安靜和沉默的表態讓統治者看到道教的逍遙和佛教的頓悟,使社會免遭詩人情感沖動反應的傷害,即使歸隱,選擇沉寂,詩歌依然是和諧帝制宇宙的忠實維護者。因此,宇文所安認為無論是公共文學還是私人文學里,詩歌都是效忠帝王及其政府的象征行為,在帝制宇宙下,詩歌使宇宙相關論從一種單純的詩歌手法轉化成了一種對皇權的信仰。
四、結語
宇文所安眼中的“詩歌與帝制間的共謀論”雖然挑戰了國人對中國古典詩歌雅潔可敬的經典認知,但他卻為當下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錢鐘書先生曾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文學研究理應具有兼收并蓄的世界眼光和開闊胸襟。宇文所安帶著他純善友好的學術態度、學貫古今中西的匯通性思考,讓中國的古典文學進入了全球化的視域,他身在美國,遠離了中國學術傳統,雖不能充分借鑒中國的學術成果,但也得益于此,他對作品的分析便擺脫了中國歷來文學史家所限定的框架,也沒有遵循現代文學批評家慣走的軌道,他不因為自己是美國人,就認為與中國的作品之間存在了離間或異己的關系,也不因為自己是美國人就少了一份闡釋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刻,他憑借自己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摯愛與敏感,帶著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立場與視野,重新審視中國的古典文化傳統。在審視的過程中當然會發生一些變異,但這些變異卻印證了一種民族的文化品質在本民族之外的文化鏡照下反而能夠更加澄明、通透,正如田曉菲教授所言:“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個廣大幽深、精彩紛呈的世界,但時至今日,我們亟須一種新的方式、新的語言對之進行思考、討論和研究。只有如此,才不至再次殺死我們的傳統,使它成為博物館里黯淡光線下的蝴蝶標本、恐龍化石。”
注釋:
[1]黃嘉德譯,林語堂:《吾國與吾民》,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頁。
[2][4]陳小亮譯,宇文所安:《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第11頁。
[3]周振甫:《文心雕龍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頁。
[5]趙復三譯,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頁。
[6]刁承俊譯,顧彬:《中國詩歌史:從起始到皇朝的終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導言第6頁。
參考文獻:
[1]賈晉華譯,宇文所安著.盛唐詩[M].北京:三聯書店,2014.
[2]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三聯書店,2009.
[3]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三聯書店,2001:1.
[4]田曉菲譯,宇文所安著.他山的石頭記[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