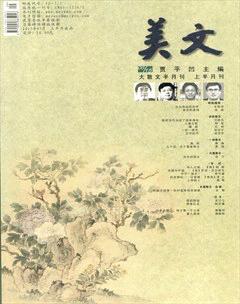三秦之歌
阿瑩

三秦大地是一個盛產民歌的迷人地方。
——作者題記
一
我每每去陜南,總覺得是去青山綠水的地方休閑,尤其是劃船來到某個湖心,你會遠遠聽到從水里從林間飄來的歌聲,像鳥兒,像銀鈴,啘囀清純,細膩悠長,稍不小心男人的春心便被撩動起來,你激我逗,打情罵俏,平時說不出口的葷句就蕩漾在悠悠的湖面上了。如果有姑娘藍衣花褲,或站船頭,或藏樹下,回眸一笑,嘴里便飛出甜蜜蜜的歌來,剎那間就把人的思緒帶入田園般境界了。我于是想閉目養神放松身心,卻總有好事者詢問我對陜南民歌的看法?我睜眼便說,陜南民歌最大的特點就是歌唱生活!
的確,陜南民歌大多是對生活的贊美,是人們從心底流淌出來的生活贊歌,不僅表達愛情真摯幽默,表達生活尤其自然純樸,聽來愜意輕松。正說著就有人唱起了勞動歌謠《過漢川》:“上河那個漲水下河渾,河里那個站的是打魚人,打下那個大魚長街賣,打下那個小魚下酒喝,站在河邊打魚哇,我們眾位唱起歌。”有人尚覺不過癮,高喊來段帶色的嘛,于是一段情歌飄起來:“郎在對門唱山歌,姐在房中織綾羅,那個短命死的、發瘟死的、挨刀死的唱的個好哇,唱的奴家腳帊手軟、手軟腳帊踩不得云板丟不得梭,綾羅不織聽山歌呃。”那歌聲貼切自然,惟妙惟肖地刻畫了墜入情網的姑娘對意中人的思念。似乎在陜南民歌中,幾乎聽不到人們的惆悵和嘆息,更多的是人們對生活的憧憬,是勞動情感的流露,所以那一支支曲調,要么委婉細膩,要么輕盈活潑,聽來如墜夢里呢。
上得岸來,我們又聽有女子在山澗唱歌,但遠遠望去,歌兒卻激起水波漣漪,只聽音韻不見倩影。此情此景仿佛就概括了陜南民歌的魅力,陜南秦川,綠水青山,每條澗都是綠水潺潺,每座山都被綠色覆蓋。是的,在漫長的農耕時期,大山里的人們生活困頓惆悵,但人們流連于山間,絕沒有生命的威脅。當有自然災害來臨,人們可以輕易捕捉到賴以生存的飛禽走獸,可以隨意采集到山果野珍;盡管缺少美酒佳肴,簡單的生活照樣可以在山里延續。所以,置身在這般美妙的環境里,叫人怎能不歌唱?男女怎能不唱歌?人們歌唱這里的山,歌唱這里的水,歌唱這里的風情萬物,直把所有聽歌人醉倒才歇息呢。其實若細心搜尋過去,與陜南鄰近省份的山歌,也許都是這么個韻味吧!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一不小心就會軟軟陷進去,歌聲就會從喉嚨里流淌出來,融入青翠的山山水水,將人帶入到溫柔之鄉,也就會忘卻了所有的憂愁和煩惱,忘卻了生活的艱辛和苦悶。
呵呵,想休閑,去陜南。
二
走進蒼茫的陜北,我們聽到的信天游就少了輕松啘囀的韻味了,那高亢悠長的曲調,總是帶著一種蒼涼和悲憫。跋涉在陜北的溝壑,人們常常渴望裹著白羊肚手巾的后生,腰系粗粗的布繩,甩起清脆的叭叭羊鞭,信天游脫口而出飄蕩耳畔,那叫一個享受呢。是的,長久以來人們喜愛陜北民歌,往往會被那悠揚而自由的信天游所傳達出的情緒所感染,尤其是那一曲響徹環宇的《東方紅》,更將陜北民歌的旋律帶到大江南北的各個角落。而今人們的文化生活豐富起來,經過三十多年各種文藝風潮的洗禮,很多流行的旋律都拋到人們的視線后了,但陜北民歌卻以其獨有的魅力愈來愈受到群眾的喜愛,這實在是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啊!那天,一位撰寫了陜北方言大全的作者與我探討起陜北民歌的特點,我就直截了當說,陜北民歌最突出的特點是歌唱生命!
君不見置身黃土畔,站在黃河邊,或是呼朋喚友酒桌旁,只要那信天游一出口,人們的情緒便立時被帶向悠遠,帶向苦難,帶向生離死別。似乎陜北人天生就執著投入,即使談情愛,也要愛得死去活來,使人感覺到強烈的靈肉震撼和魂魄鞭笞;即使是販糧運貨走西口,也都雄赳赳地提升到生命的高度。你聽那動人魂魄的《走西口》,不管扯到哪個版本,都突出了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糾結于生命的磨難,有今沒明的那種沉在心底的憂慮,會折磨得你呼吸急促蕩氣回腸。“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走路走在大路口,人馬多來解憂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里頭,這一走要走多少時候,盼你也要盼白了頭。”聽到這段信天游心里只有一個苦了。又比如那膾炙人口的《蘭花花》,盡管演繹的是司空見慣的鄉間愛情,卻愛得你死我活。“三班子吹來兩班子打,撇下我情哥哥抬進了周家。前晌你死來后晌我走,拼上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見到哥哥我有說不完的話,咱們倆死活在一搭。”如此坦蕩的情懷,常常令人唏噓不已。而且令人感慨的是,即使是流傳在街頭巷尾的那些俚語酸曲,也都洋溢著敢愛敢恨的奮不顧身精神,昂揚的生命力量在歌聲里得到刻意的彰揚。
我情不自禁哼起了“天上有個神神……”
這位沉浸在陜北方言里的陜北人,以為我寫了一部陜北歌劇便喜歡對陜北民歌加以推崇。其實這陜北民歌所以會有這般特征,實在是因為陜北長期以來是一塊承載著民族苦難的黃土地。君不見土崖荒坡,戈壁沙漠,一眼蒼涼,一旦狂風沙暴,人們被封在家里許久出不了門,吃飯喝水都是困難;一旦旱魃肆虐,干燥的空氣都能擦著火,人們連啃樹皮的機會也會被無情剝奪;倘若冬日嚴寒降襲,凋敝的軀體在風中顫抖,生命在無奈的痛苦中慢慢流逝。所以人們要走西口,要祈天雨,要唱信天游。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人們對生命的渴望在這里演繹得格外精辟,誰都擔心上蒼的懲罰哪天會降臨到自己頭頂。所以人們在沙蒿里,在窯洞口,在販運路上,在冰冷的灶臺旁,喜歡用民歌來排遣時光,用信天游來抗爭命運的殘酷。所以,那一曲曲愛的旋律,那一聲聲狂飆般的呼喚,都蘊含著深深的憂慮和惶惑,都飽含著對生命的眷念和珍惜。生長于斯的方言大全作者聽聞此言居然一把將我抱了起來。
是啊,想釋懷,去陜北!
三
那天我問一位音樂家:關中民歌的特點應該是詠嘆命運?
他略加思索點點頭。
誰說不是呢?我們走在關中的土地上,常常會感覺進了一片濃重的撕扯不開的迷霧地帶,壓迫得你想喊又不敢。有位剛從北京來陜掛職的朋友找我述說,關中這地方太神奇了,濃濃的塵埃厚厚的封土,永遠彌漫著古風雅韻,幾乎每一腳下去都能踩到歷史,碰到已經沉睡多年的皇親國戚。你在關中可以輕易見到秦國威武的戰車,看到漢朝長安的瓦當,揀到大唐東市的三彩,踢到有明一朝的銅錢。人們說一場大雨就能沖出一個博物館來,絕對不算夸張的。但是,我告訴他,這樣的氛圍卻不適宜原生態的生長,不論是郊外沃野,還是城閭街口,若想采風民歌竟是困難的奢望。好像關中人的演唱功夫一夜間被褫奪了,你難以在城墻根下聽到居民們縱情的宣泄,也難以在田間麥場聽到老農們自由的歌唱。只是偶爾在遠離城鎮的鄉間小路上,身背褡褳的老農腳夫會迎著暖洋洋的夕陽,借助秦腔曲調一板一眼地喊上幾句,其音也啞,其調也涼啊!所以,生活在關中這片皇天后土上的人們,似乎一輩輩走來變得愈發循規蹈矩,失去了張揚而放肆的天賦。
音樂家驚訝了:你怎么還研究起音樂了?
什么研究呀!我驅車鄉里,東尋西覓,聽到的都是些不很地道的關中民歌,比如老腔,比如關中道情。然而聽得多了,就有了一種感覺,這些貌似原生態的歌兒,不管曲調多么詼諧,也不管歌詞多么豪放,其實都在努力抒發一種哲理,都想用民間最質樸的語言傾倒出個真諦,骨子里隱含著那么一股參透世界的情緒。你聽那流傳在關中城鎮的《賣餃子》《賣面條》《賣針線》《賣饸饹》等等貨郎們走街串巷吆喝聲,幾乎都隱隱想闡釋什么。那首人們耳熟能詳的關中歌謠《大舅二舅》,讓人在憨笑中清醒:“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還有那首《遠看鐘鼓樓》更有一股玄味,讓人聽著如墜霧里:“遠看鐘鼓樓,近看是木頭。木頭用了千千萬,沒用錛子和斧頭。”這些詞句都隱含著不管人們成就如何,都是要吃要喝要呼吸的人,要看到事物的本質,用平常心看待喜悅與煩惱,那字里行間體現的都是濃郁的宗教般的憂患意識,告誡的是人世間簡單而又深奧的哲理。
音樂家聽著笑了:有點意思。
其實,這樣為關中民歌煽情絕不是我的本意,是因為關中地區是我國周秦漢唐四大朝代的京畿之地,也是歷代文人墨客極為重視的治學重鎮,文化交流和商品流通使得關中歷史上比較繁華昌盛。因此,當年這里的百姓受到的繁文縟節的熏陶更為細致,一方面必須合乎禮數地生活,生怕突然亮嗓破壞了禮俗秩序,也怕哪句唱詞引來厭惡和麻煩。所以,久居關中的人們很少會恣意率性地抒發自己的情感,只是拿腔捏調地在街頭巷尾哼幾句小曲,即使行走在偏僻的鄉間小路上,也只愛吼幾句戲詞,以借助那些刻板的程式來抒發自己的情緒。
所以,那關中民歌在這種市井文化的熏染下,便愈發衰落和萎靡了,當然也就自然喪失了原生態的鮮活魅力,也就很少有人去傳承了。如今,我想附庸風雅去找幾首地道的關中民歌,竟然也變得十分奢侈,人們能夠聽到的都是些經過文人墨客斟酌提煉出的詞曲,一字一句,顯得那么沉穩那么精致。
所以,想修身,到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