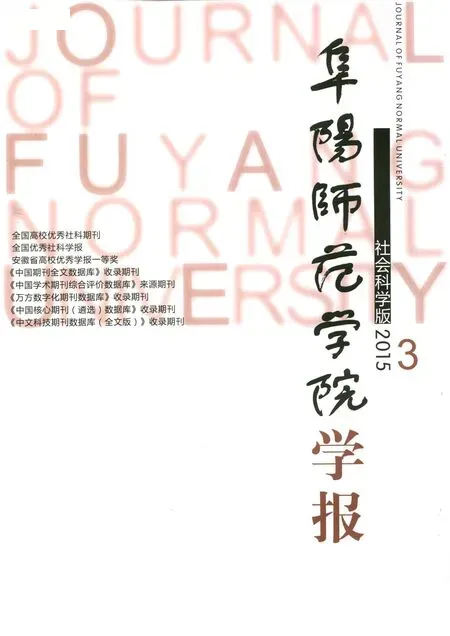“才盡”“田家語”與陶詩評價
——論鐘嶸審美思想的折中傾向
郭世軒(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文學研究
“才盡”“田家語”與陶詩評價
——論鐘嶸審美思想的折中傾向
郭世軒*
(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在整個東晉南朝時期,鐘嶸是在審美坐標中率先對陶淵明做出相當中肯評價并予以較高定位的文學評論家。從《詩品》的“才盡”“田家語”等評語中不難發現,鐘嶸對陶淵明的評價與其審美思想的折中傾向之間具有某種關聯。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著鐘嶸在審美矛盾中的綜合平衡與無奈選擇。這種審美矛盾間接透露出他在審美趣味、審美表現和審美境界等方面所作出的權衡與規避。
陶詩評價;鐘嶸;審美思想;折中傾向
在整個東晉南朝時期,對陶淵明做出相當中肯評價并在審美坐標中予以較高定位的文學評論家莫過于鐘嶸(約 468~518)[1]585!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史料可以看出,鐘嶸給陶淵明詩歌創作以“中品”評價,盡管在今天看來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在當時已屬非常不易,甚至是相當大膽的突破。要知道,在當時的主流娛樂圈和文化傳播媒介中,陶淵明是以“隱士”身份出現在公共視野的。這一點可以從當時文壇精英分子的文學價值觀和對陶淵明詩文創作的評價中充分顯示出來。至少從文學本位的立場上來看,鐘嶸把陶淵明看成真正的詩人,而非其他。即使是“隱逸詩人之宗”,至少也是詩人呀!從《詩品》的“才盡”“田家語”等評語中不難發現鐘嶸對陶淵明的評價與其審美思想的折中傾向之間的內在關系。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著鐘嶸在審美矛盾中的綜合平衡與無奈選擇。這種審美矛盾也間接透露出他在審美趣味、審美表現和審美境界上的權衡與規避。本文試圖在鐘嶸評價陶淵明等詩人的相關信息中尋繹出問題的答案。
一、審美趣味:趨新與典雅
在審美趣味的時尚選擇中,整個南北朝時期是趨新求變的。南梁文論家劉勰(465-521)的《文心雕龍·時序》既已提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2]527的主張。南梁史學家蕭子顯(489-537)的著名言論充分表明了這一時代的追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3]340恰恰體現出該時代文學以變求新的極端重要性:要想成為一代青史留名的文壇英才,就必須在前輩權威的基礎之上做出新的變化以取代舊的權威。一個凡人如何才能擺脫沉重肉身的束縛而留下身后不朽英名?這是困擾人類的一個大問題。中國古代賢者建立了“三不朽”即“三立”的留名范式,那就是要在德、功、言三個層面上永垂不朽。蕭子顯這句話分明包含著這一時代詩人在建功立業觀念上的突破:在立言上進行自我實現,在立言中實現對立德、立功的超越。因為立德并非人人可立,在德性上要想做到德高望重,必然要通過社會評價系統的高度認同;即便如此,道德完善的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尚需時間的考量和歷史的淘洗。況且,言人人殊,要想取得社會的高度認同,也絕非輕而易舉。立功,需要的是機會與能力、膽識與才干同時兼備。飛將軍李廣雖具曠世奇才,但時運不濟,最終歸因于“數奇”[4]2202。相形之下,他那才能平庸的堂弟李蔡卻能飛黃騰達[4]2201。李廣之孫李陵雖戰功赫赫,卻因北匈奴的重兵包圍而寡不敵眾、戰敗假降而導致滿門抄斬、母親妻子滅族的曠世奇冤[4]2068,連路見不平、仗義執言的司馬遷也卷入其間,成為“發憤著書”[5]2201的奇特案例。而只有著書立說,執著于“立言”,才是最可信、最現實、最可為的——無需外求,全靠自身,獨立自主,立言不朽!“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作篇籍。”[3]14這里深藏著文人學者在亂世中求生存的最新思考:如何在年壽不假、禍福不定、時運不濟、德性微薄、功業難成的生存語境中,播撒自己的光和熱,使自己青史留名?揚雄“悔其少作”[6]459而作《法言》和《太玄》,桓譚對揚雄的推崇(稱之為“揚子”,視《太玄》為玄經)[6]490,王充對“鴻儒”的呼喚[6]512,曹丕對“經國”文章的強調[3]14,無不為這種著書立說、立言不朽的觀念提供了反思與深化的理論資源。可以說,這就是“影響的焦慮”[7],是時代的焦慮,而不僅僅是個人的焦慮!
“為人須規矩,為文須放蕩”[3]354,旗幟鮮明地亮出這樣的立場:為文和為人是兩碼事,不可混為一談。前者要規規矩矩,以理性為準繩,明確區分善惡是非,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要界限分明。后者則是以感性為依據,出奇制勝,變幻多端,美在耳目,賞心樂事,無限風光在筆端。這可以說是對儒家“變風”“變雅”[3]334觀念的認同與改造,對“溫柔敦厚”[3]275詩教和“心聲心畫”[3]463說的質疑與顛覆。“放蕩”,主要指在審美想象王國中可以盡情展現奇思妙想,在藝術形式和意象經營中,不拘一格,爭奇斗艷,鼓蕩人心,產生驚心動魄之奇效!這里既有對偏重規訓與統一的漢代文化精神的反叛,也有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式的權宜之計和文化選擇。漢代的輝煌已成為過去,并且一去不復返。天下大一統的時代難以再現,一匡天下的雄心壯志積重難返,巨大時空的輝煌成就感和征服感遺失在昨天,偏安于風景秀麗、人杰地靈、豐衣足食、佳麗如云的錦繡江南之現實處境直接決定了南朝文人的感性風貌。現實生活環境直接制約著文學的生存空間。鑒于此,南朝的文學風貌也隨之煥然一新:內容漸趨新奇小巧,形式偏于新奇驚艷,格調聚焦奇句淫詞、聲色犬馬與視覺享受,趣味喜歡奇情麗采、錦心繡口,氣象拘于曼妙艷麗,境界囿于玲瓏剔透和賞心悅目。相比較整個南朝日益趨新的審美趣味,陶淵明的審美趣味則顯得相對保守,表現為淡雅而持中。
因此之故,在對陶淵明的評價中,無論是顏延之的“文取旨達”[3]269,還是蕭統的“尚想其德”[3]335,都是這種審美趣味的有聲表達。謝靈運、劉義慶和劉勰等文學家對陶淵明的漠視,更是這種審美趣味的無聲默認。即便是對陶淵明傾情有加的鮑照、江淹也只有在失意與落魄、激情與憤懣中偶一為之。這些皆源于陶淵明詩歌的獨特追求。有研究者認為,陶淵明的詩歌追求在于自然清新,表現形式在于“高情淡采”[8]。因此,陶淵明獨具特色的審美追求明顯不符合南朝文壇主流的審美趣味與審美期待,遭到無視與強評(勉強論之)的待遇自然就在意料之中。從上品詩人的源流譜系中不難發現,鐘嶸是比較喜歡氣象宏大、辭采華麗、境界開闊、趣味雅致的詩歌作品的。他的這種審美趣味既是時代的表征,也是個性的體現。無論是曹植、王粲還是陸機、謝靈運,無不以辭采華麗和意象多變而著稱,總體格調偏于華艷靡麗。至于氣象宏大、境界高遠、趣味高雅的曹操、曹丕和陶淵明、鮑照等人也只能在無奈的選擇中屈居中、下品第。其中,追求清新雅致的審美趣味終于使他將陶淵明從被文壇遺忘的角落中發掘并置于中品的位置。這也許又是他折中思維的無意識表露。置于上品,會引起很大爭議;置于下品,又于心不忍。放在中品,可謂恰如其分,便于自己在爭辯中左右逢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事實證明,鐘嶸是深刻領會“無私于輕重,無偏于憎愛”[2]586這種客觀求實的精神的。其中蘊含著一位優秀文學評論家的無奈與智慧。在一千四百多年之后的今天,這種智慧的選擇依然令我們心動,不禁為之擊節嘆賞!
二、 審美表現:華麗與清新
南朝文壇追求新變的結果就是直接表現為華麗的語言與精巧的形式。劉勰在劃時代的巨著《文心雕龍》里專門開辟《情采》篇予以重點關注。這也許就是一個時代的審美趣味最顯著的審美表現。
如前所述,被南朝文人視為文壇巨匠的大都以辭采華麗而著稱。盡管在個別作家(如曹丕與曹植)的評價上,鐘嶸和劉勰不盡相同,但總體說來兩人的審美趣味大體相似。尤其是在對王粲、劉禎、陸機、左思與謝靈運等重要作家的評價與定位上,則是大同小異。比如對王粲、陸機和謝靈運的評價則顯現出基本的一致性。至于對曹丕與曹植的分歧,可能源于兩人同情心和世界觀的差異。劉勰基本上是揚丕抑植的,這既與曹植的行為狂放、以小凌大有關,也與劉勰的正統觀念和宗經思想相連。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對“三曹”的褒貶中見出分曉。曹操、曹丕作為帝王詩人在劉勰筆下熠熠生輝,而曹植作為落魄王侯則顯得有點美中不足。一般說來,“三曹”中的曹操戎馬生涯,轉戰沙場,詩風顯得古樸蒼健、氣勢恢宏;而曹丕、曹植兄弟不僅是錦衣玉食的王公貴胄,而且年少輕狂,相對地養尊處優,因此在詩風上則是后出轉精,后來居上,尤其是在語言表達與技巧運用上。當然,這既可以看出時代的差異——曹操為漢聲,曹丕曹植為魏響,也可以看出因年齡與經歷的差異而導致不同的人生體驗:曹操為風云變幻的時代英雄和一代領袖,具有雄才大略;而曹丕、曹植兄弟則為王孫公子,二者又有王侯與君臣之別。大體說來,曹丕、曹植兄弟在詩歌創作中,語言華麗遠遠超過乃父,其中曹植又略勝于乃兄。劉勰的這種觀念使得他迥異于南朝的其他作家與評論家。而鐘嶸對“三曹”的評價基本上大異于劉勰,來個乾坤大挪移。曹植作為建安之英的地位處于上品中的高端,可以說是建安以來詩人的頂峰,享受最高的稱譽。相比較而言,他分別給曹操與曹丕下品和中品的地位,尤其是對曹操做出了不恰當的評價,為后世評論家埋下了紛爭與不滿的伏筆。當然,鐘嶸的評價也是言之有據的,并非隨意處置的。他褒貶曹植與曹丕的主要依據就是趣味的華美與構詞的精巧。
事實上,作為“詩人之冠冕”的曹植之所以成為南朝文人大加追捧的對象,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曹植更能迎合南北朝文人追新求變的審美時尚,代表華美綺靡的審美方向;其二,作為政治上的失敗者、多才多藝的文人和英雄末路的落魄者,直接激發了南朝文人的情感共鳴,從而為自己的失意與不幸找到傾訴的對象和投射的目標。鑒于此,曹植順理成章地成為“三曹”中的翹楚,這在無形中暗合了鐘嶸的審美理想。有人認為鐘嶸建立了布衣文學觀[9],從這里也可以得到佐證。相形之下,劉勰則充分體現出典型的貴族趣味。最為極端而又典型的例子就是,劉勰遺忘陶淵明,鐘嶸抬高曹植并發現陶淵明。南朝政治生態的惡化與偏安一隅的局促,使得文人難有大的作為。政治上,門閥士族和軍功階層把持了各種晉升的渠道,一般寒門士子若想出人頭地,不會投機取巧和見風使舵就只能英俊沉下僚。作為布衣文學家,鐘嶸自然而然地力挺曹植與陶淵明,徘徊在華麗與清新之間,在迎合時代的審美潮流之外,又為南朝文壇招徠清新偉岸之風。在這里,我們還可以見出鐘嶸為了捍衛清新之風而作出的甄別工作和詮釋理由。那就是“田家語”[10]66與“才盡”[10]73之說。
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都是圍繞清新與華麗而做文章。“華麗”的反面就是古樸,針對江淹而言,那就是“才盡”。在南朝史料中,涉及到詩人作家“才盡”者,一個是江淹,另一個就是任昉。任昉以筆見長,善于寫實用文體,如表奏書啟之類的文章。“沈詩任筆”之說似成定論。“彥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10]75鐘嶸在這里介紹的任昉為詩不工之處與任昉深恨之情,充分說明“不工”在詩壇與文苑絕不是一個好詞,有可能是一個極端負面的評價。與之僅一步之遙的詞語那就是“才盡”。《南史》記載,任昉對世人評價他的“才盡”也是“深恨之”。[11]970這可以與鐘嶸的《詩品》形成互文進行參考。對于任昉這樣地位較高的貴族階層,鐘嶸只能避重就輕,僅寫次要的“不工”,而將語氣更重的“才盡”留給史學家置喙。而對相對貧民出身而主要成名于南齊時代的江淹似乎就沒有那么客氣啦!直接在《詩品》率先引用民間傳說,從而使“江淹才盡”成為千古流傳的典故,而青史留名的江淹之文名反而不顯,流傳在后人口中的就是江淹的幸運成名與不幸才盡。考之于江淹文集中的創作,似乎在印證著鐘嶸記錄的符合度。關于江淹才盡、江郎才盡的原因有許多種解釋,但這一傳說的出現與傳播似乎提供給人們更多值得推敲的信息:一個作家的創造力與作品受歡迎的程度成正比;一旦創作力衰竭就將為時代所拋棄。而創作力衰退的最直接表現就是文采不再,缺少文采就是思竭才盡。這則負面消息透露出社會公眾對江淹的不感冒和極大的失望,從另一側面也彰顯著整個文壇與詩苑對華麗辭采的極端重視與趨之若鶩!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南朝士人對文采的高度重視遠遠超過對財物的占有。這一點在任昉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在乎財物的多寡,而在乎文名的受損[11]969-970。這也是時代使然,“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11]976。
當時南朝大多數士人之所以輕視陶淵明詩文的原因,大概與他詩文中田園生活的題材與語言相關。在士族文人看來,農村生活本來就夠寒磣的,再用方言土語或村夫野老之言來表述無異于雪上加霜。鐘嶸在《詩品》的座次排列中為他辯解的理由是:“豈止田家語也?”[10]66不難看出,鐘嶸為尋找真美的境界而付出切實的努力!也就是說,陶淵明雖用“田家語”來表現,但依然能夠突破“田家”話語的限制而抵達很高的審美境界。況且,陶詩還使用“歡言酌春酒”之類華麗清新的語言來表述。顯而易見,這種辯解還是很勉強的,因為這種語言與曹植、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等人相比還是顯得極為樸實與淡雅的。
三、 審美境界:真美與巧制
巧制的篇章所要傳達的審美境界難免顯得做作與拼湊、堆砌與匠氣,在繁瑣與沉悶中顯得孱弱和輕浮。在空間呈現上,顯得局促與狹小,視角單一,偏于一端,如嚴冬臘月,了無生機。而真美的詩歌給人的審美感受是:清新自然,“直尋”以抵達真美境界。這種真正的詩歌給人的感覺就是氣象廓大,其中的人生百態,全面展開,如春暖花開,萬物萌生。真美的詩歌與巧制的詩歌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需要“直尋”。
何謂“直尋”?無需借助于理性知識和邏輯演繹而直接抵達詩意的境界,使人感受到活潑潑的詩情畫意和生活樂趣撲面而來。有人又稱之為“妙悟”[12]132,確實很有道理。“直尋”就是直接尋找詩意,毋須過多的理性旁證與文史用事。相比較而言,任昉等人的文名不高多與此相關。直尋的詩歌如沐春風,自然清新,巧奪天工。而非直尋的詩歌則需要借助于華麗辭藻與歷史典故。這種區分在南朝以來就已經表現出來。比如,謝靈運與顏延之的區分,一個如芙蓉出水自然婀娜,一個似花團錦簇疊床架屋。前者給人春風拂面、神清氣爽之美感,后者使人感覺過度華麗令人應接不暇和審美窒息之壓迫。相比較而言,居于上品的幾位“大”詩人多偏于用典少、多清新,而《國風》、小雅和漢樂府民歌更上層樓。當然,曹植、陸機和謝靈運這“三杰”無不以華麗著稱。即便是王粲、劉禎和左思等居于上品的詩人也是麗詞與故實并重、學問與才思齊飛的。只不過才思、情感更占上風,在二者的關系上處理得比顏延之更為巧妙而已。但同樣也存在著美中不足之處。其美玉有瑕的表現就是知識才學與華麗辭藻過甚,往往掩蓋了詩歌的真美。太康詩人與元嘉詩人之所以遠遜于建安詩人處主要不在辭藻的華麗,而恰恰輸在情感的真實及其表現上。
一般說來,詩人的創作是源于情感的自然流露,源于生活環境的激發與碰撞,是感動于外物變化和內在心靈的觸動和呼應的結果。語境的變化使得自身在心靈感受上有所失衡。再加上身體狀態的變化、人生處境的變遷的疊加效應,即使外物尋常的變化也會在詩人心中產生不同尋常的反響,從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瀾。“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343被激蕩起來的情感漣漪必然通過身體語言和文字語言來表現,如同遭遇到冷空氣的突襲而得了感冒必然要打噴嚏一般,這應當是不可遏止的、情不自禁的必然反應。“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發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13]232也就是說,作家詩人只有處于這種創作狀態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狀態。這也就是劉勰所極力主張的“為情而造文”。否則,為了創作而創作,為名為利為其他而滋生的創作就是“為文而造情”[2]405。這樣的創作狀態則是偏離了真正的情感真純的狀態,結果必然會在詞藻上下功夫,這就是“情”不夠“采”來湊。“為文而造情”難免出現文過飾非、“為賦新詞強說愁”[14]9383的不自然、不真實的局面。為何會出現這種局面呢?這是因為文學藝術創造是最真實的情感表現,沒有自然情感的真實體驗就難以有審美情感的提純與升華,在話語與境界的追求上必然會有所偏差。莊子所說的“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15]823就是這種效果。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所以即使做出再大的努力,哪怕你登樓登山登科都解決不了這種愁苦的本真自然的問題。畢竟是“強說”“亂說”和“瞎說”的結果,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淪為虛假做作的濫說,陳詞濫調如隕落的鮮花自然就難以動人。因此,華麗的名言辭藻和豐富的歷史掌故難以遮掩藝術天賦和情感體驗的不足,最終會陷入虛假創作的羞怯與難堪之中。
相比較而言,《詩經》之“國風”“小雅”、《楚辭》之《離騷》、漢樂府之民歌、古詩十九首之所以成為不朽的傳世名著,恰恰在于這些都是詩人生命體驗無可替代的絕代詠唱。《莊子》《離騷》《史記》、杜詩《西廂記》和《水滸傳》之所以為金圣嘆(1608-1661)贊之為古往今來的“六大才子書”[16],實在是因為這六者不僅僅是真情實感的體驗極致,而且也是優美與淳樸有機統一的文辭絕境。同樣,建安文學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古,也與其亂世中求生存、艱難中求超越的生命絕唱密不可分。“雅好慷慨”[2]537的時代風格與個人標識是由來已久、事出有因的。無論是“三曹”還是“七子”,抑或是其他建安詩人作家的創作,在如此短暫的歷史時空中留下生命足跡的詩意表現無不與深刻的生命體驗和獨特的人生書寫密切關聯。因此之故,被鐘嶸列入上品之詩人絕大多數是實至名歸的,而有些詩人的定評也存在著明顯的爭議。而被列入中、下品的部分詩人也有不當之處,留有更大爭議的空間。這當然不能以今天的標準來強求古人,而應該從當時的閱讀語境和審美時尚來判斷。前者如陸機、謝靈運和潘岳,后者如曹操、曹丕和陶淵明。陸機作為太康之英,謝靈運作為元嘉之英,皆可以成立。但如果將時代再放大放遠一點,這種說法就值得推敲,難免存在時代審美趣味的偏差與審美鑒賞的前見。遠的不說,即使和曹操、曹丕和陶淵明相比,這三位上品詩人就難以自持。甚至鮑照、謝朓等詩人也會超越其上的。這是時代的審美標準所致,在此毋須贅言,將是另一篇文章所要討論的主題。陸機、謝靈運和潘岳之所以高出曹操、曹丕和陶淵明,恰恰在于審美趣味的偏差和崇尚辭藻詩風的制衡。如果從情感真純與詩語本色的高度統一來看,上述兩組六人可以進行重新洗牌,來個顛倒。
相形之下,曹操、曹丕和陶淵明更接近于真美,或者說陶淵明就是真美的化身,而陸機、謝靈運和潘岳更多接近于巧制,或者就是巧制的大師。前者傾向于“為情而造文”,后者則更傾向于“為文而造情”。鑒于此,鐘嶸在時代的審美風尚和閱讀同情上偏向于曹植、陸機、謝靈運和潘岳等人,而在審美的真純上還是不自覺地傾向于陶淵明。這在當時不能說不是一個大膽的抉擇!在這種難以平衡中進行抉擇,既是他進行折中權衡的結果,也表明他超凡脫俗的一面。當然,這種超越還不太徹底,那就是對曹操、曹丕等“為情而造文”的優秀作家之真正價值尚未給予公正的評價。而拘泥于審美時尚給予“為文而造情”的作家以不恰當的高評。這也許就是一個作家或評論家不能超越時代的具體表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鐘嶸能給予陶淵明中品的評價已經相當了不起!對比一下劉義慶、顏延之、沈約、劉勰等人對陶淵明的態度,鐘嶸可謂高標一時,冠蓋古今。這也許就是一位卓越批評家的遠見卓識的獨特表現:見常人所未見,言常人所不能言,道常人所不敢道。
事實上,鐘嶸不僅在詩歌鑒賞中表現出如此的折中傾向,而且這也是他人生經歷與選擇的正常反映。也就是說,詩歌鑒賞是他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必然表現。他的思想基本上屬于儒家。儒家思想在漢代鼎盛之后的漢魏六朝轉入中衰,齊梁之時一度抬頭。齊高帝即位之后,長于經學、禮學的王儉大振儒學。正值青年時代的鐘嶸諳熟儒家經典《周易》入國子學,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被舉薦為本州秀才[17]480。這說明鐘嶸曾受到儒家思想較深的熏陶。在天監元年(520)上書建議清理軍官中士庶寒門混雜的現象[17]481。這正是其世族出身門閥觀念的反映。這種出身士大夫的階級意識在《詩品》中就必然表現為重“雅”輕“俗”的審美趣味。儒家的折中思想又使之兼顧思想與藝術、世族與寒門、丹采與風力、《國風》與《楚辭》之間的關系,始終保持著某種藝術張力而不至于走向極端。有宗經思想但不突出,同時尊重藝術規律,使之越出儒家藝術思想的藩籬[1]588。
總之,從審美趣味之趨新與典雅、審美表現之華麗與清新、審美境界之真美與巧制來看,鐘嶸像絕大多數中國古典知識分子一樣,表現出一定的折中傾向,但是這并未能遮蔽他的遠見卓識,尤其是對陶淵明這樣較為低調而詩名未顯的大作家,一旦符合他的審美標準,他會毫不猶豫地予以認同,并作出在當時難能可貴的評價。這一點足以證明他是優秀的的大評論家。可以說,他穿越“才盡”“田家語”等時代偏見,最終抵達陶淵明的詩歌境界,并最終發現了陶淵明的偉大價值,實為《詩品》的偉大價值之所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鐘嶸無愧于他的時代和他的稱號。
[1]呂慧娟,劉波,盧達.中國歷代作家評傳(第一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
[2]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M].濟南:齊魯書社,1995.
[3]郁沅,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0.
[5]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
[6]張少康, 璘盧永 .先秦兩漢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7][美]布魯姆.影響的焦慮[M].徐文博,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8]郭世軒.蕭統為何對陶淵明高評低選[J].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
[9]方志紅.鐘嶸“布衣文學觀”初探[J].思想戰線,2008,(2).
[10]周振甫.詩品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11]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
[12]朱良志.中國美學名著導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3]蔡景康.明代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14]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辛棄疾詞新釋輯評(上下)[M].北京:中國書店,2006.
[15]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6]金圣嘆.杜詩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前言1.
[17]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
I206
A
1004-4310(2015)03-0060-05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14
2015-03-08
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晉-宋時期的文學傳播與陶淵明的經典化歷程”(ahskf09-10d79)。
郭世軒,男,安徽臨泉人,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博士,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點基地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