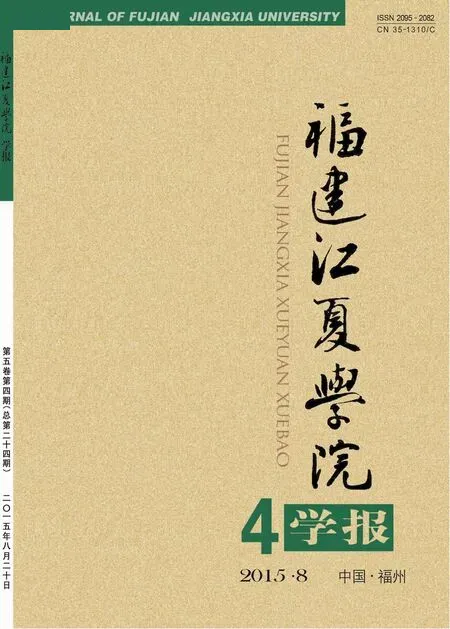《列女傳頌》:中國現存最早的題畫詩
魏伯河
(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山東濟南,250031)
多年來讀劉向(約前77—前6)的《列女傳》,常有一種困惑,即講述完每則故事后,作者已經模擬《史記》“太史公曰”的體例,用“君子曰”①《列女傳》各篇此類表述不盡一致,或“君子曰”、或“君子謂”“仲尼謂”,這里的“君子”應指劉向本人;亦有個別沒有此類領屬語而直接加以評論者,或當屬脫文所致。式的評述性語言,對故事的涵義進行了必要的闡發,而且還全都引用了《詩》《書》或《論語》中的名句加以印證,可謂言盡意足,何必還要于每篇之后再用一段“頌”來概述故事呢?以布局謀篇而論,豈不是畫蛇添足嗎?那時造紙術還不發達、印刷術還未問世,著述條件遠不如后世簡易便捷,主要通行的書寫材料還是竹木簡,數量多了,就相當笨重,以至于“(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1]因而我們的古人寫作無不力求儉省,惜墨如金,何以此書中如此反常呢?最近通過研讀有關史料與研究成果,這一困惑終于得到解決,而且借此有了新的發現。
一、《列女傳》本來就是一部與圖畫相輔而行的書
班固(32—92)《漢書·楚元王附劉向傳》載: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2]1958
這一記載,說明:(1)《列女傳》的資料來源于《詩》《書》所載,不是無根之談。(2)《列女傳》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讓天子——漢成帝劉驁(前51—前7年)引以為“戒”,也就是說,此書是劉向的另類“諫書”,并且對漢成帝也曾產生了觸動。至于成為民間流行的讀物,用于對婦女、兒童的啟蒙教育,則是宋代以后的事。有的論者徑直將其視為幼學啟蒙讀物,②如日本佛教大學教授黑田彰在《列女傳圖概論》一文中,就徑稱“《列女傳》與《孝子傳》同屬幼學啟蒙讀物”。是有失妥當的。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有班固自注云:
《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2]1727
這一注文告訴人們:傳世的《列女傳》一書又名《列女傳頌圖》,也就是說,此書本來就與一般純文字作品不同,是由《列女傳》《列女頌》《列女圖》3部分組成,三位一體,其中的“頌”并非傳文的組成部分。這一點,還可通過《太平御覽》所載的《七錄別傳》佚文得以證明。劉向在這篇奏疏中說:
臣與黃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3]
這一佚文的價值,在于說明了:(1)劉向的兒子劉歆(前50—23年)參與了《列女傳》(即《列女傳頌圖》)的編撰,以后世觀念論之,劉向《列女傳》之著作權是與其子劉歆共享的;(2)《列女傳》“七篇”是就文字著作而言,而圖畫是根據傳文而作;(3)《列女圖》最初是畫于劉向家中屏風上的,后來才將其奉獻于漢成帝。盡管佚文到此為止,沒有說明其是否呈獻,但通過前引班固《漢書》的記載,可知劉向父子肯定曾送成帝御覽。至于劉向父子煞費苦心進諫的結果如何,通過漢成帝此前此后的表現來看,可知并不理想。
因當時造紙術還不發達,紙張尚未用作書寫和繪畫材料,劉向父子所作(更大可能是請畫工繪制)、以列女為題材、先畫于屏風四堵、后進獻于漢成帝的《列女傳頌圖》,其傳文未必不是竹簡,但畫圖則應為帛畫。1972—1974年間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畫,是漢文帝時期的作品,其繪畫藝術已達到相當水準;至漢成帝時,帛畫流行且更適于觀賞,應無疑義。而在帛畫上題寫文字,是很容易的。劉向著書,采取以圖文相輔的形式以方便讀者接受、擴大社會影響,應屬創舉。③參見黑田彰《列女傳圖概論》。作者雖然沒有從題畫詩發展史的角度立論,但指出這種圖文結合的形式“是《列女傳》作者的發明”,是有見地的。傳世資料證明,《列女傳》之外,劉向還有一部《孝子傳》,也是圖文相輔的。該書雖不見于史志著錄,但《法苑珠林》《文苑英華》均載有其佚文,且后世征引者頗多,或稱《孝子傳》,或稱《孝子圖》,可知也是有傳、有圖的。[4]
值得一提的是,劉向父子初創的在屏風上圖畫列女以規諫皇帝的做法,在后世亦有繼其遺風者。據《后漢書·宋弘傳》:
弘當宴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5]
這一資料說明:至少到了東漢初年,在光武帝劉秀御座旁的屏風上,也有圖畫的《列女傳》故事。至于是臨摹劉向父子原作,還是另有丹青妙手重新繪制,已難以考證。可能是這些列女們都被畫得傾國傾城,以致光武帝在接見宋弘時仍忍不住頻頻顧望。這樣,《列女圖》的作用似乎已經發生了變異,成了滿足色欲的物事。結果引起了宋弘的不滿,當面予以諫止,于是被光武帝隨即 “徹(撤)之”了。其實,《列女圖》何辜?觀賞《列女圖》未必就算是好色,宋弘未免責之過苛了。
根據《太平御覽》所載《七錄別傳》佚文,邢培順以為:“劉向的《列女傳》不是史學意義上的人物傳記,而是對畫在屏風四堵上的列女圖的說明”。[6]此說近是,而猶未盡確。下面試作進一步探討。
按照常識,對圖畫的說明文字,一般應寫于畫面之中,至少應該附于畫面一側或其下方。要之,必須連為一體。否則與圖畫分離,不僅閱覽不便,而且容易丟失。而《列女傳》傳文每篇少則數百字,多則一兩千字,無論寫在畫面之中、畫面一側或其下方,都無可能。顯然是無法直接起到圖畫“說明”作用的。
此路不通,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今通行本《列女傳》各篇后面的“頌”。為了了解“頌”在《列女傳頌圖》這一特殊著作中的地位,需要回顧一下《列女傳》的版本流傳和變異情況。
在《列女傳》版本流傳中,其篇(或卷,當時篇、卷通稱,故無區別)數屢有變異。《七錄別傳》劉向佚文自稱“七篇”,應為專指傳文(包括《母儀傳》《賢明傳》《仁智傳》《貞順傳》《節義傳》《辯通傳》和《孽嬖傳》)而言,是不包含《列女頌》在內的;《漢書·藝文志》及《漢書·楚元王附劉向傳》均著錄為“八篇”,當為《傳》文七篇外加《列女頌》一篇,共合八篇;而在《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均著錄為“《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當為班昭(即曹大家,約45—約117)加注以后,文字增多,于是將《傳》文每卷析為上下兩卷,共十四卷;加《列女頌》一卷,合為十五卷。北宋嘉佑年間,蘇頌(1020—1101)、曾鞏(1019—1083)、王回(1048—1101)等人根據頌義、篇次,重新整理,把《頌》分別加入各傳之后,定名為《古列女傳》,以與各種后起的《列女傳》加以區別,成為今天的流行本。[7]這樣編排,固然是方便了后來的讀者,但卻肯定不合劉向當初編次的原意。因為,《列女傳》的《傳》與《頌》雖然內容上有相關性,但決非一體,而且它們與圖的關系也是有區別的。日本學者黑田彰指出:“將頌置于文末的這種形式并不是《列女傳》原本的形式,這是南宋蔡驥編定本以后才出現的現象。這些頌原來單獨成為一卷,與《列女傳》的七卷正文是分開的,因而,《漢書·楚元王傳》記載的《列女傳》加上頌一卷共有‘八篇’。那么,《列女傳》的文末形式本來是‘君子謂’和‘詩云’這兩部分,‘頌曰’之后的內容與正文的敘述沒有關系,而是為了其他的目的而被放置于文末的。”[8]108此說除《古列女傳》編定者存在異同外,對《傳》與《頌》關系的判斷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前文已述及,因為《列女傳》傳文篇幅太長,不可能寫進畫面或附于一側,能寫進畫面之中或附于一側的,以情理揆之,只能是簡潔凝練的“頌”詞。我們看到,這些從形式上模擬《詩經》,均為四言八句,長短一致,檃栝了故事梗概的“頌”,實為簡短的敘事詩,無論寫在畫面上或附于畫面一側,作為讀畫提示都是很相宜的。讀畫時同時閱讀“頌”,可以了解畫面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因為僅看畫面,讀者未必能明其所以;而借助于“頌”,則可以“知其然”。黑田彰指出:“《列女傳》文末的‘頌’主要是點明故事特點,展現故事主要情節,讀者閱讀‘頌曰’部分,就能了解故事整體內容。”[8]108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列女傳》的傳文,則是每幅畫的本事,除了事先作為創作圖畫的依據之外,在畫作完成后的欣賞過程中,恐怕只能集為一冊,置于畫旁,以便讀畫者作進一步了解、“知其所以然”之用了。由此可以知道,當初劉向父子為了規諫皇帝,是何等的煞費苦心。
弄清楚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列女傳·頌》為什么內容與傳文重復,只是言簡意賅地檃括故事,卻于傳文無所發明,因為其作用本來就是作為畫面提示,而并非用來對傳文進行闡發的;也才能理解為什么劉向自稱《列女傳》為“七篇(卷)”,因為寫于畫面(或附于畫面一側)的“頌”本來就是附著于畫面,而不是寫在書內或附于書后另作一卷的;而早期(劉向之后、宋代之前)的《列女傳》版本把“頌”另外作為一篇(卷)附于前七篇(卷)或加注后的十四篇(卷)之后,也是因為“頌”與“傳”文本來并非一體;“頌”是專為題畫而作,原本分散于各張畫面之上,是后人輯錄起來作為一卷附于書后(或單獨成書,見后文)的。再到后來,因原畫早已失傳,整理者不知其意,或為了實現新的編輯意圖,將“頌”與傳文強行連綴起來,才導致疊床架屋之弊。
至于在劉向父子合作的《列女傳頌圖》中,《傳》與《頌》孰為主次的問題,有人以為“這些頌是為了讓婦女、兒童們更容易背誦而放置于此的。頌的特征使其能夠巧妙地壓縮故事的內容,通過背誦這些壓縮的內容而聯想起故事的全部。像這樣單獨的一篇頌與《列女傳》正文的關系充分體現了《列女傳》作為幼學啟蒙書籍所特有的性質。一般來說,幼學書籍由正文(韻文)和注(散文)兩部分組成,幼童首先背誦正文,然后再跟隨老師學習其內容(注)。如果我們把《列女傳》的頌當作正文,把每個傳的故事當作是注,便很容易明白這是一種對于婦女和兒童來說很正確、傳統的學習方法。”[8]108-109此說把頌視作正文,而把傳視為注,是完全把《列女傳》視為幼學啟蒙讀物的產物。按照中國傳統幼學啟蒙讀物的樣式,這樣的說法似乎可以言之成理。用以評論經宋人改編后作為通俗讀物的《古列女傳》,于人不無啟發,但以劉向父子當初創作《列女傳頌圖》的初衷來說,則顯然并不符合,乃至近乎荒謬。因為該書最初的特定讀者是漢成帝,其時絕非幼童;而且頌本來是附著于圖的,與傳文絕非正文與注的關系。
二、《列女傳頌》是中國早期的題畫詩
《列女頌》如果是直接題寫于《列女圖》畫面之上(或附于其一側)的頌詩,便成了畫作的組成部分。這類詩歌,是中國詩歌里的一個專門種類——題畫詩。
何謂“題畫詩”?有人以為:“題畫詩,顧名思義,是一種以畫為題而作的詩,其內容或就畫贊人,或由畫言理,或借畫抒懷,或另發議論。但因這些詩都是緣畫而作,所以統稱題畫詩。”[9]1此說大體不錯,但把題畫詩解釋為“以畫為題而作的詩”,這樣“顧名思義”,顯然是有失準確的。因為“題畫詩”之“題”,其本義為“書寫”,而并非指“題材”。只是到了后來,題畫詩這一概念的涵義泛化之后,才把所有“緣畫而作”的詩都納入了廣義的題畫詩的范疇。
中國的題畫詩,是世界藝術史上一種極其特殊的美學現象。把文學和美術二者結合起來,在畫面上,詩和畫契合無間,渾然一體,成了一幅美術作品構圖上、意境上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詩情畫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因此,畫面之有題畫詩,是中國畫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獨有的民族形式和風格。
關于題畫詩的起源,眾說紛紜而分歧頗大。
有人認為:《周易》中的“卦象是圖畫,畫下有彖象釋詞,且多為詩歌韻文,詩畫一體,不可分割,是中國畫與題畫詩之濫觴。如果《彖傳》確為孔子所撰,據此推知,中華人文史上第一位題畫詩(作)者,當是孔子。”[10]99稱之為“濫觴”,或無不可,但《周易》中的圖文離人們普遍認可的題畫詩,距離未免過于遙遠。
也有人認為屈原的《天問》為中國最早的題畫詩,其依據是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中有言:“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11]若果如其言,是屈原“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則《天問》至少應與題畫詩有關。不過,姜亮夫(1902—1995)、游國恩(1899—1978)、郭沫若(1892—1978)等《楚辭》研究名家均不認可此說。而堅持此說者仍頗有人在。如劉繼才在《中國題畫詩發展史》中就力排眾議,認為“云氣鬼神圖式當是戰國時楚人祭祀時天人交通的一種媒介。屈原的《天問》也當是詩人看到祠廟壁上所繪的神靈圣賢像而引發聯想,呵問詠嘆。”[9]24如果此說成立,《天問》的創作當為由賞畫引起,但是否寫于畫壁,仍宜存疑。因為《天問》涉及的眾多神奇瑰麗的景象,不可能全都出現于壁畫;而把一首長詩寫于早已完成的壁畫上,可能性也大可懷疑。如果并未題寫于畫面,沒有成為畫作的組成部分,還能不能算是題畫詩,便很值得商榷了。
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準盜掘魏襄王(前318-前296在位)墓,得竹書數十車,共75篇,其中有“《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12]據此可知,戰國時代已有“畫贊”之類作品。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信息,可惜這篇《畫贊》今不傳,其具體內容已無從詳考了。
上述觀點之外,還有以下幾種說法:(1)認為東漢武氏祠石室畫像的贊文是最早的題畫詩;(2)認為題畫詩產生于魏晉南北朝之際,如西晉傅咸的《畫像頌》、楊宣為宋纖像所作的頌等;(3)認為庾信的《詠畫屏詩》“是題畫詩始作俑者”;(4)認為題畫詩從北宋開始;(5)認為題畫詩起于元代文人畫興起之后,等等。[9]21之所以有這樣多種差距甚大的認識,除了掌握材料的多寡之外,對題畫詩內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應為主要原因。
題畫詩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題畫詩特指寫于畫面中的題詩,作者可以是畫家本人,也可以是別人。但題詩內容應與畫作有關聯。因為題詩要以書法的形式呈現于畫面,而中國書法又是一門獨特的藝術,所以畫作、題詩與書法珠聯璧合、均臻上乘者往往被譽為“詩書畫三絕”,成為藝術珍品。廣義的題畫詩,除包括狹義的題畫詩之外,還包括賞畫者受畫面內容或其作畫藝術引發所寫的詩。這類題畫詩,獨立于畫面之外,嚴格地說應屬于對畫所作的詩體評論(故有人稱之為“贊畫詩”或“評畫詩”)。至于那些僅以畫作作為引子,其實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的詩作(如屈原《天問》),嚴格講來,是否還可以算作題畫詩,已經十分勉強了。
比劉向略晚、而與劉歆同年的揚雄(前53—18)曾應漢成帝之命為趙充國畫像作《頌》,因而也有人以為“揚雄此作似可作為中國第一首題畫詩”。[13]此《頌》載于《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列傳》,其文為: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后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后。[2]2995
孔壽山認為:“中國題畫詩最早起源于人物肖像畫贊頌體,完全符合中國繪畫的發展規律。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揚雄此作似可作為中國第一首題畫詩。”[13]說“中國題畫詩最早起源于人物肖像畫贊頌體”,是不錯的,但是,具體就揚雄所作《趙充國畫像頌》來說,盡管與趙充國畫像有關,但并非與畫像同時所作,④趙充國畫像作于宣帝時,揚雄的頌則作于成帝時。而且其文長達128字,不可能直接題寫于畫面之上;其內容僅為頌揚歷史人物趙充國功績,與畫作并無直接關系,最多可以算作“廣義”的題畫詩,而與后世人們普遍認為的題畫詩尚有距離。論者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于是接著說道:“我們認識到揚雄所作的《趙充國畫像頌》只是以趙充國畫像為贊頌的對象,本是《趙充國頌》,并未涉及繪畫本身,還不是今天我們所謂的詩與畫相結合之題畫詩。”
回頭再看《列女傳頌》,就會發現,與屈原《天問》和揚雄《趙充國畫像頌》不同,它應該是劉向、劉歆父子撰述《列女傳頌圖》之初,即已納入三位一體的整體構思,而且很有可能是直接題寫于畫面之上(至少是附于一側,與畫作相輔而行),因此應屬于比較正宗的題畫詩。不僅如此,《列女傳頌》的創作時間應該早于揚雄的《趙充國頌》。因為揚雄到了40歲,才于永始四年(前13)經人舉薦入朝,而劉向早已是朝中老臣,并且從河平三年(前26)就已經開始受命與劉歆一起校中秘書了。因此,就中國題畫詩之歷史而論,《列女頌》應屬存世最早的題畫詩;而且其數量多達百余首,這樣的發現無疑是令人驚喜的。
有人認為:“總起來看,中國的題畫詩從西漢揚雄《趙充國畫像頌》,中經曹植、傅玄、陸云、陶淵明的畫像贊,而至南朝之江淹、沈約、蕭綱、庾肩吾的看畫詩,逐漸轉變為北朝的庾信正式以《詠畫》命名,為題畫詩的形成及其體制完備作了實踐和理論上的準備,是題畫詩這一藝術形式上的萌芽期。”[10]99這樣的排列,總體趨向不錯,但完全無視很可能早于《趙充國畫像頌》的《列女傳·頌》在題畫詩發展史上的存在和重要作用,顯然是一個嚴重缺陷。究其原因,應是論者僅僅把《列女傳》看作一部文字古籍,而沒有注意到《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和《太平御覽》所引《七錄別傳》佚文,尤其沒有意識到《列女傳·頌》的獨特功能和實際用途所致。
三、劉歆應為《列女傳頌》的作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內府藏本)”條對《列女傳頌》的作者曾作辨正云:
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王)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詆其誤信顏籀(字師古)之《注》。不知《漢志》舊注,凡稱“師古曰”者乃籀《注》,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之《自注》。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顏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訛傳《頌》為歆作,始于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14]
據此可知,在《列女傳·頌》作者問題上,歷來頗有爭議。堅持《列女傳·頌》為劉向所作者有曾鞏、王回,認為為劉歆所作者有顏之推(531—約595)、《隋書·經籍志》作者及晁公武(1105—1180)。四庫館臣則贊同曾鞏、王回的意見,不認可顏之推等人的意見,似乎對這一爭議做出了定論。
但這一所謂“定論”并非沒有商榷的余地。
不錯,《漢書·劉向傳》和《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是把《列女傳頌圖》的著作權系于劉向名下的。但這應該是就其主要作者而言,不代表沒有其他人參與。這與《漢書》僅主體為班固所作,前由其父班彪開其始,后有其妹班昭續其書、班昭門生馬續補其缺,歷來著錄卻只系于班固一人名下,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注意到《太平御覽》所載《七錄別傳》之佚文所說“臣與黃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的話,則劉歆曾參與《列女傳頌圖》的寫作,是毫無疑義的。至于劉歆所做工作為其中哪一部分,因佚文為斷簡殘編,雖已難得其詳,但可以推測。作為此書主體的《傳》文,理應屬于劉向的作品,劉歆最多做過一些輔助工作;列女畫像圖,有可能是劉向父子的作品,但也很有可能是劉氏父子另請畫工所作(因為存世材料尚未發現劉氏父子兼工丹青的其他證據);而《頌》詩,則只能是劉向父子之一所作。劉歆參與《列女傳頌圖》寫作,既然已有《傳》文和畫像,他所能做的,也就只有《頌》詩了。他作完之后,自然也會請其父過目審核,提出修改意見,但這并不能改變他撰寫《頌》詩的事實。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劉向父子在準備進獻給漢成帝《列女傳》與《列女圖》時,考慮到對方在欣賞圖畫時翻檢傳文多有不便,所以才又由劉歆為每幅畫題寫了頌詩作為畫面提示。
如果上述意見尚屬推測之詞的話,顏之推《顏氏家訓》所說與《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則可視為有力的書證。筆者認為,顏之推關于“《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15]的說法,顯然是合于情理的。盡管他是否還有其他材料作為依據,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但劉歆的學術造詣不次于乃父,“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2]1967是載于史傳、人所共知的,他參與《列女傳頌圖》的寫作,自不應無所作為,由他來為《列女圖》作《頌》,順理成章而且可以應付裕如。否則,劉向是沒有必要把《列女傳頌圖》作為他們父子的共同作品的。班固著錄《列女傳頌圖》,系于劉向名下,蓋因劉向是第一和主要作者,并無不妥。由此觀之,《隋書·經籍志》著錄“《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16]未必僅僅是因襲顏之推之說,而極有可能是當時府藏圖書確有與“《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和“《列女傳贊》一卷,繆襲撰”并存、署名為“劉歆撰”的單本《列女傳頌》同時存在,史書作者僅為實錄而已。也就是說,在唐人編定《隋書》時,劉歆所作《列女傳頌》很有可能仍有單本存世。四庫館臣于1000多年后,在缺乏有力佐證的情況下,輕易否定顏氏之說和《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未免失之于武斷。其原因,蓋由于過分拘泥于《漢書》記載,又沒有注意到《太平御覽》所載《七錄別傳》之佚文,故而做出了完全排除劉歆曾參與其事的結論。
若此說成立,劉歆以《列女傳·頌》而躋身于現存中國正宗題畫詩之第一人,應無爭議。
四、結論
劉向《列女傳》一書記載了先秦至西漢104位女性的故事,具有多重開創性意義。首先,此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以記載婦女生活為對象的專著,對弘揚優秀女性的美德、引起人們對女性社會作用和社會地位的關注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在史書體例上,此書與其另外兩部著作《新序》《說苑》開創了史籍“雜傳”類的先河。這都是人們所公認的。現在看來,不僅如此,此書還是傳世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與圖畫相輔而行的著作,其中的“頌”更是中國最早的題畫詩,而《頌》的作者,則應當是其子劉歆。劉氏父子之后,為圖畫作頌贊乃大行其道,以至發展為一種新的文體了。
筆者于讀書中偶有所得,特不揣淺陋,草成此文,以為野芹之獻,謹供研究中國題畫詩發展史及《列女傳》之學者參考。
[1] 司馬遷. 史記·滑稽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3205.
[2] 班固.漢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62.
[3] 李昉,等. 太平御覽(第七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6.
[4] 李劍國.略論孝子故事中的“孝感”母題[J]. 文史哲,2014,(5):54-60.
[5] 范曄. 后漢書·宋弘傳[M]. 北京: 中華書局,1965:904.
[6] 邢培順. 論劉向《列女傳》中所載齊魯女性[J]. 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3,(6):47-55.
[7] 詹曉青,谷文珍. 劉向《列女傳》研究的成績與不足[J]. 龍巖學院學報,2010,(3):23-26.
[8] 黑田彰. 列女傳圖概論 [J]. 雋雪艷,龔嵐,譯. 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3):107-122.
[9] 劉繼才. 中國題畫詩發展史[M].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1.
[10] 東方喬. 題畫詩源流考辨 [J]. 河北學刊,2002,(4):97-100.
[11] 王逸. 楚辭章句·天問序[M]// 洪興祖. 楚辭補注. 北京: 中華書局,1983:85.
[12] 房玄齡,等. 晉書[M]. 北京: 中華書局,1974:1433.
[13] 孔壽山:《論中國的題畫詩》[J]. 文藝理論與批評,1994,(6): 105-109.
[14] 紀昀,等.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十三·傳記類一·古列女傳(第2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7.
[15] 顏之推. 顏氏家訓[M]. 北京:中華書局,2011:272.
[16] 魏征,等. 隋書·經籍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73:978.